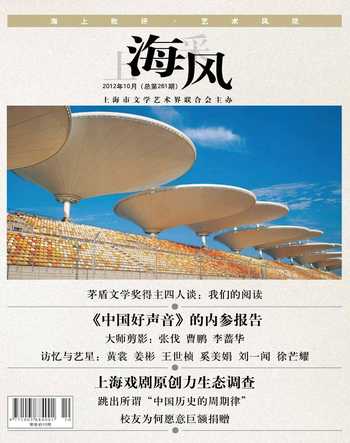一個看守的話
楊仲文

在那場假文化為名的政治大革命中,在上海,除了尊敬的前輩音樂家賀綠汀先生之外,我極少見過有人在批斗會上血脈賁張地高聲抗辯道:“我不是反革命!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的人才是反革命!”
這位以言、以行捍衛(wèi)“士可殺不可辱”信念的錚錚關(guān)東漢子,就是著名的已故表演藝術(shù)家張伐。
在干校里,一次很失敗的張伐批斗會之后,工、軍宣隊把我叫到營部去,交代我一個“十分重要的任務”:做張伐的看守。我為難地說:“我同張伐不在一個連隊,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專案組,對他的問題一點也不了解……”我知道張伐跟看管他的人吵、同外調(diào)的人頂是出了名的,而且我還要對他的生命負責,防止再次發(fā)生意外。看管性格如此剛烈的人責任太重也太難了。工、軍宣隊無奈地講:“實在找不出合適的人選,難得的是張伐本人挑中了你,同意由你來看管他。”
今天的年輕人會覺得十分奇怪:怎么可能讓一個專政審查對象自行挑選他的看守呢?殊不知這確是張伐拼死抗爭得來的一個悲壯的勝利啊。工、軍宣隊當時講的是大實話,我也找不出更多的理由來推托,于是,勉為其難地應承下來。
我?guī)蛷埛ヌ嶂纳钣镁撸屗岬轿腋舯诘拇蹭伆差D下來。進門之后我對張伐說:“這張床空了有一陣子了,咱們把床上的草褥子拿到打谷場上曬曬,見見太陽吧。”張伐不作聲點了點頭,我們兩人就一前一后提著草褥子來到打谷場上攤開曬著。我找了個避風的地方坐在草堆上,對張伐說:“坐下吧,我們談談……你的問題歸專案組管,我一概不問,有什么補充交代,你找他們。你不是說,除了在文藝黑線下面犯的錯誤,沒有其他的問題嗎?如果你再有什么錯誤念頭就更說不清楚了。你要相信群眾相信黨,千萬不能再有這種念頭。”
張伐聽了低著頭,兩手籠在棉襖袖子里,默不作聲。
我接著說:“你要替家里人想想,萬一這么做了,就把什么問題都壓到了他們的身上……”
見到張伐有點動容,我趕緊剎車不往下說了。前陣子他女兒到干校來探望他的時候,這位專長演硬派小生的漢子還掉了眼淚哪。
我換了口氣說:“我剛才對你提出了要求,我也有個交換條件……”
我注意到張伐認真地聽著,大概他以為我會宣布什么紀律要他遵守。
我嚴肅地說:“我以我的人格保證,我一定不讓任何人侮辱你的人格。我不在場的時候,你不要跟人家發(fā)生正面沖突,那是沒意義的事。我是你的看守,保持你的尊嚴是我的職責。不過你有什么想不開了,一定要對我說出來,我可是你自己挑中了做你的看守的,有什么事我要背上一輩子的責任。”
坦白說,我當時實在沒有那么偉大,絕對扯不上什么人權(quán)衛(wèi)士的事。只是人命關(guān)天責任重大,萬一他受辱之后想不開,我的擔當就大了。
最后,我說:“你年紀比我大,這些道理都懂,我不多說了。你同意了,咱們的交換條件就這么定了。”
張伐點了點頭,我們就站起身回宿舍去,臨走把攤著的草褥子翻了個身,讓它曬個透。路上我對張伐說:“勞動量力而行,別死扛著跟自個兒過不去。得空給家里寫個信,我拿去營部讓工、軍宣隊過過目,再貼上郵票幫你郵了。有什么事什么想法別憋著,千萬得對我講出來……”
從此我就跟張伐朝夕相處形影不離,一個看守跟一個專政對象就這樣拴在一塊兒了。
過了幾天就是月底,大部隊回上海休假,干校宿舍里空蕩蕩的就留下我同張伐兩個。那天下午我匆匆從伙房奔回宿舍,對張伐說:“快拿上換洗衣服,伙房采購有車,咱們到南橋鎮(zhèn)上去洗個澡。”
不知是我的語氣急促了點,還是張伐積了一肚子的怨氣,也可能是他的自尊心習慣使然,覺得這種“磋來之食”他不能隨便接受,竟然冷冷地回答我:“謝了,我不去。”
我催促他說:“快,快,車等著呢,走吧,走吧。”
他還是斷然說:“我不去。”
我一時也顧不上跟他多爭幾句,趕緊又跑回伙房去,對駕駛員說不去了,不能讓一車人等著。返回宿舍的路上我不禁又氣又惱,寒冬臘月的,經(jīng)過一個月的體力勞動,洗個熱水澡泡泡該有多美,真是上上等的享受啊!何況我又在伙房燒火挑煤,蓬頭垢面,一個月積下的汗垢使我的內(nèi)衣像一層殼兒似地粘在身上……不過路上一陣北風吹吹,倒是冷靜了下來,得,不跟他計較。
那個下午,我同張伐就一人一張小板凳坐在宿舍草棚外,彼此一言不發(fā)地冷戰(zhàn)著。我這個人有潔癖毛病,手里拿本英文字典在看,冬日的和煦陽光一曬,頓時覺得背上奇癢,就回屋去拿出金焰給我的他自己手工制作的不求人(俗稱扒扒撓),從衣領處伸進去,使勁在背上撓著。周圍沒人靜悄悄的,這撓背扒癢的咯吱咯吱聲夠響的。聽到了這個聲音不要說背上,我全身都癢起來了,真是越癢越搔,越搔越癢。再看看張伐,他像老僧入定似的在小板凳上默默坐著,我更是氣惱,更是用勁在搔……
天漸漸陰了下來,開晚飯的軍號聲傳來,張伐站了起來,一邊進屋去拿碗筷,一邊低聲說了句:“吃飯去吧。”真是菩薩開金口了,平時都是我這個看守招呼他去吃飯,現(xiàn)在倒是他先來招呼我去吃飯。得,大家都收吧,冷戰(zhàn)就此結(jié)束。在去食堂的路上,他吶了句:“你的英文不錯嘛。”我的氣還沒有完全消掉,就隨口應了聲:“還可以吧。”他聽出了我的不滿,帶著歉意說:“你怎么不去洗澡?”
我更是氣不打一處來,回了句:“你不去,我怎么好去洗澡!”
對啊,一個看守怎么能擅離職守把監(jiān)管對象丟在空曠的海邊,自己一個人去鎮(zhèn)上洗澡呢?監(jiān)管對象竟然剝奪了看管的美好享受。我想這個時候,張伐該充分認識到我倆的處境吧,他被剝奪了自由,我呢,為了職守也失去了自由,講得不嚴重點吧,至少是泡一個久違的熱水澡的自由。
等到大部隊休完假回到干校,我立馬去營部說,以后每月休假期間要安排留校審查對象去鎮(zhèn)上洗澡,他們不洗我們這幾個看守也得洗一洗啊。打這以后就有了不成文的規(guī)定,連問題最嚴重的隔離審查對象都去。我沒有對張伐說向營部提出了洗澡這件事。不過,他再也沒有對我耍過態(tài)度了。
有一天上午,專案組通知我說,有外單位來人外調(diào)張伐。我就把張伐從大田里叫回來,同他拿好熱水瓶、茶缸,拿些報紙和一本《毛選》,進到宿舍盡頭的工具間里,讓他避一避不讓外調(diào)的人看見。張伐朗聲地說:“我去見他們,聽他們怎么說!”我盡量和緩了口氣對他說:“我知道你不怕他們,可我怕他們不守政策亂來。”張伐就不同我爭了。
我一把將工具間的蘆席門關(guān)上,在門外對張伐說:“你先坐著,我不招呼你別出來,我去去就來。”
一路小跑到了工、軍宣隊營部,只見有外單位的三四個人在著。我大模大樣地看了他們的介紹信之后,開口問他們要外調(diào)張伐的什么問題。
他們七嘴八舌講了一通,都是些面上的問題。我就知道了他們無非是打著斗、批、改的旗子來親眼看看張伐這位名演員,文革當中總是有些無聊的人以革命的名義專干些無聊的事。我就說:“你們提的問題專案組都已整理成檔案了,我叫專案組摘抄一份蓋上公章交給你們,請你們坐一會兒等一等。”
他們當然不依不饒,我就軟磨硬頂。邊上工、軍宣隊早已厭煩了這種人到干校來看西洋鏡繞勿清爽,也就由得我同外調(diào)的人搗糨糊。看著他們不見到張伐決不罷休的勁頭,我就信口說起來:“最近有些階級斗爭新動向,審查對象蠢蠢欲動,我們將牛鬼蛇神圈了起來隔離審查。我們正處在一些大案要案的攻堅階段,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支持我們。春橋同志說‘電影廠是洪洞縣里沒一個好人。江青同志說‘要抓緊斗批改,盡快整出一個廠子來。我們歡迎各條戰(zhàn)線上的造反派同志們參加我們的斗批改,將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我鼓動如簧之舌,將社論、毛選、中央紅頭文件、首長傳達講話等等,倒過來順過去說了一大通,就是不讓他們直接面對張伐。
這伙人還真有極大的革命熱忱,捱到了中午還不走,幾檔子外調(diào)的人擁在干校大食堂里指指點點,將干校學員一個個輪番審視過去,還大聲地議論著:“迭格是啥人啥人,迭格勒拉啥個戲里做過壞人,迭格人是啥人啦?面孔哪能熟得來名字叫勿出……”我見狀就幫張伐打好飯菜,讓他坐在宿舍里吃,免得去受外調(diào)人員的騷擾。當我捧回飯菜交到他手里時,張伐連聲說:“這怎么好意思,謝了,謝了。”這在沉默寡言的他來說,是極難得的了。
打這以后,我們倆在眾人面前是一個看管和一個審查對象,私底下就和緩了許多。張伐的確少言寡語,一落到了審查對象的地步話就更少。不過每逢大部隊休假的四天,他的話慢慢就多了起來。據(jù)心理學家分析,在當時的狀況下,如果張伐沒人說話或者不愿意講話,人很快就會精神崩潰,喪失語言能力。據(jù)說胡風出獄之后,說一句短短的話都要想半天才能講得出口。現(xiàn)在看來,張伐挑選我做他的看守不無道理,當然我也不能洋洋自得,因為他還可以同看守吵嘴來保持自己的語言能力。當時我們這批看守都是業(yè)余級成員,沒有受過訓練用保持沉默來不同專政對象交流。真把張伐憋死不同他說一句話,就會讓一位演員喪失語言能力,這就太駭人聽聞了吧。
千把號人困在荒蕪的奉賢海邊,張伐同我談論的無非是身邊周圍的人和事,有時他也會對我講講電影圈里的軼聞掌故,趣人趣事。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臧否人物極有原則,公允客觀,對我這個后生小子很有教益。記得一次他講過,“某某很多人都不喜歡他,可是他從來沒有亂咬過人,更沒有亂咬過跟他有過過節(jié)的人,這個人可是個好人哪!”我說:“齊衡也從來不亂咬人的。”張伐接著說:“要不當年我們大家怎么會稱他‘齊圣人呢。”我驚訝地說:“我只知道以前梨園界尊稱蕭長華和姜妙香兩位老前輩是圣人,原來齊衡也是此般德高望重。”張伐說道:“解放以后經(jīng)過思想改造,批判說這是封建殘余,大家才逐漸不叫他了呢。”
有一次談到運動中“學生老是打老師”的現(xiàn)象,我說“你的關(guān)門弟子史久峰不錯,盡管他的處境不容易,他就沒有為了劃清界線亂整你。”張伐說:“當時文藝界有這么一股拜師風氣,領導也挺主張,劇團找我說了,我看這孩子挺厚道,演戲也很用功,就答應下來了。說實在我真沒教他什么。”我就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自身。他有你師傅這么一個榜樣,得益匪淺哪。”
突然張伐話鋒一轉(zhuǎn),“我們都知道,走在路上遇到了,邊上沒人,你還是稱呼王世禎‘王老師,叫張駿祥‘張校長。他們還偷偷搖手叫你莫喊。”我說:“我是覺得他們能有什么大問題呢?再說了,‘一日為師,千日為父。他們總歸是我的恩師吧。”張伐說:“我們對你的評價是守政策,這是從你寫的大字報和批判會上的發(fā)言可以看得出來的。”張伐嘴里說的“我們”,就是代表了當時的一大批受審查的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人物”,全都是我的老師輩和太老師輩,他們這么說,可真是太抬舉我了。
我連忙講:“這都是導演強明老師教我的,要守政策。”張伐聽了有點驚訝,抬起眼睛看看我。
我說:“我是1966年6月15日從青浦農(nóng)村調(diào)回來的,此前的大規(guī)模四清運動已經(jīng)告一段落,我跟著強明做復查工作,他是組長我是秘書。后來當?shù)厣鐔T稱我們是‘摘帽組,因為講是講復查,一查下來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復查報告也就寫成了摘帽報告。”以前宣布戴什么地富反壞右帽子是大張旗鼓,開轟轟烈烈的全體社員大會,可這時我跟強明老是晚上黑燈瞎火偷偷溜進人家家里去,宣布把戴上不久的帽子摘了,這么做是怕傳開來了引起連鎖反應,不好收場。強明到底有經(jīng)驗,他對我說,‘每次搞運動都是這樣,開頭帽子一大堆,到了最后定案沒幾個。我問過他為什么有些人就這樣不負責任呢?他說‘我跟你就不要這樣不負責任吧。”
張伐沉聲地說:“強明心臟病很嚴重,還不知道能不能挺得過去呢。”
我跟了一句:“我是記住了他說的話,守政策主要是實事求是吧。”下面就是兩個人沉默以對,在漏風的蘆席棚里聽著海邊的朔風咆哮,間夾著陣陣低沉的海潮聲,我同張伐都知道這樣的話題是萬萬不能繼續(xù)下去的。
有時候張伐也會跟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講些閑話,記得他告訴過我,他有部小奧斯汀汽車,邊講邊用手勢示范給我看,這部車的排擋是H形動作的。看到他這樣信任我,我也如實告訴他,我爺爺有過一部福特牌的老爺車,從家里留下的照片上看,怎么也是一個大玩具。講罷兩人相視一笑。反正只有我們兩個在,說話就隨便多了。他還告訴我,“二茬的膏藥最好,用過的傷膏藥不要丟掉。”我問他什么道理,他說,“北方的車把式(趕大車的人)說的,練武賣解的也這么說的。”他早年是東北來的流亡大學生,我當然相信了,不過也一直沒機會撿到人家用過了丟掉的傷膏藥。現(xiàn)在這種傷膏藥只有在影視劇里才見得到了,是一張整個巴掌大一點的紅紙,上面黑糊糊地涂了一團中草藥熬出來的黑藥膏,除了拍戲誰還會用到它。
說實在,在我們的干校談話中,真沒聽到過他說什么人不好。這在當時,工、軍宣隊高舉紅彤彤的照妖鏡,哪一個“文藝黑線人物”不是被斗得墨墨黑,可張伐堅守自己的為人之道,那是十分值得尊敬的了。我們是講起過一個人,我說這個人因為害怕極了才咬出這么多人來。張伐嚴肅地說:“人不是鐵打金剛,誰都有害怕的時候,可害怕是害怕,害人是害人,不能因為害怕了去害人,還連帶害了人家的家屬子女,這種事絕對做不得。”我老老實實回道:“是,絕對做不得,我一輩子不做。”
我很少(恐怕是第一次)見到張伐臉上滿意的表情,因此,至今還清楚地記得。
終于到了張伐的專政待遇降了一級,我們的約法三章也就執(zhí)行到了頭。張伐搬回自己的連隊去住了,可以回上海去休假了,看管與對象的專政關(guān)系也就解除了。
結(jié)束干校生活回上海之后,我同張伐來往很少,我始終認為不能謬托知己,也不應該去打擾人家的正常生活。不過有一次幫他搬房子,我跟史久峰、祁明遠和孫棟光一起去的,因為他子女不在身邊,需要強勞力幫手。這次搬家過程中,有幸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張伐夫人,雖然歲月無情,歷盡劫難,依然可以看到張伐夫人身上的大家風范,那是當今大小美女明星們怎么學也學不來的。
偉大的俄羅斯戲劇藝術(shù)家、一代宗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過:“一個偉大的演員在舞臺上成功塑造的形象,都是他本人的一座座藝術(shù)豐碑。”張伐在話劇舞臺和電影銀幕上成功創(chuàng)造了許許多多座豐碑,希望這篇小文能成為豐碑底座上的一顆小石子,此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