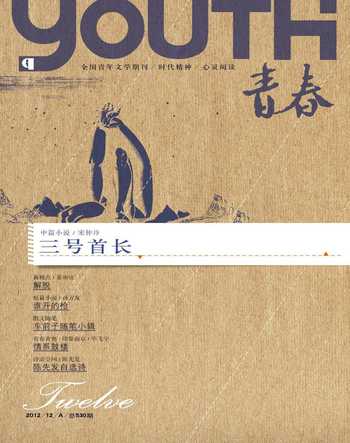返回金色村莊
蘇寧
葬親之地
我將寫的這個村莊,由一條河流的名字命名,它是遼河一個支流,如今早已干涸不在。前年清明,因為祖父去世,一心希望埋在那里的緣故,我們送他的靈柩回到那里安葬。
那是我離開那里多年之后第一次回去。再不是記憶里的樣子了。我也再沒有找到那條曾經的河流,連河床舊跡也已隱約難辨。這個以河流為名的村莊,我幼年時在此住過。曾經有著廣闊無邊的原野的美麗村落,因為比鄰的城市的不斷擴展,一點點被圍進去,先是一些年輕的孩子,他們無法拒絕那些有時代感的東西,從內心向外無法抗拒時尚誘惑,在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在他們所接收的信息中,城市中心地帶仿佛是人生夢想的所在之地,樓堂館所,華裳美飾,一切氣息,形態(tài),聲音,都有近于理想的年輕的味道。年老的人,或者被他們的孩子慢慢帶進城里定居,或者因為年邁和疾病死去,成為樹林空地中一堆一堆沉默無語的墳塋。房子破舊了,再無人翻新重建,在時光中頹敗下去……好像終于完成了守護那一家?guī)纵吶税滋煨菹ⅰ⑼砩习裁摺⒉槐伙L吹雨淋的重任。房子一間間空出來,因為沒人住了,草也變得有勇氣從房頂上墻垣上四處長出來,愣頭愣腦,像沒有管束的孩子,衣寬袖大,滿世界瘋長瘋跑。
那一天,我走過一村的院落,也看到一些人,可已經沒有人認得一個多年前在此住過的孩子了。我也是想上半天也記不起其中任何一個名姓。在村子正街前面的一條街上,我抓住一個正跑著追一只皮球的小孩,說:知不知道我也在這里拍過皮球?旁邊咪著眼曬太陽的老人,也許一霎那隱約想起當年曾見過我這么一個小孩,也仿佛是自言自語,他對我說:還好,你回來趕上看它一眼了,這些房子全要拆掉了,這塊地,早被人買走了,過不了幾年,它就沒有了,那些樹,肯定也不要了,那些墳地,也要平掉,已經通知要不遷走,要不原地挖深深埋,人老歸天,貓老歸山,這個村子,也老了,人老了沒樣子,它也老得沒樣子了。
這個不曾在地圖和地方志中出現(xiàn)過的村子,在那個下午使我無比悲傷。因為有我幼年的記憶。回來后,心意難平,我開始試圖用文字把它在紙上做一點保存,希望它在文字中的存在使我的童年,還能有一點溫度,有一個出處,也許它也是很多在那生活過的孩子共同的記憶。它曾經存在,但越來越像一個難以追索的夢。是多年后無法找到憑證的生命的重要部分。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很多這樣的鄉(xiāng)村,成為城市的伸延,使它做了它的一部分,卻又是疏離的,兩者若為母女,它得不到它待親生骨肉地疼,若為夫婦,貌合神離卻不分手,未來如何融合慢長而未知。
我的童年,正處于改革開放之初那段時間,關于這個時段的鄉(xiāng)村生活景象和民風,還是樸素和純凈的,四處是春意盎然之象,它的生氣和真誠可坦然相待于萬物。關于這一時段的鄉(xiāng)村生活景象,我所見記載亦不多,這也是我所以決定記下的另一個原因。我想,它應該還是我內心對文字的信仰的一次表達。對于記憶里的鄉(xiāng)間風物氣象,以及民眾的精神情懷,呈現(xiàn)于紙上,不免要沾染個人理想情懷和精神意志的味道,況且,記憶這東西,是難以忠誠于光陰的,在不停流動向前的光陰中,記憶中的人事總會因光陰帶來的個體成長而使它本來狀態(tài)發(fā)生微妙變化。但我確信,一個孩子所看到的事物在時光中的樣子,總是會過了很多年仍被這孩子記得清晰。希望這個記錄能喚回它,像一個母親在幼子成人之際再一次喊出乳兒之名。一切的記憶,都沒有死去,它會活得比我們每個人都長久一些。
土地、童年、故鄉(xiāng),它們到底是我們生命中的什么?生活日新月異,每一天都將比前一天更燦爛和美好。在一些安靜的黃昏,我希望有一個人,終于看到了我這些文字,他把它放在枕邊,讓它陪伴自己過一些長夜。在我們寂寞的成年時光中,那曾經存在但又消失的一條河流或者一個村莊,相信它們都會回來,只是可能換了一個名字。那存在過的一些事物,消失也就消失了,不必記得太深。
現(xiàn)在,當我寫這些字的時候,寫到這片我童年時代住過的土地的時候,我面前全是秋天的景象:成垛的金色的玉米、成垛的金色的麥子,成片的金色的稻田,一畝一畝地排過去,稻穗沉得快彎到地上了,孕期已深的母親的樣子,好像我的親人都還才從那稻田里除草歸來。
草木衷親
開篇說過,我幼時所住過的拉馬河村有一條筆直寬闊的大路貫通東西。這條路,我出生時便是這么虎虎生風地存在了,只是在我于此生活的十幾年時間里,我忘了問一問誰,這條路是何時所修,且不知當?shù)赜蟹襦l(xiāng)志并于其中記載。
若以今日之我估算,這條路長于我十年二十年總是有的。有一年開春,我大約總在五六歲,已經識字了,好像是才第一次真正跑到這條路上來,我一下驚住了,兩旁高高的白楊樹,所有枝杈正一齊拱出嫩而淺綠的葉芽,卷卷的,細細的,正要舒展,此時樹干還是灰白枯裂的受了嚴冬敲打的樣子,這齊展展的輕柔的懸在枝上逶迤遠去的兩隊新綠仿佛一下子就把一個孩子的心教會了飛,仿佛才是第一次真正讓一個小孩看到春天結隊而來的樣子,看到除了她出生的小村之外,還有同樣的小村,綠色的春天,也要到達那里,要一直綠到最遠方。
這些樹既不大結果,也不大開花,綠葉展開到足夠大就是真正的春天,然后結出一串串小穗子,孩子們可以用它做項鏈,綠色再深些,那小穗子就揚出絮子,飛得滿天,天女單單散著一種花似的。雖說有些像花,但究終不是花,所以在我,這些樹好像都是雄樹,在我六七歲,也許是五六歲時,它們就已經長了有十年八年了,這些白楊靜靜分列在大路兩邊,列隊遠去,每邊都種有三兩行,偶爾見到一棵大楊樹,很高很壯,似乎已經是一根檁子或一只大車轅的料了,剛被砍倒,那根就隨之被挖出,在這原地,一棵小楊樹苗連夜種了下去,就剛種進去的小楊樹就像一個小孩子,被夾進了大人的隊列里,在和大人一起吃飯干活、東張西望間,跟著一溜煙地長大著。
路邊植楊,河邊植柳,這規(guī)矩因何而來,從何時而來,我至今亦是不太明了,也許所謂約定俗成吧。這路與河都是人們生息的重要場地,也許因此,這人家的房前屋后也沾親帶故似的種著一些楊樹柳樹,楊樹是雄樹,可以看家護院,柳樹多女子氣,所以種了多半是為賞心悅目,能種在院里院外的還有榆樹,這是很硬氣的樹,鄉(xiāng)下人不大會轉彎罵人,但若這人太笨到不可以教化,不開竅,即為“榆木腦袋”,我住過的村里歷來也是有幾個長著榆木腦袋的人,真是笨得不可浪費紙張細表。榆樹之葉,我們呼之為榆錢,圓圓的,初上枝頭最嫩時,色若新金小貓似的溫柔可愛,久之老掉即沉重漸白。嫩時一嘟魯一竄的,葉密密的擠在枝上,味道甜甜,是孩子的小點心也是水果,還可燒湯為菜,有如百任可當。榆樹歷來還被有些人看作招財聚寶之樹,既然這樣,真是不可不種,所以家家都要種上一棵。不過也不知為著什么,我們一村的人都把一棵榆樹種在房子后面靠著墻院最邊上,不知是何意,也許是家家如此,過日子嗎,不便出格。后來去和紳家,他也種了一棵榆樹,位置卻是他家水塘的邊上,看來他確實比我們村里的人更愛聚財。《齊民要術》中曾有“收榆之青莢,小葵曝曬,冬至而釀酒,滑香,宜養(yǎng)老”,只是村中如此多的榆樹,年年生莢,老去,卻無人用之釀酒,真是可惜得很。
柳樹多是笨柳,沒有我長大后在南方一些水邊所見的那么婀娜,可那十分的婀娜在我看來不免有些嬌情任性,不如村中幼年所見柳樹的樸素。
家里打柜子打箱子做房梁的多是松柏木,堅韌有耐力,可這松柏多長在附近的小山坡上,地氣好,又是空地,人人來種,十年二十年便是林子,林子中還有老人永久安息,所以,漸漸的,也是一塊墓地了,此地風氣,墓地前后,植幾棵樹,為著墓里的人也許寂寞,也許要憑著一棵樹來辯知四季節(jié)氣,松柏雖說是長青之樹,但在鄉(xiāng)下的人還是能在一枝松枝上看出日月輪回已到何處的。松樹,柏樹,這么好看的在漫漫嚴冬里唯一綠著的樹,我一直很喜歡它。
這些樹,年年月月的生息下來,陪著一個村子的人,也許只有這些樹,它們會均勻地愛每一個人,憐惜一切它自己以外的眾生,它不為單獨的任何一個人而綠或枯老,它們?yōu)樗腥怂惺挛镄膽驯瘧懀鼈円矎牟惶呓覀儽揪鸵押芗拍纳睿皇沁h遠的打量。保持尊嚴距離。
也許,一個心懷憂愁的人,他在田野或山坡中走,一棵一棵樹木從他眼前移過,這些樹,也許比他還要寂寞,還要老,或者它們比他還要年輕,但這些樹總是朝氣盎然的樣子,讓他一望之下,覺得自己的寂寞煩惱不過是天地之間最微小地最不值得為之一苦的,或者是另外一種情況,他心中另有所思,他走遍一百里的長堤,一百畝田野,就像在什么也沒生長的大地上走著一樣,那些樹只是天地之間一組靜物,他的目中有如空無一物。是的,他們是另一種人,可以不必在此時非得看到這些忠誠義氣的樹,只有我,現(xiàn)在想來,仍覺得那每一種每一棵仍如我的親人,在苦痛時,獨獨可以抱著它們大哭一場。
跳大神
有些人生了病,雖經中醫(yī)搭過脈,又在那村縣的衛(wèi)生所中打過針,還是百般不好,去不去城里的醫(yī)院看看呢?一院子的瑣碎事情,實在拿不定主意。
人生在世,生幾次病是尋常事。可一些上年歲的人一心想知道病起何因。兼之歷來的風俗逢年過節(jié)有病遭災,都要找仙姑來看看才安心。
謂之仙姑,當然是位女仙,既為仙,一定是要漂亮的,長得不好不要緊,但要會打扮。頭上一朵大紅花,春天簪芍藥,再遲些,石榴紅的卷蓮,稱之為蓮卻是旱地里長的。西番蓮開了,那西番蓮花也是很美的,有紫有紅,摘一朵戴在頭發(fā)上。雙朵的紅牡丹,瓣重色艷,帶了尤其好看。月季雖然小,別了總比沒別強。秋天往后,園子里時興的鮮花都謝的謝,敗的敗,那用紅綢子做一朵花好了,同樣紅艷艷、水靈靈,而且能一直帶著而不壞,這花只不過太完美,比西番蓮壯實,比牡丹圓潤,比芍藥色更正。出神時簪上,不出神可能是不須簪的,天天出神時有著這樣一朵花,也是底氣,平時,可不能,她也要煮飯,要炒菜,想必煮燒時也是要像凡間女子那樣在灶前彎下腰的。我住過的村子里早前也有仙姑,但后來據(jù)說沒有了。我出生時,村中來的仙姑已為外請,她坐著馬車一來,就已打扮好了,接仙姑多用馬車,三匹馬套著,若是冬天,那車上往往還鋪著棉被,讓仙姑坐在車上,用棉被蓋住腿,仙姑那么端端正正一坐,手上往往還挑著一只大煙袋。
她穿著一張鮮艷的大裙子,是有著被面上的大花朵般的紅花布裙,使人以為那就是一張被面,被面雖說多繡著鴛鴦戲水、龍鳳呈祥,但那染著大牡丹、大芍藥的被面子也是有處賣、有人買。
上身那斜襟襖的顏色也是鮮亮的,一個接一個的蒜瓣子大盤扣,比真正的蒜瓣子還要粗肥很多,雖說也是青布條盤的,但一望之下,尤如大蝴蝶一只一只從下頜的領部至腋下再至小腰斜落成排。
這一身打扮一望之下也是讓人感覺仙氣飄飄,心生敬畏。她的腋下,掖著花手絹,煙荷包不是灰黑色也是花布的,尤其她下了車,一走起來,也不知是腰里還是腳脖子上仿佛都系了小鈴鐺,叮當?shù)仨懼?/p>
夏天來村里唱戲的戲班子,有一出戲就叫《跳大神》,是一女一男兩個人,一個是仙姑,那仙姑因為是神仙,所以叫大仙。大仙總要有跑腿的伙計,那男的雖說做著伙計的活,但因為畢竟和仙人在一起,所以,也封了一號,謂之二仙,北方的男人略笨一些,所以,即便為仙,也是二仙。
唱詞中有好長一段是唱主人招待仙姑所備的食物,極盡華美,從酒到菜到肉到湯到煙,從天南到地北,所有物產未必都是家中所有,但要一一承報一番,為著什么?十分的敬和愛罷。如他對仙姑言:
要吃面更不難,我把面名報一番,有個伙計王老四,搟的面片賽雪片,拿刀一切一條線,下到鍋里團團轉,挑到碗里蓮花瓣。
因這一出戲人人皆知的緣故,所以跳大神必是男女二仙共同起舞的場面亦是深入人心。可若只來了仙姑,而未帶二神,大家心下雖然一疑,但一想,也許那二神另有公干(實際是忙著連日出馬,玉米地早荒了,他要在家忙著鏟二遍地),而這仙姑既然能自己來,想必也是胸有成竹的。
仙姑來到,先以好酒好菜招待,這仙姑酒量又好,五六十度的高梁燒亦覺得可口,她三杯兩盞的一飲,愈發(fā)使人覺得她的可親可敬,不高高在上,亦食人間煙火,如此的可親近,那醫(yī)病問卜的效果自然高上一層。她若在家是吃了飯而來,那自然不餓,所以亦是可免掉宴飲而直接跳神的。四平八穩(wěn)的八仙桌,用一張紅布蒙了而為香案,再殺一只大公雞,就可以跳大神即謂之出仙了。
這跳大神的功能有:一可驅邪祈福,二來問病因,三是好多人還深信仙姑可幫著看病。
若二神沒來,旁邊要找一個經過事的幫著打鼓,鼓聲一響,女仙即神色端穆,然后全身有韻律地擺動,那身體柔軟至極,是真正的滿族宗教儀式還是關東的民間舞蹈?或者是兩者已默默無聲地于時光流水中慢慢相融?一開始她是慢慢舞,慢慢搖,然后越旋轉越快,她有時一只手還打著另一只小鼓,鼓點聲越來越密,她舞得越來越快,是急急落下的夏天的一場雨。落雨聲中,鼓聲嘎然止住,她唱一聲:仙童來呀哎(也許是仙姑或仙人)……聽得不真切。這一聲呼之后這仙姑便不是仙姑而是另一個人了,這個人也許是神仙,也許是那病人祖上的魂靈,這從她那說話的口氣才可以知道。既而她表情更莊嚴,舞姿趨緩,開始唱曲,曲調婉轉悠長,詞意也能聽得清,兼或停下問一聲病人生辰八字或家鄉(xiāng)年庚之類,唱詞中兼有去年八月犯口舌,或報柴垛時不小心拆了黃鼠狼的窩之句。
誰家一請了來跳大神的,那一村子的人都放下正干著的活,來觀看,看的人越多她越歡喜,小孩子往往一心看她跳舞,大人們往往邊看邊琢磨她所唱出的句子,并不停地點頭,低頭默想以印證,而那病人家里多跪伏在地,只耳朵豎起來聽唱詞,并在心下一一記著。
那舞蹈,是我小時候見過最詭異而美麗的舞蹈了,那女仙也許年紀大了,但在小孩子看來,仍是當年鄉(xiāng)下最神密而好看的女人,加上出語成章儼如奧妙經文,真是一個通天地神古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子,安慰了人們普遍的對于生老病死十分的懼怕和無限的寂寞。有了她,仿佛那生病也不是可恐懼之事,仿佛有來自她或天地自然的力量幫著抵擋似的。兼之一些仙姑本來脾氣就不大,且說話又能慢言慢語,則更為可愛可敬。哪怕最末,她說:這病恐怕來勢洶涌,要去城里醫(yī)院瞧瞧或一定要找人搭脈開藥這樣的話,也不覺得奇怪而只覺得更像親人。
二人轉
寧舍一頓飯,不舍二人傳。關東的小孩子都是聽著二人轉長大的。也聽評戲、京劇、大鼓書,但也許因為是聽得少,所以感情有些淡。評戲中,聽來聽去而不厭的,有《花為媒》、《茶瓶記》、《劉巧兒》,聽戲,要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聽,才解得況味。鄉(xiāng)間年年都唱幾次戲,盼看唱戲如盼過節(jié),村中空地上有專門為做戲臺而搭的土臺子,土不經風雨,常常要修補,后來聰明的人想到用四臺拖拉機的車斗一拼,四周鑲上松柏枝子,可是最好不過的鐵戲臺。戲班子一到,那炒瓜子的、賣花生的、蘸糖葫蘆的、賣雪糕的,也傾城而動,那花生、瓜子都是論茶杯而賣,大一點的一茶杯一毛,小一點的一杯五分,不用稱量,盼看戲的小孩樂趣不在聽戲而在吃。
唱二人轉的一個戲班子頂多六七人,拉弦的一兩個,演員三四個,有的班子才四五人,我自幼見過的最奢華的戲班子多不過十人,二人傳,就是兩個人一起唱戲。我幼小時亦曾在鄉(xiāng)下看過趙本山的《瞎子觀燈》和《摔三弦》。他在鄉(xiāng)村戲臺上演得遠比在電視上好,那么放松,如魚在水的感覺,他的每個笑,他眼睛微一眨,仿佛都是和一個人在秘密交流一件心照不宣的事,而每個人都能看到這樣的眼神,而他,有這樣的力量,竟使每個人都覺得那一眼獨獨是和自己一個人之間的交流,而其它人卻對此一無所知似的。《瞎子觀燈》之好,竟使每個聽過一遍的人都能唱起來。那《摔三弦》是個新戲,是為拉場戲,不是一男一女,而是一男二女(主要演員),我也非常之喜歡,到今天多少年過了,我想我仍能通篇將臺詞背誦如流,寫這個本子的若不記錯應是兩個人,亦是此地前輩,李忠堂和崔凱,所以覺得如果不背一背,真是太辜負了。可惜對白多,這一個戲寫的主題是計劃生育。二人轉男演員中聲音最好聽的我以為是韓志平,圓潤綿甜,心平靜氣而且蓬蓬勃勃,他一出來,永遠一幅書生打扮,在他之后,好像從沒有人把《回杯記》、《樓臺會》、《大西廂》唱到那樣好,松馳,嚴正。
另一位演員安志彬我也是看過他的戲的,他也唱過《回杯記》、《樓臺會》,但我覺得他的聲音里有蒼涼而不像韓志平那么溢年輕書生的朝氣。兩個人唱的《回杯記》是同一個本子,開頭都是女演員先出來道白:
一只孤雁往南飛,
一陣凄涼一陣悲,
雁飛南北知寒暖,
二哥趕考不知歸。
然后一聲嘆息,仿佛不是嘆息,有壓抑不住的喜氣洋洋和調皮,讓人聽了歡喜。所以搭檔很重要。《大西廂》這兩個人也都唱過:(女)崔鶯鶯穿花越柳向前走,也不怕露水打濕(男)身上的鸚哥服,(女)也不怕花枝扎破(男)繡花衣裳。真是又綿遠又凄涼,但后面唱到西廂觀畫中上一簾下一簾左一幅右一幅的對子時,歷數(shù)今古,一問一答,應和如流,才情四溢,扇子飛似的扭來扭去真是美得眼花繚亂,讓看的人每個人都為那唱的人提著一口氣似的。還有很多演員,現(xiàn)在不大記得名字了,《梁賽鑫搟面》、《豬八戒拱地》、《水漫蘭橋》、《包公陪情》、《馬前潑水》等也很不錯。《水漫蘭橋》我不知作者,寫得非常好,魏奎元半路喝水遇青梅竹馬的蘭瑞蓮,兩個人相認然后相約私奔,互留定情物:
男:我把小扇遞過去。
女:我把小扇接手間
男:三更若有小扇在,燒火丫頭我不嫌,三更若無小扇在,九天仙女我不攀。
…………
女:我把金釵遞過去。
男:我把金釵接手間。
女:三更若有金釵在……
兩人約定三更蘭橋相見,可惜,夜里大雨,水漫蘭橋,兩人雙雙被洪流沖走。
《楊八姐游春》也是我喜歡的一出,最喜歡佘太君向包公要彩禮一段,包公代皇上向佘太君提親娶楊八姐,佘太君張口應下,包公以為平時看錯了佘太君,不禁目瞪口呆,以為佘太君也是攀龍附鳳之流,佘太君應下親事,卻說女兒出嫁要為女兒按風俗要些彩禮,這戲的彩出來了,佘太君的禮單如下:
我要那一兩星星,還有二兩月;
三兩輕風,四兩白云;
五兩泰山,六兩氣;
七兩火苗;八兩雷音;
張果老的毛驢我也要,我女兒騎它好回門;
何仙姑的笊籬我也要,我女兒撈飯待親人;
曹國舅的葫蘆我要它半拉(半個之意),我女兒用它裝線針;
(男)呂洞賓的寶劍啊,我也要;
(女)我不要,
(男)為什么?
(女)老身我最恨貪花戀柳、戀柳舍花那路人
……
這出戲前面還要有小帽,可以是《放風箏》:
三三三月里,放呀放風箏,
桃紅柳綠草兒又發(fā)青,姐妹二人來在郊外放風箏。
大姐姐放的是花蝴蝶,小妹妹放的是蜻蜓。
邊扭邊唱,這小帽多為潤場之用。每出戲前都唱一段,因這二人轉每出戲不管戲里多少人物,也只由這一男一女來唱,他們一會扮演男女主人公,一會又扮主仆其它人等,還可以邊演邊道白評判。男的多穿書生的長衫帶著兩條軟紗翅的帽子,或肥紗褲,穿鑲金邊走銀線的坎肩,一手執(zhí)扇,扇子是紗的,或水紅或翠綠,邊上一轉紗邊,打開來一朵大荷花似的,一手執(zhí)繡滿花邊的八角手絹,這手絹舞起來上下翻飛,左右搖擺,拋到半空也可以接回來,女的多穿綢緞的裙子,古代小姐的打扮,非常符合大家的審美也經得起所有觀觀眾評判。不像現(xiàn)在所見一些二人傳演員,那么不正經的打扮,二人傳越來越沒樣子了,不像以前那么嚴肅,只是唱一個本子,從不靠其它戲外的東西華眾取寵。
兩人一上場,總是先唱小帽暖場,這經典的小帽除了《放風箏》、還有《游西湖》(是寫白娘子和許仙的一段:徐郎夫啊,徐郎夫,那一年,你我二人搭船借傘、借傘搭船成夫婦……)還有《月牙五更》、《小拜年》(大年頭一天啊,人人都把新衣服穿,也不管那男和女啊,也不管那老和少啊,都把新衣穿。大年初一頭一天啊,少給老拜年……初一到初八啊,新媳婦住媽家……)這些小帽中,亦可見鄉(xiāng)俗民風。唱過小帽,兩人要說說話,三言兩語介紹自己或劇情,然后自報幕,戲歸正傳,從不羅嗦。
曾經很喜歡《月牙五更》,因為很多戲開場前都唱它,一來二去竟有了許多版本。一般都是一男一女兩個演員唱,只是一個女的小姑娘、大嬸不拘的唱則為單出頭,單出頭中有《紅月娥做夢》,也有《月牙五更》:一更里呀月牙上窗欞,手扶欄桿呼喚梅香,銀燈掌上……,單出頭的曲目內容多為閨怨。
小帽、單出頭、二人傳和后來出現(xiàn)的拉場戲,戲文都質樸之極,多為關東方言俗語,簡潔明白,內容多涉忠誠、義氣、愛情,多截至歷史傳說中的一段,但皆有頭有尾,使人聽了不覺得有缺陷,那語言不僅生動,也是幽默的。演員們因愛而唱,端正虔敬勤勉,外人所謂臺風不端、藝不入流之說只見于目下浮燥之時而非先時風氣。
聽一出二人轉,而見北方民眾性情之堅忍、忠義、幽默、豁達,并非虛言。而怎樣廣袤的土地歷經多少年滄桑才哺育得出這樣才情四溢的戲文?人生若戲,亦或戲若人生?一二十年過去,當年那一批批游走在草屋清巷,將二人傳的至美漫天漫地不拘鄉(xiāng)間街市恣意播灑的美青年們是否廉頗未老?也是否還有那么樣多人喜歡他們,戲臺搭起來,便三天五天徹夜無眠,四面八方不約而至,萬人空巷?聽者專注,唱者也不拘臺下聽者貧寒貴賤?
責任編輯⊙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