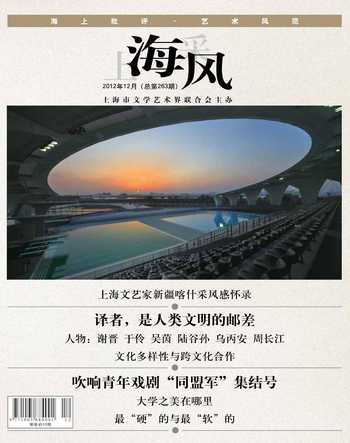莫言的美學及其政治性
張閎
在現代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中,文學所扮演的角色非同一般。在某種特殊狀態下,它甚至會以一個“救贖者”的面目出現,承載著世人的全部夢想。北島式的“救世主義”色彩的文學,始終是中國人心目中的文學范本。文學在諾貝爾獎壇上的缺席,甚至比其他獎項的缺席來得更令人痛心疾首。它所彰顯的不僅是文學和精神文化上的不足,更是被視作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整體性的精神萎頓的象征。人們對于文學的訴求并不只是在語言藝術方面,政治正義和道德純潔等方面的使命同樣也要求文學來承擔。
當代中國文學對這個時代欠債太多:現實關懷的債務、政治正義的債務、道德擔當的債務、藝術完美性的債務,等等。作家們的怯懦、無聊,乃至無恥,無不觸目驚心。現實生活中道德愈是淪喪,對于文學的道德潔癖就愈發嚴重,文學的“救贖”使命就愈發迫切。然而,莫言的獲獎被理解為對當下文學的整體性的肯定,這讓人們的“文學救贖”夢想突然間歸于破滅。現在,既然在莫言身上集中了中國作家的榮光,他也必將承載他們的恥辱。事實上,莫言本人十分清楚這一筆債務的性質,他的文學寫作,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還債”,他在現實生活中的虧欠,在文學中要加倍地償還。在我看來,這也正是他在文學中不斷追求藝術上的神奇效果和現實批判性的動力所在。但還不夠,在他獲獎之后,他還必須還當代作家的集體性的債務。無論是在精神贖罪的意義上還是在文化消費的意義上,他都必作為頭生子,成為獻給文學神殿的祭品。對于莫言來說,今年的斯德哥爾摩既是神壇,又是祭壇。
從根本上說,莫言的文學是1980年代的那場“新文化運動”的產兒。在那個既開放又禁錮的年代,有限的表達自由使得文學表達顯得更為重要,也更有用武之地。莫言在藝術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也正是他跟現實生活和政治之間糾結不清的關系的結果。現實生活中的莫言,正如他本人的筆名“莫言”所表達的那樣,他深諳“禍從口出”的生活教條,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規避迎面而來的政治旋風。而他在自己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則是通常為人們所詬病的所謂“無節制的”聒噪。文學對于他來說,似乎是一種補償。莫言身上表現出一種言說的悖論。一方面是話語的膨脹;另一方面是噤聲。一方面是言辭的聒噪;另一方面是沉默。依靠不斷地聒噪,不斷地向空氣中吐露著話語的泡沫,以掩飾內心失語的焦慮和對禁言的恐懼。這是“沉默的辯證法”。莫言深諳這種辯證法,他通過矛盾的話語暴露了當下中國言說的悖謬處境。莫言的文學話語活動,即是一種言說與沉默的自相矛盾。
這同時也是一種“沉默的政治學”。他的作品有時是以一種空前的勇氣,突擊到現實生活中的危險地段,而且發出尖銳的批判之聲。另一方面,他又以不斷膨脹的話語泡沫,來掩蓋其真實意圖。只有在這些讓人不勝其煩的聒噪聲中,莫言才敢大聲說話,并說出他對現實的不滿和對不公的憤怒。這個不停地吐露泡沫的螃蟹,偶爾露出他的那對有力的大螯,構成對現實的抗議和威脅。
莫言文學的政治性是顯而易見的。莫言自己也宣稱,他的文學大于政治,很顯然,他在提醒讀者,不應該將文學的政治性與政治本身等同和替換。莫言文學的政治性,即是在他的話語的世界里,顛覆現實中的政治秩序。莫言的這一政治批判的慣用手段即是“戲仿”。戲仿的修辭規則是游戲性的,這是莫言小說最重要的文體方式之一。戲謔的言辭、動作和儀式,構成了制度化話語方式的嚴肅性的反面。戲仿文本以一種與母本相似的形態出現,卻賦予它一個否定性的本質。它模擬對象話語特別是對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嚴肅的外表,同時又故意暴露這個外表的虛假性,使嚴肅性成為一具“假面”。這也就暴露了意識形態話語的游戲性,或干脆使之成為游戲。戲仿使制度化的母本不可動搖的美學原則和價值核心淪為空虛,并瓦解了制度化母本的權威結構所賴以建立的話語基礎。因而,可以說,戲仿的文本包含著至少是雙重的聲音和價值立場,它使文本的意義空間獲得了開放性,將意義從制度化文本的單一、封閉、僵硬的話語結構中解放出來。從這一角度看,戲仿就不僅僅是一種否定性的美學策略,它同時還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念和價值原則。這一點集中地體現在小說《歡樂》中,混響的“聲音”,雜蕪的文體,開放的結構,形成了一種典型的(如巴赫金所稱的)狂歡化的風格,既是感官的狂歡,也是話語的狂歡。但這種看上去仿佛巴赫金所稱的“狂歡化”風格,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是一種偽裝。好像一位頑童借過節的喜慶氛圍,大干平日里不敢的惡作劇。
莫言的小說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現代小說的范本。他并不因為對寫作的倫理承諾的恪守,而把敘事藝術處理為一種簡單粗劣的道德美餐。各種各樣的人物聲音各自擁有自己的“真理性”和一定支配權力。在這個權力的國度里,嚴肅性和“硬度”是話語的權力的保證。但莫言的戲謔性的模仿則打破了這些話語自身的完整性和封閉性,打斷了其支配力的連續性,使之變成了種種荒謬的東西。話語各自的“硬度”被相互抵消,抵消它里面包含的支配的權力。莫言的文學世界錯綜復雜,詭黠怪誕,呈現出一種極為復雜的結構和重疊交錯、自相悖謬的立場。在莫言看來,不如此不足以表達當下中國現實生活的復雜性和荒誕性。惟其荒誕,才顯寫實。從這個意義上說,莫言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而所謂“迷幻現實主義”(Hallucinatory Realism),在表達現實的時候,肆意制造迷幻的效果,在莫言那里,既是美學策略,也是政治策略。莫言的文學以其內在的復雜豐富,來反抗外部的簡單粗暴;以其悖謬和滑動,來抗拒政治權力對文學的直接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