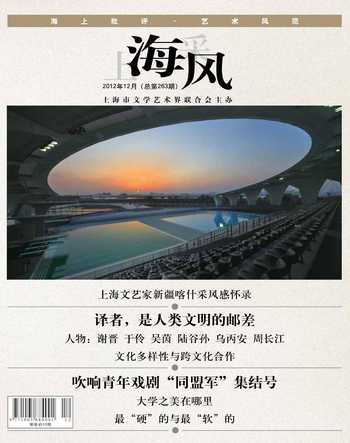最“硬”的與最“軟”的
王焱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硬道理”一說被泛化成了社會中的流行話語,有被濫用之嫌。
將世界上的道理區分為“硬”的與“軟”的,按照這一說法,凡屬于“硬”的道理,就意味著這一道理是不容討論的,是必須強制執行的。而凡屬于“軟”的道理,則都是些可有可無的,可以任意犧牲的,輕易就可以被替換掉的東西。
在硬道理流行前,我們常聽說的是“抓綱治國”。所謂“綱”就是羅網上的大繩,漢代的班固說:“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在班夫子看來,抓住羅網上的大繩,就可以萬事皆理。比起“目”,即網上的網眼來說,“綱”就是硬道理。于是,我們有過“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最后發展到“階級斗爭是個綱,綱舉目張”。但是吊詭的是,在“以鋼為綱”的年代,引發了大煉鋼鐵的狂潮,但是除了自然生態遭遇了滅頂之災外,真正可用的鋼產量卻并沒有增加。在“以糧為綱”的年代里,竟然發生了罕見的大饑荒。說起來,只有階級斗爭這個綱落到了實處,但造成的結果卻是不僅冤獄遍于國中,連國民經濟也跌至了崩潰的邊緣。
由于抓綱治國論忽略了經濟,荒廢了民生,因此后來者就不得不變成了逆向的抓綱治國論,即強調只有經濟增長才是硬道理。但是多年過去以后,網絡上廣為傳播的卻是央視主持人白巖松的這樣一段話:“三十年前你們宣傳‘計劃生育好,政府來養老,我們信了;二十年前你們改為‘計劃生育好,政府幫養老,我們依然可以接受;十年前你們徹底顛覆了過去的承諾,改成了‘養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們交錢養老也認了;現在我們老了,又說養老金不夠了,要我們活到老干到老!”這其中每一句話的前一句,其實當初都被視為是“硬”的道理,但是發展到后來,卻無從兌現,結果又變成了“軟”的。在經濟增長被視為“硬道理”的年代里,社會的正常發育,經濟成果的分配公平,公民的自由尊嚴,法治框架的實施與建立,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等等,都被當成是實現硬道理應當付出的代價,未能予以充分重視,導致了很多負面的后果。這說明,即使“硬道理”硬了,并不意味著被視為軟道理的其他價值就能夠自然實現。
硬道理為什么能夠“硬”起來呢?說到底,硬道理的“硬”,依靠的是政治強力。也正因此,我們可以把這種說法視為一種依賴政治強力的話語。在官民分立的社會,“硬道理”大都是出于官之口,這又意味著老百姓講的都是軟道理。
追源溯流,硬道理的發明,來源于軍事斗爭時期的習慣和思維定勢。戰爭沖突中,關鍵在于取勝,至于所付出的代價,往往不是軍事主官考慮的問題。在這種兵家思維的支配下,軍事話語到處流行,命令—服從的等級關系被復制到整個社會關系之中,結果往往是扶得東來西又倒,按下葫蘆浮起瓢。這意味著,中國在完成完善一個正常國家的制度建構上,還有一段路要走。
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認為,所謂現代性,意味著社會各個價值領域的不斷分化(differentiation),不同的社會領域各自有其不同的主導原則,換言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不同領域各有各的硬道理。如果以政治強力為后盾,將一個領域的單一道理強行覆蓋到整個社會,將會導致社會的功能紊亂,結構失調。從這種意義上說,社會話語中硬道理的泛濫,又說明我們距離真正的現代社會還很遙遠。
既然如此,為什么硬道理還是如此泛濫呢?美國漢學家墨子可曾經分析過中國文化中的幾種深層的未經充分反思的預設,這包括:1、樂觀主義認識論,2、全民政治,3、萬能政策,4、中式烏托邦,5、迷信可以由上而下加快歷史進步的步伐。總而言之,這是一種“天下可運于掌”的信念。這種信念認為,少數精英人物有能力參透道德的真理、歷史的本質,有能力找到一條唯一的出路,來解決人類社會道德、文化和歷史的問題。
而在那些成熟的現代社會中,占據主流的卻是一種悲觀主義認識論。在這種認識理論看來,社會的秩序結構是許多人的行動與規則系統之間互動的產物,而并非個別人主觀意圖的后果,更不是單個或少數精英人物設計的結果,因此制度的設立與進化,比一種意識形態的發明,或歷史目的論的預設更為重要。那種總是要求全體民眾全力以赴的短期政策目標,其實并不是真正的“硬道理”。治國理政就像是像彈鋼琴,哪一個琴鍵都是重要的,如果只是反復敲擊一個琴鍵,即使強力推薦這是硬中之硬的道理,得到的恐怕也很難是和諧的樂章。如果說有一個執政者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那么應當是現代國民國家制度的構建與完善,而杰出有為的政治家,可以在這一制度框架之內,利用市場和法治這些文明的杠桿,去實現自己的施政目標。
生活是千姿百態、異彩紛呈的,人們的價值觀也是多種多樣的。要說真正的硬道理,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理想的中心是人,人是生活著的。”(黑格爾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