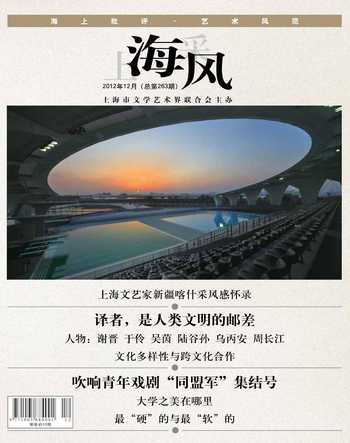上海漫記
彭見明
我認識上海是文學聯的姻。
我的小說處女作發表在上海的《萌芽》雜志,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我的一篇能夠被不少人在一些年后還能說出篇名來的小說也是《萌芽》雜志的提攜,因我如今還是吃的文學飯,寫字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這些“第一”是我不能忘記的。
我與上海的一些文學編輯聯系密切,在我的印記里他們普遍認真、敬業、規矩。我剛開始寫小說時不懂規矩,一個短篇小說用復寫紙復寫了三份,一份交給我那搞文學的舅舅,他所在的單位正辦著一份文學雙月刊;一份交給在省里一個綜合性青年刊物當編輯的同學;還有一份留著也沒用,見報紙有個《萌芽》復刊的消息,便寄了去,反正其時寄稿子,在信封寫上“稿件”二字再剪去一角,不必貼郵票的。那時我對前兩份寄予厚望,對第三份不作打算,因為前兩份有“后門”和“人情”的含金量,而遙遠的上海就純粹是靠蒙了。結果是舅舅和同學都沒有幫上忙,《萌芽》卻用了我的稿子,還給我評了當年的“萌芽文學獎”。我去上海過門并領獎時,責任編輯錢建群先生在家里做了一桌菜專候我。現在回想起來我真不懂事,當時怎么不給錢老師帶點禮物呢?我此生有幸,剛出道就碰上了這么好的編輯。
我第一部長篇小說的責任編輯是當年和巴金先生同坐一室辦刊的馬云老先生,那可是要讓我等抬頭仰望的高人哪,可就是如此高人,因我那稿子要先在刊物發表,由于版面原因需拿掉三五千字,馬云先生硬是讓我去上海親手改定。我在電話里懇求先生隨便替我摘去幾段,可他堅持說編輯不可隨便改作家的作品。此言一出,當即讓我無地自容,在老先生面前,鄙人算得什么作家?但他對作家的尊重絕對是真心的。
《上海文學》的資深編輯厲燕書先生,二十年來一直和我保持密切聯系,盡管我給她寄去過兩次稿子,均沒有能在該刊發出,從此我也不給她寄稿子了,但這并沒有影響她對我的關注。
《小說界》的編輯王肇岐先生有一次在老上海火車站接我,因火車晚點,他在冰天雪地中等了兩個小時。他每年都要來湖南看望作家,與大家稱兄道弟,編輯做到這個份上,還有什么說的……
這就是上海的編輯!他們甚至是可以代表上海的編輯!這些細微末節足可以令我回味一生。
我收到過全國各地幾十家報刊出版社的稿費,惟有上海的稿費計算到“分”,有人說上海人小氣,我不這樣看,這恰恰體現了上海人辦事的認真和規范。我不懂經濟,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事實證明了在經濟生活中上海的作為堪稱楷模,這大致已無爭議。如此建樹,當然是由上海人打造的。上海的編輯地道,看來有某些必然性。
我不喜歡大城市,人一多車一多,心情就無法好起來。但我初見上海的外灘就生出許多喜歡,從情感上講我憎恨昔日洋人在上海最好的地方趾高氣昂修高樓,但那十里洋場的房子實在好看,中國城市除北京天安門外再也沒有這么好看的建筑群和整體環境了。
八十年代初我常去上海改稿、寫作,免不了是要抽出點時間來去逛逛大上海的。其時代步的惟有公共汽車,擠公共汽車無疑是最煩人而又迫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但在上海乘公車使你略感心里涼快的是那些女售票員普遍貌美溫柔,叫買票的聲音像唱歌一樣的好聽,而且明明看到有人不買票也不認真計較且絕不謾罵。我回鄉后與人談到上海女子好時,我舉不出別的例子,就說到上海坐公交車可以不買票。于是不少朋友噓唏曰此生要是能討個上海女子做老婆就好了。上海女子好是好,只是如果你賺不到多少錢、沒有多少養家的本事,就難圓美夢了。大上海的子民講究生活質量,可不像山野村姑那么能打粗。罷,罷,上海女子做不了咱內地人的老婆并不能說明她們不優秀。
以我的游歷經驗,我認為中國內地的所有城市中當屬上海最干凈,八十年代的時候,上海的大街小巷就一塵不染,那是何等深的功力。因此一斑,足見上海人的管理水平和生活質量了。
“大上海”這個稱謂被人叫了許多許多年了,究竟都“大”在哪里?我并非研究這些問題的專家,但我想我所親歷的這些細節也是構成上海之大的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