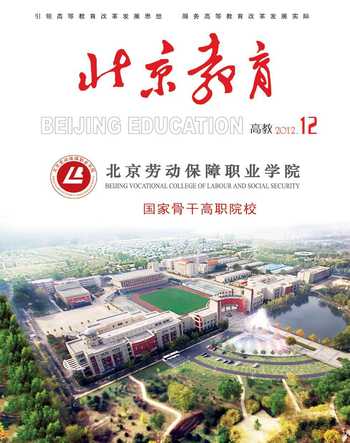大學(xué)自治與司法節(jié)制
吳文靈
近年來隨著一系列高等學(xué)校與受教育者之間的學(xué)位授予糾紛的發(fā)生,學(xué)位授予案件的司法適用問題日漸引起社會的廣泛關(guān)注。從高等學(xué)校來講,往往基于大學(xué)自治、學(xué)術(shù)自由的理念,而對于司法介入持一種排斥態(tài)度,而法院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也往往對于有關(guān)學(xué)位的糾紛持一種小心謹(jǐn)慎的立場。美國對于學(xué)位案件的司法審查適用司法節(jié)制原則,這對于我國界分大學(xué)自治和司法審查的關(guān)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對于我國法院是否審查學(xué)位授予糾紛以及實行何種審查強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美國司法節(jié)制原則的主要內(nèi)涵與審判實務(wù)
司法節(jié)制原則,是美國法院傳統(tǒng)上對于學(xué)術(shù)案件采取的一貫態(tài)度。所謂“司法節(jié)制”,是指高等學(xué)校的學(xué)術(shù)決定往往被法院給予高度尊重。如果不是恣意或變幻不定的處罰,法院一般不愿改變關(guān)于入學(xué)、評分、學(xué)位要求和其他純學(xué)術(shù)事務(wù)的決定。[1]
布朗(Brown)是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的碩士研究生,其學(xué)位論文最初被由三人組成的論文委員會所批準(zhǔn)。他隨后增加了“致謝”部分,并冠之于“不謝”,且運用不敬的語言,攻擊某些行政人員和組織。當(dāng)他意欲把論文提交給大學(xué)圖書館時,此部分被發(fā)現(xiàn)了,其學(xué)位論文被返回給了委員會。委員會隨之認(rèn)為該部分不符合學(xué)術(shù)出版物所要求的專業(yè)標(biāo)準(zhǔn),要求該生刪掉攻擊部分的內(nèi)容,才會被授予學(xué)位。布朗提起了訴訟,認(rèn)為大學(xué)拒絕授予學(xué)位侵犯了他的憲法權(quán)利。初審法院同意被告簡易判決的提議后,布朗就本案向第九上訴法院提出上訴。上訴法院認(rèn)為1988年最高法院的黑茲爾伍德學(xué)區(qū)訴庫爾邁耶(Kuhlmeier)案有著指導(dǎo)意義。本案中,布朗被交給了完成學(xué)位論文的學(xué)術(shù)任務(wù),并被提供了完成學(xué)位論文的合理標(biāo)準(zhǔn)。要求刪掉學(xué)位論文的“不謝”部分,是論文委員會出于正當(dāng)?shù)慕逃康模ソ逃祭适裁词菍W(xué)位論文格式的專業(yè)規(guī)范。原告還指控道,校方拒絕授予學(xué)位時,沒有事先舉行聽證,侵犯了他的第十四修正案規(guī)定的程序性正當(dāng)權(quán)利。然而,上訴法院認(rèn)為,校方的行為性質(zhì)上屬于真正的“學(xué)術(shù)性”,而不是懲戒性。只要推遲授予學(xué)位的決議是“仔細(xì)且審慎的”,并不要求舉行聽證。[2]
雖然法院尊重高等學(xué)校的學(xué)術(shù)決定,但這種尊重有其限度,高等學(xué)校在拒絕授予學(xué)位時不能有恣意或是惡意的行為。在坦納(Tanner)訴伊利諾斯大學(xué)董事會案中,坦納完成了學(xué)位論文,并通過了綜合考試,卻被通知兩者都不被接受,因為他的學(xué)位論文委員會從來沒有被大學(xué)正式承認(rèn)。坦納請求法院發(fā)布強制令,命令伊利諾斯大學(xué)授予他學(xué)位。雖然他的訴求被下級法院駁回了,但上訴法院裁決認(rèn)為,按照坦納訴狀的說法,他已提供了足夠的證據(jù),證明大學(xué)有恣意和變幻不定的行為。[3]
由此可見,美國的司法節(jié)制原則,是從法院的角度來考量司法與學(xué)術(shù)案件的關(guān)系,講的是司法一般應(yīng)保持一種謹(jǐn)慎的立場,尊重高等學(xué)校的學(xué)術(shù)決定,只有在濫用裁量權(quán)的案件中,如恣意或變幻不定,司法才會代表學(xué)生的利益予以介入。
司法節(jié)制原則對于我國學(xué)位授予訴訟的啟示
對于我國的學(xué)位授予訴訟,行使審判權(quán)的法院同樣應(yīng)堅持司法節(jié)制立場,實行有限審查,尊重高等學(xué)校的判斷余地,其正當(dāng)性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五個方面:
一是公共政策的正當(dāng)考慮。當(dāng)教育機構(gòu)向其學(xué)生頒發(fā)學(xué)位證書時,實際上是在向社會證明,該生具備了他就讀的教育機構(gòu)所要求的全部知識和技能。然而,為了使社會能完全信任由學(xué)術(shù)機構(gòu)頒發(fā)的證書,確保這些證書的有關(guān)決定留給專業(yè)教育者作出正當(dāng)判斷則是必要的,教師處于判斷如何幫助學(xué)生完成學(xué)業(yè)的最好位置,必須有必要的裁量權(quán)以保持課程和學(xué)位的完整。[4]事實上,從社會的觀點來看,如果法院放棄節(jié)制做法,而開始要求教育機構(gòu)向那些實際上不合格的人授予學(xué)位,那么這些證書的價值將會受到嚴(yán)重削弱。[5]
二是學(xué)術(shù)評價的普遍正當(dāng)性。雖然有關(guān)學(xué)位授予的訴訟此起彼伏,但是這些爭議相對于高等學(xué)校做出的學(xué)術(shù)評價來講仍然只是屬于少數(shù)。學(xué)位評定是教師做出的專業(yè)判斷,教師受過的訓(xùn)練使其處于更適合做出這種判斷的位置上。不可否認(rèn),在高等學(xué)校,教師做出的對于學(xué)生的學(xué)術(shù)評價大部分是真誠的、善意的,且是相當(dāng)?shù)目陀^準(zhǔn)確;不過,由于有的教師的偏見或粗心,也出現(xiàn)了少部分評價不準(zhǔn)確、不公平的情形;因此,一般情況下,但并不總是,不可能由第三方如法官去判斷做出何種學(xué)術(shù)評價,去判斷什么是準(zhǔn)確的評價。
三是法院負(fù)擔(dān)過重的擔(dān)憂。法院尊重教育判斷的另一理由在于,他們擔(dān)心可能出現(xiàn)對于教育判斷不滿的學(xué)生會掀起起訴高等學(xué)校的訴訟狂潮。正像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鮑威爾(Powell)法官在戈斯(Goss)訴洛佩茲(Lopez)案的異議中所清楚表達的,“人們可能只是猜測,若是賦予每個學(xué)生在法庭上質(zhì)疑老師的任何判斷的權(quán)力,公立教育會混亂到何種程度,而且我們有理由認(rèn)為這樣做會侵犯州政府授予的教育權(quán)力。由于州立法機關(guān)把控制大學(xué)的權(quán)力主要是交給了當(dāng)?shù)氐拇髮W(xué)管理委員會,因此法院拒絕干涉立法政策。”[6]
四是法官自身的專業(yè)局限性。學(xué)術(shù)判斷,從根本上具有主觀性和評價性,缺乏嚴(yán)格的規(guī)則、指南或純粹的經(jīng)驗數(shù)據(jù)。[7]對于學(xué)生的學(xué)術(shù)判斷不同于司法和行政機關(guān)傳統(tǒng)上舉行完全聽證的事實調(diào)查程序,不符合司法或行政的程序化裁決方式。而教育過程天生不具有對立性。相反,它強調(diào)師生關(guān)系的延續(xù)性,作為教師必須承擔(dān)多種角色——教育者、指導(dǎo)者、朋友,有時是代理父母。[8]因此法院沒有能力對學(xué)術(shù)判斷做出判決。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密歇根大學(xué)董事會訴尤因(Ewing)案中重申:“當(dāng)法官被要求審查一個純學(xué)術(shù)決定的實質(zhì)內(nèi)容時,他們應(yīng)當(dāng)對教師的專業(yè)判斷表現(xiàn)出高度的尊重。很清楚,除非專業(yè)判斷是如此地實質(zhì)違背了可接受的學(xué)術(shù)規(guī)范,以致于表明負(fù)責(zé)人或委員會事實上沒有作出專業(yè)的判斷,否則法官不會推翻這個判斷。”[9]與此同時,許多法院還認(rèn)為教育問題無法開庭審理。
五是維護大學(xué)自治和學(xué)術(shù)自由。在學(xué)位授予中,教師的學(xué)位評定權(quán)既體現(xiàn)了大學(xué)自治權(quán),又體現(xiàn)了個人的學(xué)術(shù)自由權(quán)。這是在于,教師不是以個人的名義,而是受高等學(xué)校的委托,作為答辯委員會委員,基于其專業(yè)背景和學(xué)術(shù)能力,對于學(xué)位論文是否符合學(xué)位法律法規(guī)以及學(xué)位授予細(xì)則的要求而做出的判斷,因此其評價結(jié)論的行為效果歸屬于高等學(xué)校,是高等學(xué)校對于學(xué)位申請人做出的學(xué)術(shù)評價,而不是教師個人對于學(xué)位申請人的學(xué)術(shù)評價。與此同時,對于教師而言,在學(xué)位評定中對于學(xué)位論文的學(xué)術(shù)水平,需不受干擾地自主做出評價結(jié)論,因此,也是在行使作為個人基本權(quán)利的學(xué)術(shù)自由權(quán)。
學(xué)位授予訴訟中堅持司法節(jié)制并不意味著受教育者不能就學(xué)位授予案件向法院提起訴訟,也不意味著有關(guān)學(xué)位授予的問題完全免除司法審查。即是說,有限審查不是不審查,因此學(xué)位授予案件可以進入法院的大門;這種節(jié)制不是講的審查范圍,不是講的法院能不能進行審查的問題,而是講的審查強度,講的是法院怎樣進行審查的問題。但是法院的審查是有限審查,是只進行形式和程序的合法性審查,并不進行實質(zhì)內(nèi)容的合法性審查。法院的尊重態(tài)度主要體現(xiàn)在學(xué)位授予決定的實質(zhì)部分,也就是說法院不能代替高等學(xué)校做出學(xué)術(shù)判斷,不能以法官的判斷代替教師的判斷,而高等學(xué)校于此享有判斷余地,免除司法審查。對于學(xué)位授予決定的法律問題、程序問題,法院對于高等學(xué)校不再采取尊重的態(tài)度,并且法官可以以自己的判斷代替教師的判斷,而高等學(xué)校于此不再享有判斷余地,不能免除司法審查。
結(jié)語
高等學(xué)校是決定誰能獲得學(xué)位的唯一裁決者。不同高等學(xué)校的學(xué)位意味著不同的榮譽。如果法院適用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來評判學(xué)術(shù)成績,高等學(xué)校學(xué)位的個性就會減弱。而且如果作弊者和說謊者的不誠實行為未受到制止的話,那么把他們推向社會的代價是巨大的,且遠遠超出高等學(xué)校的控制范圍。實際上,學(xué)術(shù)評價要求的是一種累積信息的內(nèi)行評價,不適合司法或行政的程序性裁決方式,高等學(xué)校更適合對學(xué)生的表現(xiàn)做出判斷。[10]因此,司法以維護學(xué)術(shù)自由為由對于學(xué)位授予行為采取尊重立場,具有一定的正當(dāng)性,但是這種尊重應(yīng)是有限的尊重,而不應(yīng)當(dāng)是絕對的尊重,無論是學(xué)術(shù)自由還是大學(xué)自治都不能創(chuàng)造出一個法外空間,學(xué)位授予領(lǐng)域不應(yīng)成為法治國下的一個隙裂。
因此,關(guān)于司法介入與學(xué)術(shù)自由、大學(xué)自治的關(guān)系,要避免出現(xiàn)兩種認(rèn)識誤區(qū)。一是司法權(quán)完全凌駕于學(xué)術(shù)自由,無視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自身規(guī)律,以司法判決代替學(xué)術(shù)判斷。二是司法權(quán)以學(xué)術(shù)自由和大學(xué)自治為借口,對于有關(guān)學(xué)術(shù)事項的學(xué)生與高等學(xué)校間的爭議置之不理,怠于行使司法監(jiān)督職能,不能對于相對人的權(quán)利予以充分救濟。[11]司法介入高等學(xué)校,涉及司法權(quán)與大學(xué)自治權(quán)的關(guān)系。司法介入高等學(xué)校,也并不意味著法院簡單地以自己的判斷代替高等學(xué)校的判斷,不是侵越高等學(xué)校的職能,而是側(cè)重從法律的角度,以保護受教育者權(quán)利為中心,同時監(jiān)督高等學(xué)校依法行使權(quán)力,保障學(xué)術(shù)自由。不過,由于高等學(xué)校因自治而具有的特殊性使司法的審查并不是全面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限度,即是尊重高等學(xué)校的判斷余地,只進行形式和程序的合法性審查,并不進行實質(zhì)內(nèi)容的合法性審查。
司法介入和學(xué)術(shù)自由、大學(xué)自治的關(guān)系,并不僅僅關(guān)涉到高等學(xué)校和司法的關(guān)系,畢竟司法介入有受案范圍的限制,而且司法本身具有自身的局限性。高等學(xué)校和受教育者之間的學(xué)位授予糾紛,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不能單單依靠司法救濟手段,還應(yīng)完善校內(nèi)申訴、教育仲裁、行政復(fù)議等多種制度,暢通救濟渠道,始能既保證高等學(xué)校的學(xué)術(shù)自由、大學(xué)自治,又能實現(xiàn)司法的依法監(jiān)督,還能維護受教育者的合法權(quán)益。
參考文獻:
[1]K.B. Melear.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 and institution:disciplinary,academic,and consumer contexts, 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193(2003).
[2]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in Huntsville.A Matter of Degree[EB/OL].http://www.uah.edu/legal/pdf_files/a_matter_of_degree.pdf,2011-03-21.
[3]Tanner v.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363 N.E.2d 208, 209,210 (Ill. Ct. App. 1977).
[4]Bruner v. Peterson, 944 P.2d 43,48 (Alaska 1997).
[5]Olsson v. Board of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402 N.E.2d 11503(N.Y. 1980).
[6]419 U.S. 565, 95 S. Ct. 729 (1975).
[7]Johnson v. Cuyahoga County Cmty. Coll., 489 N.E. 2d 1088, 1090 (Ohio Ct. Comm. Pl. 1985).
[8]Board of Curators of the Univ. of Mo. v. Horowitz, 435 U.S. 78, 90, 98 S. Ct. 948, 955 (1978).
[9]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v. Ewing, 474 U.S. 214, 225 (1985).
[10]Carol J.Perkins.Sylvester V. Texas southern university: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of judicial deference to academic decisions[J].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1998,(25):422-423, 433.
[11]周志宏.學(xué)術(shù)自由與大學(xué)法[M].臺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94-177.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xué))
[責(zé)任編輯: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