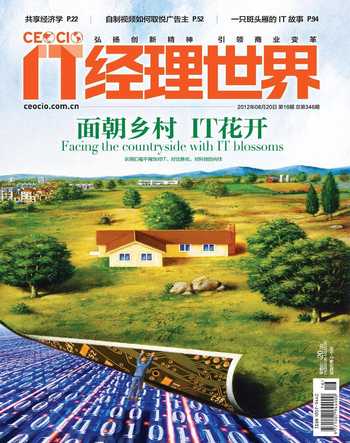中國經(jīng)濟(jì)新“地理梯度”警示
劉西曼

截至2012年8月初,中國大陸各個省份、自治區(qū)和直轄市的GDP增長速度排名已經(jīng)發(fā)布完成,按照可比價格計(jì)算,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增速分別為7.2%、7.2%、7.4%、7.4%,成為僅有的四個低于8%增速的省市;而重慶、貴州、四川、陜西的增速則分別達(dá)到14.0%、14.0%、13.0%、13.0%,均位居全國各省份的前五名;中部地區(qū)的增速則多數(shù)位居中間——中國經(jīng)濟(jì)增速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明顯的西高、東低、中平均的“地理梯度”。
如果我們進(jìn)行以下簡單的對比,20年前,亦即上世紀(jì)90年代初市場經(jīng)濟(jì)發(fā)端的時候,東部地區(qū)因受益于改革開放、輕工制造業(yè)大發(fā)展一直領(lǐng)跑,東部地區(qū)增速往往在10%~15%這個區(qū)間的上限發(fā)展,遠(yuǎn)高于中西部,經(jīng)濟(jì)上的“地理梯度”是東高西低;而在10年前,隨著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的推進(jìn),以及重工業(yè)的發(fā)展,東中西部的增速一度比較接近,全國也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速。
關(guān)于這些現(xiàn)象,已經(jīng)有不少學(xué)者從各個維度進(jìn)行過解讀,我希望從“經(jīng)濟(jì)紅利”的角度對其進(jìn)行簡要的再解析。
經(jīng)濟(jì)的“地理梯度”源自各種紅利
20世紀(jì)80到90年代,東部地區(qū)特別是江、浙、粵、滬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主要受益于三大紅利:市場化政策、地理優(yōu)勢和中國整體的人口紅利。因?yàn)橹袊诼L的轉(zhuǎn)軌過程中,優(yōu)先給予廣東、上海等地若干先行先試的政策,這也導(dǎo)致人才、資金優(yōu)先向這些地區(qū)流動,這是一個先導(dǎo)性的驅(qū)動力。在這個驅(qū)動因子作用下,這些地區(qū)充分利用了自身擁有的地理位置優(yōu)勢,以出口為導(dǎo)向,盤活了低端和中端制造業(yè),也讓全國的大量農(nóng)村富余勞動力趨之若鶩——從而讓三者形成了合力,最終促使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長達(dá)30年的持續(xù)發(fā)展。
實(shí)際上,到了2000年前后,全國各地的市場化格局已經(jīng)形成,加上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的作用,東部相對于中西部的政策紅利已經(jīng)不明顯了。此時,為什么東部地區(qū)依然具有很強(qiáng)的磁場效應(yīng)?這里面涉及到一個先發(fā)優(yōu)勢紅利問題。歷經(jīng)十幾年的發(fā)展,東部的很多地區(qū)都形成了非常好的產(chǎn)業(yè)聚集,比如東莞的IT制造、紹興的紡織制造等等,因此從效率上也仍然占據(jù)著很大的優(yōu)勢,因此,西部大開發(fā)提出10來年中,中西部增長仍然沒有顯著超越東部,反倒是東部地區(qū)的生產(chǎn)日益從輕工業(yè)擴(kuò)散到重工業(yè),保持了較為均勻的快速跑——從增長質(zhì)量上,西部的快速增長主要建立在資源品、投資等基礎(chǔ)上,仍然是遜于東部的。
但是,歷史總是在悄然變化。2008年前后,即便沒有金融危機(jī),這種經(jīng)濟(jì)地理格局也自然會發(fā)生重要的變化。因?yàn)椋袊娜丝诩t利正在快速退潮,東部地區(qū)的制造業(yè)再也不能10年不加工資了,東部的政策紅利相比西部來說已經(jīng)開始變得更少、而不是更多,原來產(chǎn)業(yè)集群形成的效率優(yōu)勢也不能無限提高……于是,我們看到中部和西部地區(qū)的增長并非突然變快,而是東部地區(qū)“跑不動”了。
新的增長梯度形成了。
新增長紅利需回歸本源
但是,新的梯度結(jié)構(gòu)卻與原來的梯度結(jié)構(gòu)有重要不同:東高西低時代,西部低,意味著潛力,生產(chǎn)力隨時可以從東部擴(kuò)散過去;而西高東低時代,實(shí)際上意味著東部地區(qū)的生產(chǎn)力向上增長更為乏力,而幾年后中西部地區(qū)也必然面臨類似挑戰(zhàn)。
換言之,過去的快速增長源自對受壓制生產(chǎn)力的釋放,而目前我們看不到多少受壓制的生產(chǎn)力——即便對于很多民營企業(yè)來說,特別是在科技創(chuàng)新方面,也并沒有蘊(yùn)含多少潛在的生產(chǎn)力。在這種情況下,打破現(xiàn)有的一些壟斷行業(yè)壁壘,固然可以有所幫助,但是,那也不過是一次性的短期收益和財(cái)富的再分配,其價值和效果恐怕比不上80年代初的個體潮、90年代初的下海潮、2000年代初的科技潮……
這時候,當(dāng)我們擠去各個省份的增長水分看,中國二季度GDP同比增長7.6%,其中出口順差帶來的紅利已經(jīng)極少,投資仍然占據(jù)半數(shù)、處于偏高水平。假定讓投資增速回歸到2倍于GDP的正常水平,未來出口趨于均衡的情況下,中國目前的潛在增長速度可能就是6%~7%,步入中速增長階段。
因此,原有的人口紅利消失,你不可能因此去鼓勵生2胎甚至多胎,這樣由人口基數(shù)帶來的GDP數(shù)字性增長只會對人均生活水平進(jìn)一步稀釋;當(dāng)政策紅利日趨減少的情況下,你不能期盼有比80年代改革開放、90年代市場化、2000年后城市化和地產(chǎn)市場化更大的改革,只能是小修小補(bǔ);當(dāng)中國的高儲蓄率已經(jīng)被轉(zhuǎn)化為高投資率,以至于中國的綜合債務(wù)水平已經(jīng)到達(dá)一個危險水位的時候,你也不能期待中國繼續(xù)給出更高的投資率,況且這些儲蓄本身也是為了未來老齡化儲備的;當(dāng)中國的匯率日漸市場化、人力成本日漸提高的時候,我們也無法繼續(xù)依靠順差進(jìn)一步拉動GDP……
那么,中國的經(jīng)濟(jì)改革動力只能回歸到經(jīng)濟(jì)增長的本源:通過挖掘人力資源潛力提升生產(chǎn)力,即教育;通過科技提高生產(chǎn)力,即研發(fā)和管理——這些對中國也并非是新紅利,但是,卻可能是必須的、需要更大投入的可行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