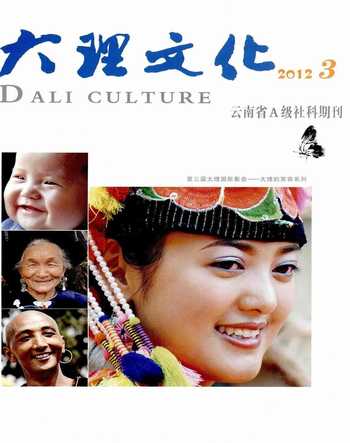蒼山筆記
張乃光
一
山間遇雨,是登山大忌,卻也無端增添很多情趣。林子里,林子外,無數水聲在纏繞,陡然生出一種突圍感,想沖出雨去。水聲無數,腳下的路卻只有一條。
正是深秋時分,深秋時分多雨。一把一把小雨傘,撐開林間一朵一朵色彩繽紛的蘑菇,給迷蒙的雨景增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效果。雨小下來的時候,蟬聲突然密集起來。一株高大的核桃樹下,滿地落滿了帶著綠皮的核桃。這是核桃樹對養育它的大山的回贈。
泉彎腰揀了一個,樹梢傳來人聲——“呃,呃,呃呃呃!”
抬頭,樹梢立著一個披著蓑衣的山里漢子。威嚴,像立在天空的山神!
泉不好意思,仰頭,笑:“就揀一個。”
樹梢上的聲音軟了:“揀幾個就揀幾個唄!”說完揮舞手中的竹竿,辟哩叭啦又有幾個核桃掉了下來。
山里的空氣,被雨洗過,干凈得不含一點雜質。沿著山路徐徐向上,經過幾座廢棄的破房,一株上了年紀的核桃樹,等候在老地方。我們曾無數次來過這里,在樹下休息。牛毛細雨中,眼前叢生著野草,早已不見舊時痕跡。
笑聲。隱隱的笑聲,穿越了時間——又看見五年前的場景,看到五年前的小奉,看見了五年前的泳友。核桃樹下,我們席地而坐,吃著帶來的饅頭。小奉照例帶來了她腌制的鹵腐,一伙人爭著搶著,從她手里接過鹵腐瓶,用調羹,用小勺,把糯軟的鹵腐細細研抹在饅頭上。
“這可是我們這座小城的特產——奉氏鹵腐啊!”又聽見了泳友打趣的笑聲。
小奉是一個紡織廠的下崗工人,離異,孤身一人,常來游泳。她披著一頭烏黑而發亮的頭發,笑時露出白白的門牙,一邊說話一邊用眼睛左看看人,右望望人,很逗人喜愛的樣子。
舌尖還殘留著鹵腐的味道,小奉卻因一場車禍離開我們。她的死與鹵腐有關——因為泳友們喜歡她的鹵腐,每到冬天將臨,她都要收集一些罐頭瓶,腌制些鹵腐,郊游時帶去。出事那天,她騎著摩托去向要好的朋友討幾個腌制鹵腐的罐頭瓶。朋友等急了,給她打電話,無應答——自然是無應答的,她被一輛駛進加油站的貨車撞倒在地了。
一陣一陣雨聲,滴落在心頭。雨滴被上了年紀的核桃樹所放大,在滴答的雨聲中吃帶來的饅頭,卻無論如何再也吃不出記憶中的味道。那種糯糯的香香的醇醇的味道,已隨逝者遠去。
雨聲淅瀝,心情也像細雨,迷茫。想起了小奉,就想起核桃樹北那條草莽中的小徑。我們曾一次又一次踩著那條小路,去看那院隱藏于樹蔭和草莽間的破落的舊房。
小奉走了,路也丟了,只有一片草。Z揮著手中的木棍,探路,走了一截,搖了搖頭,退回來了。
水聲漫漶,突然想起小奉曾好奇地問過我這片破房為什么叫“單大人”。當時的我只能一知半解地回答她,這地名其實是人名——據說清朝時一個叫單大人的官員曾居住于此。后來,我也曾想對這位單大人的身世作些詳細了解,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向小奉介紹。可惜,小奉在我還未了解清楚前就出了事。
這片已經頹廢的房屋,當年造得很有氣勢——主樓坐北朝南,兩側還有廂房,走進去的路兩邊也有房子,路的右手邊還蜿蜒著一條小溪。一個身世飄零的孤獨老人,守住那條小溪,守住一個小小的發電機,用小溪的水發電,來供給他看電視的電源——不知道那發電機是誰供給他的。他可算得上是一個匠心獨具的隱居者。老人如今已不見了,他賴以棲身的房屋也倒塌于一片荒草間,只留下了一個撲朔迷離的夢一樣的謎。
單大人顯赫的身世經不了風雨,如今只剩下倒頹的墻,朽壞的屋檐,歪傾的門面,下陷的木地板,還有一條隱藏于蕁麻與雜草間的小徑。記得一次來這里,小奉從草叢中的路徑走進當年的小院,曾對著頹樓左顧右盼,聲音里透露出惋惜和向往:“當年,也許樓上住過一位繡花的小姐,月亮升起的時候,坐在窗前,等待著房后桂花樹下傳來三弦聲呢!”
頹院西邊小路邊那株桂花樹還在。深秋時分,它總開著金黃的米粒大的花,馥郁的香氣在很遠的地方就能聞到。小奉每次來,喜歡折上一枝兩枝無主的金桂,一路上聞馥郁的香氣。
如今,金桂被亂草遮住,香氣也聞不到了,我猜想是過了季節的關系。
庭院,已深深地頹廢于荒草之間。那個因小奉的詢問而引起我關注的單大人的身世,也堙沒于荒草之間。有人對我說,他曾經鎮壓過杜文秀起義,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但我查不到有關他的蛛絲馬跡的任何文字。山間核桃樹下揀核桃的山民中,有姓單的,問起單大人,他們的回答比我了解的還少,只含含糊糊說是祖上的一個官。
朦朧的雨,使山林模糊,又使一些記憶變得清晰。在這片山間的途中,廢棄著零零星星的庭院和房屋,幾年前,一個庭院的門兩邊還看到褪了色的結婚對聯,山民告訴我們,一對外地來打工的青年曾經把它作為洞房。小奉偏著頭,臉上的表情帶著羨慕:“能夠與自己相愛的人棲身在這樣一院沒人打擾的房子,也是一種人生的福分呀……”
雨中想起小奉臉上那種表情,一滴一滴的雨,又落在心上。
一切都是個謎,單大人,寄居者,包括小奉。在小奉的喪禮上,我看到了她的前夫,傷心欲絕的神情。他們為什么要離婚,對我是個解不開的謎。
雨又大起來了,同行的伙伴催促著下山了。
回到核桃樹下,看到一只螞蝗叮在泉的脖子上。泉尖叫,急急用手去抓,螞蝗卻緊緊叮住不放。連忙幫著用手去逮,狠命一逮,鮮血冒出來了。
心倏忽一動:小奉也曾在這片亂草中,被螞蝗叮過,也是這樣尖叫,也是急急用手去抓,也是急急用手去逮,狠命一逮,鮮血便冒出來了……
殷紅的血,模糊了雨,模糊了記憶。一切都在雨中逝去。是得下山了,這片草叢間,多的是螞蝗。我的腳桿、腳踝開始隱隱地疼,褲管里,褂子內也鉆進了螞蝗,緊緊叮在肉上。
W見我們一個一個忙著抓螞蝗,傳授了一個秘訣:不要死逮,要用手連續猛拍或用煙頭灼。
果然奏效,螞蝗很快就掉落在地。但叮咬處仍然有殷紅的血。
在返回的途中,一株核桃樹下,路邊草叢里,掉著幾個核桃,我撿到一個,剝去綠色的皮,卻咬不開,是個“鐵核桃”——“鐵”得就像“單大人”,像已經消失的種種往事。
這時雨卻意外地停了,我們回到了就餐的寶靈寺,聞到了飲煙溫暖的味道,還有雞肉和魚的香味。
蒼山斜陽峰麓,這個名叫“單大人”的地方,這雨中的山林,給我留下的,是與殷紅有關的一串記憶。
二
如果天氣好,進蒼山逛逛,在山坳里烤烤太陽,是很不錯的一件事。
大理的陽光,到了冬季就變得溫暖。冬天一到,大理人喜歡蹲在墻根角,或在小院里、陽臺上,烤太陽——曬太陽不叫“曬”,而叫“烤”,可見在冬天,大理陽光的作用是什么了。
進山,一路楊樹、水冬瓜樹、栗樹,浸潤得空氣濕濕的。經冬的楊樹葉子有些泛黃、泛紅,像出自畫家之手的幾筆寫意。漸走漸高,松樹多起來,一片蒼郁之色,看不到冬天的影子。
這時候,山里最燦爛的是陽光。一灘灘,一汪汪,金燦燦。
形容陽光用“一灘灘”、“一汪汪”,絕無因為修辭而刻意煉字的意思,而是眼前景致最直觀的表現。蒼山到了冬季并不是一片蒼綠的,山間凹地、緩坡,茅草地魔術般地變成了一片片金黃。一片片浸透陽光的金黃色的緩坡、茅草地,被周圍的墨綠的松樹、蒼翠的栗林包圍著、映襯著,就有一灘灘、一汪汪的感覺。
我們就在這樣的天氣,到蒼山佛頂峰白王廟后的山凹間,在一片金黃柔軟的茅草編織的山凹間烤太陽的。這個時節,核桃已經打盡,梨、桃、梅、李、蘋果等水果也已收完,只有蒼山斜陽峰南側一帶山坡外地人承包開墾的冬桃園等待著采摘——一星期前我們曾經去買過冬桃,樹上的冬桃還硬,只好在園外山箐里一塊巨大的石頭上烤了一個下午太陽。今天,我們選擇的地方是遍生著茅草的山凹,一躺下,感覺自與一周前大不相同,經霜的茅草溫暖而柔軟,散發出浸透陽光的苦香。陽光在蒼山的茅草地,散發出撩人心魂的味道,這是一種使人全身心放松融入自然的味道。在城市的廣場、街道、陽臺,陽光是沒有味道的。陽光也和空氣一樣,具有著不容忽視的質量。我想起了一個外地朋友對我說的話:到大理,好像近視眼突然戴上一副適合的眼鏡,一切都看清楚了,這就是陽光的質量。大理的陽光,就像純凈的溪水,沒有受過污染。
幾頭老牛搖響脖子上的響鈴,從茅草地的邊緣悠閑地經過,放牛人赤膊著上身,跟在牛群后面慢慢走去,留下一個溫暖的背影。不知名的鳥在山間有節奏地叫,像在說:“瞧瞧,瞧瞧。”不知它們在瞧什么。也許是在瞧我們這群“多余的人”。對于亙古常在的山林,我們不過是偶爾闖入的外來者。我們的皮膚很少受到過山野陽光的撫摸和溫暖。我們的嗅覺中早已失去了陽光原有的味道。想起詩人于堅說過這樣的話:“多余的人只是拒絕跟著時代盲目前進。他熱愛生活,熱愛每個日子,相信世世代代積累下來的生活經驗。”在大理,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超然生活在時髦的生活之外,與世隔離,過著一種像蒼山的陽光一樣簡樸的生活。到蒼山烤太陽,這未嘗不是遺存在我們基因之中的一個世世代代積累下來的生活經驗。
這樣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不少的外來者。我知道在山腳下的村落間,就棲藏著很多文藝界的名人,作家余世存就是其中的一位,用他的話說,他是“卜居古城一塔寺旁”。他每天都在他租賃下來的白族院落里靜靜地烤太陽。我曾問過他,打算在大理呆幾年,他笑:“也許一兩年,也許更長時間。”大理的陽光,一定會被余世存先生收藏在他的文字之間。
躺在陽光里,再次聞到了陽光的苦香。手機突然“嘀嘀”一響,接到一條短信——是一個北方的朋友給我發來問候。我告訴她我正在蒼山上,她問“冷不冷啊?”我回復她我在山間一片茅草地烤太陽。她很快回復了兩個字:“呵呵”。我明白這兩個字里包含的全部意思。
溫暖與寒冷是同時存在的。此時的北方,正是冰封雪凍的日子,我的朋友龜縮在房子里已經很長時間了。冬天的寒冷,使得蒼山的茅草地變成一席碩大的溫暖無比的金絨毛毯。四圍的喬木和灌木是它深綠色的滾邊。三三兩兩色彩各異的服裝,成了它造型優美的圖案。陽光暖暖地覆蓋在身上,幾個年長的,閉上眼睛躺成個“大”字,什么也不說,只靜靜望天,望天上偶爾飄過的云,臉上的表情很滿足的樣子。幾個閑不住的年輕人,去山道邊採來山地蘆葦,一枝枝白色的絨花在陽光下搖曳發亮,白的葦花、黃的草地、綠的青松,煥發出感動人的異樣色彩。
我們就在山間茅草地,在暖暖的太陽下,度過了一個溫暖的周末。
三
去蒼山黃龍潭,行到半山起霧了。滿山響起了“楊偉,楊偉!”的叫聲。
楊偉是一個瘦弱的年輕人,斯斯文文的樣子。他第一次參加我們的登山活動,途中突然不見了。起霧后,更是看不到他的影子。大家都急了,怕出意外,一陣一陣猛喊。
蒼山上曾經有人因為迷路而凍死在山間的事發生,大家的焦急是自然的。我的一位朋友,曾經向我講起過他在蒼山迷路的經歷,在山上走了一天一夜,又冷又餓,幾乎到了絕望的境地。特別在沒有星光的夜里,除了冷和餓外,還要忍受恐懼。他幾乎是發了狂,高一腳低一腳揀低矮的地方走,直到拂曉時分僥幸地遇到一位山間砍柴的山民,才一頭栽倒在地人事不知。
我想起了這位朋友的事,也開始焦急起來,跟著“楊偉,楊偉”地喊。
楊偉終于出現了,他落在后面。同行的登山者都是冬泳隊員,楊偉是一個泳友領來的,平時少鍛煉,體力自然無法與大家相比,更何況據他說還走錯了路。
所有的人又歡呼起來,山谷音回蕩著“楊偉,楊偉,楊偉……”
望著白凈而單薄的楊偉,我忍不住一陣笑,滿山的叫聲似乎在叫“陽萎,陽萎,陽萎……”
繼續上行,山路更陡,山勢很陡。路上遇到了一些水,這是蒼山上零零星星的洼地積下的雨水,水中叢生著模糊的植物,預感黃龍潭應該不遠了。
腳下的路在這緊要關頭卻不見了,只剩下茫茫的霧。我們開始在刺蓬中鉆,在陡地上爬。白茫茫的霧,填平了山箐,掩蓋了溪澗,蒼山變成了虛無,我們行走在一片虛無之中。
終于鉆出了刺蓬,腳下的地面變得平緩,叢生著各種看不清楚的低矮的樹木。我的身邊匍匐著幾株枝干盤屈的杜鵑,還有一片低矮的灌木和蒼青的石頭。灌木叢不遠,立著一株株冷杉模糊的身影。我們都停下腳來,躊躇著不知該往哪個方向走。
Y在這關鍵的時候突然消失了。Y喜歡采集蝴蝶做標本,每次上山總是獨往獨行,經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又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消失。在這樣高冷的山巔,是不應該有蝴蝶的,蝴蝶只在山腳一帶蘆葦和山草叢生的地帶。霧很大,我擔心Y會迷路。我正想說出我的擔心,霧中傳來了一陣驚喜的叫聲:“水,水,水!黃龍潭在這里!”
是Y的聲音。他走在了所有人的右前方,我記得他一直走在我身后的,也許,他走了另一條路。有時,意外的發現,總是屬于獨行者。Y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發現了一片水,他認定那就是黃龍潭。我們朝著他的聲音走去,模模糊糊的霧里,閃現出了一片晃晃蕩蕩的東西,定睛細看,是水,冷冷的水,像一雙雙偷窺的眼睛,像一片片粼動的魚鱗。在晃晃蕩蕩的水之間,露出隱隱忽忽的樹影,黃龍潭就這樣以猝不及防的方式與我們見面。反應敏捷的C開始舉起相機照相,我也慌忙掏出相機,鏡頭中好像出現了水的影子,冷杉的影子,巖石的影子,人的影子,所有的影子交融在一起,卻又模糊成一片。我捕捉到了一株水中的樹影,正要按動快門,卻又找不到它躲到哪里了。
這一天,我照了很多照片,結果卻一張也不清楚。只有一張照片,隱隱忽忽露出一襲長裙,和一綹飄忽的長發。長裙的一部分還有奇怪的花紋。同行的人中沒有人穿裙子的,我始終猜不透是誰無意間闖入我的鏡頭?蒼山上的龍潭,有很多關于龍的怪異傳說,我疑心無意間邂逅了龍潭中的某個妖女。
我到過蒼山玉局峰頂海拔3960米的洗馬潭,并在洗馬潭洗過澡,與它有過肌膚相親的接觸,而位于蒼山三陽峰巔海拔3980米的黃龍潭,它的若有若無卻意外地給我留下遠勝于洗馬潭的印象。后來我看過其它登山者有關黃龍潭的照片,很驚異它竟是那個樣子,不過是高山洼地里、陡削的巖壁下一潭澄澈的湖水,清楚得伸手可觸,徹底失去了神秘的感覺。霧中的黃龍潭,給我的印象卻是深刻而靈異的,它在我的記憶里始終是灰蒙蒙的霧中一片若有若無的水,一種靈動的水,飄渺的水,朦朧的水——可見而不可見,也許正是蒼山黃龍潭存在的一種最佳方式。
四
每次去蒼山看雪,都是在雪下白了的時候。興奮莫明地帶上相機,去山上踏雪,拍照,帶回的關于雪的記憶都是經久難忘的。
近幾年我很少去蒼山看雪。事實上,蒼山雪已經在悄然地遠離了我們。
蒼山的雪,據說并不只在冬季有,過去的書上就常看到“蒼山積雪終年不化”的說法。印象里分明也有這樣的感覺,小時候,春天、夏天也能看到蒼山山巔上的積雪,銀亮亮白晃晃的一片。在一些街場上,還看到有人挖了蒼山上經年的積雪來賣,用松毛捂得嚴實的背簍里塞得滿滿的蒼山雪,調羹一舀,勺子一壓,再澆上熬好的糖稀,白雪就使了魔術般變成了一個小巧玲瓏晶瑩剔透的工藝品。牙齒一咬,咔嚓一聲,冷、甜,冷到骨髓里,甜到心里,那種強烈的刺激感,是當下市場上所有人工冷飲所無法相比的。
想起過去的蒼山雪,踩在雪地上腳下嗞嗞的聲音,嗞嗞的響聲中雪陷下時骨穌筋軟的感覺,山頭眩目的白,那種強烈的感覺是歲月之手抹不去的。
在蒼山遭遇雪,是在一個秋末冬初的日子。天氣晴朗得無與倫比。頭頂一片藍,山間一片綠。一片藍與一片綠之間,是咻咻的喘氣聲。目的地是位于海拔四千零九十二米的蒼山中和峰頂的蒼山電視臺,號稱世界海拔最高的電視差轉臺。一路行走,絲毫感覺不到雪的影子,滿頭大汗,烈日當頭,走著走著,松樹少下來,冷杉也跟著少了下來,低矮的杜鵑就一簇簇冒了出來,長滿苔蘚的石頭也冷冷地露出了臉,像一群森林中的妖怪。突然間,腳下就閃現出了白色的東西,一堆一堆,一片一片,在高山的陽光下白得耀眼。
是雪!久違了的雪。生在南國的人,很久就看不到雪了。
一開始,白色的雪只是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出現,喜悅的情緒在隊列間蔓延。越往上攀登,白色就不斷擴大,綠色不斷地減少,笑聲也跟著少了。眼前除了天空的藍就剩下了一片白,嗞嗞的響聲連接起一串蜿蜒向上的隊列。
當接近蒼山電視臺時,一片陡坡上就變成了眩目的白。腳下變得堅硬,每踩一步都有往下滑的感覺,雪坡上留下一串腳印,有大有小,一律呈現半透明狀態,在我們到達之前已經有人來過。對于生活在林海雪原中的北方人,對這樣的雪景大概是不以為奇的,而對于在四季如春的大理長大的我和我的同伴,這確乎是難得的景色——我們只在電影里、電視上看到過這樣的景色。一開始是一陣歡叫,在群山間震蕩,漸漸的叫聲微弱下來,變成了沉重的喘息。到了后來我聽到自己的心臟發出很響的跳動聲,一聲一聲好像震動著山谷。漸漸地就有支撐不住的感覺,腳下一滑,手中的拐杖突然間像遭到神咒,斷裂了。我只能匍匐在地,腳手并用,像一頭狗熊,笨拙地向上爬。
已經接近四千多米的高度。沒到過冬季的北方,無緣看到北方的林海雪原,但眼前的雪景,是高原的雪景,想來與北方的雪原應該有著不同。它有自己的個性,這種個性就是高度,在這樣的高度,所有挺立的樹木都消失了,松樹、冷杉、竹林都躲在腳下的山坡地帶,只有被雪覆蓋了的巖石和山地,雪地變得堅硬。眼前一片白,眼睛慢慢地疼了起來,我忘了帶墨鏡。
體力漸漸消失,心突然慌了起來。心情肯定與眼前的一片白色有關。任何顏色,單調到極致,世界便會呈現一種或瘋狂或恐怖或抑郁或絕望的狀態,世界的色彩是由紅、綠、藍三原色按不同的比例混合而成的,讓人賞心悅目,而白色是在三原色以相同的比例混合、且達到一定的強度時候出現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白色是對紅、綠、藍三原色的抹殺。在高原強烈的陽光下白得刺眼的蒼山雪,讓我無端地便想起了“白色恐怖”這個詞。一股股寒意從四面八方向我涌來,鉆入心里。
山頂一片白,眼前一片黑,這是我在即將登上山頂時的感覺。我把自己的感受事后告訴了一位朋友,他笑我這是文學的夸張。但親身經歷了這次登山經歷的朋友K卻說我的這一描繪非常貼近,他也有相同的感受,在臨近山頂之前,他曾一度發黑暈,像暈車一樣的感覺,他甚至動了折身下山的念頭。眼前的黑暈,是身體極度虛脫的表現。
我在白色的山坡上匍匐著前進,盡量閉上眼睛。后來,我跌了一跤,睜開眼睛已跌落到山道下的一片雪地。
一只手向我伸來。是同行的瓊。在除了白色還是白色的蒼山之巔,她的出現,給我的眼睛增添了另樣的色彩。她的花絨衣在雪中溫暖著我的眼睛。我們都落在了隊列的后面。她輕輕地笑著,黑色的眼睛讓我心神安寧。“喏!”她向我遞來一樣東西。伸手接過,是一顆包著糖紙的水果糖,甜意瞬間在我舌間水波一樣蕩漾開來,漸漸浸漫了全身。
一顆水果糖,在瞬間產生了神奇的力量。這是一顆冰天雪地間的水果糖。我站了起來,喘著氣,繼續在雪地上向上挺進。腳下的雪,“簌簌”地響,比原來的“嗞嗞”聲更多了些沉著,身體恢復了重量。陽光開始明媚,天空變得透明,我和瓊緩慢地向著白雪覆蓋的小岑峰頂前進。我抬起頭來,看到了在藍天閃閃發光的電視差轉天線。
大雪可以覆蓋山巔,卻覆蓋不了天空,大雪可以凍僵一切生命,卻凍僵不了一顆水果糖所傳遞的友情,雪地里的一顆水果糖,有時足可融化一座雪山!
我們終于登上了山頂,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在這白茫茫的雪山,突然醒悟人需要的其實并不一定很多——當大雪刪除了一切多余的東西之時,對于一個登山者,一顆水果糖足矣!
責任編輯 王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