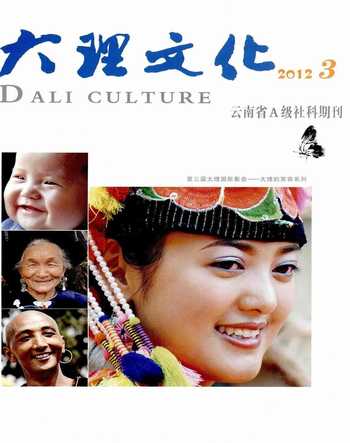哀牢小村人物
狗 妹
小村小。
全村二十來戶彝家竟沒個廁所,各家養了幾條吃屎狗,內急了,便跑進后陰溝或地邊柵欄下,嗷嗷喚狗,大肆方便。
小村是小,小到不論哪家娃打架打傷了、哪家田里地里莊稼被哪家牲口吃了、踏平了,或是哪家的貓抬了哪家的臘腸、哪家的老鼠藥鬧死了哪家的豬、羊,當事主婦只需怒氣沖沖站在村頭“無名高地”——土包上雞啦驢啦……拍屁股大罵一通,保準全村震得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小村是小,這里方才憤怒難平地退下“高地”,那里又心平氣和地或笑著相互借油借鹽有來有往,或站在土包子上邀約著去村中打歌場上摟肩搭脖歡快地打歌。
小村確實是小,小到從唐末逃難隱居于此到如今祖祖輩輩就這樣點著松明,唱著“日子過得不自由,唱個山歌解憂愁”的山歌,住在鳥窩大的山旮旯里,看著巨蟒般的黑■江滾滾而來,咆哮而去……
“我想去闖江湖!”
有一天,村長的獨子阿狗終于憋不住,說了這么一句。
“人乏一飽水,馬乏一盆料。江湖人雜,險惡著哩,莫去莫去……”小村人輪番勸阿狗。
“楸木開花不結果,秧草結籽不開花。松毛裝攏靈芝草,象牙裝攏狗骨頭。黃狗卵子充麝香,你拗什么?!”村長阿土抬起長煙鍋桿瞪大眼吼了兒子一聲。
阿狗言聽計從,最后當了小村“一師一校”小學的民辦教師。
可有一天,小村人突然發現小村的人多了起來,雜了起來。在那個雨嘩嘩下個不停的日子,小村人一覺醒來,發現峽谷兩岸全是人——操著各式各樣口音的人。
三大五粗的男人在挖洞打樁搭棚子。
聽說要在小村峽谷建個好大好大的水庫發電。
“江湖來了?”最初小村人惶惶不安。但慢慢地,小村人發覺,“江湖”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怕。連祖祖輩輩爛在樹根的鬼李子,也可以拿到峽谷兩岸工地上換成錢。工地那些“老表”好像一群狼,隔三岔五就到小村買雞買羊,老說生活太苦。
小村有了江湖?!
狗妹靈機一動,決定闖一闖,于是在小村村頭的那幾轉爛墻院上搭了幾間茅草房,置了幾套碗筷,開起了飯店。
狗妹哪點人?
她就是小村寡婦張阿姥的獨女,是小村唯一和村長兒子阿狗到過山外,念過“暗歌你戲”的“女秀才”。
店開張了,然而吃的卻只有自家的豬臘肉和蕎面粑粑。剛開始,工地上的“老表”都說狗妹的山歌好聽肉好吃,可時間一長,都搖頭。
狗妹為這事急得如同火上了房。
看著漫山遍野跑的吃屎狗,狗妹心一亮,私下暗想:狗肉補,又治跌打勞傷,好哩!
當夜,便點著松明火把,系了個扣子下在院子里,把自家的吃屎狗套住了。
天麻亮,狗妹便燒狗剖肚忙個轉。
很快,大鍋里就煮了一鍋用核桃油、臘肉、糊辣椒炸黃的狗肉坨子,惹得工地“老表”老遠聞見香味,就一窩蜂跑來“打牙祭”。
“每碗十塊。”狗妹說。“不貴,不貴!只可惜缺了提神酒。”“老表們”歡歡喜喜吃完肉,歡歡喜喜走啦。
從此,狗妹便天天唱山歌賣狗肉湯鍋,“老表們”酒自個捎上,肉越吃越香。
狗妹家穿的吃的用的越來越好,還玩起了“卡拉OK”。“老表們”吃飽喝足,還在店里五角一曲鬼哭狼嚎唱“卡拉OK”。
狗妹呢,穿上迷你紅裙和白高跟皮鞋,整日挺著高高的胸脯,在小村人面前走來走去。她今天唱“正月花甲口中梅,朵朵拜下屬鼠人,小鼠咬爛含香籠,露出美女繡花鞋”,明天唱“三根竹子一樣高,一刀砍來做吹簫,白天吹得團團轉,夜晚吹得妹心焦”,后天唱“阿妹有錢無使處,買給一副人籠頭,把你拴在妹身上,阿妹不動哥不走”,永遠有唱不完的山歌。
狗妹惹得工地“小老表”和全村山哥心神不定,他們心癢癢的,老想到狗妹店里閑,有時干著活放著牛也會偷偷跑到店子背后,從爛了的墻縫里瞄幾眼“過過癮”,幾個膽大的山哥甚至整夜在店背后的山包上唱:“情妹呀,隔山隔水嘜難相生,格是嘍——說給情妹你聽去,你繞山繞水嘜繞攏來,哎咦喲”、“情妹呀,不怕千山嘜十八凹,格是嘍——說給情妹你聽去,誓將妹嘜娶到家里來,哎咦喲”。
小村的山妹們又急又恨,一齊跑到狗妹的店里看看這,看看那,她們搓搓紅裙、摸摸高跟鞋,問狗妹:“哪里買,哪里買?”。
“壩里,盡是!”狗妹滿臉得意洋洋。
小村山哥山妹們癢手癢腳,也想開個狗肉湯鍋店。可是,他們的阿爸阿媽阿爺阿奶一百個不準。他們的阿爸阿媽阿爺阿奶關上大門,提著燒火棍大罵:“冷死不向佛燈火,餓死不吃貓兒飯,偷狗賣?呸!傷風敗俗,欺公滅祖!丟盡南詔先祖臘羅巴呢臉!……”
山哥山妹們誰也不敢碎,不敢把這話傳給狗妹。話丑撕面子,她們孤兒寡母的,過日子也不容易,再說手頭不便了,還得向狗妹借個十塊、八塊的,把狗妹惹日氣了也不好。
小村人不聲不響,把自家的狗拴好看好,防止它們別去踩那扣子。可狗多了,拴著喂不贏,只好睜只眼閉只眼。“管毬它,全村又不是只有我家這幾條吃屎狗。”很多人都這么想。
但是,小村人堅決反對自家的山哥山妹,堅決不允許干這種傷風敗俗、欺公滅祖的殺吃屎狗賣的事。
小村山哥山妹們嚷嚷鬧鬧仍不肯罷休。
這可激怒了阿爸阿媽阿爺阿奶。
阿爸阿媽阿爺阿奶牛眼冒火,舉著吆牛棍大罵,要把山哥山妹趕出家門,斷絕關系。
山哥山妹可憐巴巴地整天嘆氣,滿眼淚花看著狗妹挺著高高的胸脯,在她們眼前走來走去……
然而,有幾家阿爸阿媽阿爺阿奶嘴里罵得很兇,心里卻巴不得自家的山哥山妹也能多掙些錢。
小村終究又開起了幾家店子,也賣狗肉湯鍋,可他們賣的狗肉卻不如狗妹的“味足”。山哥山妹的狗肉削價賣也賣不完,于是便天天賣餿狗肉,最后再也沒人吃了。
“小小公雞才學叫,拍拍翅膀又歇掉。噶佩服?!我說你們這些欺公滅祖的敗家子,叫你們搞不得搞不得,你們不聽。這回噶見啦?噶還想再搞?!……”阿爸阿媽阿爺阿奶們得意洋洋地說。
“有心繞到這邊過,搭妹要口涼水喝。不是別家要不到,妹的涼水才解渴”。
狗妹依舊穿著迷你紅裙、白高跟鞋,賣著香噴噴的狗肉,唱著優美的山歌……
村里的狗越來越少,各家不得不在自家的核桃樹梨樹下挖坑蓋廁所。
阿嘎老姆在自家的七條吃屎狗全都失蹤后,終于忍無可忍地跳到村頭“無名高地”上,破口痛罵,滿嘴都是“爛草墊”啦、“破襪子”啦,臟話滿天飛。
后是阿九姆。
再是村長阿土老婆……
“無名高地”變得熱鬧異常。
狗妹老媽在忍了七天七夜之后,終于也忍無可忍,一腳躥到“無名高地”,指天劃地,捶胸頓足,聲淚俱下:“他爹呀,你睜睜眼,蚊蟲虱蚤子亂來叮,人家在欺負我們母女倆;南詔務底老天呀,你睜睜眼,不要臉的人借走了兩千多塊錢不想還……”
小村的狗風波,以狗妹媽的最后“淚訴”平息。
狗少了,小村“嗷嗷”喚狗的習慣沒了。
沒狗上扣,狗妹的狗湯鍋也賣不下去了。
在村長阿土和阿土老婆的極力游說下,在那年的臘月,狗妹背著被老熊抓瞎了眼的老媽嫁到村長家,做了阿狗的老婆。
不久,工地上的“老表們”也三三兩兩地走了。
小村依然還是那么小,小到只要有人站在村頭“無名高地”上雞啦驢啦拍屁股大罵一通,保準全村震得雞飛狗跳,人心惶惶;小到這里方才息怒退下,那里又心平氣和地笑著相互借油借鹽,相邀著去打歌。
小村沒變。
唯一變了的是,巨蟒般滾滾而來的黑■江到了小村,在那里匯成一個清清的湖……
老張老爹
逢年過節喜白兩事,海吃米酒,大坨吃肉,打歌唱調,這些都是彝家最古老的習俗,小村很好地繼承了。
然而,小村幾十號人中,與這習俗完全無關的還有一個,一個非常古怪的瘸老爹。
沒有人知道瘸老爹的年紀,沒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人?叫什么姓什么?只知道他古古怪怪,愛吃耗子,愛吃麻蛇肉,愛一個人自言自語,愛一個人瘋了似地笑……
小村阿公講,這老爹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里的一個冬天,拄著一根拐杖,背著一包破衣物來到小村的。小村的彝家兄弟姐妹見他憨厚老實又可憐巴巴,便讓他住在隊里的場房里,給他飯食……
初來時,這老爹不言不語,也不和村里人一起打歌唱調。村里人送給他飯菜,他也只嘰哩呱啦說些小村人聽不懂的話。但小村人從老爹淚花花的眼中,看到了老爹善良的心地。
老爹便這樣活下來了。
村里人不知道該怎么稱呼他。見他非常愛吃耗子、麻蛇肉,又不吃油鹽,都覺得非常古怪。村里有位老爹,年輕時到過很遠的地方挖過飛機場,見過這樣的人,也一樣地愛吃耗子肉和麻蛇肉,他們都叫“苗子巴”(苗族人)。
后來,有人聽見老爹說了個“張”字,便以為他姓張,便把老人叫作“苗子張老爹”。
每逢過年過節和過冬,小村人都爭著給張老爹送柴送飯。小村人自來信奉只要在世的時候“積陰功行陽善”,將來死了就不會下地獄,于是張老爹自打來到小村后不愁吃也不愁穿,生活得不錯。
老爹有時樂了,會一改自言自語的傻樣,笑瞇瞇蹲在小村口逗小孩,把小村里沒人看管的小孩照顧得好好的。慢慢地,老爹也會學著小村人唱:“大理有名三塔寺,蒙化有名巍寶山,每年二月朝山會,人滿山頭彩云間”、“會打歌的來打歌,不會打歌干站著,得以來到歌場上,不來打歌白來玩”……他常在村頭的包谷地里轉,常操著呱呱的話把進了莊稼地的牛馬豬羊轟趕出來。
張老爹就這樣,不言不語地在小村里生活了十多年。農村土地下放到戶的時候,小村人分給他一只母羊和一塊好地,直到這時老爹才淌著眼淚開口說了話。
“他也會說我們彝家話?”小村人驚奇地看著老爹,奇怪老爹竟能講一嘴彝家話,雖然有些詞句有些拗口,卻也字字句句都說對了。老爹張嘴笑了:“學!我來了這么多年,怎學不會?”
小村人更加喜歡張老爹了。
從此,老爹變得活躍起來。他又唱又跳,唱的盡是《東方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之類的歌,跳的盡是小村人從未見過的“抬腳舞”。小村人很愛聽,也很愛看。
老爹見小村人喜歡,便講起了“古本”。老爹講的盡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毅、賀龍等英雄人物的“古本”。老爹講得有頭有尾,津津有味,尤其講到爬雪山過草地死了好多人,老爹流淚了,小村人也哭了。
老爹天天講,夜夜講,講得小村人越聽越過癮,就像村里來了電影隊似的。
小村人每天早早收工,匆匆扒完飯,便三三兩兩牽著小孩一窩蜂擠進場房里,聽老爹講紅軍打鬼子的“古本”。
小村讀過點書或到過山外壩里的人都很奇怪:老爹講的“古本”怎這么好聽,這么細致,有些書上和電影里沒有的,老爹也能一一講出來……
“老爹是什么人?”老爹的身份,他從未提起。
后來,老爹去世了。小村人按照彝家自南詔便流傳下來的古老風俗,用喂狗的葫蘆瓢給老人洗凈臉、蒙上黑臉布,胸上壓上裝有雞蛋和米的碗,為亡人裝魂。床底下放一個盛有熟飯、肉片,插兩炷香的碗,祭亡人。請來畢摩念經:“……今晚院心里,蓋起松毛房,地上鋪松毛,彩紙扎花棚,靈前豎燎錢,紙馬千萬匹,送你到陰間……”《開吊經》,并打了三天三夜的歌。
在清理老爹遺物時,小村村長阿土從老爹當初背來的爛麻包口袋里,翻出一個用油布包得很緊的包。打開,一層又一層。翻到最后,掉下一本紅彤彤的小書本。阿土打開一看,哇——是黨員證!里面夾著一張發黃的紙:
我叫張貴根,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加入中國共產黨。六八年蒙冤,從此與組織失去聯系。包里的七百八十三元五角六分是我補交的黨費……
小村人對老爹的身世感到更加神秘。
此事傳到壩里。縣里知道后,派來兩個干部,把老爹的東西全取走了。
再后來,小村人終于知道:老爹是個老紅軍連長,爬過雪山,走過草地,打過無數勝仗。文化大革命開始,老爹就被革命小將們斗倒,批斗中,他那條曾經被子彈射穿的左腿舊傷復發,因得不到醫治而弄成了殘廢。一天夜里,他趁看守不注意,一顛一跛地偷偷從牛棚逃走。文化大革命結束,地委李書記——張連長的警衛多次派人四處找尋張連長,可最終杳無音信。幾十年過去了,大家都以為張連長早已在文革中悄然離開人世……
誰也沒料到,曾經立過赫赫戰功的張連長,為躲避黑白顛倒的批斗而逃跑,而在小村里隱居了二十多年!頭發胡子花白的地委退休老書記找到小村里來,他眼淚花花地在張連長墳前站了整整一個下午。
這事很快轟動了小村。
“怪不得老爹會講那么多古本。”小村人感慨地說。
阿嗚雄
阿嗚雄無兒無女,是小村里唯一“領國家工資吃國家飯”的孤寡老爹。
阿嗚雄是小村遠近數百里山林的護林員。
小村人都叫他“護林老爹”。
國家發給老爹一支電警棍防豺狼。老爹整天唱著“一條大路通大理,路邊有對姑娘花;前邊那個隨她走,后頭那個不放她;一把拉著圍腰帶,不說實話不放你”、“郎彈弦子無人唱,自彈自唱自寬心……”之類的山歌,領著三條獵狗,扛起電警棍在山林里悠轉。
國家抓“天保”工程沒幾年,小村山頭的松樹齊刷刷長到了房子高。“再小的螞蚱也是肉,樹小可以砍來當椽子。”小村的一些小年輕人又在打松樹的主意了。
這可惹火了老爹,老爹見人便說:“不要再砍松樹了,再砍再砍,山可要變了,又要整人了”。可小村人不愛聽,砍一天椽子能撈個二三十塊錢,偷偷賣掉,夠花銷兩街了,小村人算的是這盤賬。
“國家不讓砍,咱偷砍!”小村人開始跟老爹鬧貓貓玩轉轉。
這可把老爹的胡子氣飛了。
老爹一腳縱到村頭“無名高地”上,啊咳一聲清清嗓子,開始高聲宣告:“各家各戶聽著,從今天開始,不準再到山林里來砍木料了。貓不在家鼠打歌,你們偷砍不是跟我阿烏雄過不去,而是跟你們自己過不去。你們噶記得,往年山光禿時雨水咋個些?風不調雨不順,再砍再砍,你們噶想吃飯?老天不饒人……我阿嗚雄一個堂堂正正的國家人,吃的是國家飯,說的也是國家話,要是哪個不聽話,再來砍,我阿嗚雄一電警棍電斷他的狗腿!”
不知是害怕阿嗚雄的電警棍,還是終于從“風不調雨不順”中領悟到了點什么,小村人從此很少再到山林里偷砍木料了。
可是仍有狗膽包天的一兩個婆娘不服管,邊罵漢子窩囊,邊帶上漢子背上彎刀麻繩,趁月亮摩挲亮的時候,偷偷摸摸上山砍木料。漢子在林子里偷砍,婆娘就跑到阿嗚雄守林的山棚穩住阿嗚雄。阿嗚雄不吃這套,婆娘一來他就扛起電警棍準備去轉山林。
婆娘死皮賴臉纏住老爹:“歇一下得了,這冷天凍地的哪個來?”婆娘邊用火辣辣的目光粘住老爹,邊用手往老爹褲襠里亂摸。
老爹不理不睬,大步跨出棚子。婆娘急了,一個縱步攔在老爹前面,一把扯拉住老爹的手唱起火辣辣的情歌: “得已來到玩笑處,不玩幾回心不甘;鮮花不采白開敗,人不風流白托生……蠶豆豌豆豆腐豆,一家一樣抖攏來……”
老爹氣得全身發抖,二話不說,閉上眼睛把電警棍對準婆娘的臉大吼:“滾遠一點,我阿嗚雄堂堂呢南詔王后裔噶是那種騷爛人?!”
“老鴰莫說母豬黑!”婆娘嚇得灰溜溜地跑了。
老爹的威名從此傳開了。
另一件事更是讓老爹的威名倍增,使他成為小村最有影響力的人。
有天傍晚,老爹唱著“砍柴割草要約伴,灰迷眼睛要人吹”、“郎脫衣裳妹抖床,妹脫褲子郎吹燈。小郎脫得黑麻麻,阿妹脫得白生生。齊奪奪呢睡下去,象牙筷子一小雙……”的山歌優哉游哉轉林回來,聽見村背后的林里有人在咕噥咕噥說話。老爹躡手躡腳走近一看,呸!原來有一個山哥正在扯山妹的褲子。
老爹大吼一聲:“哪個膽大包天,竟敢大白天來偷砍木料……”
林里靜悄悄的。老爹又大吼一聲:“出來!”
林里仍靜悄悄的。老爹假裝自言自語:“沒人?剛才咕噥咕噥說話的難道不是人?啊咳,哪是什么?喜鵲老鴰叼雞吃,罪名背給餓老鷹……”老爹裝作尋找的樣子開始在旁邊轉圈。
山哥山妹嚇得連滾帶爬溜回了家。
第二天大清早,老爹啊咳一聲站在“無名高地”上宣告:“房屋破了還能補,花蕊損了花自敗。各家各戶的山哥山妹聽著,我阿嗚雄身為國家人,要說國家話,唱唱情歌豐富一下生活是可以的,但若是要亂來傷風敗俗,丟南詔老祖宗的臉!啊呸!往后要是還有誰敢跑到林子里來亂搞,我阿嗚雄一電警棍電斷他的狗腿!”
小村老少聽到這,都撲嗤笑了:“老爹管得真寬!”
阿嘎姥姆
阿嘎姥姆開了個飯店?!
小村人笑得前仰后合眼淚像核桃花一樣落。
誰去吃她屎爪子抓出來的飯菜?
阿嘎姥姆也是小村的“拉羅巴”彝族本家人,住在村西頭大麻栗樹疙瘩下花椒箐里。
小村人曾把阿嘎姥姆稱為嬸,那是在她剛結婚的時候。
一年后,他漢子見她肚子老癟著,就醉熏熏唱了調“向陽桃子背陰梨,濕處核桃熱處桔;四季握你不掛果……”之后,便鬧了離婚。
小村人不再把她尊稱為嬸。“她不配!”小村人都這么認為。
阿嘎姥姆不會生育,全村人都把她改稱作 “漂沙人”。
阿嘎姥姆開了一個飯鋪。
阿嘎姥姆開飯鋪?!小村人笑得前仰后合,直到笑出了眼淚還在笑:哪個傻蛋會去吃“漂沙人”屎爪子抓出的飯菜?!
一日,阿嘎姥姆的前漢子賣完菜,灌了壺酒唱著“太陽落坡山背黃,豹子下山咬小羊,咬豬咬羊只管咬,莫咬我的小情妹”、“左腳一搭右腳上,好像蝴蝶戲牡丹。繡花枕頭郎不靠,專靠阿妹手彎彎。一更赤龍下海島,二更白虎在山朝,三更鴛鴦對舞好,四更蝴蝶繞花梢……”的山歌從阿嘎姥姆鋪子門前經過。
阿嘎姥姆的前漢子也住在小村,也是小村人。他甩了阿嘎姥姆后,討了隔村的狗花做婆娘。狗花嫌他又懶又貪吃喝,罵他“一夜說得胡子嘴,天亮還是光下巴……有錢能使鬼推磨,還有懶鬼不愛推”。于是跟他離了。
阿嘎姥姆的前漢子在小村,可算個人物哩!他會掐八字擇吉日祭神送鬼,村里小到劁豬騸狗大到結婚抬死人都離不了他,都得求他。每出臺一回,一只雞一壺酒一升米,一把鹽一串辣子穩拿了。漢子倒也生活得有滋有味,像個“半神仙”。
“三窮三富不到頭,九轉十八不通頭”。土地下放到戶后,小村的人漸漸不再來請他,再不管什么吉不吉利了。
“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小村這群沒心肝的坯子!沒老爹我給你們看的好地基,沒老爹我給你們掐的好八字,沒老爹我給你們擇的好吉日,你們哪來的好日子過?!”阿嘎姥姆的前漢子時常這么憤憤地想。
小村雖然還有幾家仍尊他為“神仙”,但東西拿來的越來越少。他的日子實在“有了筲箕無笊籬”過不下去了,種田種地酸筋痛骨三天兩病的,做生意又沒本錢,最后只好揀了個“種著河邊田,圖個手不閑。收成有不有,不必掛心間”輕便活兒——種菜。
每逢街天,他打早雞叫頭遍走起,把菜背到蛇街賣,賣完菜后稱米稱鹽稱油,整半斤蛇酒回來。
阿嘎姥姆見到她的前漢子,熱情地和他打招呼:“阿山哥,進來歇一下咯”。
老爹一聽得這聲甜甜的喊,納悶了。心想,二十幾年了,狗日的婆娘還從未叫過我一聲哥呢,就在同房時也不曾這么親熱地叫過!今個咋啦?
他混想的當兒,阿嘎姥姆又親親熱熱地叫了一聲。他樂了,心想,這 “漂沙人” 是不是想復婚哩?他用那雙死魚眼盯著她,心里一喜:賊婆娘沒生過娃,還嫩著呢!
“阿哥,今個生意咋個些?”阿嘎姥姆滿眼含笑地問他。他連答:好!好!
阿嘎姥姆招呼他坐下后,端了一大碗豬肉坨子和一大碗酒擺在他面前,催促著:吃,快吃哩!
他望著肥滋滋的一大碗肉,饞得口水瀝瀝啦啦直往下掉。他遲疑著不肯下筷子,心想:這菜錢可是大爺我一個街子的口糧哩,一頓吃了不成。
吃呀阿哥!阿嘎姥姆見他遲疑,又甜蜜蜜地叫了一聲,隨口唱了一調:“太陽落了有月亮,姊妹黃昏好粘連;妹是一只無窩鳥,阿哥懷里先歇歇。”他心底一樂:看來錢不用付哩。
他大口大口啃起肉坨子來,滿嘴巴油。他一面啃,一面樂滋滋地看著阿嘎姥姆,暗自得意:這《三世演禽婚姻簿》真格應驗了,大爺我老來有福,“天上孤單是月亮,地上孤單我一人”、“一只筷子難夾菜,一個漏碗難裝湯”,大爺我孤苦生活就要結束了。嘿嘿,說不定“漂沙”還不“漂沙”了哩!這回復后要對她好點,再不懶,再不貪吃貪喝……
酒至半酣,他“啪”一聲砸碎酒壺,對天發誓:“火燒芭蕉心不死,我……我從此不再吃酒貪懶……我阿……阿山對不起你……我不是人……”阿嘎姥姆看著他發紅的雙眼,心里一顫,倏地變了臉色:“豬心豬肝街上賣,人心人肝各自帶。阿哥,人活著為哪樣?不吃不穿,錢往那撂”?
他更樂了。這賊婆娘真會體貼人,我阿山真個老來有福了“大河漲水小河清,不知小河有多深。揀個石頭試深淺,試妹真心不真心?”……
正這么想著,突然黑云翻滾,旋風陣陣,風雨欲來。
阿嘎姥姆一面收碗收筷,一面看著天自語:“螞蟻趕街,老天變篩,天快黑哩,要來大雨了”。
他暗自道:人家在暗示哩,再不走又要遭小村這幫浪娘胡猜哩,“刀尖頭上舔蜜吃,嘗倒嘗得要小心”走走走……
阿嘎姥姆見他站起身,不緊不慢地說:阿山哥,菜錢五塊,酒錢八毛。
轟——
一個雷在屋頂炸響,震得他搖搖晃晃,酒全醒了——
“做夢跌深谷,馬騎騾子上大蛋了!”。
“黑山神”得旺
小村有個混漢,矮矮胖胖墩墩實實,滿臉皺紋填滿污垢,褲腰斜系一根大拇指粗的從舊馬鞍上割下來的皮條,整天敞開肚皮,露著黑漆漆的圓肚皮,見人便滿臉嘿嘿堆笑“阿老友、阿老表”地叫個不停。小村村中央一路的牛屎馬糞路上,數他吹牛吹得最過癮,就他講得最天花亂墜。他有本事把自個年輕時渴急了撲母牛背的丟人事也講得津津有味,也有本事把別家媳婦與野漢在野外瞎搞的事編得有聲有色具具體體。得旺最大的本事是淌著口水瞇眼,吹噓他昨晚夢見挖到金山掏著了銀窯騎著大紅馬做了縣太爺,然后嘿嘿一臉傻笑……
這混漢叫得旺,自小聰明又機靈,四歲就能吹白話唱調子。壞就壞在那年的一天,小村來了個算命先生,得旺媽領得旺去算了一卦。算命先生閉眼掐指節一算,突然伸大拇指贊嘆:“此娃乃大貴之命,成人必當大官!”從此,得旺便洋洋得意地不學好,東家誑西家誆,“以后長大當官我罩你!”成了他的口頭禪。從此他充當娃娃頭到處騙吃騙喝欺負別的村里娃。小村人處處讓著捧著得旺,父母也慣著他。得旺越學越壞,上學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小學未畢業就跑回家“等著發跡當官”。輟學回村的得旺更野了,攪得小村雞飛狗跳。得旺父母便早早給得旺娶了親,巴望媳婦管住得旺。無奈得旺鐵了心硬了腸仍惡性不改,整天游手好閑吊兒郎當,餓了偷缺了拿,回家還拳打腳踢沖媳婦發氣發火,最后氣死了老媽氣瘋了老爹,以后得旺更沒人管了,也更野狂了。
小村人對得旺忍了又忍,怕的是得旺時來運轉當官,二來是大家都是血親家族誰也下不去手,再說得旺這小子臉皮厚人也尖,偷小不偷大,摸黑不摸明,捉到也不抵不賴嘿嘿笑著討好,甚至一把鼻涕一把淚乞求“都是你家侄餓壞了,被逼得沒法了!”事主也只能發善心讓得旺把東西帶走。全村人只好整日整夜提心吊膽守好自家東西,不讓得旺偷到。得旺雖然過得窩囊,但也和村里人相安無事多年,這讓整上二兩小酒后的得旺有時還自鳴得意。
可有一件事把得旺弄臭了,令得旺虱叮蟲咬著實坐立不安慌了幾日。就在那年的秋收時節,也虧得旺這混人窮急了想得出,跑到遠村大姐家借驢,謊言洋芋大豐收背不完,借姐家驢馱幾天,還驢時順便馱馱洋芋給姐。大姐不在家,大姐夫聽了很高興,舅子終于出息了便爽快地把驢借給了得旺。可日子過了幾天又幾天仍不見弟弟還驢。阿姐便買上一包糖來到得旺家。得旺這混人一見姐就笑哈哈跑出大門滿嘴“阿姐來了噶?阿姐辛苦了!”熱情地把大姐迎進家門,樂得阿姐甜滋滋提不起半個驢字。第二天臨走,阿姐才說明來意。誰知得旺這混人說:“阿姐你說哪樣?說什么說!我什么時候拿了你的驢?從你左手里牽過驢繩還是從你右手里牽過驢繩的?”氣得阿姐氣都緩不過來。阿姐哭嚷嚷跑到村長家,請村長評理解決。村長說:“我確實沒見過得旺牽回家什么驢”。最后,得旺姐夫也趕到村長家。村長又說:“誰不知得旺是塊又臭又硬的廁所里的石頭?人窮得不疼不癢,要說要勸的我早說早勸過了。得旺聽進去了半句?要叫得旺賠?一間爛草房搖搖欲墜,全家吃了上頓沒下頓,拿什么賠?再說你們血親姐弟……”氣得得旺姐哭哭啼啼不肯善罷甘休又跑到派出所告狀,值班民警和藹地勸得旺姐:“大媽,算了,得旺的情景你又不是不知道,怎抓?”
“告就告吧,抓就抓吧,我巴之不得,坐牢有什么不好,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再為一家老小七八口奔忙口糧,抓?嘿嘿……”
隔村阿狗證實,得旺在路上把驢賣給了四處串門買牲口的漢家老表,可得旺抵死不認。自此,小村人沖得旺臉黑心黑私下把他稱之為“黑山神”。“黑山神就黑山神,有什不好,山神不消為吃為住發愁,多自在!嘿嘿……”
小村人有些容不下得旺的無賴行為……
村長便硬著頭皮去勸得旺開塊山地種點蕎豆,好好養家活口。得旺這混小子竟不識好人心,嘿嘿兩聲冷笑“有福之人你莫忙,無福之人跑斷腸”末了痛罵村長看不起他嫌棄他欺他窮,唬得村長一拖煙桿就跑。說來也巧,那年秋天,得旺孤寡老舅放羊砍犁彎掉下老鷹巖去世了。得旺作為小村唯一的財產繼承人接收了老舅家的蕎地和羊。得旺還四處吹噓:“噶是我就說了有福之人你莫忙?!”
這可真激怒了小村人,借姐家驢抵賴、撿老舅家蕎和羊還洋洋得意,這可把小村有良心的有識之士的肺泡全氣炸了,小村人再容不下這號人了,先前怕得旺當官報復,如今三十年過去了,得旺都快四十歲了,“那鬼算命先生瞎說,怕個球,好好收拾不要臉的黑山神!”
“好嘛,試試看嘛,你們敢收拾我,老子先下手為強!”得旺竟把老婆拖到村口,吊在村口的大青樹上毒打,向全村人示威“收拾黑山神的神圣還沒在小村投生!”得旺罵個不停。第二天得旺老婆趁得旺不在家,牽著娃背著娘家陪嫁的嫁妝哭哭啼啼回了娘家。得旺回來可不得了,跳跳腳抄起自家扁擔滿嘴山東話直奔岳母家。這天正好岳父和岳哥幫人家殺年豬,岳母家只岳母和得旺老婆在家。得旺一沖進家門便揪住老婆左右五六個耳光,又一巴掌打得前來助戰的老岳母滿嘴血水跌倒暈在地。得旺罵罵咧咧把老婆扭翻在地,一個縱步騎在老婆身上拳打腳踢一頓毒打。打夠了,還尿了泡尿在老婆身上。得旺老婆鼻青臉腫一時氣竅堵塞,昏倒在地上。得旺發泄完怒氣,抽支煙,見老婆倒在地上不哼不喘氣了,便摸了摸鼻子,沒氣了。回頭一見岳母倒在血泊中不動不扭,嚇得臉倏地煞白,一個雀躍奔出了岳母家門,一路恐恐慌慌跑回了家。得旺這混漢這回真慌了急了,殺人賠命,人頭不保了。得旺大汗淋淋褲衩濕透如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得旺認為這回死定了,沒救了,玩完了。越想越恐懼,最后便嗚嗚哭著腳抖手抖找了根麻繩吊在自家草房梁上一命嗚呼。弄得一時休克又活過來的得旺老婆又哭天喊地連夜回家披麻戴孝葬得旺,得旺的幾個娃哭著喊著扯著阿媽的褲腳要阿爸。
得旺死了,小村人又悲又喜,悲的是小村人志志氣氣、清清潔潔活了七八代,竟出了個欺公滅祖、臭名遠揚的偷雞盜狗的無賴,還是個吊死鬼,敗壞了小村風清氣正的風水,全村人也可憐得旺老婆和孩子。喜的是這早該天收的背時鬼終于不會再行兇了,小村又恢復了平靜……
小村人一直贊成把得旺葬在全村人放牛、砍柴、上學、趕街上路就能一眼看到的路邊土包子上,好讓全村人世世代代記住,不能聽信算命先生的話,不能好吃懶做偷雞摸狗,不能……
從此,小村牛屎馬糞路上大白天吹爛牛的懶鬼漸漸少了,村里什么雞啦瓜啦蛋啦核桃啦也不再莫名其妙丟了。
編輯手記
讀只廉清的小說,有一絲欣喜。作者扎根鄉土,汲納民間文化,將民間的語言,民間的山歌小調,自然地融入自己的創作中,形成了獨特的敘述風格。同時,鄉間人物形象躍然紙上。這種植于泥土的寫作方式值得大理寫作者借鑒。
責任編輯 楊義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