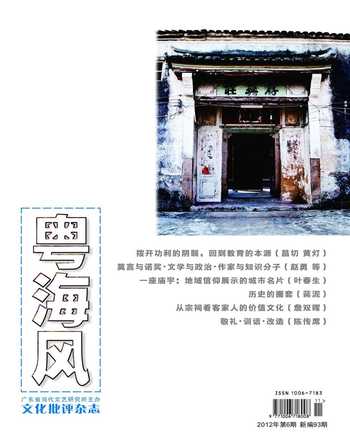來自宗教的慰藉
蘆笛
胡適生前熱衷于勸其老輩朋友們寫自傳,意義在于“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林長民、梁啟超、梁士詒、蔡元培、張元濟、高夢旦、陳獨秀、熊希齡、葉景葵等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是他所懇勸的對象(見胡適《四十自述》自序)。他的校友兼傳記文學愛好者——1927年于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博士學位的農學家沈宗瀚先生(1895—1980),也在1937年撰寫了一部自傳,后由臺灣正中書局于1954年出版,題名《克難苦學記》。
這部不足百頁的自傳初版時,前有教育家蔣夢麟、學者胡適的序,以及作者自序,后有農學家錢天鶴的跋;到了1962年第五版時,書前又增印了胡序的手稿全文影印件,書名也換上了胡適的親筆題簽。僅至1970年,此書便已修訂到了第十版,可見其在臺灣讀者中的風靡程度。將《克難苦學記》首次引進大陸的,是科學出版社于1990年根據正中書局第二版(1954年12月)內容印行的簡體字本,書前增加了裘維蕃的序。其中“內容簡介”部分稱“本書原版于1954年3月臺灣正中書局”,有誤,“3月”當為“9月”,這可能是由于見沈氏自序作于“三月二十九日”所致。此后,除了科學出版社在2010年又將此書重印外,黃山書社也于2011年將此書出版,作為《沈宗瀚自述》的上部,中部和下部分別為《中年自述》和《晚年自述》。后兩部自傳講述作者回國后之種種作為,雖多可圈點,但終不如《克難苦學記》曲折起伏,動人心扉。
名人自傳多以成功收尾,然成功之標準則往往各有不同。鄙意以為自傳中最具有普遍意義也最值得普通人借鑒的地方,乃在于鍥而不舍地追求夢想的精神。這種精神在《克難苦學記》中一以貫之,讀來令人備受鼓舞。胡適在序的開頭這樣評價道:“沈宗瀚先生的《克難苦學記》,是近二十年來出版的許多自傳之中最有趣味、最能說老實話、最可以鼓勵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傳。我在海外收到他寄贈的一冊,當日下午我一口氣讀完了,就寫信去恭賀他這本自傳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胡適1910年初入康奈爾大學學農科時對蘋果的分類甚感頭疼,終而棄理從文,適與沈宗瀚在康大鉆研農學成一有趣對照。
《克難苦學記》全書始于故鄉和家世,終于1928年沈宗瀚入選Sigma Xi科學榮譽學會,用半文半白的形式寫成,共六章:故鄉與家庭、家鄉的教育、筧橋甲種農校、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五年教學生涯、游美留學及研究。沈氏在自傳中交代,其自傳的創作動機是“(父親)喪事既畢,為追思父澤,乃立志寫此自傳,一以述吾父遺訓,或可代表我國舊文化之精神,并述吾苦學經過,或可說明新舊文化過渡時期之遭遇也”。可謂立意高遠,并非簡單地為一己立傳。把個人際遇置身家國社會之變化,這是沈氏自傳的高明之處。
沈氏此書既已有多位學者撰寫序跋,本毋庸筆者贅述。然而作者在自序和正文書中多次提及基督教信仰對其克難苦學的精神助益,這是這本自傳的與眾不同之處。眾多序跋中只有胡序曾對此一筆帶過,而現在看來這個方面似不無探討之價值。
“克難苦學”中的“難”,不只是經濟上的困難,還有家庭期望與個人志向之間的沖突,亦即胡序中所謂的“‘繼續求學與‘就業養家的沖突問題”。沈宗瀚在余姚誠意高等小學堂就讀期間(1909—1913)即流露出不喜應酬、厭惡庸碌的性格,并且因自己出身農家而立下為農民服務的志向。由于他出生于一個近二十口人的大家庭,其父分家后,小家庭中也有七口人(加上一名長工),因此他家的收入雖屬中等,但因人口多之故,經濟狀況并不樂觀。小學堂畢業時,父親第一次要求他工作,以還債養家。他痛哭哀求,方得以籌借學費,繼續考入杭州的筧橋甲種農校讀書。1914年,他因感收獲無多,在經歷因費用不足而不能赴日留學之后,決定從農校退學,轉而報考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以期將來能赴美讀書。得知消息后,父親老淚縱橫,說:
汝筧農難關始渡,復欲上升,經費難以為濟,筧農與北農均不能畢業,則將如何?人貴知足,汝二年前謂筧農畢業于愿已足,今貪得無厭,我何時得用汝錢耶?我將為經濟逼死。你即能畢業北農,而于心安乎。
然而窘迫的經濟條件也不能阻止他求學。最終,沈宗瀚再次多方借款,得以在1914年底進入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先讀預科一年,再讀本科三年。四年時光免不了許多開銷,故而經濟負擔越發沉重。再加上父母的不理解,二十歲的沈宗瀚于是年冬天開始信仰基督教。次年四五月間,父親不顧其求學之志,決意迫其完婚,以至于:
回家途中同鄉同學頗多,均興高采烈,余默自深嘆:人皆有福我獨無。
豈知新婚第三夜,他的二哥就和家人前來,就去年冬天借出的四十元正式訂立借據,年息一分。他說:
是夜,余精神上甚感苦痛,此款卒于民國九年二月十二日還清本息,計為六十四元。
北農的授課也令他失望(最后的畢業典禮亦未參加),但為了日后能有留美的機會,他不能再退學。于是他在好友的建議下偷偷報考清華高等科二年級,但終因英語口試和年齡沒有過關而落第,只能繼續待在北農。他期間結交了不少在北京生活的中外基督徒,大量閱讀宗教書籍,參加查經班,因而信仰彌堅。在基督教的影響下:
余漸感耶穌與罪惡戰爭之精神,故由沉默自好而漸趨積極活動,余提議改聘不良教員數位,如英文、園藝及農場實習等三四教授,全班從之,向校長再三要求,逐漸實行。
1918年6月,24歲的沈宗瀚畢業,但并未立即做赴美的準備。雖然自傳中對此沒解釋,但想來也不外乎是經濟窘迫所逼。他為求學借款甚多,而且業已成家,故不得不先緩和一下家庭的艱難境況。從1918年到1923年,他因缺少人際關系之故,雖學業優異,最初不免四處求職,八面碰壁。求職失敗回家后:
父以家庭經濟急盼余助,事既落空,怨責備至,益增余之苦悶。家人亦多笑言:“苦學何用,終究回家吃飯了。”深感茫茫人海中,無一可訴,無一知己,惟有虔誠禱告上帝而已。……余茍不信基督,必病,將無人生樂趣矣。……家人往往于困窘之時,加以訓責,甚至冷言譏笑,何堪忍受。
之后,他最先從家庭教師做起,收入和生活頗為安適。但在1918年秋冬,家中經濟又變得異常困厄:
父諭命余月寄三十元,惟迄今二月之薪金已告罄,奈何!……誠年長一年,經濟苦難亦年增一年歟?茍無基督信仰,余將為錢逼死矣。
面對如此現實和壓力,若無基督教信仰和留美求學之信念,沈宗瀚恐怕真要身心崩潰了。終于,在1918年12月25日,他在中華圣公會接受洗禮,成了一名基督徒。那時北京同學師友中嫖賭之風盛行,他仍百毒不侵:
彼輩邀余同游妓院,余婉謝,獨自歸寓讀書。
基督教為他減輕了精神上的痛苦,讓他感到“失望之余,似尚有一線曙光”。他甚至寫信勸家人信仰基督教,但卻遭到了父親的強烈訓斥:
吾父復諭,責余信教為不孝……破壞家風,且斥耶教為迷信,余大失所望。
然而他的父親是一個自私自利,不顧兒子死活的父親嗎?自傳中有一段十分真摯的敘述:
我父今年已六十四歲,從十六歲管家,負債到如今。自朝至暮,勤勤懇懇的教書。節衣縮食,事事儉省,沒有一次專為自己買肉吃。我母買給他吃,他還要罵她不省錢。我去年暑假回去,他偏自己上城買魚肉給我吃。這魚這肉實在比魚翅、燕窩好吃萬萬倍。他罵我欠節省,我有時不服,但看他自己含辛茹苦,勤奮教書的光景,我就佩服到萬分。
父親希望他本本分分,結婚生子,養家糊口,過安穩日子;而他則立志要為國家做大事。即使在赴美前夕,其父仍拿“父母在不遠游”這樣的古訓勸他。他的父親雖也教了一輩子書,但終究秉持傳統讀書人的思想。繼續求學與就業養家的沖突,也就是現代與傳統的沖突。他們父子處在清朝滅亡和民國建立之際,新舊社會的轉型加劇了保守和進步之間的摩擦。最終,沈宗瀚得以兩度赴美,并獲博士學位。這既是克難苦學的豐碩成果,也是現代社會價值觀念和人生追求的勝利。這位父親是疼愛兒子的父親,而這位兒子也是敬愛父親的兒子,但是在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時期,父子價值觀念的激烈碰撞,現實與理想的鮮明反差,致使沈宗瀚只有沐浴在基督教的信仰之中,才能找到實現抱負和繼續生活的精神慰藉。他那信仰基督教的大哥可能對他早年接觸基督教有很大關系,而當時北京的歐美傳教士和基督徒之多,則又成了他日后篤信教義,并接受洗禮的重要外因。
關于沈宗瀚求學期間精神上倍感痛苦之根源,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中有一段文字或可為之詮釋:
一個人讀書中舉而后成為官員,如果認識到他的成功和幾代祖先息息相關,他就不能對他家族中其他成員的福利完全漠視。何況這種關心和幫助也不會全是無償的支付,因為沒有人能夠預測自己的子孫在今后不受他們的提攜。這種經濟上的利害關系被抽象而升華為道德。固然,這種道德觀念并不能為全體民眾所奉行,從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間爭奪產業以至斗毆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這種情形正好從反面說明了教養的重要,有教養的人則決不能以利害義。(見《萬歷十五年》之《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
這段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沈氏父親的思想和要求。因為在他看來,他自己的生活以及他兒子的讀書機會,實在有賴于家族宗親在經濟和生活上的幫助,而他兒子畢業還債以及養家糊口則是道德上的義務,這樣他的孫子和后人才能繼續享受和給予這種源于宗族的福利。一切都按部就班,緩緩向前推進。這種程式在古代社會受到了良好的執行,但是在那動蕩激變的近代社會,它又缺乏速度和變化,跟不上時代的腳步了。
(作者單位:英國肯特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