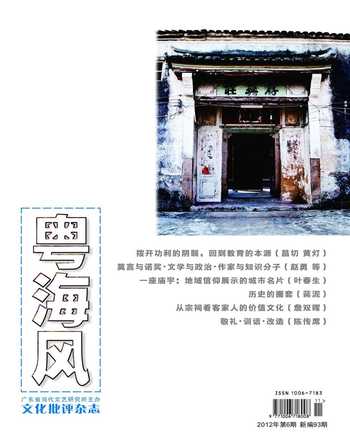就“文學史”敬答嚴家炎先生
嚴先生:
您好!收到您的來信,驚恐不安。原以為先生定不會理睬我等之愚陋,豈料先生如此襟懷,晚學自責不已。同時也為自己的疏淺和無知而自慚,冒犯不敬之處,罪不可逭,尚望先生萬勿自擾。
以我之陋見,《二十世紀文學史》的上、中兩冊以及下冊的絕大部分章節,確如您及學界的諸多老師所言,厚大精深,很有分量。而拙文所涉及的一些章節,實在令人難以恭維。我知道一點學術界的規則,也知道您年事已高,不能每一行文字都親自過目。但作為參編者,即使自己無暇請別人代筆,最起碼也應該認真地把關,這是對自己的尊重,也是對您的尊重,同時也是對學術和讀者的尊重。我之所以寫文章,正是因為沒有對學術和讀者的尊重。當我在課堂上給只相信教材的學生反復糾錯時,一種道德上的“義憤”也在不斷地升級,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豈容這般的草草敷衍。正是這種“義憤”使得我不能為尊者或名家“諱”,我覺得自己可能很淺陋,但這種“義憤”應是沒有錯的。
您談到我論述中的一些武斷和偏頗,確如其是,提供的一些材料也開我眼界。但我也有一些疑惑,比如宗璞的《我是誰?》的問號問題,幾本流行的文學史都沒有,您和馮先生的談話是否能作為依據,是不是以最初刊發時的原貌為準妥當一些?當然,這些都是枝葉問題。如果您留意,會發現我的主要目的是比較和陳思和《教程》的相似問題。您說的我“責備現在這部文學史介紹作家時,沒有采用規范的統一格式”也顯然是誤會了問題的指向。我覺得,可能因為這兒拼一點,那兒貼一點,才導致作家介紹時出現的這些問題。再如杜鵬程和柳青的相互影響問題,我們也不能因為杜讀過《銅墻鐵壁》就說他受過柳青的影響,這得有可靠的依據。否則的話,就這個問題誰也講不清了。還請您有空批評。
您在來信末尾提到我的分析“缺少分寸感和準確性,失去了一個‘度”。是的,正如您所言,我過于意氣、過于激動,但我的分析多多少少還是有依據的,并不是信口雌黃。“誤人子弟”、“嚼飯與人,徒增嘔穢”的話是重了點,但您如果仔細讀一下論及《白鹿原》的部分、論及莫言的部分(對著陳思和的《文學史教程》讀),我相信,大多數行內的人是難以忍受的,只是希望,這套教材如果再版,能作修改是最好不過了。在我讀過的文學史中,下冊的錯訛多到了令人不可忍受的程度。教材和一般的學術著作不同,影響面積太大。以我校而言,這一年級十余個班級四五百人在使用。如果學生用其作為考研的參考資料,這些差錯難免會影響學生的成績甚至或前途。這也是我沖動撰文的原因。
文章刊出后,接到幾位師友的電話,說我“惹了事”,甚至是“自找麻煩”、“自毀前程”,我一笑置之。不過說實話,我自己也有些后悔,當然不是怕前面所提的“麻煩”,而是覺得這種事情我可能少見多怪,自己列一個勘誤表,印發給學生就行了。我給您寫信的意思,也只有想讓您(筆者按,原信少“讓您”二字)知道此事而已,別無他意。當然也沒想過您能回復。您和孟繁華、程光煒先生都是我十分仰慕、尊敬的學者,你們的著作無論是在我的學生時代,還是如今,都提供給我豐富的營養。但這種仰慕和尊敬不能讓我對錯誤和敷衍閉上眼睛。我一直主張,對年青學者可以寬松一點,對于著名學者要嚴厲一些。因為著名學者的背后,有很多目光;而年青學者,正在成長。就我而言,鼠目寸光,學識淺薄,又易激動、易偏激,因而有自知之明,能做一個認真的教書匠即可,“前途”是沒有的,這是我“犯上作亂”的原由,也是我對師友告誡關愛一笑置之的原因。
感謝您,能語重心長地指出我的問題。在一個說假話盛行的時代,您的坦誠、關愛使我如沐春風,感念不已。再次為我自己的淺薄無知向您道歉、請罪,不敢奢望您的原諒,只是希望此事不帶給您些微影響。同時,麻煩您,若有機會,轉達我對程、孟二先生的歉意。若有機緣,定當當面謝罪。專肅
即叩
鈞安!
晚學王鵬程頓首上
四月十二日
又:
嚴先生:
您好!有幾點需向您說明:
一、收到您的來信之后,我很糾結,不回復,沒禮貌;回復,怕沖撞您。我自始至終都沒有冒犯之意,只是向您說明此事而已。拙作寫成后,曾征詢教研室同事意見,他們覺得有必要向您說明此事,這也是我給您寫信的主要動力。
二、此文執筆者為我,錄入電腦者為魯老師,她曾修改潤飾,因而出現您指出的敘述主體不清的問題,特向您及刊物道歉。
三、上課時,有老師糾正下冊中的錯誤,學生說:“您說人家錯了,為什么您不去編?”老師只能啞笑。本、專科學生,大多只信書本,因而糾錯是十分必要的。
您乃學界泰斗,年高德劭。吾儕狂妄無知,冒犯之處,惶恐不安,唯望先生勿以自擾。
王鵬程再拜
四月十四日
(作者單位:咸陽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