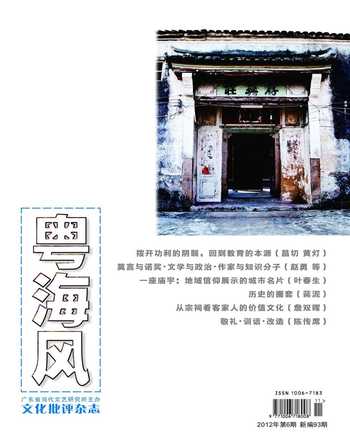“繼續革命”視野中的反官僚主義小說
閆作雷
引言
反官僚主義作為官僚理性秩序的對立面有一種或潛在或顯在的“繼續革命”訴求,這主要表現在共和國新一代左翼知識青年的文學創作和實際行動中。這里彰顯的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或“激情和理性的沖突”,而是內在于革命邏輯和建國后不得不然的“自我否定的機制”之中,他們的作品顯示,延宕革命理想和目標的官僚主義與“繼續革命”訴求之間有著難以調和的沖突。“當代文學”中的各個階段,比如“百花時代”、大躍進時期、1960年代初和“文革”等,是“當代歷史”不斷自我否定進程中的連續性一環,而非斷裂。
當然,不同時期的反官僚主義有著不同的政治目標和表現形式,但那種內在的“繼續革命”訴求卻是相通的。1955—1957年“百花時期”反官僚主義的主體是充滿革命熱情和社會主義理想的左翼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以個人的方式對抗官僚集體;他們響應了1955年毛澤東加快農業合作化速度的政策和進入“社會主義高潮”的號召,然后以“干預生活”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為口號向當時所謂“保守思想”和官僚主義者開火。“文革”及其前夕的反官僚主義者則是具有高度無產階級覺悟的工人、農民和復員軍人等。他們以集體的方式反對個別的官僚主義者;他們響應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因此“兩條路線斗爭”的模式更明顯地具有了“階級斗爭”的性質。“人民”被調動起來——這特別類似于中國革命興起時的情形,革命依靠的對象,以左翼知識青年始,以工農革命終。
在“文革”結束后的“撥亂反正”時期,1960年代以后響應“階級斗爭”的作品被否定,而“百花時期”那些“干預生活”的作品則作為“重放的鮮花”在“反官僚主義”這一主題上得到肯定。然而此時的“反官僚主義”含義已經不同于前兩個時期“繼續革命”意義上的“反官僚主義”;當時通過“重放的鮮花”實際上是要建立官僚統治秩序,修復前此被破壞的官僚理性。因此就產生一個悖論:那些要求“繼續革命”的反官僚主義文本作為“重放的鮮花”,要恢復的“正”卻是建立官僚理性秩序——那些內部充滿了“繼續革命”沖動且參與到當時“政治辯論”中去的小說文本在新時期初期卻成了“去政治化”進程開始的標志。
“百花時期”的反官僚主義
1955年是很有歷史意味的一年[1],這一年中共高層發生的關于農業合作化速度的爭論直接影響了“當代歷史”的走向,這一爭論的結果也鮮明地反映到文學創作中來。尤其是“鳴放”初期那些出自青年作家之手的反“保守思想”/反官僚主義的作品是直接參與到這一爭論中來的,這些作品在當時被作為“干預生活”的代表作——不過它們與另一些所謂揭露社會“陰暗面”的作品的訴求是截然不同的[2]。回到當時的語境中看,這些青年們反對保守僵化,主張“熱情”和“創造”的作品才真正符合當時“干預生活”這一口號的初衷。唐摯最先提出的“干預生活”的口號,主要目的是為了鼓動人們要有參與生活和“社會主義高潮”運動的熱情。作者充滿“熱情”地寫道:“冷淡,永遠將是一部作品的致命傷,因為這總是意味著作家和人民生活的某種距離。”“作家,必須是熱愛自己的人民和生活,必須是大膽干預生活,用全心靈去支持一切新事物的猛將!”[3]顯而易見,作者所說的“干預生活”是要“加速”生活,去“干預”生活的“常規”節奏和毛澤東所謂“小腳女人”似的官僚主義者。
分析當時的爭論不難發現,中共高層對農村合作化和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分歧的焦點是:比較穩健地按常規發展,還是依靠群眾的熱情加速發展?主張后者的毛澤東認為農村工作部的“保守派”(即主張收縮,放慢合作化速度)代表了資產階級和地主、富農的利益,認為他們沒有顧及農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貧下中農”的利益,沒有看到后者“走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從1955年7月31日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開始,毛澤東對堅決收縮的“保守思想”進行了猛烈批判,并將其上升到“兩條路線斗爭”的高度。到這年年底,“保守派”被徹底打了下去,中央農村工作部鄧子恢他們被迫作了檢討。毛澤東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而是保守干部們被“勝利嚇昏了頭腦”,他們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他們只是用蘇聯的經驗“來為他們的爬行思想作掩護”。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用富于文學性的語言寫道:
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嘴臉,被區分得清清楚楚。黨內也是這樣。[4]
毛澤東認為這不僅僅是“保守思想”的問題,而且是“脫離群眾”的問題,而這種指責在當時意味著是官僚主義作風的表現;而且不僅僅是官僚主義的問題,還是階級立場、階級斗爭的問題。
毛澤東也首次把眼光投向青年,因為他們“最有生氣”、“最少保守思想”[5],而此時懷著理想主義、要求“繼續革命”的王蒙們就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了,他們將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向“保守思想”和官僚主義開火。
1950年代后期,毛澤東越來越關注“一五”計劃和采用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后果。知識分子的貴族化和官員的官僚化所導致的官僚體制形成了一個有其特殊利益的“管理階級”和“俸祿階層”。也就是說采用“列寧主義”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開始形成保守思想和官僚主義;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專業化、科層化和官僚理性秩序將社會主義的理想和目標無限延宕了——手段本身成了目的。因此毛澤東試圖打破這種經濟上高度集中的管理方法和政治上日漸僵化保守、沒有了革命理想和社會主義熱情的官僚主義體制。
在“社會主義高潮”和整風運動的背景下,1955—1957年出現了一些青年作家所寫的反對“保守思想”和官僚主義的作品。在1957年整風開始之前的所謂“鳴放”的第一階段,青年作家們主要批判的是“保守思想”,而“保守思想”實際上也就是官僚主義的代名詞,而且對這些“保守思想”的指責已經上升到“兩條路線斗爭”的高度。而在1957年整風開始之后的“鳴放”的第二階段,青年作家們反對的主要是“三害分子”(指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這一時期,由于受到國際環境和毛澤東整風時期批評官僚主義的講話的雙重影響,北京大學爆發了“5·19學生運動”[6]。
左翼青年作家對“保守思想”和官僚主義的批判顯示著建國后形成的官僚理性秩序與青年們要求“繼續革命”的沖突[7]——當然,這既與他們“真正的社會主義”要求相關,也與他們響應了毛澤東的號召相關。
以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為例。這篇小說被普遍忽略的背景就是,當時關于農村合作化速度的沖突之后整個社會所出現的反對“保守思想”/官僚主義、要求進入“社會主義高潮”的時代氛圍。而反對“保守思想”/官僚主義和要求參與“社會主義高潮”正是“繼續革命”的兩個維度。
“社會主義高潮”一語在小說中多次提到,其中一次很有代表性,即林震、趙慧文兩個青年人的談話:“兩個月前,北京進入社會主義高潮,工人、店員,還有資本家,放著鞭炮,打著鑼鼓到區委會報喜,工人、店員把入黨申請書直接送到組織部,大街上一天一變,整個區委會徹夜通明,吃飯的時候,宣傳部、財經部的同志滔滔不絕地講著社會主義高潮中的各種氣象;可我們組織部呢?工作改進很少!打電話催催發展數字,按年前的格式添幾條新例子寫寫總結……最近,大家在檢查保守思想,組織部也檢查。拖拖沓沓開了三次會,然后寫個材料完事。……哎,我說亂了,社會主義高潮中,每一聲鞭炮都刺激著我,當我復寫批準新黨員通知的時候,我的手激動得發抖,可是我們的工作就這樣依然故我地下去嗎?”不難看出,這篇小說的“繼續革命”訴求主要表現在對官僚主義、保守思想的批判上,后者的“冷淡”與整個社會樂觀昂揚的熱烈氣氛不協調。具有保守思想的官僚主義者不僅對“社會主義高潮”沒有熱情,而且還對青年人的熱切響應冷嘲熱諷,“有時,又覺得區委干部們的精神狀態是隨意而松懈的,他們在辦公時間聊天,看報紙,大膽地拿林震認為最嚴肅的題目開玩笑,例如,青年監督崗開展工作,韓常新半嘲笑地說:‘嚇,小青年們腦門子熱氣起來啦……林震參加的組織部一次部務會議也很有意思,討論市委布置的一個臨時任務,大家抽著煙,說著笑話,打著岔,開了兩個鐘頭,拖拖沓沓,沒有什么結果。”
而曾經是北大自治會主席的熱血青年劉世吾現在已經變得僵化保守,他已經“看透了”,某種程度上已經被官僚化的“組織”給異化了,他只有在新來的年輕人林震身上才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曾經的熱血、激情和不妥協的“戰斗精神”——這也是小說中劉世吾并非完全是一個負面人物的原因,他說:“那時候……我是多么熱情,多么年青啊!我真恨不得……”“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習慣了,疲倦了。解放以來從來沒睡過八小時覺。”他理解林震所做的一切,但是現實卻是“那又如何呢”。這篇小說無意識中顯露的不僅僅是青年人和官僚主義者的矛盾沖突,而且還有官僚組織的無處不在的異化力量。
這篇小說發表后受到毛澤東的關注。毛澤東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到這篇小說并為之辯護。毛澤東如此關注這篇小說的原因在于:首先,它是一個只有22歲的青年作家寫的,且文章的內容與毛澤東一貫相信青年人具有創造精神和較少保守思想的看法是一致的;其次,更為重要的是,這篇小說讓毛澤東看到了一種希望,小說中的年輕人盡管還不成熟,但是他有著拒絕保守僵化的“繼續革命”訴求。正是這篇小說在反官僚主義和反保守思想表層之下還有一個“繼續革命”的訴求和追求“真正社會主義”的沖動,才是毛澤東為這篇小說辯護的真正原因。
對于毛澤東來說,他看重的絕不僅是王蒙的小說提供了一個反官僚主義的標本,而是他對小說中林震那樣的青年人抱有更高的期待——期待要求“繼續革命”的青年能夠克服“一五”計劃的負面后果及日漸形成的官僚主義現狀。所以,雖然小說中的正面人物還沒有完全成熟,但總起來說,毛澤東還是很認可這個人物的。青年人林震有著永葆革命熱情的“繼續革命”訴求和比較高的無產階級覺悟,在他身上毛澤東看到了一個新的、潛在的“繼續革命”的主體(青年/學生),所以他“力挺”這篇小說,把否定這篇小說的李希凡和馬寒冰批評了一頓[8]。
毛澤東對這篇小說不滿意的一面,也不在于林震的“戰斗性”不強,而是他還沒找到一個“合作者”、一個能夠領導他“繼續革命”的領袖或者精神指導者去戰勝官僚主義。毛澤東最終繞開官僚集團直接面向青年人(包括青年學生)并號召青年人打爛這個體制,重組一個“繼續革命”(不忘記革命目標)的、有著“自我否定性的國家體制”(這當然造成了災難),因為“反右”和大躍進而延宕到了十年之后。可以說這篇小說標示青年毛澤東主義者的初步出現,他們與十年后的青年學生有著相同的精神氣質,只不過,這種精神的連續性因“反右”而暫時中斷。——左翼內部的自我否定是更激烈、更為有力的自我批判。
“文革”及其前夕的反官僚主義
1957年的反“三害”及隨后的“反右”聯系著“文化大革命”。“反右”加固了官僚化的統治,一種“政治終結”[9]的局面再次出現。毛澤東其后發動的進一步沖擊“按常規走路”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的大躍進又遭失敗;而大躍進之后,在毛澤東看來的“資本主義復辟”政策又使其將黨內的政策分歧上升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高度。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口號。這一方面有反官僚主義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政治終結”焦慮的內在必然。
1960年代初調整時期的政策,在毛澤東看來是“資產階級復辟”。實際上,毛澤東對之前中共八大的決議和社會主要矛盾的結論是不滿意的。他認為“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有那么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毛澤東認為階級斗爭不能“緩和”,因為“樹欲靜而風不止”,資產階級要“吹臺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說黨內的“整改”“也包含兩條路線的斗爭”,“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黨內存在這三個東西,這個賬要掛到資產階級身上”。[10]這樣,黨內的整風也就具有了階級斗爭的性質。
“反右”之后的毛澤東越來越向此前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左翼青年的主張靠攏——毋寧說他們本來就是一致的。事實上,當時的“反右”并沒有仔細區分那些真正反對社會主義的右翼言論和左翼內部的“繼續革命”訴求,因此,今天的“右派”一詞帶有一種本質主義的遮蔽性,它容易讓人產生“壓迫—反抗”和自由主義者受難的想象,盡管這也是事實,但當時的情況無疑要比這復雜得多。左翼知識青年反對官僚主義、要求“真正社會主義”和“繼續革命”的訴求卻成了他們反社會主義的證據,這不能不說荒誕之極;他們的“蒙難”不是因為自由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主張,恰恰是由于他們反對自由主義和堅持“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緣故。他們響應了毛澤東的號召,但是在“反右”之后卻被否定。實際上,他們的精神氣質和十年之后的青年學生非常接近,而十年之后,這些青年通過小說的形式又一次出現,盡管前者已經是否定和批判的對象,但是,從“百花時代”的左翼青年,從十年之后浩然小說中的年輕人再到“文革”中的青年學生,他們那種左翼革命內部的理想主義激情和“繼續革命”訴求卻是一脈相通的。
毛澤東在“文革”前夕號召“思想戰線”上的階級斗爭的時候,呼喚一種具有徹底的無產階級覺悟和不妥協精神的新人出現。然而實際上,在“百花時期”的整風——民主運動中這種新人已經出現了,只不過很快被“反右”運動給夭折了;“大躍進”時期這種新人又開始出現,最后終于在“文革”中成長起來。例如趙樹理的《“鍛煉鍛煉”》(1958)中出現了一個叫楊小四的年輕人,他是村合作社的副主任。小說中另一個重要人物社主任王聚海,是一個“和稀泥”的“和事佬”的形象,也就是毛澤東所謂的對階級矛盾“緩和”的“八大”式人物,他對“小腿疼”和“吃不飽”這樣的落后人物抱有同情的態度,還有他那種對年輕人要“鍛煉鍛煉”的官僚主義作風,引起了楊小四的不滿。這篇小說具有從“百花時代”的反對官僚主義/ “干預生活”的小說向浩然的鮮明階級斗爭(在中國“當代歷史”的語境中“階級斗爭”實際上是反對官僚主義的另一種形式)的小說過渡的性質。王聚海對落后人物的“寬容”,馬上就會被指責為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他是馬之悅等人物的雛形。而楊小四這個對資產階級思想不妥協的年輕人,富有理想,有能力,沒有中年干部的思想負累,他如梁生寶一樣,是曼海姆所說的那個離開了村莊又回來的年輕人(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的青年主人公都是回村的復員軍人),他可以從更高的社會主義和革命理想的角度打量這個村莊。楊小四是潛在的蕭長春、高大泉,他與王聚海的矛盾已經出現,只不過此時還沒有發展到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的程度。——趙樹理的本意可能并不是如此,但這篇小說顯示的那種政治無意識卻具有一種歷史中間物的性質。事實上,這是當時小說中的一個普遍現象,這在其后出現的工業題材反映兩條路線斗爭的小說中得到充分表現。這些小說的矛盾主要集中在黨委書記和廠長之間,前者主要依靠工人們的社會主義熱情和精神力量,后者被表現為僵化保守,不相信工人們的創造性,只依靠“規章制度”且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官僚主義者[11]。可以看出,這仍然是“百花時期”左翼青年的“繼續革命”和官僚主義、“保守思想”沖突的延續[12]。
分析《艷陽天》[13]中的蕭長春和“百花時期”左翼青年的歷史聯系是有意味的。“1957年麥收之際”——這是《艷陽天》中的“故事”發生的時間,這也是當年左翼青年作家反“三害”和北京大學學生運動發生的時間——的蕭長春們與左翼青年作家筆下的人物或北大學生運動中的譚天榮驚人地相似。焦淑紅對鄉長李世丹偏袒馬之悅的行為質問道:“上級怎么樣?上級不辦正確的事就行嗎?”“他(指蕭長春——筆者注)當了九個月支部書記,他領著大伙兒跟天斗,跟地斗,跟投機分子斗,跟地主富農斗,也跟那些要走資本主義的富裕中農斗過;現在還給他拉開一個新的陣勢,還要跟一個錯誤的上級斗……(李世丹)心里沒有群眾,現在又發展到給敵人加油,給群眾潑冷水。這是原則問題,路線問題,李世丹損害了黨的利益;在一個黨員來說,沒有比黨的利益更高的利益了,應當豁出個人的東西,堅決保衛它;如果在這樣的問題上讓步,那就是最大的罪過!”李世丹要求釋放馬小辮他們,結果遭到“群眾們”的反對。
這里要稍微說到1957年整風時期(也就是“1957年麥收之際”)北大學生運動中的代表人物譚天榮。當年要求“繼續革命”的譚天榮在1957年對待“三害”也是如此地堅決,他聲稱“活著,就得戰斗”——向“三害分子”戰斗[14],他的革命覺悟和戰斗激情一點不比蕭長春和他的“同志們和戰友們”差。李世丹對“群眾”“造反”的指責恰如當年《人民日報》“這是為什么”的質問,當時譚天榮對《人民日報》的轉向批評道:“人民日報組織的十字軍,充分表現了沒落階級的情緒”,“紅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劍;這是最后一場戰斗!讓真正的勇士們前進吧”[15]。像“1957年麥收之際”的蕭長春把黨內分為走社會主義和走資本主義的兩類一樣,譚天榮等左翼革命青年也是把黨分為“進步勢力”和“保守勢力”兩類——他們的批判對象其實是一樣的[16]。如果說譚天榮(后來被劃為“右派”)對當時的中國現實作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批判,我們就不能說《艷陽天》沒有這種批判——實際上越是類似《艷陽天》這樣被稱為“頌歌”的作品反而越是最有現實批判性,它的受歡迎不僅僅是因為它符合了當時的政策和有“農村生活氣息”,更重要的還有它對現實最激烈的革命批判——那種“現實”肯定不僅僅是憑空“虛構”出來的——這些作品典型地反映了那個時代“自我否定性的國家體制”所具有的特征,它來自于左翼革命內部的自我否定和批判;事實上,這些作品與“林震”們以及北大整風時期青年學生的批評是殊途同歸的。
因此,浩然的小說也可被反向稱之為“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因為“批判”與“肯定”實在是只隔一層紙。浩然這種用“大民主”對待黨內官員的方式正是“百花時期”的青年學生所希望的“狂風驟雨”的整風方式。不過差別在于,浩然小說中的李世丹是一個“右派”(他是一個事后的“右派”,這是小說的暗示)的形象,這樣小說才有敘述的合法性,不過悖論或裂隙也就此產生:這個“右派”也正是當年激進的青年學生所批判的“保守勢力”和“三害分子”[17]。整風轉向之后,正是“李世丹”們清算了那些左翼青年作家和激進的青年學生,并把他們的“造反”、反對官僚主義、要求“繼續革命”和“真正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為定為“右派”的證據,如今浩然的小說把這種“被顛倒的歷史又顛倒了過來”,這不能不讓人驚異:當年左翼青年作家筆下的“林震”們以及現實中的譚天榮不是又“殺”回來了嗎?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于,同一個時期的革命青年“蕭長春”和譚天榮卻是截然相反的命運——這不僅僅是權力移位的結果,而且是1957年那場運動的必然后果。
余論
1955—1957年“百花時期”那些被稱為“干預生活”的反官僚主義作品和1960年代以后那些反映兩條路線“階級斗爭”(內含著反官僚主義傾向)的小說,在“文革”結束之后的新時期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在所謂“撥亂反正”的政策下,前者被當作應該返回的“正”得到肯定,后者作為應該清除的“亂”被完全否定[18],而否定它們的理由卻經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文革”剛一結束時,對“文革”及“文革文藝”(如浩然的小說等)的定性為“極右”,當時似乎還要堅持“文革”“繼續革命”的理念,因此只有將對立面定為“極右”才有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但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這一定性就被否定,“文革”及其文藝被定為“極左”。
當時對“百花時期”那些“干預生活”小說的肯定是基于它們的“反官僚主義”主題,但是當時一些評論者立刻注意到“反官僚主義”的“極左”性質,因為在他們看來,“反官僚主義”是和“文革”緊密聯系著的,這些評論者認為“文革”正是建立在“反官僚主義”的敘述之上的[19]。這種看法雖然在當時被認為是“左的”,但是它從左翼革命的內在邏輯出發作出的觀察,實際上是正確地看到了“當代歷史”的連續性,因為那兩個時期在“反官僚主義”以“繼續革命”的訴求上是一脈相通的。
這就意味著“百花時期”的那些作品作為“重放的鮮花”必然會經歷一次改寫,以合于當時對穩定政治秩序的要求。吳舒潔注意到,《重放的鮮花》的出版并不意味著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終結,相反,它恰恰是要以“反官僚主義”來批判前三十年“極左”思想并以此干預現實政治。然而更重要的是,作者注意到了《重放的鮮花》所謂的“官僚主義”是對“百花時期”的“官僚主義”的重寫。它將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以“群眾路線”和“大民主”(“階級斗爭”)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方式,做了一次意識形態的置換,即變為依靠“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來尋求“安定團結”的“秩序”的方式;一句話,新時期初期所謂的“反官僚主義”通過將官僚主義算在“封建主義”頭上的方式,實際上內含了重建“官僚理性”(包括技術理性)的意識形態訴求。在這一置換中,不僅文學轉換了新的功能,而且整個社會也開始了“去政治化”的過程[20]。
也就是說,從1955—1957年“百花時期”、1960年代之后的“文革”到“撥亂反正”的新時期,“反官僚主義”流變的歷史也就是“當代中國”在其“自我否定性”中延續、改寫和重建的歷史。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
[1]毛澤東說:“在中國,對于許多人來說,1955年,可以說是破除迷信的一年。1955的上半年,許多人對于一些事還是那樣堅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們就堅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參見毛澤東:《<所謂一切鄉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493—494頁。
[2]這些作品總起來說還是符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要求的,因為它們在批判現實的同時還有一個鮮明的、要求“繼續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指向,這與當時那些所謂“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對現實的僅僅批判是不同的。因此,我們應該對那些后來被稱為“毒草”的作品作具體分析,因為它們的訴求是不同的。
[3]唐摯:《必須干預生活》,《人民文學》,1956年第2期。
[4]毛澤東:《<機會主義的邪氣垮下去,社會主義的正氣升上來>一文按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522—523頁。
[5]毛澤東:《<中山縣新平鄉第九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青年突擊隊>一文按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頁。
[6]事實上,要求“繼續革命”和追求“真正社會主義”是“百花時代”左翼青年的普遍訴求。1957年5月北京大學青年學生發動了“5·19學生運動”,學生們的言論及貼出的大字報,雖然主張、意見不盡相同,但其中一個主要的訴求就是反對官僚主義和“繼續革命”。關于這次運動的經過和當時青年學生們的具體言論,可以參看北京大學思想教育委員會編《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反動言論匯集》(內部參考,1957)及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印《校內外右派言論匯集》(內部參考,1957);另外,對“百花時代”左翼青年作家要求“繼續革命”的反官僚主義作品和“鳴放”后北大學生運動的經過、訴求等的詳盡分析,可參看筆者的論文:《“百花時代”左翼青年的反官僚主義話語(1955—57)》,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7]韋伯在其《以政治為業》的著名演講中預言了社會主義革命之后不可避免的官僚化命運,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只能是“行政管理專政”(dictatorship of administration):“情緒高昂的革命精神過后,隨之而來的便是因襲成規的日常瑣務,從事圣戰的領袖,甚至信仰本身,都會銷聲匿跡,或者,更具實效的是,變成政治市儈和實用型專家常用行話的一部分。在為信仰而從事的斗爭中,這一發展尤其迅速,因為領導或發動這種斗爭的,通常都是真正的領袖,即革命的先知。情況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在這里,就像領袖的每一架機器一樣,獲勝的條件之一,就是將一切都空洞化和事務化,簡言之,為了‘紀律的緣故,變成精神上的無產者。信仰斗士的追隨者,取得了權力之后,通常很容易墮落為一個十分平常的俸祿階層。”參見韋伯《以政治為業》,《學術與政治》,三聯書店,2007年,第113—114頁。
[8]“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使人讀不下去,文章的頭半截使人讀不懂。”毛澤東替王蒙“解圍”:“最近北京發生了一個‘世界大戰,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滅他。總而言之,講不得,違犯了軍法,軍法從事。我也是過甚其詞,就是那么幾個人,寫了那么幾篇文章。現在我們替王蒙解圍,要把這個人救出來,此人雖有缺點,但他講正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官僚主義。”參見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萬歲》,出版者不詳,1967年,第114—115、175頁。
[9]韓毓海在《革命中國的興起及其話語紛爭》一文中提出這一概念。他還認為,“政治的終結”造成了一個類似于資產階級的中間管理階級:“現代社會的高度集中化,有可能使社會統治權力,既沒有集中在無產階級,也沒有集中在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手里,而是集中在‘現代官僚階級手中”,“正是由于現代社會的這種發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建立在所有制方面的對抗,變得不那么清楚了——‘集中化的后果是,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沒有受到無產階級或者資產階級支配,而是被‘經營和管理社會生產的‘官僚所支配。”參見韓毓海編著:《20世紀的中國 學術與社會》,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1頁。
[10]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繁體豎排版,1977年,第509—510、506頁。
[11]實際上,在中國“當代歷史”的語境中,所謂“階級斗爭”從來不是或很少是“無產階級”同建國之后那些拿“定息”的真正“資產階級”(也包括民主黨派)的斗爭,而主要是指黨內的路線之爭及堅持社會主義理想的革命者同官僚主義的斗爭。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提到了如何徹底消除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僚體制”以及最終消滅國家的問題。但是消除官僚制和消滅國家只是最后的目標,在“社會主義階段”,“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參見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88頁)。因此,盡管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中國大陸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但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形式還是存在的;而且,雖然沒有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但卻形成了官僚理性和技術理性的統治(韋伯所謂“行政管理專政”)。因此,中國“當代歷史”中的“階級斗爭”盡管外在的口號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但是其主要表現形式卻是黨內的路線斗爭、“政治理論辯論”以及“繼續革命”與“政治終結”的沖突。
[12]有評論者分析這些工業題材的小說,認為其寫作模式可概括為“‘激情與‘理性的爭斗”。參見徐剛:《“激情”與“理性”的爭斗——1950—1970年代工業題材文學及其文化政治》,《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第5期。
[13]這里要分析的是《艷陽天》(第三卷),本文用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的初版本。
[14]譚天榮:《致朱志英同學》,《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反動言論匯集》(內部參考),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委員會編印,1957年,第50頁。
[15]《這是為了反對三害》,此文是譚天榮對《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么?》的回答,見《校內外右派言論匯集》(內部參考),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印,1957年。
[16]有論者也發現了《艷陽天》和之前相同題材小說的連續性:“這部作品從整體來看,與建國初期表現農村合作化題材的小說有千絲萬縷的瓜葛。這首先是一種思想哲學觀念上的聯系,使前后作品都有讓階級斗爭情節賴以確立的基礎。”——之所以有這種“思想哲學觀念上的聯系”是因為它們面臨著相同的、貫穿“當代歷史”始終的“政治終結”與“繼續革命”的沖突——這種沖突在“當代歷史”的非常語境中表現為“階級斗爭”的形式。參見董之林:《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46頁。
[17]從林希翎當時的思想狀況可以發現當時激進的青年學生對“保守勢力”和“三害分子”的“痛恨”,他們與“同一時期”(“1957年麥收之際”)的“蕭長春”一樣嫉惡如仇。林希翎說“反官僚主義人人有責”:“在青年報上有文章說小資產階級看問題有偏見,會發生匈牙利事件,害怕小資產階級片面地反對官僚主義。我看只要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都有偏見。主席沒有偏見還革不了命,赫魯曉夫的報告沒有偏見嗎?工人罷工沒有偏見嗎?工人最有偏見。工人對不合理的事情非常不滿。我國五億多小資產階級,五億人不反對官僚主義,什么人反對官僚主義呢?五億小資產階級總比官僚主義好得多吧,五億人總是寶貴的,除開五億,剩下一億,這一億中真正的產業工人沒有許多,工人和小資產階級有許多聯系,這樣歸根到底只剩下了領導者。這個論調等于不讓大家反官僚主義,我說:反官僚主義人人有責,甚至是反動的人。”(《我的思考》,見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 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唯一的不同是,蕭長春的“階級斗爭”和反對官僚主義已經沒有了受“小資產階級偏見”指責的擔憂。
[18]董之林注意到新時期小說那種要和“錯誤的時代劃清界限”以開辟一個文學“新紀元”的努力,但是其創作仍與“十七年”和樣板戲有著眾多聯系。參見董之林:《亦新亦舊的“新時期”小說》,《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70—271頁。
[19]王若望:《反官僚主義和“干預生活”》,《社會科學》,1980年第6期。
[20]參看吳舒潔:《〈重放的鮮花〉與撥亂反正》,《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