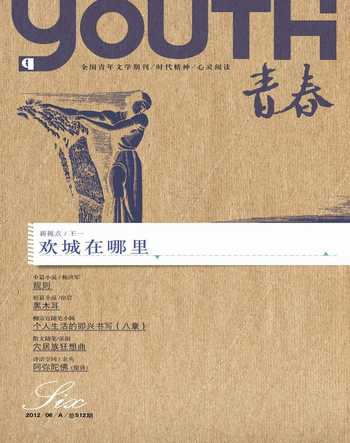無物之陣
朱芷萱
一
“跑!”
威子大喊一聲,手上足了勁,將籃球一個長拋扔過了學校的墻頭。眾人醒了過來,撒開腳丫四散而逃。快步奔來的教導主任臉上能刷下一層冰,連喝站住!站住!
威子回身要拿掛在球架上的校服,不料被教導主任搶先一步,撈在手里。威子急紅了眼,伸手就要去奪。教導主任瞪眼喝道,“你哪個班的!”威子的膽子到底包不住天,立時失了氣焰,手觸到衣服上就頓住了。
吳震本已跑出兩步,回頭見威子被抓,腳下一慢,也被教務主任一把攥住手腕。
“知不知道晚飯時間不許打球?學校三令五申,嗯——?!”教務主任抬頭睨著兩人,“你們是哪個班的?”
海風和夜色一樣漸漸濃重起來,吳震腦袋里像瞬間被搬空了一樣,白茫茫的空蕩,知道這次是逃不過去了,只得機械性地張嘴報了班級。
高三了還打球!教導主任慢慢將字吐出來,吳震沒敢看他表情,只聽出了四個字——罪加一等,遂又想起上上周和人打架鬧出來的風波,心想這回真得“二進宮”了。
吳震和威子被教導主任領著去見他們班主任。教導主任個子不足一米五,兩人高馬大的高三男生走在他后面,可以清晰地看見他頭頂發黃的發旋。晚自習的鈴還沒響,三人一路走來,受了不少學生小心翼翼的指戳。吳震無來由覺得這場景特滑稽,單看身高,就像一個小孩領著兩個大人在游街,搞得他直想轉身逃跑。但終究沒鼓起這個膽,小個子手里拎的外套就像條無形的狗鏈,扣住倆人脖子,牽著他們往人多處走。
海風刮得肆意,威子沒穿外套,一身熱汗被吹得透涼,梗著脖子連打了好幾個噴嚏,直到進了老師辦公室才緩過來,吳震有點想笑,又有點可憐他。這時候辦公室里只留了幾個晚自習值班的老師,開著筆記本電腦等著收菜,看教導主任領著兩個學生進來,都各自瞄來一眼,“喲,這是怎么了?”“打球的,被我抓住了。”教導主任鼻子里哼出道氣,將他倆交給他們班主任,又是一頓好訓。特別是吳震,在他們班主任眼里就是恨不得天天上房揭瓦的主,整一慣犯,更是被恨鐵不成鋼地特別“關照”了一番。
倆人被批了一會,坐在旁邊的教導主任擺出張紙,拍下筆。
“跟你們打球,剛才跑掉的還有誰?寫下來。”
吳震沒動,威子也沒動,垂著頭釘在地上。
“怎么不寫?跟誰一塊打球的都不記得了?”
靜了會,吳震咬著字尾,憋出了幾個字,“……不認識。”
“說什么?大聲點。”
“不認識。”
“不認識能一起打球?別以為你不說我就查不出來。”教務主任一拍桌,把頭扭向威子,“——你來說!”
威子無聲無息地站在一邊,半個字也沒有,像是突然失聰又失聲了一般。
二
問不出來也不能干耗著,兩人被罰了一會站就被放了出來,威子也拿回了他的外套。從老師辦公室出來,晚自習已經開始了,教學樓內燈火通明而又靜悄悄的。吳震這才感到身上的汗早就蒸發光了,背脊留下一層油膩,白霜似的涼,直往脊梁骨里滲。
“哎,你看他們能查得出來嗎?”走廊上威子問。
“只要他們沒腦子抽風自己站出來,沒咱倆的指認,附近也沒攝像頭,他們就抓不到證據。”
吳震知道這件事還沒完,后勁大著呢,而他和威子身上,正擔著數個兄弟的安危!想到這,一股責任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真真有了幾分義氣悲壯的勁,這種情緒甚至蓋過對自身倒霉的憂慮。吳震莫名想到《甲方乙方》里那出逼供戲,管他辣椒水老虎凳,還是軟硬兼施美人計,吳震知道自己只有那六個字,“打死我也不說!”
吳震他們走進教室,好幾個人偷偷抬頭瞅了兩人一眼,都是剛剛幸免于難的。吳震裝作沒看見他們探尋的目光,關門時卻故意弄出些響動,衣袂生風地從秦煙身邊走過,卷起了她的書頁。約莫十分鐘后,高跟鞋噔噔輕響,吳震在位置上沒抬頭也知道是班主任進來了,于是憋住了呼吸做英語完形填空。高跟鞋在教室里轉了一圈,帶著一個人出去了,吳震這才敢抬頭,與威子交換了警覺的眼神。教室里只有一個位置空了,是主席的。
班上的任何一個男生,吳震總有幾分識人的把握,唯獨對主席,吳震心里沒底。主席自然不是姓主,名席,而是貨真價實的官職名。主席不止現在是學生會主席,初中的時候也是學生會主席,小學沒這官職,吳震猜想就憑主席那氣度,最起碼也得混個少先隊大隊長。這樣一個人,自然不會和吳震威子他們一起頂風作案打籃球,不過都是一個班里進進出出,主席的同桌又是參與人之一,這辛德勒的名單,主席就算不知道個十成十,十之八九總是跑不了。
主席會不會說?吳震盯著窗外鴉翼色的海岸線胡思亂想,想到最壞的可能,只覺得自己剛剛在老師辦公室扯謊的樣子如跳梁小丑,平白給了教導主任他們事后談笑的對象。
主席去了沒多久就回來了,班主任也沒再出現。
磨到第一節晚自習下課,主席卻自己背著手,踱到吳震桌子邊了。吳震看著主席臉上一貫笑瞇瞇的親切樣,就想起威子早先說的話:看見他就想蹦起來立正稍息大喊三聲“首長好!”
“小吳啊。”主席將手掌輕輕放在桌上,“你猜班主任剛剛叫我去,問什么了?”
“問什么了?”吳震只能接口。
主席卻沒回答,眼中透出幾分神秘的調侃,轉了話頭,“我知道你們打球去了。”
“……你說了嗎?”
“沒說,我說我也不清楚。”
吳震感到欣慰,主席到底還是個正常的學生,是站在他們這邊的。
喧囂的教室中,吳震感覺到秦煙的目光有一瞬間落在他倆身上。那道目光竟是淺藍色的,輕輕的,薄薄的,待到吳震再要去捕捉時,它已經如煙一般裊裊地滲入空氣。
三
班主任給吳震他媽打了電話,將他兒子新犯的事通報了遍。吳震晚自習一回來就被他媽堵在客廳,劈頭蓋臉罵得抬不起頭來,好不容易趁著他媽接電話的空,跑到別墅三樓廁所呆著。安穩了沒多會,吳震他媽把廁所門敲得砰砰響。
“怎么還不出來?”
“我拉屎你都要數時間!”
“你說你還像高三學生?天天就知道玩!知不知道學校不讓打球?”
“知道。”
“知道你還打!我問你,和你一塊打球的還有誰?”
“很多人。”吳震輕描淡寫地說。
“怎么就逮了你們倆個,其他人呢?”
“跑了。”
“你傻啊!你怎么沒跑?”
吳震有點煩躁,“沒跑掉!”
“怎么跟媽媽說話呢!”
吳震他媽隔著門板數落吳震,吳震摸出手機,給秦煙發了條短信,然后開始玩游戲,只當沒聽見。他媽媽念叨著上輩子造了什么孽,給在外出差的孩子他爸打電話,讓他找學校領導解決這事。吳震在廁所里聽得清楚,感覺怪窩囊的。白燦燦的燈光射在白燦燦的瓷磚上,以各種角度反射到吳震身上,將他整個人也聚焦得白燦燦發燙。頭昏腦脹間,吳震反而有了幾分釋然。
第二天周六傍晚,一起打球的朋友聚在學校后邊的海灘吃燒烤。威子被他父母輪番“文武”教訓,關了一整天,眉眼都耷拉著。威子他爸當年是船老大,日日在海上漂著捕魚,眾哥們便開玩笑說他爸是做海盜的,威子大罵胡扯。夜幕降臨,那池被人工建筑包圍的海水隱去了細節。目力所及的只留白色的沙灘擁著一圈墨色,映著點點橙黃的燈火,靜謐而柔和,頗為楚楚動人。朋友們笑鬧一陣,威子的神情也逐漸輕松起來,突然想起昨天被自己扔過墻的籃球。那籃球是吳震的。
吳震一愣,“這都一天了,估計早不在了。沒事,也不值什么錢。
威子仍是過意不去,站起身便去找。眾人都知道威子倔,向來不聽人勸,喊了幾聲,便作罷了,由著他漸漸走遠。
一幫人便又自顧自笑鬧,似乎沒過多久威子便回來了,兩手空空,說太黑了,沒找到,非要賠吳震一個。吳震覺得麻煩,朋友們也覺得威子麻煩,七嘴八舌,遂不了了之。他們一邊吃烤得香辣的烤魷魚,一邊聊起秦煙,聊起吳震送給她的價值十個籃球的錢包。他們對教導主任家考了三年才勉強混了個二本的女兒大肆嘲笑,后來又說到主席,都認為雖然主席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歡當官,但人還是靠譜的。吳震對眾人說,這次大家算是欠了主席次人情,下次得找時間好好請他一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