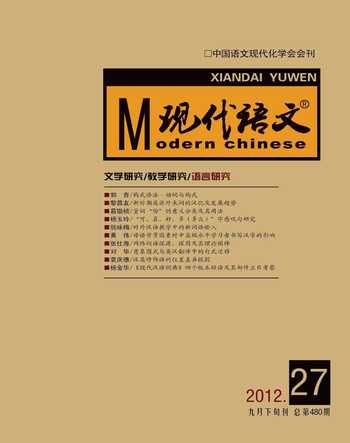漢字起源年代的字測定方法
鄭曉行 曹杰旺
摘 要:阿里內提出的“詞匯自測定方法”值得借鑒,它可以用于建構“漢字起源年代的字測定方法”,彌補國內漢字起源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更客觀地測定漢字起源年代,形成更科學的漢字觀:漢字由其使用者共同創造,歷史相當久遠,伴隨著我國人類進化的整個進程;它不是漢語的附庸,而與漢語同時起源,同步發展,并在漸進發展過程中保持很高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在這種漢字觀觀照下的“漢字起源年代的字測定方法”在理論上是可能的。
關鍵詞:詞匯自測定方法漢字起源字測定方法
當代國內學者主要運用考古文物資料來測定漢字的起源年代,由此得出的結論因“對資料的不同定性及漢字起源在階段上的不同認識而有所不同”[1](P239),有“三千多年說”[2](P16)、“四千—五千年說”[3](P55~58)、“六千多年說”[4]、“七千—八千年說”[5]、“八千多年說”[6]、“九千多年說”[7]、“盤庚遷殷至武丁時期說”[8](P74)。隨著新的考古發現,未來還有可能出現更多關于漢字起源年代的說法,因此,筆者認為,僅僅依靠考古學的方法只能把年代一步一步向前推移,無法科學地測定漢字的起源年代,不可避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意大利著名語言學家阿里內(Alinei,Mario)提出了“詞匯自測定方法”[9~12](lexical self—dating)來測定印歐語言分化的具體年代。這種方法用于建構測定漢字起源年代的新方法,彌補了我國漢字起源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因此,筆者試圖提出基于漢字自身來測定漢字起源年代的方法,稱作“漢字起源年代的字測定方法”。本文討論該方法的理論背景與基本觀點,論證其理論可能性。
一、理論背景
20世紀90年代,阿里內等人根據“烏拉爾連續理論”[14](P3~14)(The Uralic Continuity Theory)提出了“印歐語言研究的舊石器連續范式”[11]、[13](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 for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以下簡稱PCP)。他們認為,語言的歷史要比傳統理論界定的幾千年久遠得多,按照托拜厄斯(Tobias,P.V.)的觀點,語言的歷史至少要追溯到距今250萬~100萬年的“能人時代”之前[15](P87~94)。與語言一樣,詞匯的歷史也相當久遠,應該按照人類進化的整個進程對所有語系及其語言的詞匯發展進行歷史分期(lexical periodization)[13]、[16](P132)。
為測定印歐語言起源及分化的時間,阿里內在指出其它語言年代測定方法——如最早文字記錄測定法、語音嬗變測定法、詞源測定法、斯瓦迪士[17~18](Swadesh,M.)的語言年代學方法(glottochronology or lexicostatistics)的各自特點及不足的基礎上提出了“詞匯自測定方法”[9~12]。作為文化與語言系統之間的接口(interface),詞匯記錄著言語社團無數次文化歷史變革的軌跡,是言語社團歷史的全景體現,詞匯的歷史對研究言語社團的歷史與文化發展有相當大的價值,透過詞匯這面鏡子可以看清語言發展的整個歷史。具體說來,一個詞就如同一個考古現場,它揭示的不是某個單一時期的歷史,而是像考古層位一樣揭示了多個時期的歷史,測定一個詞產生的年代與考古一樣,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每個歷史時期都有相應的層位與之對應。只要詞所反映的歷史文化事件本身發生的年代可以確定,詞產生的年代就可以測定。根據詞的不同性質,詞匯自測定方法區分了“歷史可測定指稱對象”(historically traceable referents)和“歷史不可測定指稱對象”(historically untraceable referents)。人類勞動的所有產物和絕大多數社會產物都產生于特定的時間,指稱這些對象的詞的產生年代一般是可測定的,而那些用于指稱自然產物、先于人類存在的事物、情感和抽象概念的詞的產生年代一般很難測定,甚至不可測定。
二、漢字起源年代的字測定方法的基本觀點
(一)漢字的歷史相當久遠
阿里內等人提出的PCP推翻了吉布塔(Gimbutas,M.)的“黑海——里海起源說”[19](P155~198)和倫夫魯(Renfrew,C.)的“小亞細亞起源說”[20],認為印歐語言的分化時間不是紅銅時代也不是新石器時代。印歐語言從原始印歐共同語分化成各種非標準變體或方言的過程極為漫長,到冰河時代結束時(距今約1.2萬年),原始印歐語已經分化為原始凱爾特語、原始意大利語、原始日耳曼語、原始斯拉夫語、原始波羅的語。自舊石器時代以來,這些語言的使用者就一直生活在歐洲[13] 、[16](P135)。
筆者認為,與印歐語系諸語言一樣,漢語的歷史也相當久遠,可能在我國人類“還是動物的時候,就有了語言”[21](P2)。許多國內學者也持有類似的觀點,如孫常敘認為:“現代漢語,這一民族的共同語言,是在形成民族之前的部族和部落中就已胚胎,孕育,逐漸滋長壯大了的”[22](P170)。劉民鋼認為:“原始中國語的誕生已經具有漫長的歷史,根據人類誕生發展的時代推算,它不可能早于450~500萬年,依據現代漢藏語系諸語言的可比較性和古人類及舊石器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遲于180萬年。”[23](P111)
“文字的起源問題與語言的起源問題難以分開”[24](P39),作為漢語的一種重要模態(modal)(“語言的多模態性”,漢字的歷史也相當久遠,不僅僅因為目前所見最早用漢字記下的文字資料距今已有3000多年,更重要的是,“早在商代以前,中國漢字已經經歷了一段相當長的發展過程”[29](P3)。裘錫奎認為:“文字的產生,本是很自然的。幾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有很好的繪畫,這些大抵是動物跟人像,這是文字的前驅”[30](P55);“凡是象形字,雖則都是原始字,可是它們的發生時代不會一樣,兕和象的圖畫,也許兩萬年以前就有了。”[30](P77)可以看出,他對文字產生年代的推定遠遠超出了趙誠[7]界定的九千多年。誠然,相對于個人而言,九千年相當久遠,但相較于漫長的人類發展史,九千年只不過是極其短暫的一瞬而已,把漢字起源時間或者“漢字系統成型”[8](P68~83)時間限定在這短短的一瞬間都是不科學的,這些觀點不僅低估了史前人類的語言能力,還小視了他們的認知能力和思維能力。
(二)應該按照我國人類進化的整個進程來考察漢字的歷史
阿里內認為,應該按照人類進化的整個過程對所有語系及其語言的詞匯發展進行歷史分期。[16](P132)黃亞平認為:“對漢字起源、形成問題的討論一定要有人類學眼光,僅用純文字學的理論是不夠的。”[31](P23)根據吳新智提出的“連續進化附帶雜交”假說——“自舊石器時代以來,我國人類進化發展模式的主流是連續進化,附帶有少量與境外人群的雜交。”[32](P276~282)筆者認為,漢字在我國人類進化的過程中是連續發展的,要弄清漢字起源年代問題,就必須按照我國人類進化的整個進程來考察漢字的歷史,而不應該把漢字看成是某個時間突然產生的事物,也不應該把漢字看成是由漢民族獨立創造的,更不能把新發現的考古資料的年代直接認定為漢字的起源年代。
(三)漢字與漢語不是附庸關系,二者同時起源,同步發展
亞里士多德的文字觀——“文字是口語的符號”[33](P55)對西方學術界影響至深,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也沒能逃脫,以致于在討論語言與文字的關系時仍然認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成的。[34](P47)但索緒爾可能意識到漢字與印歐語言的文字之間的差異而對亞氏文字觀的普適性產生了懷疑,他對人類的文字體系進行了二重區分:表意體系和表音體系,對中國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34](P55)鑒于兩種文字體系之間的巨大差異,索緒爾明確指出,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體系。而“許多漢字研究者忽略了索緒爾的二重區分,將索緒爾對歐洲文字性質的判斷,視為人類文字的共同屬性,并用以指導漢字改革的理論實踐”。[35](P414)因此,國內學者一般認為:“文字是歷史的產物,是人類進入文明時期后才產生的,文字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是輔助語言的交際工具。”[29](P25)
讓·雅克·盧梭也說過,文字的最初形式并不描繪語音,而是要么像墨西哥人那樣直接描繪對象自身,要么像古埃及人那樣以象形的方法來描繪對象[36](P25~26)。陳望道認為:“假若追溯源頭,文字實與語言相并,別出一源,絕非文字本來就是語言底記號。”[37](P74)哈里斯(Harris,R.)指出,文字并不只是為了記錄口語,文字與口語是兩種平行的符號系統,文字遠比語音更有權勢[38](P35)。筆者認為,就個體發生(ontogeny)而言,漢語與漢字可能有先后之說,而就系統發生(phylogeny)而言,二者應該同時出現于群體的社會活動之中;漢字與漢語并非同出一源,認為漢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記錄漢語是不科學的,有盲目跟風之嫌,持此觀點者沒有真正弄懂索緒爾的理論,也沒有真正認識漢字的個性特點,有削足適履之嫌;更不能認為漢字產生的基礎是漢語,漢字的產生基礎是漢字使用者所處生存環境的特征及他們在與所處生存環境的交互過程中形成的對自身和所處生存環境及其相互關系的認知。申小龍認為:“漢字的象形象聲象意之構造是社會大眾約定俗成的結果,它真實而又客觀地反映當時代全社會的認知水平和認知成果。”[35](P430)
漢字與漢語之間不是附庸關系,它存在的理由不是為了表現漢語,它也絕非用于記錄漢語的符號,二者作為一個硬幣的不同側面,應該同時起源,同步發展。
(四)漢字形成的歷史是漸進的,不是突變的
阿里內認為,受神創論和進化論的影響,19世紀的西方學術界形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突變論(Catastrophism)者”和“均變論(Uniformitariamism)者”,就語言而言,語言的發展變化是漸進的,而非突變的[16](P122~126)。孫常敘認為:“語言的發展是逐漸的,不是爆發的。漢語從氏族語言、部落語言、部族語言轉變成民族語言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不是消滅舊的語言另創新的語言,而是經過長期的逐漸發展,通過舊質要素的逐漸消亡,新質要素的逐漸積累,使語言逐漸豐富發展起來的。”[22](P170~175)筆者認為,與漢語一樣,漢字形成的歷史也是漸進的,不是突變的,它是我國人民在社會活動中隨著社會及自身的發展逐漸形成的,而不是在某個時刻某個地點由某個人突發奇想單獨創造出來的,也不是“圣王”或“巫師”[31](P24)的專利。正如唐蘭所言:“所謂倉頡作書及文字起源于結繩或八卦的傳說都是不可靠的,最初的文字絕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眾人的創造。”[3](P12)
漢字形成的過程與人類認知世界的過程一致。人類不可能在某個時間和空間一次性認知所有的事物或某個事物的所有特征。人類認知世界的過程是一個漸進而漫長的過程,時至今日,人類仍然處在認知世界的漫漫征途中,而作為我國人類表征其認知的世界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漢字的形成過程也自然是漸進而漫長的。
(五)漢字形態具有穩定性
阿里內認為,保持穩定是語言發展的規律,變化是例外。[13]、[16](126~128)漢字形態也是這樣。“穩定是漢字發展傳承的基礎”,“在漢字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字形的穩定和統一是一條主線”,“漢字是一個在多因素制約下形成的相對平衡穩定而又不斷發展的系統。”[39](P74)有人比較現代《新華字典》和漢代的《說文解字》兩部字書,發現其中有50%左右的字匯的形體和字義完全相同,這些均是漢語基本詞匯。[40](P35)另據研究[41](P143),從《玉篇》《干祿字書》《五經文字》《新加九經字樣》《龍龕手鑒》到《復古編》,再到現代漢字,楷體漢字字形結構表現出高度的傳承性和穩定性:六部字書中出現的字,形體與3500個現代漢語常用字的規范字形全同者共2185字,占3500字的62.43%。筆者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文字改革之前,古今漢字形態與意義吻合度應該更高。
從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漢字的形態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但漢字形態的穩定性并不意味著漢字形態自古至今始終保持固定不變,而是在保持字形穩定和統一的基礎上的“動態平衡”[39](P74)。實際上,漢字在歷史上經歷了很多次改革,如秦始皇的“書同文”、唐代的“辯證文字”、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文字改革”等等,但這些文字改革并不是以一種文字替代另一種文字,并沒有導致漢字形態發生根本性變化,而是“萬變不離其宗”,或者說“形變而神不變”,在保持漢字基本形態的基礎上進行的調整,這些調整使得漢字形態更加規范,更有利于人們交際的需要和社會的發展。
(六)漢字起源年代可以自測定
以往關于漢字起源年代的研究要么運用考古資料,要么“運用傳統文獻流傳的漢字起源的說法”[1](P238),這些方法無法客觀而科學地確定漢字起源的具體年代。作為“漢民族思維和交際最重要的書寫符號系統”[35](P424),它包羅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映射社會文化的每一個細節,展示社會文化的多維層面,是一座恢弘的歷史博物館,不僅是歷史文獻記載的工具,而且它本身為我們提供了早于歷史文獻的遠古歷史文化信息。[35](P430)雖然無法找到最早的漢字記錄,但作為歷史的“活化石”[40](P11)、“文化之根”[8](P125~152)、“文明之母”[8](P153~176),這些最早的漢字記載著我國人類進化的歷史、傳承著中華文化、孳乳著華夏文明,就像“基因”一樣仍然存在于當今的文字之中,所謂“前人所以垂后”[42](P316)。透過這些信息,找出這些漢字的“基因”,并以地質學之父赫登(Hutton,James)[16](P128)、[43](P31)提出的“現在是通往過去的鑰匙”(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為指導原則,基于漢字自身來測定漢字的起源年代,在理論上是可能的,所謂“后人所以識古。”[42](P316)
當然,基于漢字自身的漢字起源年代測定方法要解決的問題并不是“漢字是什么時候產生的”“漢字起源于何時”這一類問題,而是著重解決裘錫奎先生提出的問題:漢字這一文字體系的形成過程開始于何時,結束于何時?漢字是怎樣從最原始的文字逐步發展成為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30](P22)
三、結語
受文物(獻)資料自身的局限性的制約,加之“一般通過訓練而成為歷史學家、金石學家和考古學家的文字學家很少將他們的研究與現代語言科學聯系起來”[24](P39),因而難以擺脫“神創論”“突變論”“個人英雄主義”“文字附庸論”等錯誤思想的影響。以往學界關于漢字起源年代的觀點不可避免地呈現出眾說紛紜,各執一詞的局面。本文提出的“漢字起源年代的字測定方法”試圖擺脫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種種制約,消除其中的錯誤思想,結合文字學與現代語言科學,提倡漢語和文字并行,同時起源,都是在其使用者認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實踐中產生并同步漸進發展的。鑒于漢字久遠的歷史,以及漢字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特征,筆者認為,以“現在是通往過去的鑰匙”為指導原則,回溯我國人類進化的歷史進程,漢字起源年代的測定在理論上來說是可能的。限于篇幅,本文僅討論“漢字起源年代的字測定方法”的理論背景和基本觀點,旨在介紹本測定方法的理論來源,論證其理論可能性,其實踐操作部分尚未涉及,筆者擬另撰文探討。
參考文獻:
[1]邵碧瑛.漢字起源問題[A].陳忠發.漢字學的新方向[C].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
[2]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M].北京:中華書局,1985.
[3]唐蘭.中國文字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發展[J].考古,1972,(3).
[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
掘簡報[J].文物,1989,(1).
[6]中國文字起源學術研討會秘書組.中國文字起源學術研討會綜述
[J].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9).
[7]趙誠.甲骨文字學綱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5.
[8]曹念明.文字哲學——關于一般文字學基本原理的思考[M].成
都:巴蜀書社,2006.
[9]Alinei,Mario.Il problema della datazione in linguistica
storica,con commenti di Ambrosini,Giacomelli,Stussi,Swiggers,Tekavcic e Tuttle,e replica dell,autore[J].In Quaderni di Semantica,XII,1991:3~19; Commenti 1991:21~46; Replica,1991:47~51.
[10]Alinei,Mario.The problem of dating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SLE Presidential Lecture[J].In Folia Historica Linguistica,XII/1—2,1992:107~125.
[11]Alinei,Mario.Origini delle lingue dEuropa,vol.I:La
teoria della continuità; vol.II:Continuità dal Mesolitico alletà del Ferro nelle principali aree etnolinguistiche,2 vol.[M].Bologna:Il Mulino,1996~2000.
[12]Alinei,Mario.The Problem of Dating in Linguistics[J].
Quaderni di semantica,2004,(25):211~232.
[13]Alinei,Mario.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 for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An Introduction in Progress[OL].http://www.continuitas.org/index.html,2011.
[14]Meinander,Carl F..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Finno—Ugrian Peoples[M].Helsinki:University of Helsinki Archaeology Institute,1973:3~14.
[15]Tobias,Phillip V..The evolution of the brain,language
and cognition[A].In Facchini(ed.),Colloquium VIII:Lithic Industries,Language and Social Behaviour in the First Human Forms,The Colloquia of the 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s(Forlì[Italia]8—14/9/1996)[M].1996:87~94.
[16]Alinei,Mario.Darwinism.Traditional Linguistics and the
New Palaeolithic Continuity Theory of Language Evolution[A].In Gontier,Nathalie; Bendegem,Jean Paul van; Aerts,Diederik(Eds.),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Language and Culture.A non—adaptationist,systems theoretical approach[C].Springer,Berlin,Heidelberg,New York,2006:121~147.
[17]Swadesh,M.Lexicostatistic dating of prehistoric ethnic
contacts[A].Proceeding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52,(96):452~463.
[18]Swadesh,M.Towards greater accuracy in lexicostatistic
dat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1955,(21):121~137.
[19]Gimbutas,Marija.Proto—Indo—European culture:the kurgan
culture during the 5th to the 3rd millennia B.C.[A].In G.Cardona—H.M.Koenigswald—A.Senn(eds.),Indo—European and Indo—Europeans[C].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0:155~198.
[20]Renfrew,Colin.Archaeology and Language.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M].London:J.Cape,1987.
[21]赫爾德.論語言的起源(1772)[M].姚小平譯.北京:商務印書
館,1998.
[22]孫常敘.漢字詞匯(重排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23]劉民鋼.中國境內遠古人類的語言起源時代的初步研究[J].上
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2).
[24]雅克·德里達.論文字學[M].汪堂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
社,1999.
[25]Kendon,A.Gesture:Visible Action as Utteranc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6]Kendon,A.Signs for language origins?[J].Public Journal
of Semiotics,2008,(2).
[27]Kendon,A.Languages matrix[J].Gesture,2009,(3).
[28]Kendon,A.“Gesture first”or“Speech first”in language
origins?[A].In D.J.Napoli & G.Mathur(Eds.),Deaf around the world:The impact of language[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29]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30]裘錫圭.文字學概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31]黃亞平.漢字的性質及其有關漢字形成的幾點假說[J].漢字文
化,2000,(1).
[32]吳新智.從中國晚期智人顱牙特征看中國現代人起源[J].人類
學學報,1998,(17).
[33]亞里士多德.范疇篇·解釋篇[M].方書春譯.北京:商務印書
館,1959.
[34]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35]申小龍.漢語與中國文化(修訂本)[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08.
[36]讓—雅克·盧梭.論語言的起源——兼論旋律與音樂的模仿[M].
洪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7]陳望道.修辭學的中國文字觀[J].立達季刊,1925,(1).
[38]Harris,R.Rethinking Writing[M].London:Continuum,
2000:35.
[39]沙宗元.論漢字發展和規范的動態平衡性[J].安徽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09,(6).
[40]郭錦桴.漢語與中國傳統文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41]范可育等.楷字規范史略[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42][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附檢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
[43]Alinei,Mario.Towards a Generalized Continuity Model
for Uralic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A].In K.Julku(ed.),The Roots of Peoples and Languages of Northern Eurasia.IV(Oulu:18—20/8/2000)[C].Oulu,Societas Historiae Fenno—Ugricae,2002: 31.
(鄭曉行 曹杰旺 安徽淮南 淮南師范學院外語系 23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