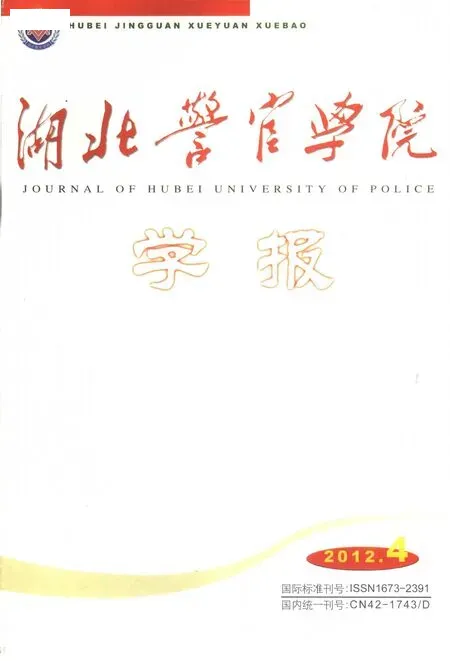對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反思
張敏敏
(湘潭大學 法學院,湖南 湘潭410005)
對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反思
張敏敏
(湘潭大學 法學院,湖南 湘潭410005)
證明標準是我國民事訴訟程序中的重要問題,在發現案件真實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經過十幾年的討論之后,我國應當走出模仿西方經典法治國家的窠臼,面對司法實務中出現的諸多問題,確立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證明標準,科學引導司法活動。
證明標準;舉證責任;客觀真實
一、民事訴訟證明標準與證明責任的關系
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指負有證明責任的民事訴訟當事人提供證據,對自己所主張的民事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也就是說,如果當事人對待證事實提供的證據達到了證明標準,那么,得到證明的這一事實將被作為法院判決的依據;反之,如果達不到證明標準,那么該當事人基于這一事實所主張的請求將被法院駁回。證明責任解決的是對于具體案件中某一特定事實應由哪一方當事人提供證據進行證明的問題。無論哪一方負有舉證責任,其提供的證據沒有達到證明標準,都要承擔敗訴的風險。一般而言,哪一方主張案件事實,就要對自己的主張提供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對于一些特殊案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其實還是屬于“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規定。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規定了因新產品制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由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對其產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承擔舉證責任。也就是說,制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在訴訟中提出的主張必定是自己的產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此時,對于自己的主張進行證明,其實依然遵循“誰主張、誰舉證”。
目前,對于舉證責任的主要功能,學者們已形成了一致意見:在待證事實模糊不清,訴訟雙方當事人均不能提出有力證據證明時,法律規定對這一待證事實由其中一方負舉證責任;如果承擔舉證責任的當事人不能提出證據加以證明,則不可避免地要承擔敗訴的風險,而另一方當事人甚至可以不作為而獲得有利結果。舉證責任直接關系著訴訟結果,而證明標準決定了承擔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所必須達到的程度。由此可見,證明標準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困境
成文法國家將公民參與民事糾紛解決的程序納入規制范圍,就必須預設相關制度來規范民事訴訟活動,并使這些活動盡量在預期的范圍內表達出我們想要的結果。但是,且不說民事訴訟程序,我國的整個訴訟程序都屬于“舶來品”,這種立法主導型的法的現代化模式以及法律制度變革在前、法律觀念更新在后所產生的思想領域的激烈斗爭已經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諸多問題。
鄧正來先生曾撰文指出:“中國法學之所以無力引領中國法制發展,實是因為它們都受一種‘現代化范式’的支配,而這種‘范式’不僅間接地為中國法制發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而且還使中國法學論者意識不到他們所提供的不是中國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同時這種支配地位的‘現代化范式’因無力解釋和解決因其自身的作用而產生的各種問題,最終導致了所謂的‘范式’危機。”[1]在經過十多年對證明標準的諸多研究之后,現實狀況出現了兩個極端:一方面,國內的相關著述洋洋灑灑,百家爭鳴,學說林立;另一方面,純學術理論的探討似乎與司法實務部門完全無關,對這一爭議性極大的問題迄今沒有得出較為滿意的答案,甚至由于未能達成通說而有不了了之的趨勢。學者們無論是研究英美法系蓋然性優勢的證明標準,還是大陸法系內心確信的證明標準,得出的結論均是我國和經典法治國家不同。既是不同,其必定比我國先進,更符合現代化法治國家的要求,因此,我們必須要建構一個與西方國家一致或者相似的制度,才能和世界接軌。正是抱著這樣的想法,我們似乎走上了一條移植西方機制—由上而下痛苦蛻變—西方機制自身危機—中國茫然無措的不歸路。
在成文法國家里,規范性制度的特點就在于以某種固定的或者超越個人意愿、活動的既成規范作為潛在前提。在這樣的固定模式下,可以很直觀地認識違反秩序的行為。作為一項“客觀存在”,出于對其進行規范的必要,我們必須按照其本來面目進行評價。但是,在判例法國家,判例所規范的并不是一成不變或者理想的成熟理念,而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的動態秩序。這種秩序在一個案例中被確立,卻極有可能在下一個類似案例中被推翻。在這樣的動態情形下,并不需要完全客觀地予以認定具體是怎樣的行為或者事實引起糾紛,因為處理糾紛的目的僅集中于權利義務關系的確定。此判例評價與一般的倫理道德相分離,所以不必苛求發現客觀絕對的真實,“對事實的認定只要達到‘社會上一般人大致能夠安心地依靠這一認識而行動’的程度就往往被認為可以滿足了”。[2]
在中國,尋求案件的實體公正在民眾的心中占據了很大的位置。這反映出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也直接反映出民眾心中只相信客觀真實,而且相信客觀真實能夠查明。因此,一味強調特定時空內特定案件的真實情況無法查明或要查明案件事實面臨著怎樣的理論缺陷和實際操作困難,只會助長訴訟的競技化:當事人為了得到利己的結果,利用審限模糊事實;法官為了遵循效率原則,依據呈現于法庭的證據而非客觀真實作出判決,最終結果只能是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都被犧牲。我國設立民事訴訟程序來解決民事糾紛,只能通過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對當事人雙方的民事權利義務作出正確判斷,以保護真正的權利人。糾紛一旦進入司法程序,“人民對法院寄予的最大希望就是準確地對事實作出認定,這一點是誰也不能否定的”。[3]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雖然具有一定的理想成分,但放棄這一理想,就會動搖民眾對司法的依賴,喪失法院的威信,甚至導致整個裁判制度的自我崩潰。[4]
正是由于我國與西方法治國家有著不同的法律文化,社會民眾有著不同的法律思維,客觀真實在西方社會判例式的司法模式中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在中國幾千年積淀下來的法治文化中卻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就注定我們不能夠簡單地移植或者借鑒西方經典法治國家的證明標準。我們不同于他們,并不簡單意味著落后,只有適合自己的制度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況且在人類浩瀚的歷史發展長河中,是否落后只能由后人評價,并不是經典法治國家的一切制度都是先進的,漢唐時期的中國也曾在人類法制發展長河中璀璨一時。
三、完善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建議
(一)堅持客觀真實在證明標準中的主體地位
首先,從民眾數千年來“厭訟”的情況來看,一旦民事糾紛進入司法程序,就意味著當事人雙方放棄了和解、調解等比較溫和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促使其進入司法程序的動力就是案件的真實情況一定要水落石出。如果此時因為司法效率等原因不能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那么,當事人無疑會對司法產生質疑:作為最后一道防線的民事訴訟程序是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為宗旨,還是以既定模式為基礎,從法律上給一個結果,而不管這個結果是否公正。
其次,民事權益屬于私法性質,國家不會主動干預。在“不告不理”模式下,當事人選擇司法程序,面對的不僅僅是法庭審理程序,還包括糾紛發生時保存證據的能力、哪些事實由自己負責舉證等一系列運作過程。在我國律師制度不太完善的情況下,其耗費的時間、精力都是無法估量的。在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我們只能選擇一方承擔敗訴風險,至于為什么選擇這一方,選擇的結果是否公正、是否符合案件的真實情況則在所不問,此時,訴訟并不比其他糾紛解決方式更優越。確定客觀真實的證明標準,可以使當事人在進入訴訟程序前衡量其是否承擔得起敗訴的風險。我們可以承認一項制度不完善,繼而努力調整;我們是法治理念的踐行者,而不是不完善的法律條文的表達者。
(二)法律真實只能作為輔助,不能成為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主體
2001年9月的“莫兆軍事件”轟動一時。一對老夫婦因為不能證明自己被人持刀脅迫寫下一萬元的欠條,盡管在法庭上作了真實詳細的敘述,最終法官莫兆軍以沒有提供相關證據,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判其敗訴。在執行過程中,這對老夫妻在法院正門外喝農藥自殺身亡,法官莫兆軍遂因涉嫌玩忽職守罪被捕。
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實際上,由于各種原因,雙方掌握的資源是不對等的。如果僅以呈現于法庭上的法律真實作為判決依據,那么越來越多案件的客觀真實就會被埋沒,無疑會出現越來越多的當事人為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采取激烈的方式或者非正常途徑解決糾紛。這是對民事訴訟制度價值最大的否定。
民事訴訟程序的設立是為了最大程度上救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接近司法未必能接近正義,因為司法不是萬能的,這就要求我們從法律之外的解決民事糾紛的其他制度中探求能夠發現客觀真實的一些方式,從存在于我國上千年歷史中已被廣泛接受的方式里尋求答案,建立我國以客觀真實為主體的證明標準,并促使其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完善。這樣的證明標準才具有更加長久的生命力,并能推動我國的法治建設。
[1]鄧正來.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上)——建構“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時代的論綱[J].政法論壇,2005(1):3.
[2]王亞新.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68.
[3][日]石井一正.日本實用刑事證據法[M].陳浩然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8.
[4]李浩.論法律中的真實——以民事訴訟為例[J].法治與社會發展,2004(3):2.
D925.1
A
1673―2391(2012)04―0176―02
2012—02—12
張敏敏,女,河南靈寶人,湘潭大學法學院。
【責任編校:王 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