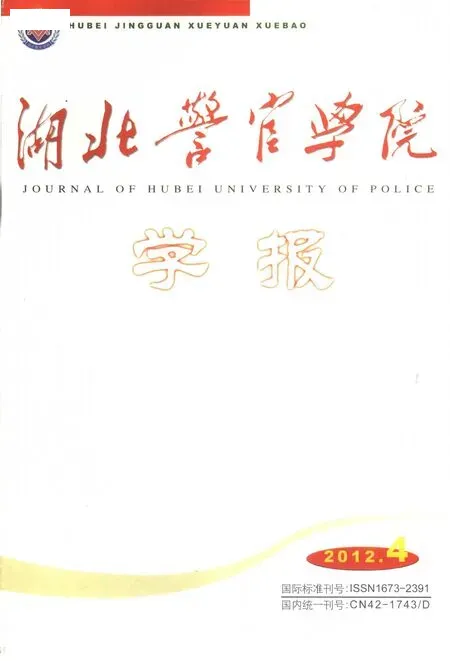從中西文化差異看中國保留死刑的必要性
徐 隱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 武漢430079)
從中西文化差異看中國保留死刑的必要性
徐 隱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 武漢430079)
自貝卡利亞以來,死刑存廢之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在中國刑法學界也一直是一個熱點問題。對死刑是存是廢,國內外尚未達成一致意見。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綜合比較中西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從理論、現實、價值三個方面來看,中國不僅不應當在當下廢除死刑,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應廢除死刑。
死刑;廢除;中西文化
自從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第一次明確提出廢除死刑的主張以來,對于死刑的評價已經爭議了二百多年。人們對于死刑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死刑是否必要、死刑是否正義這兩個層面,圍繞人的生命價值,從死刑是否具有威懾力、是否違憲、是否人道、是否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是否助長了人們的殘忍心理、是否符合刑罰目的、是否容易錯判和改正、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等方面來討論死刑的廢存。[1]但是,上述方面的考慮如果脫離了特定的、具體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是沒有意義的,必須結合實際國情來分析中國是否應該廢除死刑。
一、不同宗教文化視域中的犯罪容忍度不同
信仰在整個西方文化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宗教思想對于西方人的影響深入骨髓。在倫理學、心理學等諸多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基督教思想都被當作論證的前提。
死刑應廢除的理念,最初起源于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主義說教,“生命神圣說”是死刑廢除的最原始的一種理念,它認為生命神圣意味著生命來自上帝,它既不用任何世俗原因取得,當然不因為任何世俗的原因而喪失,只有上帝才有權剝奪生命,使人自然死亡,任何世俗組織與個人都不得剝奪生命,國家以任何理由剝奪人的生命,都是對上帝意志的違背。[2]
基督教中的原罪思想是其宗教理論的根基之一。人生而有罪、人性本惡的理念使得民眾對犯罪行為有一定的心理容忍度。韓籍青年血洗美國校園,槍殺32名師生,打傷15人之后,校方還為自殺身亡的兇手設立悼念杯。這在中國是不可理解的,但在美國卻沒有過多的爭議。
在中國,基督教的影響十分有限。基督教自從明末清初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國土以來,一直難以融入中國文化,很難得到中國民眾的認同。這是因為中國歷來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以儒釋道為根基的傳統文化卻相當穩固。“君權神授”、“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思想中很重要的內容。人類在一般情形下當然沒有權利剝奪他人的生命,但一些特定情形之下,如執法者需要懲治一些窮兇極惡之徒時,這一項權力便由上天賦予了。
二、不同“人道”語境中的個人生命權和責任主體不同
中西方對于人道的不同理解也導致這個問題上的分歧進一步加大。在前資本主義時期,死刑因其殘忍的執行方式、缺乏嚴格民主的審核程序而淪為封建勢力恫嚇民眾的統治工具。貝卡利亞提出廢除死刑正是啟蒙運動時期,這一時期思想運動的性質是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因此,貝卡利亞對于死刑的批駁也是以其不人道為主,其目的是通過廢除死刑限制封建勢力。
隨著民主的進步、程序法的發展、適用的日益謹慎、執行手段的日趨人道化,死刑的不人道性卻依然被西方學界和社會輿論詬病便有些奇怪了。其實在西方,無論死刑如何完善,死刑本身這種剝奪他人生命的刑法都被認為是不人道的。這一方面體現了西方社會尊重生命權,在另一方面或多或少地體現了西方人對于事件的分析缺乏聯系的特點。因為資本主義傳統而形成的個人主義思想,往往使得民眾將個人與政府對立起來:片面地重視罪犯的人權是否遭到公權力的侵害,而忽視了被害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損失。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駕駛私人飛機撞擊政府大樓并致2人死亡、13人受傷的約瑟夫·斯塔克會被視為抗稅英雄,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英國民眾會自發為被判死刑的毒販阿克毛舉行紀念活動了。
同時,西方把犯罪的相當一部分責任歸咎于社會環境。在西方人看來,正是因為教育、社保等制度的不完善,才使得公民走上犯罪道路。相比之下,東方則多從個人心性修養、道德情操方面評價個人犯罪的原因。因此,對于犯人所需承擔的責任大小,東西方存在著根本的分歧。
中國自古便有善惡有報的文化傳統。這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同態復仇,而是中國人對于正義和公平的樸素追求。中國的農耕文明和需要依靠集體力量治水的歷史傳統,使得中國民眾產生了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思想。在一個集體之中,每個個體不但需要考慮自己的權利,更應該考慮對于他人和集體的義務。當其侵犯和損害他人利益的時候,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當犯罪行為極為惡劣,犯罪后果極為巨大之時,死刑作為最高懲罰措施便是犯人應當為其所犯罪行承擔的責任。
三、不同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死刑威懾力不同
刑罰并不僅僅是為了懲罰罪犯,良好的預防作用也是其重要目的之一,有效的威懾力使刑法能夠守住社會的底線,死刑往往被視作最高威懾力的地位也是其存在合理性的有力證明。
然而,許多西方法學家卻認為死刑的威懾力其實并沒有通常想象的那么大。死刑威懾力的驗證,以美國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系列實證研究最具代表性。在經過一系列同一區域死刑廢除前后謀殺發案情況的比較、廢除死刑與保留死刑的不同區域謀殺發生率的比較,以及對死刑實際執行后,同一區域在一定時限內謀殺犯罪數量的下降率的分析調查,結果表明,沒有死刑的州,殺人犯罪率比有死刑的州低;同時,同時期其他國家——加拿大、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丹麥、瑞典、挪威、荷蘭、意大利和奧地利的數據也表明,死刑對兇殺率的升降沒有什么影響。[3]這一調查似乎表明,人們之前對于死刑威懾力的印象有些不切實際。
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刑罰威懾力并不與犯罪數量完全掛鉤,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公民意識是否足夠、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都會影響犯罪數量。不能因為犯罪數量的增加就否認法治的進步,死刑的威懾力也不能簡單依據犯罪數的多少和增減作為絕對的衡量標準。
事實上,刑罰對于民眾的威懾力與其所處的文化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貝卡利亞首先提出徒刑的威懾力大于死刑的威懾力,他說:“處死罪犯的場面雖然可怕,但只是暫時的,如果把罪犯變成勞役犯,讓他用自己的勞役來補償他所侵犯的社會,那么,這種喪失自由的懲戒則是長久的和痛苦的,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強有力的手段。這種行之有效的約束經常提醒我們,如果我犯了這樣的罪惡,也將陷入這漫長的苦難之中。因而,同人們總感到撲朔迷離的死亡觀念相比,它更具有力量。”[4]
這對于西方文化來說是有一定道理的。西方文化的自由主義精神使得個體將自我的自由視為至高無上的價值。從古希臘時期的悲劇普羅米修斯到象征著美國獨立的自由女神,從“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到“不自由毋寧死”,自由一直作為一種文化基因,扎根于每一個西方人的心中。對他們來說,死刑雖然很可怕,但失去自由的徒刑在一定程度上更甚于死刑。
但是,中國不同。雖然老子有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可這都不是在自由和生命中作出抉擇。強調集體主義的中國人對于自由的熱情,向來不及西方人那般狂熱。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讓中華民族對于損失一定的自由換取安定生活的延續,是習慣而易于接受的,所謂“好死不如賴活”。在這樣的文化心理下,期望徒刑在中國達到或是接近死刑的威懾力,是不切實際的。縱使死刑的絕對威懾力有限,它的地位也是不能代替的。
四、結語
東西文化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并不能因為歐美的經濟比我國發達便認為我國的文化比他們落后,更不能以歐美為絕對模板無條件地全盤照抄。文化無優劣,制度有好壞,但好壞的標準一定要符合本國國情。國情中最為重要的,便是扎根在每個民眾靈魂之中的文化基因。因此,死刑在當今中國不僅不應當立刻廢除,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要中國文化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死刑就不應該退出我國的刑法體系。
但是,我們也不否認現今死刑在理論和司法實踐方面都有弊病和漏洞。首先,死刑具有不可挽回性,一旦出現錯判,逝者已矣,不可能通過金錢彌補。這就要求我們在認定死刑時一定要慎之又慎,并完善刑事訴訟法的內容,增加審判透明度,接受公眾監督,使得誤判錯判的幾率降到最小。對于不幸發生錯判誤判的案例,一方面要盡最大努力對受害家庭進行賠償;另一方面要實行嚴格的問責制度,嚴懲相關責任人。其次,死亡痛苦巨大的死刑手段具有不人道性,要盡量使用注射的方式實行死刑,盡可能以人道主義的方式完成死刑的整個過程,降低死刑犯人的痛苦,并在執行過程中給予死刑犯人足夠的尊重,滿足其合理的遺愿,允許其立遺囑安排后事等。對于特殊主體,如孕婦、老年犯人、未成年人,排除死刑的適用。
[1]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21.
[2]曠玲.以生命權為視角論死刑廢除問題[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5(6).
[3][英]羅吉爾·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M].劉仁文,周振杰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
[4][意]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M].黃風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46.
D925
A
1673―2391(2012)04―0128―02
2011—12—29
徐隱,湖北武漢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責任編校:陶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