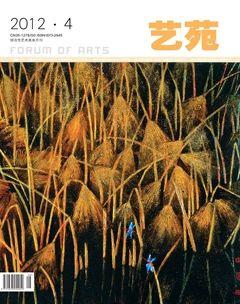二胡藝術形成的“催化劑”:中西音樂并存的近現代江南文化環境
李祖勝
【摘要】本文從文化學的視角,通過探尋劉天華與其成長的江南文化背景之間的關系,發現正是中西音樂并存的近現代江南文化環境促使劉天華學貫中西,并立志革新國樂,從而推動了二胡藝術的形成。
【關鍵詞】 二胡;江南;外因在20世紀20年代劉天華將二胡搬上獨奏舞臺從而形成二胡藝術之前,二胡一直是在江南(指包括江蘇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的長江三角洲流域)流行的民間樂器。由于江南地區所在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等方面具備的優越性,自明清以來,在江南商品經濟的帶動下,江南市鎮的興起和商業貿易、文化教育事業、民俗活動、各種音樂藝術品種等等的繁榮,為二胡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至民國初年,江南民間二胡不僅具備了寬闊的音域、良好的樂器音質音色,而且也具有豐富的左右手演奏技法,這是同時代的其它胡琴類弓弦樂器無法比擬的,它為二胡藝術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然,新事物的產生往往是內因與外因合力的結果,如果說江南社會在明清以來的各種文化因素是導致二胡藝術形成的內因,那么,到了近代,當中國社會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威逼下,引起從軍事、政治、文化、心理等各個層面的滄桑巨變時,西方音樂文化的傳入也引發中國音樂人士的國樂革新之思,這成為了二胡藝術形成的外部誘因。
在二胡藝術形成的20世紀初,江南地區由于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是西學東漸的最前沿,因而成為當時中國社會及音樂文化變革轉型的先行、樞紐地區,是中西文化共存之所在。中西音樂文化長期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并存,為彼此的碰撞、交流提供了機會,音樂文化變遷成為一種必然。文化是由人創造出來的,離開了人,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實際上是人與人之間,或是個人內心在接受了他種類型文化后在文化觀念上的排斥與認同,因此,文化的變遷是人在文化觀念上的變遷,文化變遷由人來完成。具有西方專業音樂創作理念和技法的現代二胡獨奏藝術就是在中西音樂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變遷出來的“一條新路”。引領這一文化變遷的人正是劉天華。劉天華之所以能引領這一文化變遷,與他成長和生活的江南地區正處于中西音樂文化并存的時代是分不開的。中西音樂文化并存使他得以接觸和學習中西兩種音樂文化,強勢的西方音樂文化的不斷刺激引起劉天華在音樂文化觀念上的嬗變,從而催生了現代二胡獨奏藝術。所以說,中西音樂并存的江南文化環境是二胡藝術形成的“催化劑”。
一、中西音樂并存的近現代江南文化環境促使劉天華學貫中西
近代中國,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西方文化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并逐漸被國人所接受,而西學東漸的第一站就是江南重鎮——上海。早在明末清初,以利瑪竇為首的西方傳教士曾將西學第一次傳到中國,中國知識分子中就形成了一個以上海人徐光啟、杭州人李之藻為首的“西學派”。此后,江南人由于文化水平相對較高,成了西學的主要傳播群體。上海作為西學的傳播中心,對二胡藝術形成的作用是不可小覷的。
上海地處中國沿海航線的中心點,是中國最大河流長江的出海口,北可通過東海或運河連通黃河地區,交通十分便利。并有中國經濟最富庶、文化最發達的江南地區作它的貼身腹地。地理位置與歷史文化條件把上海推向中國近代化的最前沿。1842年在南京江面上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中,上海被開辟為通商口岸。隨著對外的開放和外貿的擴大,江南的商品經濟開始融入到國際市場之中,如棉紡織業這種制作工序比較簡單的行業就受到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巨大沖擊。洋紗洋布價格十分便宜,致使土布日益被排擠,蘇南地區棉紡織手工業的衰落已成普遍現象,“而土布之銷數日絀,小民生計維艱”[1]7。為了謀求生計,江南農村大批的勞動力涌入上海,各地的商幫也紛紛涌入上海經商。上海在中西經濟的共同作用下很快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同時,由于江南各地傳統手工業的破產,在外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帶動下,江南各地出現起了一批新興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從而增強了上海與江南各地的商品流通。正是這種商品流通以及往返于上海與江南各地的商人、民工所攜帶的經濟、文化、生活各方面的信息,促使上海與江南各地聯系更加緊密,形成一個以上海為龍頭的經濟、文化整體。所以,1912年,當劉天華在讀的常州府中學堂因辛亥革命爆發而停課時,劉半農、劉天華兩兄弟也融入到前往上海打工的潮流當中,劉天華才有機會在上海的“開明劇社”廣泛接觸和學習西洋音樂。
對于西方音樂文化在近代中國的傳入,諸多學者認為主要通過基督教會的宗教歌詠、新式軍樂隊的建立和學堂樂歌這三個途徑[2]17。在這三個方面,江南地區比同時代的中國其它地區更為普遍和深入。西方教會學校具有西方現代學校教育體系中的文史哲、數理化以及音樂、體育、美術等多學科綜合教育功能。這類學校大都面向社會,接納非教徒子女入學,因而對近代中國的社會影響是很深的。據統計,1875年全國教會學校總數約800所。而江南因有便利的地理位置和領先的經濟、文化地位,教會學校亦不在少數。在上海,像徐匯公學、裨文女塾、女紀女塾、明德學校、清心學校等等,都是西方傳教士在舊上海創辦的知名學堂。教會學校開展的宗教歌詠活動開啟了中國人接受西方音樂文化的大門。當然,在西方音樂文化傳入的三種途徑中,最讓劉天華受益的是后兩者。
新制學堂的廣泛建立和樂歌課的開設對西方音樂文化的傳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末民初,歷來都很重視文化教育的江南地區,各級各類公辦與私辦的新式學堂不斷涌現,并且大多數學校的教學計劃中都開設有音樂課。劉天華之父——江陰秀才劉寶珊在19世紀末就開始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歷史剛剛跨入20世紀,劉寶珊就與當地知名人士楊繩武先生一起創辦了新式的翰墨林小學,這在當時的中國算是相當早的。劉天華1903年入學時,學校開設的課程有英語、數學、博物、體操、美術、音樂等新式課程。是一所名副其實的“洋學堂”。新興的西式教育和學唱學堂樂歌的經歷對幼小的劉天華在音樂觀念上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而進一步強化劉天華的西方音樂思維的經歷則是他在常州五中學習銅管樂的兩年。
軍樂隊在中國的最早出現也是在19世紀70年代的上海,外國人在英美租界創辦了一個上海公共管樂隊。清末民初,新式軍樂隊的建立在中國還不是十分普遍,但相比較而言,江南的軍樂隊已經算是比較多的了。20世紀初,隨著新式學堂的廣泛建立,江南的許多中學堂都成立了軍樂隊。據《中國軍樂隊談》一文記載,至該文發表的1917年,在江南存在的相當著名的軍樂隊就有:上海工部局軍樂隊、上海土山灣軍樂隊、蘇州東吳大學軍樂隊、上海南洋公學軍樂隊、常州第五中學(即常州府中學堂)軍樂隊等。[3]190-1911909年,劉天華進入常州府中學堂讀書時,學校就已經有了一個規格不錯的軍樂隊。他“參加了校中的軍樂隊,把樂隊中所有的樂器都學會了,特別是對銅管樂器更有莫大的興趣,因此在短短的兩年間,他對銅管樂的掌握已達到校內首屈一指的程度”[4]35。1915年他從上海回來,執教于母校時,由他指導的軍樂隊已經能演奏“威武雄壯的《馬賽曲》和舒伯特的《軍隊進行曲》,有濃郁民族風格的《俄羅斯進行曲》,還有《第六號進行曲》、《第七號進行曲》以及各種序曲、優美動聽的小夜曲等”[4]72有相當演奏難度的樂曲。在學習和指導西洋管樂的過程中,與中國傳統音樂迥然不同的西洋管樂的音樂風格、創作手法對劉天華在后來進行的國樂改進和音樂創作無疑都發揮了重要的啟示作用。
1912年,劉半農、劉天華兩兄弟到上海謀生,在熟人的推薦下,劉天華加入到“開明劇社”的樂隊,擔任小號手,有時還給樂隊編曲。“開明劇社”樂隊是一個中國樂器與西洋樂器混編的樂隊,鋼琴、提琴等各種西洋管弦樂器應有盡有,這使得第一次來上海的劉天華大開眼界。劉天華利用業余時間來學習西方音樂。這期間,他還加入了萬國音樂隊(即上海公共樂隊)學習,并利用一切機會,鉆研音樂理論,學習多種西洋管弦樂器,尤以銅管樂進步最快,而鋼琴和小提琴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學習的(1)。當時的上海,西洋管弦樂、小提琴演奏家的演出已不少見,劉天華又在西洋樂隊中工作。在對小提琴及整個西方音樂文化耳濡目染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環境中,使他得以比較深入地了解和學習西方音樂,從學習樂器到掌握西方音樂的音樂風格、創作理念、創作手法等方面,比在常州府中學堂學習管樂時顯然更加深入和全面。通過小學、中學和在上海期間對西方音樂文化的接觸與學習,劉天華對西方音樂從演奏技巧到音樂理念的把握已經相當精到。
當然,劉天華盡管從小接觸和學習西方音樂文化,但他畢竟出生在民間音樂傳統十分濃厚,灘簧、十番鑼鼓、江南絲竹等民間音樂盛行的江陰。江陰城內的孔廟和涌塔庵,每逢春秋祭祀,僧家佛事,都是鐘鼓、絲竹之聲不斷,廟會、集日各類民間音樂云集。劉天華從小就可聽到鄰居汪阿大用笛子和二胡演奏五更調、梅花三弄、孟姜女等民歌小調和江南絲竹器樂曲[4]27,擅長演奏笛子和二胡等樂器的涌塔庵徹塵小和尚跟劉天華從小也是形影不離,一起吹笛、拉琴玩音樂。從出生之日開始就置身于各種民間音樂熏陶當中的劉天華依然是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造物”,雖然從小也學習了西方音樂,卻并不會因此而喪失了作為傳統中國人在音樂文化方面具有的“民族性”。他在音樂文化觀念上的嬗變僅僅是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揚棄和汲取西方專業音樂創作理念的養分。
中國民間音樂文化多依附于各種穩態的民俗,民俗內涵成為音樂的主要表現內容。而作為經受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知識分子——劉天華需要用音樂來表現國家處于內憂外患之時的憂患情緒、思想以及個人的前途、人生意義。中國傳統音樂的民俗性音樂內涵不足以表現這種新型知識分子的情感內涵。通過學習西方音樂,劉天華知道西方專業音樂創作的原創性理念和技法能幫他實現這一音樂表現的愿望。但作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造物”,劉天華身上積淀的是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基因,所以,他的原創音樂依然充滿著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審美趣味。中西兩種音樂文化類型在他內心的碰撞,使他改變了江南絲竹通過改編和加花變奏等方式來創新樂曲的創作觀念以及民俗性音樂內涵,這種創作觀念的改變卻并沒有舍棄的是,他的原創音樂依然具有中國傳統音樂的線性思維、五聲性音調以及咿呀如語的滑音奏法等民族性音樂特征。
1914年,劉天華從上海回到江陰,拜師江南絲竹名手——周少梅學習二胡和琵琶,1915年劉天華便開始創作他的二胡處女作——《病中吟》。《病中吟》全曲的原創性和三部性構思體現出西方專業音樂創作理念,而源自江南絲竹的旋律和旋法則又充分體現出樂曲的“民族性”。
從劉天華的成長經歷可以看出,是中西音樂并存的江南文化環境促使劉天華學貫中西,具備了創造新型二胡音樂文化的能力。
二、近現代江南文化環境中西音樂并存的強烈反差促使劉天華立志革新國樂
誠然,中西并存的江南音樂文化環境雖然能促使劉天華學貫中西,但如果劉天華對中西音樂沒有主觀的學習興趣和目的,也不會如此努力。應該說,從小學到中學,劉天華學習西方音樂還僅憑個人興趣,畢竟此時的劉天華還未成年。1912年,經受過辛亥革命洗禮的劉天華跟隨其兄劉半農到上海謀生,當時的上海崇洋之風盛行,坐洋車、穿洋服、欣賞西洋音樂等等都成為上海人最時髦的生活習慣。西洋音樂文化與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相比,已經在人們的娛樂生活當中占據了主要的位置,傳統音樂處于十分蕭條的狀況。筆者認為,劉天華正是在上海耳聞目睹了中西音樂文化在市民音樂生活中如此懸殊的不同待遇,感受到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音樂文化與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強烈對比反差,接觸了各種立志改進國樂的國樂社、國樂研究會、國樂學會后,引發對國樂前途的思索,從而開始了他不遺余力地改進國樂的漫漫征途,而二胡成為了他改進國樂的突破口。
清末民初,中國古老的封建社會體系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猛烈沖擊下逐漸開始瓦解,開始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啟蒙。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在不求社會發展、但求社會穩定的封建統治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環境中,不需要鼓舞國民進取精神,而是被希望具有能化解階級矛盾的“中和之美”。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一直沒有走上專業化創作的道路,而在民間自生自滅,具有濃重的民俗性、地域性、自娛性特征。而西方音樂文化早在中世紀就開始了專業化創作的道路,經過14至16世紀的文藝復興、17至18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和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洗禮,西方音樂文化已經飽含著西方資產階級進步的文化屬性及資產階級先進思想中人文主義的精神內涵。這顯然比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更適于中國近現代廣泛掀起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的需要。在這種社會變革的形勢下,就需要一種以宣揚資產階級積極進取、追求民主與自由為精神內涵的新的中國音樂文化出現。因此,到20世紀初,國樂革新很快成為一種時代潮流。江南人由于文化水平普遍較高,又有江南能深入接觸西洋音樂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經濟條件,因而成為了國樂革新的主要實踐群體。立志“改進國樂”的劉天華在當時并不是一個“孤獨的夜行者”,而是眾多國樂革新者中的一員。從民國初年開始,隨著各種國樂社、國樂研究會、國樂學會等不斷涌現,出現了周少梅、鄭覲文、衛仲樂、汪昱庭、張萍舟、王巽之、程午嘉、李廷松等一大批國樂革新的積極實踐者。在劉天華1922年離開江南前往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任教之前,江南的國樂革新早已醞釀成星火燎原之勢。
那么,劉天華為何要以二胡為國樂革新的突破口呢?這來自于與二胡同為弓弦樂器并形成強烈對比的西洋樂器——小提琴。小提琴傳入中國也是在19世紀下半葉的上海,僑居上海的西洋人為了豐富他們的娛樂生活,將小提琴帶入了他們的新居住地,并運用于他們的娛樂活動中。當時的戲院演出是“華人”與“西人”都可欣賞的,中國人欣賞小提琴音樂是常見的事情。
至20世紀初,上海開始出現西洋管弦樂隊,樂隊中的提琴類樂器已經相當完備。如成立于1879年的上海公共樂隊原本是一支銅管樂隊,1907年被擴大為管弦樂隊。樂隊不僅演出儀式音樂,還經常單獨舉行定期音樂會。從1911年的音樂會節目單,可以知道當時樂隊的編制情況為:第一小提琴四把、第二小提琴四把、中提琴三把、大提琴二把、低音大提琴二把、長笛二支、雙簧管二支、單簧管二支、大管二支、小號二支、長號二支、打擊樂一人,共計30人[5]97。樂隊成員都是外國人。作為一個小型的管弦樂隊,弦樂組的樂器編制是比較齊全的。隨著小提琴音樂在上海的影響逐漸擴大,也逐漸有中國人開始學習小提琴。如學堂樂歌的先驅者之一——曾志忞,其夫人曹汝錦女士在1901年留日并學習小提琴,高壽田也于1903年留日并學習小提琴。1907年曾志忞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半工半讀式的“上海貧兒院”,并在其中特別設立了一個“音樂部”,高壽田就任該部主任。在高壽田和曹汝錦的幫助和直接參與教學下,曾志忞在學習音樂的貧兒中選出約四十人組織了一個西洋管弦樂隊,也是第一個全由中國人任演奏員的西洋樂隊。弦樂組是西洋管弦樂隊中需要人數最多的一個組,所以,在這個樂隊中,學習和演奏提琴的樂隊成員應該不下20人,這對推廣西方提琴音樂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正是因為提琴音樂在上海的逐漸廣泛傳播,1912年,當劉半農、劉天華兩兄弟到上海謀生時,劉天華才得以接觸和學習小提琴。
當時的小提琴早已是西方音樂的“弦樂之王”,而中國的二胡類胡琴樂器雖然是“環視國內皮黃、梆子、高腔、灘簧、粵調、漢調以及各地小曲,絲竹合奏、僧道法曲等等,那一種離得了它”[6]?卻仍被認為其“音樂大都粗鄙淫蕩,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正是這一中一西兩件弓弦樂器的不同命運,使得劉天華決定以二胡為突破口來革新國樂。
劉天華的胞弟——二胡教育家劉北茂先生也認為,劉天華是在上海“開明劇社”時萌發了要“改進國樂”的想法的,他談到:“劉天華在1927年8月1日給《國樂改進社》撰寫的《我對本社的計劃》一文中曾說:‘改進國樂這件事,在我頭腦中蘊藏了恐怕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國人,又是以研究音樂為職志的人、若然對于垂絕的國樂不能有所補救,當然是件很慚愧的事。(見《國樂改進社成立刊》)天華先生于1912年至1914年在上海‘開明劇社工作,距離上面所說的時間正好是‘不止十年。故上面一段話,正好可以印證他在上海‘開明劇社時已萌發了要‘改進國樂的想法。”[4]54筆者對劉北茂先生的觀點是非常認同的,對于“垂絕的國樂”的體會,只有在洋樂盛行,國樂蕭條的上海才能體會得最為深切。1914年“開明劇社”解散,劉天華回到江陰,1915年他就開始了二胡曲《病中吟》的創作,就是說此時的劉天華已經開始了改進國樂的征途。《病中吟》全新的西方音樂創作理念,顯然跟他在上海的工作和學習經歷有著必然的聯系。
因此說,如果沒有中西音樂并存的江南文化環境,劉天華就看不到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在與西方音樂文化較量中的孱弱無力,他就不會想到要革新國樂,因而就不具備有二胡藝術形成的充備的外部誘因,中國弓弦樂器地位的提升恐怕至少退后數年。反言之,正是中西音樂并存的江南文化環境成就了劉天華,成就了二胡藝術。
二胡經過江南的戲曲、曲藝、吹打樂、絲竹樂等江南音樂文化的歷史熏陶,經過歷代江南藝人的繼承和發展,積累著能形成二胡藝術的內在潛質。到清末民初,隨著西方音樂文化的傳入,江南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經濟、文化地位,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形成了中西音樂并存的文化環境,中西音樂文化的強烈反差引發以江南人為主體的國樂革新者之思,劉天華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得以學貫中西,并以二胡為突破口來改進國樂,二胡藝術才得以形成。中西音樂并存的近現代江南文化環境對二胡藝術的形成無疑起到了關鍵的催化作用。
注釋:
(1)此段內容主要參見劉北茂《劉天華音樂生涯——胞弟的回憶》中“上海之行”一節,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版。
參考文獻:
[1]朱壽明.東華續錄[M].光緒,一四九.
[2]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4.
[3]陶亞兵.明清間的中西音樂交流[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4]劉北茂.劉天華音樂生涯——胞弟的回憶[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
[5]本泰子.樂人之都——上海[M].彭謹,譯.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3.
[6]劉天華.《月夜》說明[J].音樂雜志,一卷二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