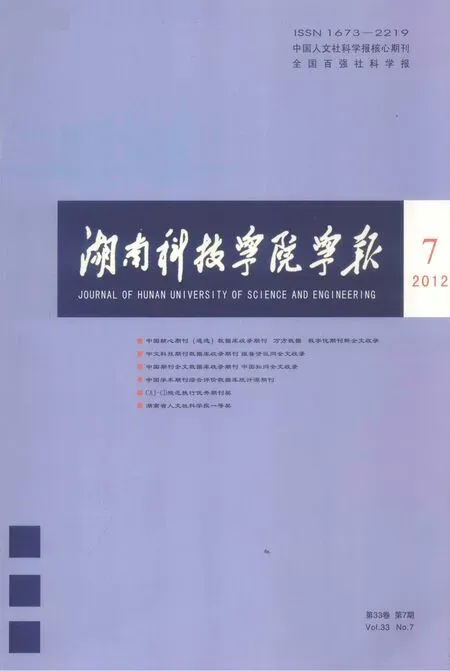女書·女人·教育
——讀樂伶俐教授《教育學視域下的女書及其傳承》
聶志成
(湖南科技學院 信息技術與教育系,湖南 永州 425100)
女書·女人·教育
——讀樂伶俐教授《教育學視域下的女書及其傳承》
聶志成
(湖南科技學院 信息技術與教育系,湖南 永州 425100)
《教育學視域下的女書及其傳承》一書以女性的眼光,女人的視角,運用教育學的理論,開辟了獨特的女書研究之路。作者認為女書學習是一種教育活動,屬于教育中的非教育形式,并大膽的提出,當地女性以女書為中介的學習,走出了中國傳統(tǒng)女性教育的困境,形成了女人自己教育女人的別具一格的教育路徑。
《教育學視域下的女書及其傳承》;樂伶俐;著作評論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男尊女卑”思想一直貫穿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成為傳統(tǒng)社會的基本指導原則。教育作為挖掘人潛能、促進人發(fā)展、推進人進步、實現人的一種重要手段和途徑,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只能成為男人享受的特權,男人地位的象征,是男人通向社會的重要標志,只能為男人所擁有,而中國女人與學校教育無緣,致使絕大部分中國女人在大多數時期充當男人的配角,社會地位相對低下,在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的權利受到制約,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因而中國傳統(tǒng)女性的智慧得不到展示,創(chuàng)造性得不到發(fā)揮,主體性得不到體現。
江永女書的出現,改變了人們對中國傳統(tǒng)女人的看法,打破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對女性的禁錮,使人們看到了一道閃亮的曙光,讓人們領略了中國古代女性智慧的光芒,聰穎的才智,創(chuàng)造的火花。江永女書,世界上唯一存活的女性文字,是文字中的一大奇觀,被譽為“中國一絕”,激起了現代人探索的好奇,各種不同角度的審視、研究紛紛出現。這其中,樂伶俐教授的著作《教育學視域下的女書及其傳承》,2009年由湖南大學出版社,具有獨到的貢獻。
一 女書學習滿足當地女性教育的需要,挑戰(zhàn)傳統(tǒng)女性教育
中國古代受“女子無才便是德”、“讀書無用”的影響,學堂與女人無關,女人被拒絕在學堂門外,不允許走進學堂與男人平起平坐、平等的享受學校教育,中國古代女人真想要讀書,勇敢者只能向祝英臺一樣喬裝打扮,變成“男人”,以“男人”的身份才能走進學堂與男人一起享受本應得到的讀書機會和教育權利,女人的求學之路是多么的艱難曲折,但絕大多數女人只能忍氣吞聲、默默地接受命運的安排,游離在學堂之外,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成為男人的附屬。
教育不僅是增強人素質、提高能力的一種手段,更是社會中每一個人完成社會化的重要途徑,還是人發(fā)展、實現自身價值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接受教育是社會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力。對于女性而言,更為迫切和需要,因為“教育一個男人,受教育的只是一個人;教育一個女人,受教育的是幾代人。”接受教育不僅是社會的要求,更是女人自身發(fā)展的需要,接受教育本是一件很簡單而重要的事,但就是如此簡單而重要的事,對中國古代的女人而言,是一種奢望,可望而不可及。
女書流行地——湖南江永,不可避免地存在同樣的現象,《女書之歌》對這種社會不公平的現象直接表達了女性的憤慨:“因為封建不合理,世世代代受煎熬。做官做府沒資格,學堂之內無女人。”但江永有這么一小群婦女,并未屈服于命運,她們敢于沖破世俗的限制,用女人的力量和能力,通過創(chuàng)制一種女性文字——女書,由女人教育女人學習女書的方式獲得自我教育的機會和權利,滿足學習的需要,盡管這種滿足需要的方式是在無意識的狀態(tài)下獲得的。該書作者通過分析女書學習所形成的女性教育與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女性教育,認為“傳統(tǒng)的女性教育是由男性向女性提供教育機會的,是由男性來滿足女性的教育愿望,女性喪失了教育的自主權,總是處于一種被動的局面”,而女書學習則是主動、獨立的,完全掌控在女人自己手中,是向傳統(tǒng)社會中在男人手里去爭奪教育權的一種挑戰(zhàn),是女人自己開創(chuàng)出的一條具有完全女性特征的教育之路,這條路雖艱難,但自由、平等。
二 女書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女書學習屬于非正式教育
女書不僅指女書文字,還指用女書這種文字書寫的作品,當地女性用女書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女書作品,大都是詩歌體,女書研究專家謝志明根據作品內容的不同,把女書詩歌分為“書信、抒情詩、敘事詩、柬貼、哭嫁歌、歌謠、兒歌、謎語、禱神詩、譯文”等幾類。“詩言志”、“文以載道”一直是中國文學作品奉行的思想。作者通過分析女書作品,認為“女書作品中滲透著中國古代所倡導的禮教、詩教和樂教的思想”,把禮教、詩教和樂教完美統(tǒng)一在女書作品中,對當地女性進行教化,使即使沒有走進學堂接受正規(guī)教育的女人,也能通過女書的學習獲得當時社會所需要的素質,使女性成為符合社會所需要的女人,女書具有強烈的“德育、智育、美育、勞動教育和心理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功能。
女書的傳承本身就是教育活動過程,女書學習更是直接的教育實踐活動。作者在考察女書學習的過程和特點之后,提出“女書學習屬于非正式教育活動,性質上歸屬于非正式教育制度”。正式教育是有著明確的培養(yǎng)目標,由確定的教師和學生在一定的教學條件和專門的學校或教育機構中展開的教育活動,而非正式教育則是個人在社會生活領域或經歷中,受到各種人和事的影響而使受教育者發(fā)生改變的教育。非正式教育具有即時性、不確定性和潛移默化等特性。當地女性基于女性間的交往,她們在進行祭祀、女紅、婚嫁、女性交往等日常活動實踐中學習女書,通過這種日常活動不僅掌握了女性語言文字——女書,同時還獲得了當時社會所需要的一定的知識、技能、思想等,這顯然與正式教育是不相同的。
但作者同時還指出:“女書學習與其它非正式教育不同,具有特殊性。”女書本身屬于女性語言文字,女書學習也僅限于女性,而且在學習女書過程中,是由女性傳給女性,并在女性的日常生活實踐中學習女書及女書中蘊含的知識經驗,女書學習獨具性別意義,具有專屬性;女書學習還具有生活性,“女書學習,把女性的日常生活實踐、社會生活經驗的積累與學習女書這種女性文字有機結合,構成一個三位一體的學習方式,使女性的學習更生活化”。女書學習在當時社會是不能進入學校的活動,是江永少數女人為了學習女性特有的文字,在學校之外、立足于日常生活而在小范圍開展的獨立、自由的教育活動,有著自己的“教師與學生、學習形式、學習內容、課本、組織形式及學習目的”。女書是特別的,女書學習是特殊的。
三 女書是中國文化的奇觀,女書學習是中國女性教育的奇跡
女書被認為是湖南江永“三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是一個民族、國家、地區(qū)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和沉淀而形成起來的共同的精神和物質方面的特征整合,是人們心靈的依托和行動的指南,是民族特色、國家認同和地區(qū)差異的象征。廣義地說,文化指的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個方面。它的內涵非常廣泛,涉及到社會的思想道德、科技、教育、藝術、文學、宗教、傳統(tǒng)習俗和語言文字等方方面面。文化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一般情況下是一個民族、國家、地區(qū)的物質和精神發(fā)展到一定時期所積淀起來的產物,為本民族、國家、地區(qū)的所有人所共同接納、認可,體現人們共同的認識和心理。
女書不管是從語言文字的角度,還是指用女書書寫的女書作品方面,還是說在女書學習基礎上的女性教育,不管哪種角度說,女書都是文化的范疇。但女書與其它文化不同,首先,女書是由女性創(chuàng)制的,并只是在少數女人之間通用的一種語言文字,女書使用的范疇只限于當地部分女性之間,使用面窄,只為女人所有;其次,女書作品大都是記錄女性個人生活、生命歷程的心靈史,并不是女人共同的心理,女書作品具有個別性;再次,女書學習也僅限于女人之間進行、由女人傳給女人,對于女書男人是不想學習的,女書學習和女書文字一樣具有性別特征。由此,作者得出“女書是中國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是世界文化的奇觀”。
針對在女書學習基礎上所形成的女性教育,作者站在女性教育史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女書學習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學習女書,更在于它的性別意義,在于它是專屬于女性的教育。女性教育在中國教育史上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道路,由家庭教育走向學校教育,由學校中的男女分校而學走向男女同校,女性一直在為自己爭取平等的教育權而奮斗和吶喊,但這條路是在以漢字為主導的男女兩性共同組成的、以男性為主導的主流社會里拼搏,為在男性世界中求得一席之地而努力,以此想與男性教育相抗衡。而以女書為中介的女性教育,走的是另一條路,是在女性王國里,自己創(chuàng)造出屬于自己的語言文字,女性教育女性,通過學習女書來享受自己應享受的教育權,滿足自己的讀書愿望,它完完全全屬于女性。”“這種教育具有深遠的意義,在中國女性教育史上創(chuàng)造了女性教育的奇跡。”
女書是女人的專利,女書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時期,由于女性處于社會底層、困于家庭而尋求自我解放、滿足自我教育需要、追求自由幸福生活、實現女人自我價值的獨創(chuàng)的女性語言文字,建立在女書學習基礎上的女性教育,豐富了中國的女性教育史。《教育學視域下得女書及其傳承》一書從教育學的角度揭示了女書、女人與教育之間的關系,為研究女書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拓展了女書研究的思路。
(責任編校:張京華)
G521
A
1673-2219(2012)07-0205-02
2012-05-23
聶志成(1965-),男,湖南永州人,湖南科技學院信息技術與教育系教授,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