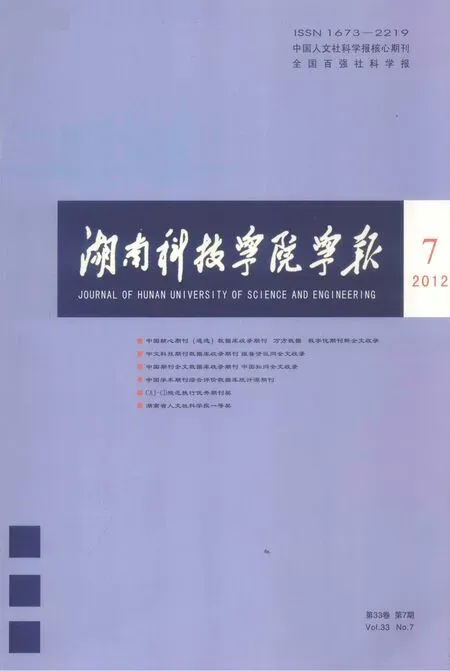歧視下的反抗與新生:《紫顏色》中索菲亞形象分析
陳 晶
(安徽大學 外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歧視下的反抗與新生:《紫顏色》中索菲亞形象分析
陳 晶
(安徽大學 外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紫顏色》是美國黑人女作家愛麗絲·沃克的代表作,該書通過對一系列的女性人物的塑造揭示了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雙重壓迫下的黑人婦女的悲慘生活以及她們的覺醒和反抗,其中反抗意識最為強烈的便是索菲亞這一人物。索菲亞是傳統(tǒng)黑人男性眼中黑人女性的“異類”,她面對黑人男性和白人的壓迫奮起反抗,最終獲得了自由和尊重以及不摻雜任何歧視的純粹的愛情。她用自己的言行向廣大的黑人婦女宣告:若想獲得自由和獨立,首先要做的就是“不服從”。
《紫顏色》;索菲亞;黑人女性;女性文學;女權主義
一 引 言
《紫顏色》(The Color Purple)是美國黑人女作家愛麗絲·沃克于1982年出版的一部書信體小說,也是黑人女權主義的代表作之一。小說以主人公西麗的成長為主線,塑造 了一批形象飽滿、個性鮮明的黑人婦女形象。通過對普通黑人家庭生活的描寫,也揭露了美國主流白人社會中各種不易被人覺察或者說被故意遺忘的種種社會問題。小說中占主導地位的問題仍是黑人男性對黑人女性的壓迫以及白人對黑人的歧視和壓迫。而同時遭受這兩座大山壓迫最為嚴重并且矛盾沖突最為激烈的莫過于索菲亞這個人物了。
索菲亞是西麗繼子哈波的妻子,身強體壯、有很強的自我意識,婚后哈波一直想讓索菲亞受自己擺布,兩人經(jīng)常大打出手,致使索菲亞帶著孩子離家出走;而后索菲亞因為不肯給白人做女傭而鋃鐺入獄,受盡折磨,出獄后最終與哈波又走到一起,因為此時的哈波已經(jīng)懂得尊重和體貼妻子了。索菲亞不像莎格那樣一直放蕩不羈,也不像西麗那樣由逆來順受轉變?yōu)楠毩⒆灾鳎@個風風火火、敢愛敢恨的女子,在一個男性作威作福的社會里艱難地生存,勇敢地捍衛(wèi)自身的尊嚴和獨立,不依附,不屈服,為自己爭取到了自由的婚姻和自由的生活。然而,也正是這種剛硬的性格給索菲亞招來無妄之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不說,半生都生活在監(jiān)獄和白人家庭的地板上。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以及經(jīng)年累月的身體和精神的摧殘,索菲亞似乎沉默了,服從了,但在她重獲自由之后,我們驚喜地發(fā)現(xiàn),這個有些殘疾,頭發(fā)灰白的婦人骨子里一直是那個可以被打敗但不會被打倒的索菲亞。而正是因為有了索菲亞這樣具有反抗意識的新一代女性,黑人女性才有可能逐步提高她們的地位和待遇,從而擺脫被無視、被欺壓的命運。
二 索菲亞不服從的原因
(一) 社會因素
黑人女性在美國歷史上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美國很少有哪個群體像她們一樣背負種族壓迫、性別壓迫、階級壓迫等多座大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是“他者”[1](the Other)。而像索菲亞這樣既是女性又是黑人的女性,可以說是“他者”中的“他者”。她們一出生便被打上了固定的性別烙印,在男女對立的兩性結構中處于從屬的角色。女人活著的意義就是生育后代,勞作,挨打,不值一錢也不能接受教育,無論是經(jīng)濟上還是人格上都無法獨立,結果便是她們淪為男性的依附品和工具,自身的個性被否認,自我意識和身份也被抹殺。可悲的是,大多數(shù)黑人女性自覺遵從了這種規(guī)定,心甘情愿在性別結構中充當被統(tǒng)治的一方。如果索菲亞選擇服從男人設定的男女準則,那無疑將斷送她的一生。
(二)家庭因素
弗吉尼亞·沃爾夫在她的女性主義名篇《一間自己的屋子》里提出雌雄同體的概念:“在我們之中每個人有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腦子里男性勝過女性,在女性的腦子里女性勝過男性。最正常、最適宜的境況就是這兩個力量結合在一起和諧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時候。”[2]縱觀索菲亞的外貌和言行,不難發(fā)現(xiàn)她是一個具有男性氣質的女性。她是一個“高大,結實,健壯的姑娘”[3]P27,走起路來“邁著大步,好像在奔赴戰(zhàn)場”[3]P26,連和丈夫打架也不處于下風。這一部分是由于性格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索菲亞在一個男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下采取的保護自己的方式,巴特勒提出,社會性別是表演性的[4],她在家庭中扮演斗士這一通常由男性充當?shù)慕巧珌砗葱l(wèi)自己的尊嚴和自由。索菲亞自己也說,“我這輩子一直得跟別人打架。我得跟我爸爸打。我得跟我兄弟打。我得跟我的堂兄弟、我的叔伯們打。在以男人為主的家庭里女孩子很不安全。”[3]P33對于一心想要控制自己并且為了打贏自己更拼命吃東西的丈夫,索菲亞采取的策略是“我愛哈波……可我會揍死他的,如果他想揍我的話”[3]P33。
(三)自身因素
社會環(huán)境和家庭環(huán)境等外部因素必須通過索菲亞自身這一內因才能起作用,索菲亞沒有選擇扮演西麗那樣被馴化了的“賢妻良母”的角色,而是揮舞拳頭,扮演誰敢冒犯她就揍誰的“母老虎”。這除了源自索菲亞天生的不服輸?shù)男愿裰猓艽蟪潭壬弦彩且驗樗鞣苼喩眢w的原因。她體格健壯,丈夫哈波根本不是她的對手,這是索菲亞反抗的一個重要資本。憑著這份強壯,索菲亞才沒有被男性“踩在腳下”。除了外在的強壯之外,索菲亞還具備黑人婦女的一項傳統(tǒng)美德——堅韌。也正是憑著這份內在的堅韌,索菲亞才能在監(jiān)獄里存活下來,最終獲得美好的新生活。
三 索菲亞的“服從”
(一)直接原因
市長夫人米麗小姐在街上看到索菲亞的孩子個個都收拾得干凈得體,認為索菲亞是一個精明強干的人,便要求她做女傭。但以索菲亞的性格,根本不會愿意去別人家卑躬屈膝,于是出言不遜接著大打出手,招來牢獄之災。索菲亞在獄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被打得體無完膚,幾乎沒人能認出她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索菲亞唯一的出路就是聽話,順從,保住性命。正如她自己說的那樣,“他們一叫我干活,西麗小姐,我就像你那樣,馬上跳起來照辦。”“我是個好犯人,她說,他們從來沒見過我這么規(guī)矩的犯人。”[3]P71但是這并不代表索菲亞真的屈服了,她內心的憤怒并沒有被經(jīng)年的勞作和囚禁消磨掉,反而與日俱增:“我做夢都想殺人,她說,不管是醒著還是睡著,我都想殺人。”[3]P71索菲亞還是那個敢愛敢恨的索菲亞,只是身處牢籠的她敢怒不敢言。
(二)社會原因
雖然索菲亞戰(zhàn)勝了家庭暴力,但在掌握著政權的強大的白人階級面前,她的反抗猶如以卵擊石。對于索菲亞這樣一個“不守本分”的黑人,在白人開設的監(jiān)獄里的遭遇并不難想象。“他們打破了她的腦袋。他們打斷了她的肋骨。他們把她半個鼻子掀了。他們把她一只眼睛打瞎了。她從頭到腳渾身浮腫。舌頭有我胳膊那么粗,伸到牙齒外面,就像塊橡皮。她不會說話了。她渾身青紫,像個茄子似的。”[3]P69-70她的經(jīng)歷說明,黑人婦女也許可以靠個人的力量在家庭這一小范圍內擺脫“第二性”的某些劣勢,但放眼整個社會,只要種族歧視還存在,黑人,當然也包括黑人婦女,就永遠不能得到解放。在黑人這一種族被白人欺壓的大前提下,索菲亞只憑一己之力是絕不可能最終擺脫低人一等的生活的。黑人婦女要么是男人的奴隸,要么就是白人的奴隸,她們沒有選擇的權利。因此,黑人婦女欲求解放,必須首先讓自己的種族獲得解放。
(三)黑人自身的問題
索菲亞的被捕,還有一個原因來自黑人自身,他們沒有團結起來共同抵御白人的欺壓。“《紫色》的重點……在于探討黑人的內部關系……從而揭示黑人自身的弊病,并提出克服的途徑。”[6]索菲和哈波打架時,是一對一的單打獨斗,和哥哥們打架時有姐妹們團結在一起,因此索菲亞幾乎每次都不會吃太大虧,甚至還一度占據(jù)上風。可是,入獄這次卻不同,她打的是白人,而且是市長。索菲亞當街受到一群白人警察的圍毆,唯一想上前幫忙的索菲亞的男友也被索菲亞制止,呼喊著讓他把孩子送回家,而自己卻鋃鐺入獄,身陷囹圄長達十一年半。而索菲亞之所以能夠提前出獄,正是因為她的親人朋友們團結在一起,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在一系列的努力和哈波女友吱吱叫的犧牲下,索菲亞才被冠以“表現(xiàn)良好”的標簽被有條件釋放——她仍然不能夠自由,而要去米麗小姐家當女傭,五年才回了一次家,那一次也只跟孩子們共處了15分鐘而已。黑人要反抗,要取得社會地位,首先要使自身這個種族強大起來,否則,即使斗爭了,團結了,所取得的勝利也是有限的,充滿遺憾的。
四 索菲亞對其他人物產生的影響
(一)對婆婆西麗的影響
索菲亞是小說中唯一不向男性低頭的黑人女性,也是第一個向西麗展示女人也可以有另一種活法的人。索菲亞在娘家時就懂得要用拳頭保護自己,她的丈夫哈波打她,好讓她“聽話”,結果被她揍得鼻青臉腫。她還告訴西麗“把某某先生的腦袋打開花……然后再想天堂的事。”[3]P31索菲亞勇敢的反抗向西麗展示了黑人婦女怎樣去爭取自己的地位,捍衛(wèi)自己的尊嚴。她的一言一行都讓西麗震撼,甚至嫉妒她會“打架”。在索菲婭進入西麗的生活以前,沒有人告訴她該怎樣去抗爭。用西麗自己的話說“我不斗,我安分守己,可我活著。”[3]P19索菲亞的勇氣和力量對西麗來說無疑是震撼的,“我喜歡索菲婭,可她的一舉一動跟我完全不一樣。”[3]P19她讓西麗看到在婚姻中,丈夫不一定總是強者,妻子也不必服服帖帖。西麗與索菲亞很快成為朋友,她們一起縫制百納被,這一行為本身就是黑人女性之間姐妹情義的獨特象征。同時,在縫制被子的過程中,西麗也開始一針一線地縫補破碎的自我。她們之間的友誼在一定程度上驅趕了西麗內心的孤寂,為西麗寒冷的內心帶來一絲溫暖。索菲亞為日后西麗建立起完整的人格起到了啟蒙和示范的作用,可以說她為西麗原本漆黑一片的人生之路點亮了第一盞燈。她也在西麗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種子,而這種子總有一天會生根發(fā)芽。
(二)對丈夫哈波的影響
索菲亞和哈波之間原本有著真摯的愛情,可是哈波受到父親的耳濡目染,也認為女人就該像西麗一樣對丈夫言聽計從,他想通過暴力的方式使索菲亞屈服,不料卻遭到索菲亞的猛烈反擊。哈波被索菲亞打傷后更是羞于承認自己打不過一個女人,便謊稱自己是被騾子踢了,甚至發(fā)展到后來拼命吃東西增肥,希望可以制服索菲亞,不料種種劣行終于逼走了妻子和孩子們。索菲亞的出走,讓哈波陷入了悲痛,也開始了思考。其實“和西麗一樣,哈潑也在努力模仿社會規(guī)范下男人的合格性別特征,隱藏了自己真正的天性”[5]。可貴的是,經(jīng)過多年的人世沉浮,哈波對索菲亞的感情依然如故,并且成為了一個愛護索菲亞、尊重索菲亞的好丈夫。正如哈波自己所說,“你總有我在支持你的,他說,你作的每個判斷我都支持。”“他走上前去,吻吻她鼻梁上縫過的地方。”[3]P224而摒除成見和歧視之后,兩人最后的相視一笑,溫馨又浪漫。
(三)對公公某某先生的影響
文中并沒有過多描述某某先生對索菲亞的態(tài)度,但我們不難推測出某某先生的想法。首先,某某先生一開始就不同意哈波和索菲亞的婚事,尤其是介意索菲亞未婚先孕,擔心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哈波的,這和某某先生的父親懷疑莎格生的三個私生子不是某某先生的骨肉如出一轍,不能不說是作者對某某先生辛辣的諷刺。倔強的索菲亞并沒有哀求某某先生的收留,而是掉頭就走,直到哈波把她接回屬于他們自己的小家,而這無疑證明了索菲亞和某某先生的第一次交鋒以某某先生的失敗告終。其次,某某先生雖然在他們婚后付錢給哈波好讓他能養(yǎng)活一家人,但對兒媳索菲亞仍然相當不滿,甚至唆使哈波打她,可惜性格懦弱的哈波體能上也不如索菲亞,反而落得個鼻青臉腫直至妻離子散的下場。某某先生一直試圖把自己和西麗的家庭模式套用到哈波和索菲亞身上,結果適得其反。索菲亞的言行很大程度上動搖了某某先生原本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觀念。如果說莎格的離開讓某某先生無奈,西麗的離開讓某某先生醒悟,那么索菲亞的離開則可看作是使某某先生達到不再蔑視女性這一質變的一次重要量變。
愛麗絲·沃克通過對索菲亞等女性角色的塑造,表達了她對黑人婦女這一處于社會底層的群體的深切同情,也通過這些女性角色的抗爭和覺醒以及獨立對黑人女性進行了熱情的謳歌。她們善良,勤勞,聰慧,她們缺少的只是一個機會來展示她們的才華。但是,沃克似乎只是一味地把這些黑人女性形象塑造得正面、積極,并沒有正視她們身上的缺點。例如索菲亞過于剛愎自用,莎格過于我行我素,她們的這些缺點在作者筆下都被描繪成值得贊揚值得同情的因素了,讀者讀來難免覺得有失公允,作者似乎只是哀其不幸,而并未怒其不爭,有“護短”之嫌。另外,小說中被索菲亞打掉兩顆門牙的哈波的情人吱吱叫在索菲亞入獄后盡心盡力地照顧索菲亞的孩子不說,竟然還為了救出索菲亞慘遭奸污,依然無怨無悔,這一情節(jié)設置似乎并不顯得那么近乎人情。對于索菲亞這個人物的刻畫也稍顯刻板,她的性格和認識一直沒有太大的進步和深入。
另外,小說中作者除了批判男性對女性的壓迫之外,還控訴了另一個尖銳的社會矛盾——白人對黑人的歧視和壓迫,而這一點在索菲亞身上體現(xiàn)得尤為突出。小說中出現(xiàn)的為數(shù)不多的白人角色大多都是反面人物,他們或者像市長和警察們那樣兇殘暴虐,或者如米麗小姐一樣神經(jīng)質,對黑人抱有不知從何而來的成見。而唯一跟索菲亞親近的她親手帶大的埃莉諾·簡小姐也被描寫成一個沒什么眼色也沒什么主見事事都去麻煩索菲亞的人,似乎在索菲亞看來,白人無外乎兩種:要么壞,要么蠢。而且,索菲亞把對白人種群的憎惡延伸到每一個單個的白人身上。索菲亞在米麗小姐家做女傭的時候埃莉諾就很親近她,處處為她出頭,可是索菲亞怎么也不喜歡埃莉諾,甚至對埃莉諾剛剛出生的孩子索菲亞也斷定這個孩子長大后必定會欺壓黑人。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黑人婦女眼中,女性之間的情誼一旦和種族問題放在同一個天平上,就顯得無足輕重了。也許在作者看來,黑人婦女首先是一個黑人,其次才是一個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種族問題不僅體現(xiàn)在小說中,在小說外也戲劇性地真實地上演著。電影《紫顏色》獲得奧斯卡 11項提名,最終竟然一個獎項都沒有拿到,成為當時電影界的奇聞,讓人唏噓不已。然而,奧斯卡的失利卻恰恰契合了紫色小說中的主題之—:種族歧視。
但不管怎樣,《紫顏色》中的索菲亞這一人物都給讀者留下了鮮明的印象和無盡的思考。作者通過這一人物不僅向大眾展示了黑人女性所受的煎熬,更重要的是借由索菲亞指出了婦女解放道路的第一步——反抗。只有首先從家庭和社會的不公平中解放出來,才有可能在經(jīng)濟上、精神上取得獨立。這不僅對黑人婦女具有積極的意義,也給所有的婦女指出了一條擺脫男權控制的道路。
[1]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2]Woolf.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9.
[3]愛麗絲·沃克.紫顏色[M].陶潔,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
[4]Butler,Judith.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New York:Routledge, Chapman & Hall,1990.
[5]王莉.從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表演角度重讀《紫色》[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11,(6):62-66.
[6]楊仁敬.美國黑人文學的新突破——評艾麗絲·沃克的《紫色》[J].外國文學研究,1987,(12):29-36.
(責任編校:王晚霞)
I106.4
A
1673-2219(2012)07-0063-03
2012-04-12
陳晶(1985-),女,安徽潁上人,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澳大利亞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