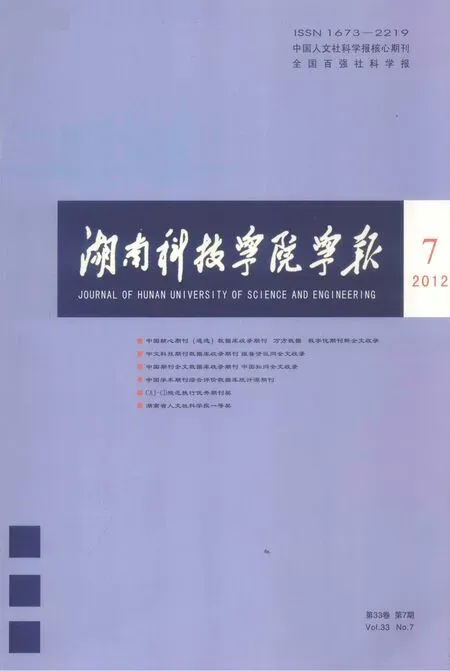韋應物悼亡詩的時間感悟與審美選擇
張 芳
(遼東學院師范學院 中文系,遼寧 丹東 118003)
韋應物悼亡詩的時間感悟與審美選擇
張 芳
(遼東學院師范學院 中文系,遼寧 丹東 118003)
論文在悼亡詩的領域中選擇了向來較少為人關注的韋應物的悼亡詩,從韋氏夫妻的家世和修養探討了其悼亡悲劇的根源,從其時間季節感悟模式的全方位闡述其內化悼亡悲劇情感的廣度,從其悼亡詩審美選擇表現模式的多角度論述其外化悼亡悲劇情感的深度,從而彰顯韋應物在中國悼亡文學中的地位和作用。
韋應物;悼亡詩;時間感悟;審美選擇
中國有關悼亡的詩篇,早在《詩經》中就有記述,《詩經·邶風·綠衣》就是一位男子睹物懷人、思念故妻的詩。而文人悼亡詩較之則晚,西晉潘岳的《悼亡詩》被認為是文 人悼亡詩的源頭。經過魏晉南北朝眾多詩人的推動,唐宋時期悼亡詩的創作繁榮起來,涌現出了像元稹、李商隱等詩人的悼亡佳作。在唐人寫悼亡詩的領域里,韋應物可以說是寫的最早的而且是最好的幾位之一,而他的十九首悼亡詩,向來較少為人所關注。
韋應物悼亡詩共十九首,除《同德精舍舊居傷懷》作于建中三年(782),其他十八首均作于大歷十二年秋至十三年秋喪妻后一年間。與中國悼亡詩的情感一樣,韋應物的悼亡詩傳達的也是一種悲情。
一 韋氏夫妻伉儷情深——悲情的根源
關于韋應物的生平事跡,新舊《唐書》沒有為他立傳,《舊唐書》并無一字提到他。從南宋沈作喆《補韋應物傳》開始,到孫望《韋應物事跡考述》、羅聯添《韋應物年譜》、傅璇琮《韋應物系年考證》、陶敏的《韋應物生平新考》,依據韋應物詩歌中提供的線索,我們努力從中探究韋應物的生平事跡。
2007年出土于陜西長安韋曲韋氏家族墓志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考據,新出土的韋妻志文曰:“以天寶丙申八月廿二日,配我于京兆之昭應。”天寶丙申即天寶十五年(756),如果按韋應物生于開元二十五年推算,韋應物結婚時的年齡為二十歲,其妻十六歲,符合當時的婚齡習慣。所以,我們認為韋應物生于開元二十五年是基本可信的。基于此,本論文中的系年及事跡我們以此依據。
韋應物出生在一個有著顯赫家世和隱逸傳統的世家大族,其曾祖父韋待價是武則天時的宰相,但到了祖父韋令儀和父親韋鑾,家道逐漸式微,但是其父韋鑾在當時是一位善畫花鳥、山水松石的知名畫家,包括他的兄長、侄兒在當時都以擅長繪畫馳名于世,韋應物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家境比較貧寒卻富有藝術修養的家庭。他少年任俠不羈,安史之亂始折節讀書,此后一直輾轉徘徊在出仕與罷官閑居之中,詩歌也在盛中唐之際的眾多詩人中卓然不群,自成一家。
其妻元蘋,墓志中記載:字佛力,生于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吏部之長女。動之禮則,柔嘉端懿;順以為婦,孝于奉親。嘗修理內事之余,則誦讀詩書,玩習華墨。天寶十五年(756)出嫁,時十六歲。二十年后的大歷十一年(776)九月卒,享年僅三十六歲。由此可見,韋氏出身名門,富有教養,美麗端莊,恪守婦道,孝奉雙親,操持內事,知書達理,才趣高雅。
正是由于夫妻間的家世、修養,使他們在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志趣相投、感情甚篤,也正是由于此,才導致韋應物悼亡詩悲劇情感的濃重與執著。朱光潛《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說道:“中國愛情詩大半寫于婚姻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別、悼亡。”所以當這份感情逝去的時候,彌足珍貴。
墓志記載,夫人病逝在韋應物的官舍,舉行葬禮時是在含光門外太平坊臨時租借的房子。胡曉明《中國詩學之精神》說道:“中國文人的情詩,一個顯著的特質,即長于吟唱一種有缺憾的愛,從中表現出一種悵惘不甘的情調。通觀古代愛情詩詞,使人們極少去吟詠那一份正在愛中的歡樂意識,亦極少以樂觀之眼光,去憧憬愛的明天,而是對消逝的往日之戀,一往情深……”由此“家貧無舊業,薄宦各飄飏”(《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的韋應物對妻子滿懷愧疚,“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傷逝》)。正是這份有缺憾的愛構建了他悼亡詩的悲劇意識。
二 時間季節感悟模式的全方位內化悲劇情感的廣度
韋應物悼亡悲劇建構模式是時間季節感悟模式,他以回憶亡妻的情感為線索,一年四季更替為經、一天晨昏晝夜為緯,構筑了悼亡悲情體系,內化悲劇情感的廣度。清喬億《劍溪說詩又編》云:“古今悼亡之作,惟韋公應物十數篇,澹緩凄楚,真切動人,不必語語沉痛,而幽憂郁堙之氣直灌輸其中,誠絕調也。”中國古人對季節的感悟和季節對人的情感影響是古已有之的,而對春秋的情感是變化傷感的。從平行的角度看,自然界的存在和變化觀照和反映了人類主體的生存狀態,作為自然界中的主體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變化。從縱深的角度看,春季的萬物勃發容易引起人們對回憶的感傷和對未來迷茫的反襯;秋季的萬物凋殘正契合了文人們失意的孤寂落寞。所以中國文人歷來的感傷詩大多出現在春秋季節,中國文學的傷春、悲秋主題便是有利的佐證。
韋應物的十九首悼亡詩,在季節時令上春夏秋冬皆有涉獵,除一首在季節上不可知外,秋季有7首、與春季有關的5首。韋氏卒于夏秋之交,從數量上可以暗合季節對人的影響和人在特定季節的感悟。
在秋季詩作中,《傷逝》中詩人感傷“逝去亦不回”的人死不能復生,卻又對“知妄謂當遣,臨感要難裁”的死而復生懷有期待的矛盾心理;《悲紈扇》中詩人表達“非關秋節至,詎是恩情改”,對亡妻的思念不會隨著季節的改變而流逝的執著情懷;《閑齋對雨》里詩人用蕭條景對幽獨心,念往事倏忽的記憶猶新;《林園晚霽》里詩人在落日余暉中人隨同游,心卻在他處的寂寞無言;《感夢》沒有夢中景,卻有夢后驚魂凋鬢的長日難挨。
在春季詩作中,《除日》“忽驚年復新,獨恨人成故”的遺憾,《對芳樹》“佳人不再攀,下有往來躅”的今非昔比,《月夜》中“清景終若斯,傷多人自老”的自我寬慰,《嘆楊花》中“人意有悲歡,時芳獨如故”季節、自然不會隨著人事悲歡離合而變遷和改變的無奈。
如果說一年四季是韋應物悼亡詩的橫向線索,那么在時間上的全面鋪開就是韋應物悼亡詩的縱向紐帶,而且在一天的時間內,晨昏晝夜都有對亡妻的思念與表達。“晨起凌嚴霜”的送葬,“風條灑馀靄,露葉承新旭”的《對芳樹》,“朝朝自難度”的《除日》,《閑齋對雨》的幽獨與蕭條,都從時間的晨與晝完成是人對妻子的思念。在十九首悼亡詩中,與夜晚有關的六首、與傍晚有關的四首。《冬夜》、《月夜》、《秋夜二首》、《林園晚霽》則在題目上直接標明了時間。
胡塞爾的《內在時間意識現象學》將時間分為內在的時間、客觀的時間和世界的時間。在客觀時間上,韋應物的悼亡詩與傍晚、夜晚有關的數量大于白天的數量,這種時間的獨特心理感受,暗合了中國古人把黃昏以后直至夜晚作為情感的典型符號,傅道彬先生說:“時間意義的悲涼和空間意義的溫馨構成了中國文學中黃昏意象的象征意蘊。”黃昏時分容易觸動內心深處的孤獨感和歸屬感,而韋應物就在歸屬感的缺失后倍感孤獨,“驚起復徘徊”、“今還獨傷意”、“郁結誰為開”、“心傷覺時寂”、“耿耿獨傷魂”,這種寂寞與沉郁可見黃昏懷人模式對唐人的深刻影響。所以清代許瑤光有“已啟唐人閨怨句,最難消遣是昏黃”的慨嘆。
所謂的內在時間是根據主體自身的體驗去把握時間,也就是主觀時間。正是這種愛的缺失痛苦,使詩人主體的痛苦體驗無限延長,再現出與客觀事實反差極大的主觀感受。詩人的主觀時間在這里有兩種表現:一種是忽視客觀時間的存在。由于季節的變化,對妻子死而復生的期待使自己出現在夢境里,如“夢想忽如睹”;看到春景復蘇,才驚感經冬歷年的變化,如“忽驚年復新”;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突然回到現實的驚恐和痛楚,如“倏忽苦驚飆”。一種是客觀時間的無限延長,在《夏日》里獨坐山中的長日難挨,在《感夢》中午夜夢醒的長夜漫漫,在《出還》中感嘆日復一日的身在他舍的神情恍惚,都使詩人由于亡妻的痛楚而在客觀時間上產生了主觀上的改變與錯位。
三 審美選擇表現模式的多角度外化悲劇情感的深度
楊周翰先生認為,悼亡詩是抒情詩的一個“亞種”,也可以說是愛情詩的支派。韋應物的悼亡詩作為感傷的愛情詩,充滿了痛楚、惻愴與郁結,無心經營、真情流露的審美選擇通過抒情的手段與途徑將其悲情的濃重與執著宣泄出來。
(一)悲劇情感外化的途徑
韋應物的悼亡詩情感外化的途徑是多元化的,在元蘋墓志里有一段記載可以讓我們多方面地印證韋應物喪妻后的悲情緣點:“每望昏入門,寒席無主,手澤衣膩,尚識平生,香奩粉囊,猶置故處,器用百物,不忍復視。又況生處貧約,歿無第宅,永以為負。”散化到十九首詩中的四個途徑凸顯詩人的主體意識和審美選擇:
舊宅故跡與生活留存:在這類悼亡詩中,無論是四屋滿塵埃的閨房保留、觸物傷摧,還是遺器、芳巾與殘工猶在;無論是掩顰人無、委篋空存,還是十載后訪東林舊扉,都為讀者展現出詩人對舊日生活的歷歷在目的不能忘卻與痛心留戀,表現出因物及人、見物思人的主體性印記和情感價值,是一種物是人非、物存人亡的個體的空沒感和凄涼感。
兒女情長與生活瑣事:在這類作品中交織著情感的反差,孩子是時悲時喜,在似懂非懂中孩子在經歷著喪母的苦痛與成長。面對兒女情長與家庭瑣事詩人則充斥著感性與理性的交雜,時而理智清醒地感嘆“顧爾內無依”、“咨嗟日復老”,時而又神情恍惚地覺得自己“錯莫身如寄”,表現出理智與情感的違逆感和錯位感,同時呈現出悲劇的延展性。
夜晚與夢境回憶:在這類作品中,詩人通過六首詩的夜晚與夢境回憶的途徑展示出其悲劇情緒價值的矛盾感。有對死而復生的期待和懷念,有茫然與雜亂;有寂寞和夜不能寐;有對現實的客觀認知與自我寬慰;有惆悵和心如死灰、情近婦人的哀怨;有夢后驚魂。劉辰翁《須溪先生校點韋蘇州集》評:“吾讀蘇州詩至此,初怪其情近婦人,非靳之也。”
天氣景物與端居感懷:在這類作品中,風雨之時限制了人的戶外活動,無聊之際再加上溫度濕度的變化帶來的生理感知失常,加劇了人的情感寄托需求,所以自然界的能喚起人傷感的天氣風霜雨雪在此都有出現,截野的飄風、倏忽的驚飆與中夜的朔風;晨起的嚴霜、皚皚的霜霰與凄凄的霜露;蕭條的疏雨、夜半的寒雨,都為我們營造蕭條景與孤寂感,這種天氣景物和端居引發的是無處不在的生命的孤寂感與無奈感。
(二)悲劇情感外化的手段
在韋應物的悼亡詩中,在詞語運用上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大量使用疊詞和連綿詞,這些詞語在情感的傾向性上有其共同的低沉憂郁的取意特征,這些平常語在聽覺上回環往復,在節奏上舒緩條達,在語言的感受力和表現力上契合其悲情主題的語言美感,彰顯其抒情意義。
與此同時,在詞語選擇上大量使用與孤獨、驚恐有關的詞語。十九首詩中,“獨”字出現13次,“單”字出現3次,“驚”字出現8次,這些詞語的重復運用,反復地申訴了詩人喪妻后的情感與境遇的孤寂、客觀與現實的無助和內心與主體的驚恐麻木、心境與現實的凄苦難奈。
以樂景寫哀情的手法是中國古典詩歌在詩歌表現上運用的一種在對比中的矛盾,矛盾中的對比,審美效果突出。《出還》中“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句,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評:“因幼女之戲而己之哀倍深。比安仁悼亡較真。”《除日》中“冰池始泮綠,梅援還飄素。淑景方轉延,朝朝自難度”,王夫之《羌齋詩話》評:“以樂景寫哀情,以哀景寫樂情,倍增其哀樂。”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之中感受到詩中難言之哀、難傳之痛,為其傷心,替其感嘆。
總之,在中國的悼亡文學進程中,韋應物以其特有的時間季節感悟和審美選擇、質樸真率的情感、個性自然的創作,為豐富中國悼亡文學的創作實踐、表現手段、審美體驗,貢獻了一份獨有價值的個案抒寫,也為中國悼亡文學的發展,特別是唐宋時期的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彰顯了他在中國悼亡文學史上的地位。
[1]孫望.韋應物詩集系年校箋[M].北京:中華書局,2002.
[2]陶敏,王友勝.韋應物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3]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3.
[4]胡曉明.中國詩學之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5]陶敏.韋應物生平新考[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1998,(1).
[6]西安碑林博物館.韋應物一家四方墓志錄文[N].文匯報, 2007-11-04.
[7]馬驥.新發現的唐韋應物夫婦及韋慶復夫婦墓志簡考[N].文匯報,2007-11-04.
(責任編校:張京華)
I222
A
1673-2219(2012)07-0029-03
2012-5-1
張芳(1971-),滿族,遼寧丹東人,碩士,遼東學院師范學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唐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