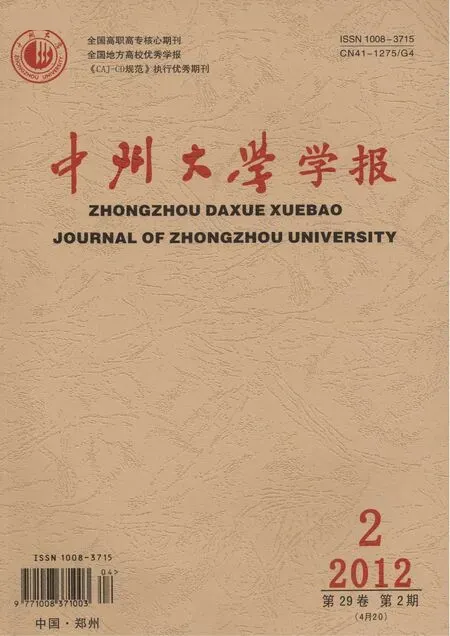評(píng)庫(kù)切的自傳體小說(shuō)《夏日》
王 影
(溫州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浙江溫州325000)
庫(kù)切的每一部新作都會(huì)不同于他的先前之作。他往往能夠涉入讀者極少涉獵的領(lǐng)域,以有限的篇幅帶我們走進(jìn)無(wú)限的感受之中。2009年的《夏日》被稱為繼《男孩》(1997)、《青春》(2002)之后庫(kù)切的又一部自傳體小說(shuō),只不過(guò)這一次,他以一個(gè)研究已故作家?guī)烨械膫饔涀髡呱矸菡归_(kāi)作品,給我們羅列出若干的日記記錄片段以及對(duì)幾個(gè)在庫(kù)切生前與之有所接觸的人的訪談?dòng)涗洠煌谧髌分懈嬷覀兊年P(guān)于約翰性情的拘謹(jǐn),庫(kù)切在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中一直都是極為大膽的,他“似乎敢于做任何事”。自《伊麗莎白·科斯特洛的八堂課》到《兇年紀(jì)事》,再到《夏日》,他在小說(shuō)的形式方面頻頻出新,“敢于把小說(shuō)寫的像論文集,敢于把小說(shuō)寫得支離破碎,敢于把小說(shuō)寫得像回憶錄”。但是,如果說(shuō)寫作旨在喚醒并展現(xiàn)我們內(nèi)心深處相互碰撞的多種聲音——關(guān)于自我、關(guān)于外部世界的聲音,那么無(wú)論小說(shuō)的外部形式怎樣變化,它終究都會(huì)回到一個(gè)問(wèn)題上,即通過(guò)這些文字,它要講述給我們什么?
庫(kù)切正是以此種方式一次次帶我們深入到人內(nèi)心的隱秘之處,引導(dǎo)我們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人類的身體和意識(shí)”,甚至帶我們“深入到非洲的內(nèi)部”。在《夏日》里,他使用一種較為松散的拼貼方式來(lái)完成這種探索,而這種方式更適宜于他的自我表述,或者說(shuō)對(duì)自我內(nèi)心多角度的深度反思。同時(shí),使用他人的話語(yǔ)而不是個(gè)人的直接表述又達(dá)到另一種保持距離的效果,這種距離感使他在談及自己時(shí)頗感自然又很動(dòng)人。如果我們不去計(jì)較一個(gè)小說(shuō)家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有意識(shí)或者無(wú)意識(shí)地添加進(jìn)去的虛構(gòu)成分,而將關(guān)注點(diǎn)集中于庫(kù)切即是約翰的身份,集中于他多少會(huì)有將自己放進(jìn)去的情況,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這些記錄片段和訪談對(duì)話具有一種客觀真實(shí)感。于是,通過(guò)這部作品,結(jié)合他鮮有保留的剖析,我們便有了對(duì)于庫(kù)切更為深入的認(rèn)識(shí)——他寫作的目的和意義,他時(shí)時(shí)拘謹(jǐn)?shù)男郧椋醇みM(jìn)又極具烏托邦色彩的保守政治態(tài)度,他個(gè)人身份的的兩難境地……
一、關(guān)于寫作——何以永恒?
在茱莉亞的眼中,《幽暗之地》是以“種種征服的形式對(duì)殘酷的揭露”,并且“這種寫作的方式是一種自我執(zhí)行的療法”,“一個(gè)自我改造的計(jì)劃,他下決心要阻止自己生活中每一個(gè)活動(dòng)場(chǎng)所的殘酷和暴力沖動(dòng),”“寫作成了某種無(wú)休無(wú)止的凈化過(guò)程”。這實(shí)際上就是庫(kù)切的聲音。有關(guān)“凈化”說(shuō),自亞里士多德以來(lái)出現(xiàn)三種不同觀點(diǎn):一種基于醫(yī)療的模式;另一種基于道德完善的思想;第三種是對(duì)戲劇中能引起憐憫和恐懼情感的事件的澄清,使觀眾從這種澄清中學(xué)到東西。歸結(jié)起來(lái),這些凈化、澄清,都是對(duì)于觀眾或者戲劇本身的情感事件而言。但到了庫(kù)切這里,“凈化”成為了作家本人的凈化過(guò)程和升華過(guò)程,為支撐起個(gè)人生活甚至改造個(gè)人生活的手段和方法,他需要寫作,需要通過(guò)寫作來(lái)拯救自己。作為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南非荒唐境遇的見(jiàn)證者,他動(dòng)用自己敏感的神經(jīng),在讓讀者觸目驚心的同時(shí),也安慰他自己在殘酷現(xiàn)實(shí)中早已深陷無(wú)奈之境的道德良心。
由此可見(jiàn),那些批評(píng)庫(kù)切只是粗淺地診斷出西方社會(huì)的弊病卻并未給出任何治療處方的言論,其實(shí)是不對(duì)的。正如本雅明在《小說(shuō)的危機(jī)》中指出:“小說(shuō)的誕生地乃是離群索居之人,這個(gè)孤獨(dú)之人已不再會(huì)用模范的方式說(shuō)出他的休戚,他沒(méi)有忠告,也從不提忠告。所謂寫小說(shuō),就意味著在表征人類存在時(shí)把不可測(cè)度的一面推向極端。”庫(kù)切用《夏日》實(shí)驗(yàn)著這種極端,并在這種極端中流露他孤獨(dú)本性之中的謹(jǐn)慎、惶惑以及擔(dān)憂——對(duì)自己身上的局限性、對(duì)自己的未來(lái)以及對(duì)自己愛(ài)恨交加的那片土地。但他終究不是一個(gè)柏拉圖式的理想主義者,不是一個(gè)憑借個(gè)人經(jīng)驗(yàn)和強(qiáng)大的想象力為社會(huì)構(gòu)建藍(lán)圖的幻想家。當(dāng)茱莉亞以不同的聲音提出:一本書應(yīng)該是一把斧頭,劈開(kāi)人們內(nèi)心的冰海,約翰將其視為面對(duì)時(shí)間的一種拒絕姿態(tài),面向永恒的努力,超越人的肉身存在的永恒。可見(jiàn),作家的犀利有很多種,而庫(kù)切更愿意像大多數(shù)注重感知同時(shí)又注重思考的人一樣,通過(guò)靠近自我和內(nèi)心挖掘來(lái)展現(xiàn)人性,展現(xiàn)一種社會(huì)情境,乃至一種時(shí)代狀況。至于作品能否對(duì)讀者和世界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這已不是他所能掌控的問(wèn)題。
二、關(guān)于性情——何以拘謹(jǐn)?
約翰闖進(jìn)了茱莉亞的生活,或者說(shuō)被帶入茱莉亞的生活,而且以一種很不恰當(dāng)?shù)幕橥馇榈姆绞健.?dāng)然在茱莉亞看來(lái)不是完全因?yàn)閻?ài)情,甚至根本一點(diǎn)兒都沒(méi)有愛(ài)情的成分,文中使用“友情”一詞來(lái)形容兩人的關(guān)系。但如果說(shuō)他們之間真如茱莉亞所說(shuō)沒(méi)有絲毫的契合,那么也應(yīng)是約翰緊閉自己內(nèi)心的結(jié)果。“他就像是一個(gè)玻璃球”,“他的那顆心通常都是裹在鎧甲里面的”。在約翰身上,我們自始至終都能感受到一種拘謹(jǐn)——凝結(jié)到性情里的拘謹(jǐn),一種羞怯于表達(dá)極度敏感之心的小心翼翼。這不僅僅表現(xiàn)在他與茱莉亞的接觸中,還有在瑪格特的心目中,約翰也一直是一副未展開(kāi)的模樣。他緊緊地保留著自己,保留著他對(duì)于家人、家族乃至整個(gè)國(guó)家的愛(ài)與恨。但對(duì)于讀者,他的孤獨(dú)清晰可見(jiàn)。從《青春》中“每一個(gè)人都是一座孤島”,到《夏日》中“很少也很難敞開(kāi)的心懷”,約翰使茱莉亞、瑪格特困惑……而且還將會(huì)繼續(xù)困惑以后接觸到他的人。他們彼此認(rèn)識(shí)、理解都已經(jīng)很久了,但是他們卻不能牢固地契合。
這些與約翰有著交集的女人們,都異常一致而且堅(jiān)定地認(rèn)為他的生活中需要一個(gè)人,一個(gè)可以照顧他的人。而他真的需要嗎?在評(píng)論戈迪默時(shí),庫(kù)切說(shuō):她作品中的南非白人“都生活在薩特所指的不誠(chéng)實(shí)中,騙自己說(shuō)他們不知道究竟發(fā)生什么事,她的任務(wù)是把真實(shí)世界的證據(jù)擺在他們面前,粉碎他們的謊言。”庫(kù)切筆下的約翰也成了一個(gè)這樣的人,沉湎在對(duì)舒伯特的幻想之中,茫然于與周遭的人和事的平常而基本的交流,他以想象的方式理解女人,并將自己構(gòu)想出來(lái)的浪漫意象安放到他遇到的人身上,甚至為此暗自欣喜,直到被想象的對(duì)象逼迫其清醒起來(lái)。茱莉亞是討厭其緊閉的不愿敞開(kāi)的內(nèi)心,還是看到了他的這種不真實(shí)?
阿德瑞娜也一樣不理解約翰關(guān)于愛(ài)情的幻象。但是,“如果我們認(rèn)同某個(gè)人們以理想之名行事的世界,在倫理上要比這個(gè)人們以利益之名行事的世界更優(yōu)越。”約翰頭腦里詩(shī)意的世界或許并不適合認(rèn)同現(xiàn)實(shí)里的人們,但對(duì)于他自己,那是另一種真實(shí)。在這種幻化的真實(shí)里,他的性情得到舒展,他的生命得到自由。
三、關(guān)于自我——只身向何處?
“對(duì)于這個(gè)具有百年的剝削暴力以及令人心寒不安的貧富懸殊之歷史的國(guó)家,他極為厭倦,厭倦它每天對(duì)他們的道德良心提出的要求。”《夏日》開(kāi)篇1972年至1975年的筆記中,首先就記錄了他回到南非看到報(bào)紙報(bào)道的慘絕人寰的槍殺,對(duì)此他憤怒,又覺(jué)得“一回來(lái)就得沾惹上這東西,有一種被玷污的感覺(jué)”,但激憤和憎恨之后也只能陷入木然和無(wú)奈了。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呢?陷在這種特殊環(huán)境造就的道德里,他被一種沖突折磨著,一方面作為不公正的目擊者,誰(shuí)也不能對(duì)此熟視無(wú)睹;另一方面,他在不能熟視無(wú)睹之后深感無(wú)力,他該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在茱莉亞、阿德瑞納不理解甚至厭惡約翰種種不合時(shí)宜的性情之時(shí),與之有著很多相通之處的瑪格特表姐對(duì)于表弟約翰的這種不真實(shí)則更多表示一種揮之不去的同情和憐惜。因?yàn)樗麄冎g有過(guò)相互坦誠(chéng)的童年,還以為可以天經(jīng)地義地跟對(duì)方結(jié)婚。她和約翰不僅有著相通的地方——血脈、親情、友誼,還有著共同需要面對(duì)的人和問(wèn)題——庫(kù)切家族、默韋維爾、卡魯?shù)貛酥琳麄€(gè)國(guó)家。“是誰(shuí)想出這主意來(lái),在這兒修建公路,鋪設(shè)鐵路,建造城鎮(zhèn),引來(lái)人群居住,然后又把他們困于此地,往他們心里鉚上釘子?”“我們?cè)谑澜绲倪@一角不毛之地干什么?如果說(shuō)生活在這兒的人生毫無(wú)意義,如果人類在這兒的整個(gè)生存一開(kāi)始就是一場(chǎng)惡作劇,我們?yōu)槭裁催€要以枯燥的勞役在這兒消耗生命?”這不僅僅是瑪戈特和約翰的問(wèn)題,更是庫(kù)切的問(wèn)題,接下來(lái)還有面對(duì)這樣的問(wèn)題他又該怎么辦?
馬丁提到自己和約翰這類人的存在“根植于一種罪惡,即殖民征服,通過(guò)種族隔離而被永久固定下來(lái)”,而在自己的感覺(jué)之中,他們只是“寄居者”,是“臨時(shí)住戶”。在這個(gè)意義上,他們是“沒(méi)有家的”,“沒(méi)有故土”,而這種在自己的情感中所培育的“臨時(shí)觀念”,使他們“不愿意對(duì)這個(gè)國(guó)家投入太深”,因?yàn)樗麄兊耐度胧恰鞍踪M(fèi)功夫”的。傳記作者由此追問(wèn)庫(kù)切的這種臨時(shí)觀念是否已超越了自己的出生地與自己的關(guān)系?顯然庫(kù)切生活的其他方面是受其影響的。當(dāng)他疑惑于心里的這份不安定,當(dāng)他不認(rèn)可自己在這片土地上的所屬關(guān)系,所有的情感處理中也都夾雜上了這些不愿完全投入的成分。于是他即便憤怒于眼見(jiàn)的暴力和不公正也終究在無(wú)奈中平靜下來(lái);即便對(duì)人懷有某種真情卻也只愿意在某一刻流露之后便倉(cāng)促收回,洶涌的情感只能在寫作中得以宣泄,并成為自我延續(xù)的方式。
沉迷于幻象的約翰,在政治立場(chǎng)上有著濃厚的烏托邦色彩。他覺(jué)得“政治激發(fā)了人性中最壞的一面”,也“把社會(huì)最壞的一面表現(xiàn)出來(lái)”,于是他期待著“有一天政治和國(guó)家都走向消亡”,在人與人之間他傾向于一種老派的原始的安寧和睦關(guān)系。
作品最后,一切都以父親的形象幻化出來(lái)。回來(lái)之后,令他吃驚的是發(fā)現(xiàn)父親大有變化,他想去握住父親顫抖的無(wú)助的手,想要父親借往昔的享樂(lè)而變得心情愉悅、重拾丟失的青春,可他們不能一直住在一起,體驗(yàn)所謂的相濡以沫,他不屬于這里,不屬于父親所在的這個(gè)世界,猶如父親和南非并不能理解他一樣。于是,當(dāng)面對(duì)身患重病的父親,他需要放棄自己的一切事務(wù)去擔(dān)當(dāng)一名護(hù)士時(shí),他突然變得焦慮萬(wàn)分——“我做不來(lái)這個(gè)”,他說(shuō),“我不能面對(duì)日夜看護(hù)你的前景,我要扔下你了,再見(jiàn)了。”從南非到英國(guó)、美國(guó),再到澳大利亞,庫(kù)切真如他之前所說(shuō),最好與自己相愛(ài)的一刀兩斷,切開(kāi)自己傷口愈合的希望。而回想起拘謹(jǐn)?shù)募s翰所沉迷的舒伯特蓬勃向上的幻象,這種決絕的背后又藏著多少的悲哀與絕望。如今這片他生于斯長(zhǎng)于斯的土地被病痛扼住了咽喉,他一個(gè)合法卻不合理的單薄之人能做些什么?他在那些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很重要的人看來(lái)又如何呢?
他同作家迪戈默一樣苦苦掙扎在泥潭之中——這就是“為一個(gè)民族寫作、為他們而寫和代他們而寫、被他們讀,意味著什么?”約翰帶著庫(kù)切,被一種難以言說(shuō)的感覺(jué)主宰著,猶如放棄想象的堂吉訶德不再尋求行俠仗義而回到單調(diào)的生活中,最終“走向黑暗,沉入他內(nèi)心的苦井”。
[1]庫(kù)切.內(nèi)心活動(dòng)[M].黃燦然,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
[2]庫(kù)切.異鄉(xiāng)人的國(guó)度[M].汪洪章,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
[3]庫(kù)切.夏日[M].文敏,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
[4]先剛.德國(guó)浪漫派的“哲學(xué)觀”[J].學(xué)術(shù)月刊,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