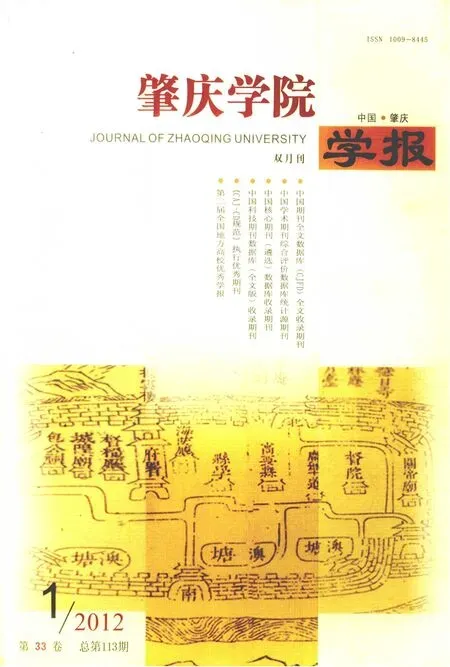原形偏正結構的語序類型
徐天云
(肇慶學院 文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一、原形偏正結構中心成分的語義功能
對于偏正結構構成成分的語義關系,語法學界一般都著眼于兩個成分之間的組合關系,認為修飾成分是揭示中心成分屬性的。例如,周國光(2002)就認為:“在定中結構中,定語都是表示中心語的屬性的。”[1]15而徐天云(2010)則根據構成成分與偏正結構之間的構成關系,認為修飾成分并不都能揭示中心成分的屬性。修飾成分能否揭示中心成分的屬性要看中心成分的類別情況:當中心成分表示范疇或是參照的意義時,修飾成分揭示的不是中心成分的屬性特征,而是偏正結構的屬性特征。例如,在偏正結構“女明星”中修飾成分“女”揭示的并不是“明星”的性別特征,而是“女明星”的性別特征。“女明星”由于有了“女”這樣的性別特征,就可以與同范疇的“男明星”互相區別開來。再比如,“西太平洋”的“西”也只是揭示了偏正結構“西太平洋”的方位特征,而不是揭示了中心成分“太平洋”的方位特征。而只有當中心成分表示原形意義時,修飾成分揭示的才是中心成分的屬性特征[2]12。
在某些偏正結構中,修飾成分的語義功能在于從某個角度描寫說明中心成分,使中心成分中已有的某個隱性意義特征顯性化,結果在所指對象上形成中心成分與偏正結構等值的情況。在這種結構中,中心成分不能作為給修飾成分分化或異化的語義基礎,而只是作為后起偏正結構的初始形式出現。我們把中心成分表現出的這種功能稱作原形,把中心成分的語義功能為原形的偏正結構稱作原形偏正結構。例如,偏正結構“廣東粵劇”中修飾成分“廣東”揭示了中心成分“粵劇”的來源特征,而這個來源特征本來就包含在其原形——“粵劇”當中,造成“廣東粵劇”同“粵劇”所指相同的結果。在“廣東粵劇”中,“廣東”的語義功能只是用來使這個劇種原來已經包含在原形中的來源特征顯明化,而不是從來源角度把“廣東粵劇”與其他“某某粵劇”區別開來①當“廣東”揭示的是“廣東粵劇”的來源特征時,“粵劇”是原形,此時“廣東粵劇”在來源范疇里沒有對立項;當“廣東”揭示的是“廣東粵劇”的流傳地域特征時,“粵劇”是內涵范疇,此時“廣東粵劇”在流傳地域范疇里與“廣西粵劇、香港粵劇”成為對立項。。這種情況在詞法結構中表現得更為典型。例如,“前額”與“額”指稱的意義完全相同,“前”的作用在于明確“額”的方位在頭的前部,而且這一方位語義特征早就隱含在原形“額”的意義中了。“簡”與“"竹簡”指稱的意義完全相同,“竹”的作用在于明確原形“簡”的質料,而且質料的語義特征早就隱含在原形“簡”的意義中了②朱德熙把體詞性偏正結構分為粘合式和組合式兩大類。從實際用例看,朱先生在粘合式偏正結構中并沒有進行嚴格的句法和詞法區分,本文遵循朱先生的處理意見,對偏正結構持廣義的理解。。
在源流關系上,中心成分指稱對象已經具有完足性,由其構成的偏正結構在指稱對象上并沒有變化,只是它的后起羨余形式。添加修飾成分(附加成分)的作用是把所指對象的某個特征凸顯出來,給所指對象做明確的歸類,后起的羨余形式比其原形具有更強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4]63-99[5]37-46。例如,對于原形“背”和后起羨余形式“后背”來說,二者所指具有一致性。而“后背”憑借“后”把“后背”在人體中的位置特征凸顯出來①“壽星”指長壽的老人,說成“老壽星”只是把年紀大的特征凸顯出來了,在意義上“壽星”與“老壽星”具有等值關系。相對來講,“壽星”是“老壽星”的原形,“老壽星”是“壽星”的后起羨余形式。后來“壽星”又引申出被祝壽的人的含義來,相應出現了與“小壽星”相對的“老壽星”。但這個意義上的“老壽星”是指“被祝壽的老人”,與作為后起羨余形式的“老壽星”完全不同。同類的例子還有“車輪”等。。
二、原形偏正結構的語序類型
對原形偏正結構可以從許多角度進行分類,例如,根據中心成分的組配能力可以把原形偏正結構區分成中心成分能單說和不能單說兩類。偏正結構中的原形中心成分有些能單說,例如“船艙”能單說“艙”,“農田”“娘舅”能單說成“田”“舅”;有些不能單說,例如“輪輻”的“輻”不能單說,“火炬”“鼻涕”也不能單說“炬”“涕”②這里的“能單說”“不能單說”是從共時角度講的。從歷時角度講,有些現在不能單說的歷史上曾經是可以單說的,例如“火炬”曾經可以單說“炬”,“芹菜”曾經可以單說“芹”。但另外一些則是從來不能單說的,例如“卡車”從來不能單說成“卡”,“雞尾酒”也從來不能單說成“雞尾”。。根據原形中心成分與修飾成分所在的相對位置,則可以把偏正結構分成前偏后正的前加式和前正后偏的后附式兩種不同的語序類型。每種語序類型下面又可以根據修飾成分與中心成分之間的語義關系分成更小的類型。
(一)前加式原形偏正結構
這種順序的原形偏正結構符合偏正結構一般說明成分在前中心成分在后的情況,只是其中心成分起不到“范疇”或“參照”的作用,而只是作為偏正結構的“原形”出現的,其構成格式為“修飾成分+原形中心成分”,例如“堂奧”“后背”。但前加成分揭示原形的角度不同,“堂奧”揭示“奧”所存在的物體是“堂”,“后背”揭示“后背”所在的方位是"后"。在前加式原形偏正結構中,前加成分從多個角度揭示了中心成分的屬性特征。根據前加成分與原形成分的語義關系,我們對出現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 《常用構詞字典》中的前加式原形偏正結構進行了窮盡性的分類統計,統計結果如表1:

對于這個表格,需要說明幾點:
1.在這種語序結構中,語義類型較多,共有“位置、承載物、功用、質料、形態、方面、物類、歸屬、附載物、品質、規模、地位、根據、結果、時間、方式”等16種類型。在16類中,沒有絕對優勢的類型,成員最多的“位置”類也只有17個成員。
2.雖然都是“承載物”,但是,“堂奧”“骨髓”有所不同,“堂”同 “奧”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骨”與“髓”是承載物與被承載物之間的關系。
3.“老嫗”“原籍”雖然都屬于“時間”類,但是,表示時間的角度又有所不同,“老嫗”側重于絕對時間段的持久,“原籍”側重于相對時間順序的在先。
(二)后附式原形偏正結構
后附式原形偏正結構的構成格式是“原形中心成分+修飾成分”。后附式的修飾成分雖出現在后面,但同樣起著說明中心成分的作用,例如,“剪刀”的“刀”在于說明“剪”是一種刀具,“星球”的“球”在于說明“星”在形狀上是球狀的。
根據修飾成分同中心成分的語義關系,后附式原形偏正結構的類型情況如表2:
對于表2,需要說明以下幾點:
1.在這種語序結構中,語義類型較少,只有“物類、形態、單位、身份、功用、位置、承載物、附載物”等8種類型。在8種類型中,“物類”是絕對優勢的類型,占到這種結構總數的78.6。可見后附式結構主要是通過凸顯偏正結構的所屬類別來說明其特征的。“形態”“單位”也不少,三個類別加起來可以占到這種結構總數的95.1%,所以前三類為優勢類型。
2.“胞衣”并不屬于衣服,而只是因為胎盤有衣服一樣的包裹遮蔽作用,所以才用“衣”來解釋這種功用特征。“乳房、法網”與此同類。
3.“蠶蟻”并不屬于蟻類,而是剛孵化的幼蠶,因為體型小,類似螞蟻,所以歸入“形態”一類,而不是歸入“物類”一類。“偶人”也并不是人,而是形狀類似人的土偶。其他“露珠、舵輪”與此相同。
4.對于帶方位詞的后附式偏正結構格式“中心成分+方位詞”,中心成分一般都是起參照作用的,例如“國外”是一國之外,“城外”是城市或城墻的外面。“郊外、野外、天上、地下”是例外,“郊外”并不是城郊的外面,“野外”不是野的外面,“天上”不是天的上面,“地下”也不是地的下面。前兩者都是古代土地區劃“城郭郊野”中的一部分。“郊外、野外”的“外”都是相對于參照“城”說的,是說“郊、野”都在城的外面。
5.“閻羅”是梵語 Yamarāja音譯“閻魔羅阇”的簡稱,意思是“地獄之王”,后來在漢語中添加了表示身份的“王”字成了后起的羨余形式“閻羅王”,簡稱為“閻王”。“閻羅王”還原為“閻羅”意義仍然明確,而“蜂王、猴王、板爺、的哥”如果縮略成“蜂、猴、板、的”就不成立了。

根據我們的統計,在《常用構詞字典》中可以認定為偏正結構的詞語共12416例,原形偏正結構共590例,占偏正結構總數的4.8%;其中前加式結構共16類93例,后附式結構包括8類467例。如果只計算前加式原形結構,那么,所占比率要低得多,只占偏正結構總數的0.75%;如果只計算后附式原形結構,那么,所占比率還是很可觀的,要占到偏正結構總數的3.76%。
對于原形偏正結構,以前在理論界只提到有限的語義關系類型,最早只是用“大名+小名”格式和“小名+大名”格式來概括。例如,俞越在《古書疑義舉例》中己經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古人之文,則有舉大名而合之于小名,使一字成文者。如《禮記》言‘魚鮪’,‘魚’其大名,‘鮪’其小名也。《左傳》言‘烏鳥’,‘鳥’其大名,‘烏’其小名也。《孟子》言‘草芥’,‘草’其大名,‘芥’其小名也。”而“大名+小名”格式和“小名+大名”格式只相當于“物類”一種類型。孫常敘(1957)在“后附成分的詞根造詞結構”中提到的“鯉魚、紙張、明晃晃”也只相當于“物類、單位、形態”三種類型[6]39,而我們的研究表明,原形偏正結構的結構類型要豐富得多,包括物類、形態、身份、單位、功用、位置、承載物、附載物、質料、方面、歸屬、品質、規模、地位、根據、結果、方式、憑依、時間共19種類型。
三、對兩種原形偏正結構的共時、歷時分析
在兩種語序的原形偏正結構中,前加式結構由于在語序上同大多數偏正結構具有一致性,所以認定起來不成問題。后附式結構由于在語序上同大多數偏正結構不一致,所以引起了爭議。
有些學者明確表示偏正結構中存在后附式結構,例如,劉云泉(1984)認為后附式結構是后一語素對前一語素從性質、程度、范圍、用途等方面加以限制,因此,都是前正后偏式偏正結構,例如“雪花”是通過比喻關系用“花”來比喻“雪”[7]108。楊錫彭(2002)不贊同這種看法,他認為:1.漢語結構中表示性質、狀態、范圍、用途的成分也可以作為偏正結構的中心成分,例如“花的嫵媚”、“大海的寬闊”;2.“雪花”同“火花、血花、油花、燈花、豆花、鋼花、禮花”一樣都是以“花”的形狀特征借代“像花的東西”作為中心成分;3.從復合詞內部結構看,“燈花、豆花、鋼花、禮花”與“雪花”的結構相同,是通過“雪”的被替換而形成的,因此,后附式結構都可以統一看成前加式結構[8]159。
我們認為,“花的嫵媚”、“大海的寬闊”都有偏正結構的標記“的”,“的”是把偏正結構與非偏正結構區別開來的明顯標記。“雪花”由于結構、語義的整體性,沒有用虛詞做標記來加以區別,兩者之間沒有可類比性。但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二者的分歧在于認識問題的出發點不同。
楊錫彭的說法是基于共時構詞法分析的結果。語言的主流部分是強勢的,會把自己的規則類推到弱勢的非主流部分上,即用主流語言結構的成分關系和成分功能解釋非主流語言結構的成分關系和成分功能。漢語偏正結構的主流是前加式的,所以,到秦漢時期小名冠大名語序取得絕對優勢,成為主導的甚至唯一的語序,而原來的大名冠小名語序則趨于消亡,《山海經》中的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名全部使用小名冠大名語序正反映了這一時期的語言現象[9]34。對于語言使用者來說,既然“火花、血花、油花、燈花、豆花、鋼花、禮花”都是前偏后正的結構,那么“雪花”在格式上就可以同樣看待。“油花”是由油形成的像花一樣的東西,“雪花”也不過是由雪形成的像花一樣的東西,所以二者通過類推合而為一,中心成分“花”被用來統一揭示“火花、血花、油花、燈花、豆花、鋼花、禮花”以及“雪花”的類屬特征。后附式結構可以同樣處理。“金魚”“帶魚”“青魚”的“金”“帶”“青”可以揭示“金魚”“帶魚”“青魚”的屬性特征并彼此區別開來,“鯉魚”的“鯉”雖然不能揭示“鯉魚”的屬性特征①因為“鯉”本身就是“鯉魚”,而事物本身解釋不了自己,所以“鯉”不能揭示“鯉魚”的類屬特征。,但“鯉魚”有了“鯉”卻足以在魚類中同“金魚”“帶魚”“青魚”等區別開來,就像“奧斯卡獎、魯班獎、神舟飛船、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林國榮大學、瑞星公司”等詞中的“奧斯卡、魯班、神舟、北斗、林國榮、瑞星”等區別性成分一樣,都是指稱某類事物的名稱。既然沒人懷疑“奧斯卡獎、魯班獎、神舟飛船、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林國榮大學、瑞星公司”偏正結構的屬性,那么認定“雪花、鯉魚、佛爺、蒜頭”是偏正結構也是有理由的。
劉云泉的說法則是基于歷時構詞法分析的結果。受到偏正結構主流形態的影響,人們確實會不自覺地把“雪花”看作與“銀耳、火柱、海米、暖流”同樣的前偏后正的結構,由這種認識出發,就會類推仿造出像“火花、淚花、血花、油花、燈花、豆花、鋼花、禮花”一類的詞。然而,不能逆推“雪花”也是用“雪”來修飾“花”的前偏后正結構。從動態的發展過程看,“雪”存在于先,為了在形態上進一步進行說明,才會在其原形的基礎上進一步添加“花”去修飾“雪”,才形成“雪花”。
后附式偏正結構古已有之,據此楊伯峻(1963)在《文言文法》中提出″附加語置于中心語之后″的定語后置說[10]22-78。今天在詞法領域存在的后附式偏正結構與古代漢語在句法領域存在的后附式偏正結構是有傳承關系的。這一結構在類型、組成成員上后世雖然有一定的調整,但后附式偏正結構作為一種構詞格式在后世并沒有消失,有些格式,例如后附物類的格式,到目前還是能產格式。例如在翻譯時用后附物類的格式把Eden、Champagne、force、bar翻譯成“伊甸園、香檳酒、語力、酒吧”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再如:
根據美軍所述,由于前一階段中國軍隊進攻中的消耗很大,目前正在試圖退回三八線以北的山地地區(《現代漢語詞典》:山地,多山的地帶。)獲得補給和補充。(薩蘇的新浪博客《紀念抗美援朝六十周年之血斗種子山》)
由陸地生物資源利用調轉向海洋水域 (《百度百科》:地球表面被陸地分隔為彼此相通的廣大水域稱為海洋。)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創建陸地水域并舉的新農業。(CCL語料庫之 《人民日報》1995年11月份)
其中的“山地地區”、“海洋水域”替換成“山地”、“海洋”并不會造成歧義,就在于替換形式與被替換形式之間具有一致性,“地區”、“水域”的功能不過是進一步說明“山地”、“海洋”所屬的物類。
在包含原形的結構中,無論是前加式還是后附式,附加成分的功能都是補充說明其所附加的另一個成分的。在以往的詞法研究中,既然可以根據修飾成分與動詞性中心成分的關系把偏正結構分成狀中結構和動補結構兩種語序類型,那么我們也有理由根據修飾成分與名詞性中心成分的關系把偏正結構分成前偏后正的定中結構和前正后偏的中定結構兩種語序類型;前加式原形結構既然被認為是偏正結構,后附式原形結構也有理由被認定為偏正結構。前加式、后附式語序不同,語義功能相同,這又充分說明決定偏正結構關系的第一要素不是成分之間的語序,而是成分承擔的功能。明確這一點,不但有助于厘清研究的范圍,也有助于消除以往理論上的一些混亂。
原形偏正結構既是組配語句的現實單位,又是語言歷史的積淀物。要了解真相,既有必要進行靜態的結構分析,又有必要回到原初狀態中去做動態的源流分析。單純的共時分析或者歷時分析都會有失偏頗。
[1] 周國光.現代漢語的語義屬性系統[J].世界漢語教學, 2002(2).
[2] 徐天云.修飾范疇語法意義的過渡性和語法形式的聚合性[J].漢語學習,2010(3).
[3] 朱德熙.語法講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4] KEENAN E L,COMRIE B..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and universal grammar.Linguistic Inquiry 8,1977:63-99.
[5] BENJAMINS J..Inferring Identifi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In Thorstein Fretheim and Jeanette K.Gundel(eds.), Reference and Referent Accessibility,1996:37-46.
[6] 孫常敘.漢語詞匯[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
[7] 劉云泉.現代漢語構詞法中的前正后偏式[J].杭州大學學報,1984(增刊).
[8] 楊錫彭.論復合詞結構的語法屬性[J].南京大學學報, 2002(1).
[9] 羅琦.《詩經》中的“木”字和“瓊”字[J].貴州文史叢刊, 2003(2).
[10] 楊伯峻.文言文法[M].北京:中華書局,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