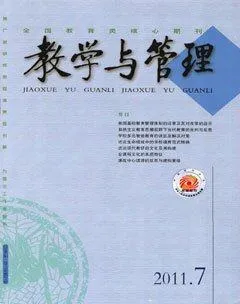課改中心話語的反思與建構策略
“課程話語”是在課程研究領域,通過對特定主題展開言談,推論性地形成課程意義的語言。“課改中心話語”即是在課改中出現的圍繞特定主題形成的有意義的語言。對課改中心話語的反思有助于領悟隱含于課改話語背后的課程思想,激活課程理論工作者對課程的思維,將研究視線更多地投向學校、教師等微小的空間,關注教師、學生及他人的日常生活。在實踐層面上,有助于課程研究者反思并改善其研究工作,也有助于課程實施者改變傳統的教學規范。
為了更好地進行課程改革,我國正大量地引進國外的課程話語。不可否認,對世界各國課程理論的研究豐富了我國的課程話語體系。但是,一種課程理論與話語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往往受制于它所處的時代、國度和社會,它在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國度,另一個社會是否同樣適用,值得商榷。大批量外來課程話語的引入,甚至逐漸成為進行課程理論研究的一種思維和行為習慣,西方的歷時性課程話語以共時性特征出現在課改話語中,而且大部分都是“復制”、“快捷”和“生搬硬套”。在國內課程領域對本土和傳統課程話語的追溯和解讀并未形成氣候的狀態下,過多國外課程話語的引進,不僅會造成對西方課程話語的假性解讀,而且會使課程改革陷入困境。在對待國外課程話語這一方面,筆者認為應秉承以下觀點:
一、立足本土打破話語霸權
自從新課程改革以來,我國的課程話語經歷了“醞釀”、“全新”、“轉向”和“反思”四個階段。[1]其間出現了大量新的課程話語,但縱觀這些話語,仍然沒有擺脫對西方話語的依賴,尤其是“山姆大叔”的那套課程話語在中國大地上依然獨尊于霸權地位。致使我們的課程理論界,恨不能把傳統的教育理論徹底顛覆,以西方話語取而代之,以致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課程改革也陷入了困境。教育學要國際化、與世界接軌,難免要借鑒其他國家的話語。但我們在汲取外國經驗的同時又要防止西化,失掉自己的聲音。所以“拿來主義”并不代表要失掉自我,惟西方霸權是聽,打破霸權謀求話語一定程度的“地方性”、“相對性”和“本土色彩”才是中國課程改革的出路。
1.珍視傳統話語
美國學者希爾斯在其專著《論傳統》一書中說,人類永遠生活在自己創造的文化傳統和文明歷史中,而不是置身其外。事實上無論我們自己多么現代化,無論我們世界多么全球化,我們都不能忘卻自己來自何方,都不能拋棄自己文化認同的根。[2]改革絕不是一切更新、從零開始的,不是簡單的推倒重建、而是在原先取得巨大成果的基礎上,開拓創新并進而完成歷史性的超越。我們的新課改也是一樣,盡管不能簡單地說新課改全盤否定了傳統的文化積淀,但在教育過程上的確忽視了對中國教育文化的繼承。我國的基礎教育確實存在許多問題,如過于注重知識的掌握、學科之間缺乏聯系、課程與學生的生活聯系不緊密、教學方式過于單一、課程評價過分強調甄別和選拔功能、課程管理過于集中;我國的基礎教育也確實需要改革,但決不能依靠徹底推翻原來的課程話語體系。任何教育理論都有其生長的土壤,都是其母體文化內涵的反映。脫離了理論的本源去謀求超越是不可能實現的,要在發展的途徑上調節新課改與傳統教育文化之間的和諧,實現過程與結果、途徑與目標的均衡。當然只依靠傳統閉目塞聽,故步自封,拒絕接受外界先進的思想和經驗,是很難適應現代世界發展的,也很難融入世界現代化的潮流。傳統和現代是不可分離的,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本身就是一種互動的關系,現代性是傳統的和現代的思想、價值及行為的一種特殊融合;傳統也可以成為現代意識和行為的準則,并賦予現代行為以合理性。反之,現代化對傳統觀念有一定的信賴性,并經常需要傳統觀念的支撐。
2.消解霸權話語
話語與權力之間有著不可割裂的聯系,國家教育體系在話語權力的運作過程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使社會在一整套界限與框架中使話語儀式化,并確定言說主體應當具有的資格,促成教條群體的形成,從而在把個人束縛于某種話語類型的同時禁止他占有和使用其他話語類型以便其成功地規范話語的使用和傳播。西方現代化教育理論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論”色彩,把西方教育作為現代教育的典范,有意無意地用西方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來批判和代替我國的傳統教育,這是現代化教育的誤區,很可能把我國優秀的教育傳統拋棄了,而被西方的霸權話語所規約。更有可能把不適合中國現實或者已被證明在西方也不成功的東西,當作現代化的因素接受過來,這樣只能結出“現代化”的怪胎,而無助于教育現代化的發展。在“歐美”課程話語占據主導地位的教育學和課程領域,我們會發現:難以理解、晦澀拗口的現象學、存在主義、解釋學、后現代哲學等與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殊途同歸。而現在的課改話語中卻看不見我國本土的字眼,信手拈來均可見西方的詞句、歐美的言語。這使得課程專家惟西方是聽,把原本可以用我們的語言表達清楚的東西偏要往人家的話語上靠,使課程實踐者不明白課程專家所講的意思。而事實上,在現代西方社會,思想文化多元,各種不同的流派及思潮從各方面對現代西方文化提出了挑戰。西方自身的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分解主義、語言學、符號學、新馬克思主義等等,都對來自西方社會文化傳統內部的批評、反思運動蓬勃興起,西方思想家們在開始懷疑自己關于普遍性的假定,衡量文化沒有普遍絕對的評判標準,文化標準的多樣性增加,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內在的價值,每個文化的獨特之處都不會相同,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尊嚴和價值觀,一切評價標準都是相對的,來自不同傳統、民族和歷史的文化成為考慮的標準,這就奠定了西方與中國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對話、相互影響的基礎,它帶給我們的必然是文化價值的多樣化和不斷增加的豐富的前景,因而中國教育學用不著非要完全跟著西方跑,也用不著非要從西方教育學的“話語”中才能找到靈感,找到共同語言。
二、立足現實生成話語方式
話語方式反映著思維方式,話語方式的界限意味著思維的限定,話語方式的貧困意味著思維的停滯。思維的行為依靠對事情的結果有一種參與其事的感覺,從此產生一種關于思維的自相矛盾的話。思維發生于偏私,要完成思維的任務,必須具有一定的超脫的不偏不倚的態度。[3]與思維方式同出一轍,話語方式蘊含著世界觀、價值觀的獨特性,不存在絕對的中立。思想和話語方式都是不可能以觀念的形式從一個實在傳給另一個實在。話語方式更要求對話語現實有一定的參與,與事件進程融為一體。基于此,生成話語方式必須打破西方話語霸權,批判地借鑒國外的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梳理我們傳統的思想,以本土化的方式澄清。
1.關注現實話語情境
人在社會文化情境中接受其影響,通過直接地跟他人的交互作用,來建構自己的見解與知識。同樣,人也要在一個實際的情境中才能形成一定的思維方式。話語方式作為思維的外部表現同樣產生于情境。情境具有引起思維和話語方式的性質,也就是說,任何話語方式都不是孤立地產生的。更進一步說,話語方式必須在賦予其意義的整體環境、相互關系中對其進行審視。課程本身就不是一個靜止的、完全預設、不能變更的教育要素。課程內在的價值只有師生在課程實施過程中,在與特定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的能動作用中才能實現,課程話語的發展也才能在現實情境中找到具有生成意義的語境和發展的原動力。如李吉林在其教學的現實境況中發展了“情感教學”,這不僅與羅杰斯的情感教學不謀而合,而且來自本身的教學需要,更是基于課程理論發展的趨勢,希望、抵抗、感悟、新奇、興奮、困惑、樂觀、悲觀等復雜的情感話語融于其中,致使在課程領域內部,真實地將人的身體、心靈、欲望等直接與課程內部的制度、實施、評價、發展等緊密聯系起來。現實中不可忽視的是關系,而不是事物。不管是自我、事物還是現象都不應被視為是從他人、歷史、背景、行動中剝離出來的對象,關系無處不在,它是實在的存在。
2.生成本土話語方式
任何話語方式都是在特定的語境下產生的,都與所處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程度、文化相關。眼下西方語境下的立場、推論、言論充斥著課程改革,西方思維方式下的理論、判斷、意見、價值觀控制著教育現實,給現實造成過多的麻煩和壞處,顯然用西方語境下產生的話語方式來闡釋中國的教育問題是無效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教育需求與實施條件,自然也就需要“地方性”的話語方式來闡述。而“本土性”的話語方式生成于一定的文化現實情境之中,例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作為杜威的學生,陶行知看到“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把生活從屬于教育,把社會縮小進學校,這樣的理論在中國是沒有出路的,生活教育是生活的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人們要過健康的生活,就須有健康的教育;過勞動的生活,就有勞動的教育;過科學的生活,就有科學的教育;過藝術的生活,就有藝術的教育。所以說生活教育是用生活來教育“也就是為生活而教育”。可見真正在中國教育界產生影響的教育學話語必然是經過“本土化”的。教育學本身就不是一個可以放到顯微鏡下觀察清楚的客觀對象,諸如教育本質、教育價值、教育意義等等都不是純客觀的研究對象,與其說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是一種精確的事實描述,不如說是一種態度的表達,它們直接關涉個人的體驗與期望,必須放在情境中有聯系地對待。在深入了解現實教育情境的基礎上,從傳統中、歷史中挖掘、開采被埋沒的有意義的話語方式。不生成自己的話語方式,就無法與西方教育學進行對話與交流,就無法形成中國特色的教育學。[4]
三、立足實踐重構話語體系
課程話語的意義最終生成于課程實踐之中。正如施瓦布曾經提出的主張恢復“課堂話語”的議論,他闡述到由于課程改革的推廣,“理論方式”的話語與知識滲透于整個課堂,教師們的“實踐方式”的話語與知識處于“瀕死”的狀態。[5]而教師在大量課程實踐中不僅積極探索與積累著新的知識、經驗,而且創造了可以言說的或不可言說的教育教學智慧和大量鮮活的實踐性話語。這些話語反映了教師在課程實踐中的廣闊視野、豐富的想象力和創新能力。同時也是教師走向專業化發展的起點,是課程話語發展的主要源泉和推動力。故而,話語體系的建構也要立足于實踐之上。一套課程體系如果其話語邏輯與理性化程度遠離課程實踐、遠離教師,就會處于被束之高閣的尷尬境地,很難有所作為。眾所周知,蘇霍姆林斯基的理論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所舉的大量生動鮮活的事例更是立足實踐,在教育理論界的知名度和美謄極高。
1.崇尚話語實踐
課程話語已不再是“價值中立”的“課程產品”或僵硬的“學校材料”的載體,而是傳遞和再創課程意義的過程。對實踐性課程話語的重視并非是一個讓理論進入實踐的問題,而是需要重新構想的實踐與理論彼此嵌入的問題。其核心并不在于是否應由理論性或實踐性課程話語統治整個課程話語世界以及探究發展,而在于在課程話語的產生和實踐中使人們產生一種敏感意識,更好地將多種類型的課程話語進行彼此的嵌入和溝通交流。因而經驗和意義的生成是在開放的、持續的交往活動中尋求的。[6]但現在課程實踐中的話語體系由于受到太多的限制而不能去真正地理解問題,更確切地說,就是不能理解課程話語本身真實的涵義和價值。每一個教育實踐者,直接面對教育原初的真實生活,以直接的、交互的、生活的態度走近教育,理論者只有走進教師、學生以及參與真實的教育實踐才會讓理論與實踐的視域實現融合,讓話語體系展現出動態、開放、深厚和豐富的意義。教師和學生也要成為專家,是他們自己的情境中的知識的專家,因為是他們自己而不是別人生活于這種特殊的實踐情境之中,要為自己的生活而負擔起探求課程的基本問題的責任。課程實踐者必須把自己從已有的自我束縛的框架中解放出來,擺脫不切實際的冥想,腳踏實地地實踐,才能重新欣賞課程領域的真實情境、才能重新聆聽課程領域的真實話語。
2.重構話語體系
課程話語對課程領域真實描述的切入點在于對教師的課程實踐性話語的重視。“實踐性”的實質是人們擁有把“實踐”轉化為“應然”的能動的創造本性。每一套課程話語體系本身都是由相互依賴的諸要素組成的“系統”,其中每一種要素的意義和價值完全是由于另外要素的同時存在而獲致的。理論根植于實踐并發展于實踐,話語來源于實踐并應用于實踐,所以教師鮮活的教育實踐理所應當要成為話語體系的根基。話語體系就應該回到教育事實本身,應該從純粹意識領域走近現實的、世俗的社會生活,教育和教育研究中所存在的過于偏重靜態的認識結論的方法傾向,恰恰缺少直接關注在兒童、教師、學校、家庭和社會豐富的聯系中尋找教育的意義。例如,在新課程改革實踐中,一線教師的案例研究、敘事研究等備受關注。這些研究在尊重每一個教師個性的基礎上采用質性研究、闡釋性研究等多種方法,以實踐案例探討和自傳性研究為中心,不僅幫助揭示了教師的個性化教學,更為重要的是充實了教師實踐性知識、拓展了實踐中思維的深度和廣度。廣大教師經歷這些研究歷程后,更好地生成了具有生命活力的實踐性課程話語,飽含了反思性實踐的意義和價值。正如派納所描述的: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歸世界,世界先于知識,并總為知識所論及,并且,在與世界的聯系中,每一種科學的系統化組織都是抽象的、衍生出的符號語言,就像在地理學和鄉村的聯系中,我們首先了解到什么是森林、草原和河流。這樣,課程話語本身將變得更加真實、鮮活和生動;課程話語體系也將得以重建并獲得新生。
參考文獻
[1] 伍雪輝.課程話語透析.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6.
[2] 張濟洲.新基礎教育改革不是“哥白尼式的革命”.當代教育科學,2005(13).
[3] 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4] 李江源.中國教育學的失語與話語重建.教育導刊,1999(12).
[5] [日]佐膝學著.鐘啟泉譯.課程與教師.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
[6] [美]威廉F·派納等.理解課程.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
(責任編輯任洪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