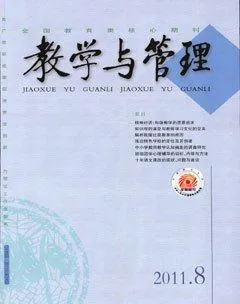論孔子德育思想的踐行途徑
德育本義應指道德教育。在我國古代,“德”、“育”二字是分開的。《說文解字》釋“德”為“外得于人,內得于己”。“‘外得于人’說的是要正直地處理與他人的關系,‘內得于己’,講的是內心修養,也就是無愧于心。”[1]可見“德”即道德。“育”在《說文》中的釋義為“養子使作善也”,即熏陶涵育子弟使其為善,“育”同道德教育。事實上,“德育這一概念的出現,從教育史上看,是起始于中國近代教育,多半是作為道德教育的簡稱和同義語”。[2]
一、主觀努力的“為仁由己”途徑
在孔子的論域里,“為仁由己”(《論語·顏淵》)中的“仁”就是一種“愛人”的品德,一種“愛人”的同情心或“仁心”。一個人只有具備了這種“仁心”,才會做到“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乃至做到“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要培養這種“愛人”的同情心,使自己具有“仁”的品德,就要從道德教育入手,發揮受教育者的主觀能動性,自覺地進行內在的道德修養,這就是所謂的“為仁由己”。
在實現“仁”的問題上,孔子特別強調主體的內在自覺。他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這里的“己”和“人”是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己”是主觀方面,是內因;“人”是客觀方面,是外因。也就是說,實行仁或做到仁主要在于自己,而不是在于別人。在孔子看來,“仁”是人之為人的內在本質和根據,實行“仁”完全是人的內在要求,而絕非任何外力的強迫所能奏效的。所以,“在道德修養亦即為仁的問題上,主觀內因是最主要的”。[3]
在孔子的心目中,德育本意中的“仁”處于非常崇高的地位,是必須終生為之奮斗的大事,雖然表面看來達到“仁”很容易,其實不然。“仁”的目標誠然高遠,但是,高,并不是高不可攀;遠,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因為,“仁”的實現總歸要落實在人的行為上,需要從點滴做起,這并不太難,更重要的是,“仁”本來就在自己心中,所以貴在有行“仁”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只要心中總想著這個目標,才可能有相應的行動,這樣,才會實現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仁就一點兒也不遙遠了。可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絕不是說不考慮現實條件,或完全排斥實踐,只在那里一味空想。它只是強調德育過程中的主動性即內心總要牢固樹立道德修養的這個目標而已。
正因為孔子特別重視德育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所以他對缺乏主觀能動性的人深表惋惜,甚至給予嚴厲的批評。他說:“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論語·里仁》)“仁”本來就是植根于人心的內在本性,在“仁”上用力,自然就不存在主觀力量夠不夠的問題。“一日”言其短,如果誰說“力不足”,那不過是他的主觀托詞罷了。孔子的弟子冉求問:“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論語·雍也》)孔子批評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論語·雍也》)所謂“畫”就是自己給自己劃了界限,停止不前。如果是半路上走不動了,別人可以給鼓鼓勁,幫幫忙,這樣還有可能趕上;但如果是主動放棄前進,那么就永遠沒有達到目的的希望了。
二、反省改過的“自省自訟”途徑
“自省自訟”(《論語·雍也》)的德育途徑與孔子的“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的思想緊密聯系。“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其意是說,君子總是求自己,向內求,尋找自身原因;小人總是求別人,向外求,找外部原因。因此,“求諸己”還是“求諸人”,便成為是區分君子還是小人的分水嶺。“自省自訟”,就是向內求,經常不斷地反省自己。
“自省”的概念,出自《論語·里仁》。孔子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這里的“思”與“內自省”指一個人面對賢人或不賢的人時,將自己和他們相比較,在內心反省自己、評價自己,努力做到象賢人一樣。見到不賢之人,就應反省自己,看自己是否有類似的缺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果分開說,自己反省自己,可以叫做“內自省”,而自己評價自己,可以叫做“內自訟”。如果合而言之,也可以說就是“內省”或反思。孔子所說的“內自省”、“內自訟”都是自我反省的德育修身方法,是實現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徑。孔子的弟子曾子發揚他“內自省”、“內自訟”的道德修養原則與方法,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的“三省”說,逐漸成為人們品行修養的重要原則。[4]
“聞過必改”是“自省自訟”的目的。孔子認為,在德育過程中,應教育學生注意改過。他說:“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即一個人有了錯誤,要及時改正。一個人不怕犯錯誤,最怕文過飾非,沒有勇氣承認和改正錯誤。孔子說他本人是不怕改正錯誤的人。他認為自己并不是一個天生不犯錯誤的“圣人”,而是一個會犯錯誤的“常人”。不過,他認為他有一個長處,就是能勇于承認和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他說:“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論語·述而》)如別人指出他的過錯時,他即表示改正,不但不埋怨,反而高興。他有聞過則喜的精神,學生倘能正視自己的缺點、錯誤,并堅決改正,那就不算缺點、錯誤了。因此,他認為教師不應老算學生過去缺點、錯誤的陳帳,而應朝前看,看學生現在的表現如何。孔子本人正是這樣看待自己學生的缺點和錯誤的。比如:“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論語·述而》)就是說,互鄉這個地方的人“習于不善”。有一天,這個地方有個少年要求見孔子,并受到孔子的接見。孔子的學生對此甚為不解,認為老師不應接待這個“習于不善”地方的人。而孔子回答說:“唯何甚?”(《論語·述而》)何必苛求于這個少年呢?“與其進也”、“與其潔也”,(《論語·述而》)應該看到這個少年現在的進步和現在品德漸趨純潔;“不與其退也”,“不保其往也”,(《論語·述而》)而不應回頭看,看重他過去的缺點、錯誤如何。
三、就近學習的“能近取譬”途徑
“能近取譬”(《論語·雍也》)就是能夠以切近的事物或行為作范例,進行比較學習,從近處著手,一步一步去做,是道德修養的重要途徑。孔子“能近取譬”的思想見于《論語·雍也》中:“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能近取譬”的“近”字可以有兩種含義:一種意思是,近就是自己,即以自己的感受來推己及人;一種意思是,近就是同自己最親近的人,按照這一意思,則應指的是自己的家庭成員或其他親近之人。[5]一般說來,一個人是愛其父母、兄弟、妻子的。以愛父母、兄弟、妻子之行為作例子,以愛父母、兄弟、妻子之心去愛他人、愛一切人,這就是“能近取譬”。“能近取譬”的意義就在于以孝悌等道德為基礎,由愛家庭成員及其他親近之人擴展到愛一切人。
“能近取譬”的德育途徑,與孔子所主張的“親親”原則、愛有差等是完全一致的。“能近取譬”,也就是“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替別人著想,這是孔子開創的一種開放式的思維方式。他要求學生根據時間和空間的變化,研究和解決面臨的各種問題,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孔子正是試圖借助這一有效途徑,實現“至仁”的理想。你自己想要的,人同此心,大家都想要,都想得到;你自己不喜歡的,別人也不喜歡,所以你也不應該把它加在別人身上。自己不愿干的事,不要叫別人干。“推己及人”就是以自己的好惡作為別人的好惡。
也就是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立,樹立,指立業,所謂“三十而立”之“立”;達,達到,指某一目標的實現。就是自己想立的業,也幫助別人立;自己想達到的目標,也幫助別人達到。這種推己及人的胸懷,便是仁人的胸懷。按照這一胸懷去行事,就是“為仁”。當然,這種以己所欲推及他人所欲,并幫助他人實現所欲的“為仁”,會受到個人能力的局限,亦即一個人的“為仁”能力,總是有限的。幫助他人“為仁”,不強加于人也是“為仁”。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顏淵》)
如果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論語·顏淵》)還是表現形式,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實實在在的內容。“無怨”,就是“為仁”的結果。子貢問老師,有沒有一句話可以終生奉行的?孔子便告訴他:“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這一次,孔子不僅講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將這一句話的意思進一步作了概括,提煉為一個字:“恕”。人跟人相處就是一個恕道,能夠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假如我是你,必有寬佑他人之心,這是一種高尚的境界即“仁”的境界。如果終身奉行“恕”,自然就是一位仁人。但難就難在堅持上,而做到“堅持”就要求必須心中有“仁”,且須將“仁”時刻存在人心之中。這樣,推己及人才能自覺,才能自如。
概而言之,從文化學的視角來說,孔子的德育思想是一種文化理念,它認為道德教育是個人自覺地將社會的道德要求轉化為個人內在行為準則的過程,其途徑主要是內在修養;它既有基于人性的對道德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倫理價值規范的正當性等諸多問題的理論論證,又有把抽象的道德理念具體化為可操作性的禮儀規范并使之能夠操持執守,付之日常生活的實踐品格。
參考文獻
[1] 沈善洪.中國倫理學說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2] 魯潔.德育新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3] 馮天瑜.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 汪國棟.孔子哲學新論.南寧:廣西師大出版社,1990.
[5] 劉寶楠.論語正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責任編輯陳國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