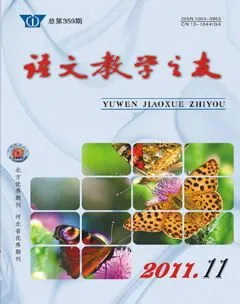構建語文課堂知識生成觀
近幾年來,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語文基礎知識大討論的歷史制高點后,語文學界又一次掀起了爭論熱潮,引起本次爭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人們對新課標中“不刻意追求語文知識的系統和完整”的不同理解;二是現實課堂教學中普遍存在著忽視和排斥教授語文知識的現象。眾所周知,語文知識是語文課程中最基礎的內容,也是提高學生語文素養和語文能力的源頭活水。更為核心的是,其他學科在教材中已經將教師要教授的知識點確定好,而語文教材僅提供教學的文本,學科知識內容大部分是由執教者自身生成和把握,因此衍生了教材、教學的多元解讀理念,不同的教育者因觀念、學識、經驗等不同而造成了差異,這種語文課程的不確定性也給語文教學帶來了很多爭論。
目前。不少語文學界的工作者一再呼吁應重視語文基礎知識的教學。雖然如此,上世紀學術研究中遺留的兩大問題——“語文知識的內涵和外延”、“語文知識的有效性”依舊是爭論的焦點,這兩個問題正是導致了語文知識命似浮萍、長久未定論的根源。
我以為,解決此問題的關鍵在于對語文知識的明確分類。在以前的研究討論中,語文知識類型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一刀切地談如何落實語文知識,忽略了不同類型的語文知識所承擔的課程功能和課程目標的差異、不同性質的語文知識所需要的教學設計不同的客觀事實。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做法致使課堂陷入了講與不講、講多與講少近乎一樣的泥淖中。
過去。關于語文知識有個約定俗成的“八字憲法”表述,即“字、詞、句、篇、語、修、邏、文”,由于這種說法并沒有具體論述分類的原因。也沒揭示相互之間的關系,與其說是語文知識的類型不如說對語文系統的簡單概述,因而顯得勢單力薄,不成一家之說。
目前,關于“知識類型”較被認可和接受的研究成果是從現代認知心理學角度將其分為: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策略性知識。此種語文知識類型的根本視域和立場是學生,符合了以生為本的教學活動宗旨,能有效結合課程與教材目標并踐行。“陳述性知識是關于事物‘是什么’的知識,它是人們對事情的狀態、內容、性質等的反映。”“程序性知識是關于‘做什么’、‘怎么做’的知識,它是人們關于活動的過程和步驟的認識。”“策略性知識是關于學習的策略的知識,即如何確定‘做什么’、‘怎么做’的知識。他的標志是明確認識自己面臨的學習任務,知道自已目前學習所達到的程度,能調用恰當的學習方法,能對自己的學習過程進行反省和調節。”③這是知識教學最理想的境界,更多的是依靠學生自我的領悟和監控。
從三個課例來看,夏志明老師的《陳太丘與友期》是以陳述性知識為主,黃德初老師的《我愿意是急流》側重的是程序性知識,張璇老師的《說數》是以分析為主要教學方法貫穿策略性知識的教導。三位老師在知識的選擇上都進行了組織和建構,并沒有出現無效知識的現象,這是其知識、經驗和能力的體現。但是,縱觀三個課例,在關于語文知識教授上有兩方面需要商議:
一、陳述性知識的有效教學方式。如《陳太丘與友期》中成語積累這一教學環節上,教師引導學生通過工具書積累成語,卻只是流于單純地積累成語,對成語的意思沒作點拔和解釋,這對初一的學生來說是很難掌握的,所以這一環節由于教學方法不妥當使得知識形成性低。而黃德初老師在《我愿意是急流》中的比喻手法、倒裝的條件句這樣的陳述性知識教授中就處理得很好。對華師附中的學生來說,對這兩個概念的理解不會存在問題,但是要讓學生確切地體會這兩種手法在此詩歌的妙處就要另花一番心思。黃老師是通過反復地比較讓學生深刻地體會其中高妙,這兩點知識就不僅在學生知識建構中得到確認而且使之建立有效的知識圖式。
從這兩個課例的比較中得出啟示:(一)陳述性知識是語文知識的基礎,也是較為簡單易懂的知識,要求的心理過程主要是記憶。這往往使教育者產生不正確觀念一易懂就易教,這是有待糾正的,因為這種觀念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陳述性知識是要求掌握的,看似懂的不一定透徹掌握,最終目的是可以靈活運用。新課標要求:學生能運用語言是對語文課程的所有類型知識的目標和指示。
(二)一種知識得以掌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學方式的使用。以體驗為主要途徑的教學方法是提高陳述性知識效度的重要策略。體驗,以學生為主體視域,旨在調動學生生理器官、思維感知以達到如身臨其境之感,拉近學生、作者、文本等之間的距離,通過直覺的方式把這些知識事實積淀在主題內部。如“引吭高歌”如果夏老師植入讓學生拉長脖子、大聲愉快地唱,學生不僅明曉“引”的意思,而且懂得在各種情況下靈活運用該成語。總之。在語文知識的教授上,執教者必須對所要教授的語文知識的目標、內涵性質有準確的認知,并結合所教的學情具體解決。
二、陳述性知識要轉化為程序性知識。中學語文教學不應以陳述性知識而是以程序性知識為主體,陳述性知識對語文教學的意義是有限的,語文課程目標在于“學生能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陳述性知識是不能滿足學生對語言運用之要求,必須轉化為程序性知識,程序性知識的教學意義是巨大的,是最需要的也是目前教學最缺乏的。而這兩者的轉化的契合點在于“用”,將陳述性知識融入某一情境中,即把知識實踐化、生活化以達到兩種知識的有效轉化或結合,這種“用”也正是程序性知識“做什么”或“該怎么做”的要求所在。如黃德初老師在《我愿意是急流》教學的最后一環節——讓學生仿照詩歌另賦新詩,此為“用”,讓學生用已學知識嘗試做某件事,即是遷移,這種教學方法對程序性知識的掌握是高效的。“用”較之感悟、體驗多了明確的指向,又較之分析、理解多了具體的操作訓練。黃老師的“用”是非常大膽的,教學設計也是本課堂的亮點,程序性知識趁熱打鐵地得到即刻落實。而且通過“用”讓學生順著外顯知識指示的方向挖掘了詩歌教學中很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緘默知識,并最終實現緘默知識向外顯知識的轉化。用外顯知識引導學生緘默知識的獲得是語文教學的難點,所以訓練的教學方法為黃老師突破了教學難點和實現了教學目標。訓練法是教學活動中常用的教學方法,不少教師用得不慎造成了題海戰術,所以訓練法必須有所針對性,做到有的放矢。它對程序性知識類型是很有效的。
張璇老師執教的《說數》是一篇科學小品文。張老師教授的知識中主要是策略性知識,對此張老師采取的主要是分析的教學方法,這點非常合理。因為只有通過理性認識和邏輯推理的分析過程才能讓學生體會科學小品文的準確性和文化之美。如:張老師在落實教學目標之一“掌握科學小品的準確性、生動性”時,設置了“是非大考場”的教學環節,她不僅要求學生對所給出的語段作出判斷,并要求學生對自己的判斷找到根據。另外,張老師課堂知識的銜接性非常緊湊且漸進有序,在學生細致體會文章的科學和準確性后,引導學生體會科學小品另一特點——文學性,這兩個環節讓學生對掌握文章中形象生動的說明方式的策略性知識有了清晰的認識。更值得肯定的是。張老師不是通過傳統滿堂灌的方式來教學,而是組織學生以探究的方式一層一層地剖開其中的“策略”,即本篇科學小品文所使用的說明方法。這種分析引導學生不斷地思考以達到深入策略性知識的“元認知”和實現學生對認知過程的自我調控。全面地理解知識生成的過程并對自身某部分的認知進行新一輪的修正和建構。策略性知識的掌握雖然更多的是依靠學生自身對認知活動的調控過程,對中學生有較高的要求。所以對策略性知識的掌握,教師的引導顯得尤為重要。而教師在教授策略性知識時所采用的教學方式又是能否有效地引導的關鍵所在。一般而言,張老師所采用的分析教學法就是針對策略性知識的,這是由策略性知識的性質、功能所決定。
這三個課例充分地展示了語文知識的類型,同時也為不同類型的語文知識所應采取的教學方式提供了啟示甚至是示范作用。語文知識再一次成為語文學科研究討論的焦點,可見這是語文學科無法回避的問題。而在考試指揮棒下,語文知識形態已被扭曲、語文知識的教學也已被異化。因此我們要正視這一問題,只有對語文知識類型的熟知并與恰當的教學方法相融,才能達到認知的高度,否則教育目的、課程目標都將會成飄渺虛無的浮空之言。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