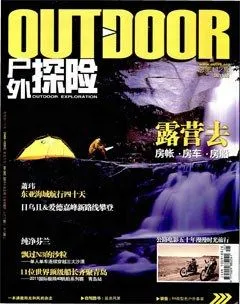在伊甸園和烏托邦里醉生夢死
為什么夢想“在路上”?
也許最初,你從公路電影中看到了頹廢和沉淪。尤其在60年代的典型作品中,回味之下,任何西方電影中隱喻色彩強烈的狀態,都與宗教不可割舍。
《逍遙騎士》的主人公懷特和比利騎著哈雷摩托,一路夕陽,自洛杉磯向新奧爾良進發,他們一無所有,風餐露宿,結識形形色色的人事——那些嬉皮士,天主教土著,賣春姑娘和酗酒的律師,猶如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簡要人物圖譜。他們的初衷在于尋找心目中真實存在的美國夢,卻未曾意識到,這場自空虛而起的旅程,最終以殛命他人之手而空虛告終,旅程的目的地便是旅程本身,全世界的青年們總是相似的,懷特和比利曾經篤信美國夢,抱有英雄主義情懷,對自由世界懷著不可救藥的樂觀向往——這何嘗不是我們年輕時的樣子,當我們津津樂道于詩人的流浪,愛情和生存,卻每每遺忘它們的共同前提:受難。
這是一枚含有濃重宗教意味的辭藻。
《逍遙騎士》在當時的好萊塢,以40萬美元成本以小博大,獲得2500萬美元的神話票房,如果這個不算什么,它其中所蘊含的宗教理想和政治訴求,才讓人驚訝于一部商業電影和沉重哲學,宗教思辨能夠如此成功共謀。美國文學史家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著作中曾闡述過60年代的美國文化,除了出世的悲觀宗教思想,還有一種八世的烏托邦宗教意識,前者沉湎于“歸去”,意即曾經的伊甸園,然而因為人們的罪孽太深,已經無法重返。后者則。迷戀秘術,推崇東方宗教術士和靜思功夫,以及通過吸毒,多態性行為或快速療法而獲得短暫的涅槃。期望更大程度上獲得感官刺激,“去往”精神和心靈的自由天國,《在路上》小說中,主人公們一邊狂歡,—邊談論東方禪學,在這一點上與《逍遙騎士》不謀而合。‘歸去’和‘去往’,是青年們面對信仰缺失的徘徊,而隨著公路片形態的復雜趨勢,老人和孩子所象征的國民群體,也在經歷煉獄和救贖的輪回往復。
誕生于1998年的巴西電影《中央車站》在影片廣告上是這樣寫的:一個孩子在尋找他的家,一個女人在尋找她的心,一個國家在尋找它的根,一個孩子在骯臟混亂的車站邂逅一位老嫗,她的生命激情早已為殘酷歲月所吞噬,不僅冷漠,甚至惡毒,騙走他母親的錢,還險些將他賣給盜賣器官的人販子,但失去父母的孩子已經脆弱到袒露無遺時,連兇險都本能地望而卻步,無助的心靈被情感缺席和失愛的悲慟所折磨,排解痛苦的惟一出路便是上路尋找,老嫗也曾有過這樣以血肉之軀迎撞粗糲世界的勇氣,也曾有過圣潔熱烈的愛的呼喚,訣別這些幾十年之后,孩子的祈求使她在不完美的生命中重拾希望,旅程的開始是這樣不情愿,過程也仿佛煉獄,但當生活原本就接近于地獄時,在路的盡頭,隱約出現了福音。
這部電影是這樣聞名,幾乎每位粗通西方宗教教義的觀眾都能輕易讀出創作者有意為之的宗教寓意,在著名的《出埃及記》中,記敘了這樣一段,摩西是耶和華的仆人。帶領以色列人脫離法老轄制,離開埃及,到達迦南的門檻,而約書亞是摩西的助手,在摩西死后被選為以色列民首領,最終帶領百姓到達流著奶與蜜的迦南之地,也許《中央車站》并不是一部傳統模式的公路電影,但在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公路電影誕生近三十年之后的這部作品,傳達了與當時美國截然不同的宗教信念,人們呼喚未知的神明,尋覓安寧的天國,渴望自己同蕓蕓眾生一般獲得庇佑,脫離不能言說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