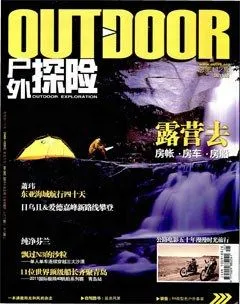一個人的野生活
2011-12-29 00:00:00蟲子圖丁王挺等
戶外探險 2011年5期

高原寡居
藏北草原的春天寒冷,靜謐。每日清晨朝陽慢慢潤紅一座座雪峰,最后透進我的帳篷,寒冷濕氣隨之散逸。遠遠山洞里的小寺廟,開始一天的誦經,法號藏鼓齊鳴。我的帳篷就扎在一座巨大的經幡陣下。這里是納木錯扎西半島的最西端,平坦,空曠,幽然。
而我的棲身處,則遠離了朝圣人們,遠離了喧嘩。即便是靜坐著,凝視湖水拍岸,鷗鳥飛掠,亦能感知獨處曠野里的自在,覺照當下的喜悅。
幾乎每天清晨,正當我睡眼惺忪的時候,就會有轉湖的藏人走過我的帳篷,并好奇地張望。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的帳篷都會成了轉湖的參觀點,甚至在正午的時候,有的藏族一家人就在我的帳篷邊過上林卡了。于是我也跟著沾光,風干牛肉,糌粑,還有青稞酒。
幾乎每天傍晚,從納木錯西岸會飄來大朵大朵的雨云,飄灑過后,便是夕陽無限,我趁著日落爬上山頂,遠遠眺望,帳篷如一艘孤立的橘色小舟,漂泊在湖邊。如此有幸獨與天地而往來,很明顯的,自我變得極度的渺小,直到虛無的狀態。這就是孤身一人,扎營于荒野極佳的觀照,觀照自我的空性,從而增添了更多茫茫世間的慈悲感。
6月里的某個深夜,被野狗的狂吠驚醒,過后則飄風大作,驚滔與雷電如萬竅怒號。天穹下竟是紫色為電,從念青唐古拉連綿至小寺廟的山頂。時不時閃電還會在帳篷不遠處直墜湖面,陣陣悶雷。若閃電有幸光顧我,則明日留下的必定只是一副帳篷的鋁合金骨架和燒焦的軀體。
雷雨,狂風繼續肆孽,在這無盡等待中,我變得異常焦躁,有一種即將被帶離塵世的慌恐,很想逃離,想直奔遠處山洞的小寺廟。可那是絕無可能的,在驟雨疾風,雷電下必定是迷路。干脆,我還是繼續躲進睡袋,閉上了眼睛,惟有等待,等待無常的降臨。
慢慢地我感受到有一種強烈的存在感,每一個念頭,每一個動作都變得異常的清晰,明確。我相信這就是生命的強烈存在感,若是回到散亂塵世里,那些人與人,人與城市相刃相糜的沖撞中,是絕無可能有這樣的覺察的。事實上這是一種極度深邃的寧靜體驗。也許只有當我們的生命處于強烈不確定時,當我們處于極端的孤立,脫離塵世的狀況下,那顆最初狂亂,恐懼的心緩緩寧靜下來后,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原本純凈的心性。這個心性就好像圣湖的水未被攪動本性是透明清澈的。
時間已經失去意義,風雨在我的靜默中慢慢停歇了。不久遠遠的又傳來野狗的叫聲,這個世界仿佛又靠近。索性拉開帳篷,原來星空早已拉開帷幕,雨后的銀河更是璀璨。我仰躺在帳篷里,在四周無盡的黑暗里仰望天穹,我這艘孤獨的小舟和著湖水拍岸聲似乎飄浮起來,在黑暗中飄浮起來。與宇宙的本真靠得如此之近,心中不免有一絲悲憫。悲憫人身的難得,人生更難得。
拔營的那天,我猛然覺得一些日子以來,正午的浮云都是被湖水的藍反射成了藍色。更精確地說,是天空之藍。天空之深邃的藍,印像了湖水,在陽光的照耀下,反射給了云。隨之云也藍,水也藍,天更藍。
和水而駐
捆扎好我拓樂車頂架上的行李,沿著緩坡,在顛簸中,慢慢靠近水岸。
初春郊外的枯黃遠遜城區的淺綠,枯萎雜亂的蘆葦在午后陽光里傲慢地挺立著,四幕無人,讓人覺得有些許凄荒,但你也不難想像,仲夏時節的荇荇水草,定將這片開闊水面遮蔽出幾番天地。推開桔葦,總算尋得一條車能近得水岸的便道,剛欲轉身,忽聽得一聲鳥鳴,呼啦啦飛將出去,貼著水面,一個閃回便消失在側岸的草叢中,水面空留下幾圈波紋。春水已暖,看來水鳥比鴨子捷足先至。
燃起爐火,讓鍋中的水沸騰,一杯普洱,讓自己沉靜下來,整理好一根魚竿,裝上漁線輪,試了試魚線輪的曳力,然后在水面打了三星漂,稍稍撒了點誘餌,打開線檔,揮竿拋投送鉤。落點在餌區的邊緣,這該是非常好的拋投。沒有等待,起碼今天沒有。我只想和水而居,獨釣,沒有目的,只為讓自己往外滲透一點,伸展一點,哪怕只是擎竿冥想,在靜水邊專注一下,直至享受片刻的遺忘,
水面沒有動靜,竿稍沒有動靜,魚沒有動靜,我沒有動靜,遠處偶有水鳥皴擦水面。
日暮,太陽的溫熱退去,水的寒氣向上彌漫,乍暖還寒太陽落山時最易體味,我燃起篝火,火的焦烈迎面沖撞,后背依然泛著寒涼,夜晚的靜寂因這小堆篝火的跳躍越發讓人沉迷,天上無月無星,一層薄云在頂空漂浮。火漸入末勢,星星閃閃,想來該是遠處他人眼中的浮船漁火。
我自入賬睡了,倒是想讓自己此刻蛻變成一條蟲,只是不像《變形記》中那位焦躁不安,我想安寧地享受郊野的靜寂,像蟲一樣,和這水土融為一體,融成一個渾圓,然后等待清晨,等待醒來的水岸,樹林。
比鄰古鎮
孤獨的人是可恥的。我想張楚唱出這句歌詞之時,縱然沒有花枝招展的戶外裝備,一樣四處漂泊流浪。
一個人的旅行,總難免帶著些自我放逐的意向,一個人露營,讓自己和自己對話。
那是在浙江一座古鎮附近的小山坡上,終究還不敢離人群太遠的,山坡位置很好,可觀日出日落,遙遙地還可看見山下小街巷里往來的村人,我好像是在天上偷瞰人間,但我只想振臂一呼,這山頭上的,都是我的!因為寂寥空曠而生出的存在感,占有感瞬間充斥了我的心懷,又或許,我只是在寬厚的大自然面前虛張聲勢?
扎過營的驢子都知道,周遭帳篷說話的聲音往往清晰可聞,如今再沒有其他帳篷里的竊竊話語,我幾乎可以感受到防潮墊下小草與帳底相互摩擦的聲音。草木的清香似乎在頑強地通過帳篷的幕布空隙要充盈整個內帳,在沒有人造燈光的黑夜里,人的嗅覺,聽覺,觸覺似乎都會變得特別敏感,我甚至覺得小草在我身下聚集露水。我想起曾有人問大家,為什么喜歡露營?我的回答是,因為隔著墊子依然可以體會到泥土的芬芳,大地的溫暖,又不可免悟地感慨起來,我們這些都市的人啊,究竟有多久沒接觸到真實的大地了?
所有的浮想聯翩,其實都是孤單帶來的,再無其他依傍,再無其他雜念干擾,獨臥帳中,我好像邂逅了真實的自我,我是誰?我為什么會在這里?我忽然完全想不起平日里抱怨連天的職場生涯,我只想起了以往跋山涉水時碰到的那些純真笑容,誠摯伙伴,每一個開心的細節,竟如此生動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其實,在真正孤獨的時候,你壓根兒想不起這句話來。
獨享山野
大地上所有的影子都越來越長,變成藍色的阻影。
這是在河西走廊之東,祁連山下。
我討厭一個人露營,因為很無聊。
我迅速支好了帳篷,落日的余暉讓帳篷里面很快有了一種荒漠中被太陽曬熱的石頭的氣味,我躺進睡袋,無聊地睜大眼睛,等待夜幕落下。
我開始在中國遙遠的西北荒灘上聽著一個美國的民謠歌手在英勇地唱著他的歌,他的嗓子沙啞得如同這片大地上的礫石,這是幾百年可能都沒什么人碰過的石頭,現在一碰就響,響起來就收不住,我覺得荒漠里那死一樣的沉寂中有著這種無比激烈的聲音是件不荒謬的事情。
前幾年曾有段時間做夢都想著雪峰,我恨不得把缺氧的高山反應當成—種人生境界,但我很少缺氧,青藏線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口下車奔跑,我他媽的一點反應都沒有,再后來,五次進西藏,兩次爬雪山,我還是沒有!我就差來次溫柔的煤氣中毒來體驗一下缺氧的感覺了。
不過這一晚,我的頭一直昏昏沉沉,不停地做夢。夢里在重新走著這段路,這段路走著貌似很艱苦,可是記憶里面沒留下什么,大部分路段旁邊都有些長長短短稀稀疏疏的綠樹,像是盲詩人周云蓬的詩行,那些道路般的水渠歌唱般橫穿公路和長城線,水是由祁連山南側的積雪融化下來的,很渾也很急,可以感到它們落差的力量和山上泥沙的氣息,我每次遇見水渠都要蹲下抹抹臉沖沖頭降溫,但是在睡夢中如果夢見喝水,十有八九意味著你的腎出現了點問題,而我這時候卻因為干渴醒來,不知道是幾點,外面除了星光,再無別的光線,我的眼睛像個原始人,不需要摸索,我準確找到了那瓶水,咕咚咕咚迅速灌下肚子,然后我覺得全身膨脹,水開始滲透每個細胞,每個毛孔,甚至包括精神狀態,夢里面那散亂的長途竣涉,就這么咕咚咕咚幾下子打發了,什么感覺都沒剩下,痛快得令我有點失望。
再次躺下,可是,沒睡意了。
帳篷外面一陣小風吹過,沒帶來什么氣味,而前幾天旅行的村野總散發著一種我已經熟悉的牲口糞和麥子的氣息,當然,還有劣質柴油的氣息,現在什么都沒聞到,夜里空氣干凈得讓我明白——我現在周圍真的沒有人,甚至,也沒什么動物,睜著雙眼在帳篷內,我想著幾天后又會回到熟悉的城市,見到熟悉的臉,他們現在肯定想不到,我獨自一人,在一個荒灘上,想著很多事情。
太陽曬醒了我,我拉開帳篷,讓自己暴露在灼目的陽光下,身上開始有了螞蟻在爬的刺癢感,一天,這樣又開始了,我不能停止奔走,但我真怕就此成為一個永遠停不下來的步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