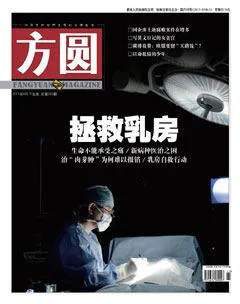新病種醫治之困
2011-12-29 00:00:00楊佳瑜
方圓 2011年8期

一種不是罕見病的疾病,為何沒有醫生會治療、愿意治療?是醫生培養機制不順,還是利益引導機制出現了失衡,抑或是醫德與觀念缺失
幾年前,肉芽腫性乳腺炎的發病率與乳腺癌的比例是1:25,人群中出現25個乳腺癌患者才會有一例肉芽腫性乳腺炎。但是,近年來它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乳腺炎專家杜玉堂在接受《方圓》記者采訪時說,“這個病比普通的乳腺炎、漿細胞乳腺炎、乳腺結核等要多得多。”他估計,幾年后它與乳腺癌的發病率比例會上升至1:2,呈現一個大爆發的狀況。
肉芽腫性乳腺炎與普通乳腺炎不同,它是無菌性的,由自身免疫系統對自己的身體過敏而致,而且它造成的結果也和普通乳腺炎不同,患肉芽腫性乳腺炎的乳房像一個多層多通道的地道。故針對它的治療不能用治普通乳腺炎的方法,像引流、穿刺、激素治療等等都不行。目前研究成功的西醫治療方法,只有通過手術去除病灶。
我國首席乳腺疾病專家、北京協和醫院乳腺首席教授黃漢源對前來看病的鄒穎說,“你想治這個病,要么是我,要么是他,不要亂跑了。”黃漢源說的他,就是杜玉堂。這兩個醫生,一位79歲,一位71歲。其他醫生常常把肉芽腫性乳腺炎誤診為其他乳腺疾病,從而也導致誤治。
治療的醫生少、誤診誤治多,這就是肉芽腫性乳腺炎的治療現狀,也是許多新病種的醫治之難。
肉芽腫是新病種嗎
醫學專家介紹,肉芽腫性乳腺炎這個名稱實際包括乳腺結核在內的多種肉芽腫性疾病,但以肉芽腫性小葉性乳腺炎(GLM)最常見,有的醫院穿刺或病理報告也常這樣寫,可以認同就是GLM。小孩3-5歲的經產婦,突發腫塊,有人微脹,有人劇痛,繼之紅腫破潰,數月難愈,早期與乳癌難辨,晚期與擴張癥難分。
但問題是,自1972年發現該病至今已是三十年,病史并不算短。可為什么現在醫生對肉芽腫性乳腺炎仍然認識不夠?即使不是癌癥,不危及生命,但它發病率高,關乎女性的身心健康,而且有這么大的社會需求,醫生為什么不去研究它?
杜玉堂解釋說,“一是認識不夠,它畢竟是一個新病種;二是醫生不重視,他認為不是癌就沒關系,死不了,就不像對癌那么重視,在思想上輕視這種病;再者,它治療起來非常困難,因為這個病復發率高,沒醫生愿意去治。”
事實上,我國提出“病種”的概念近三十年,作為一種“普通人的對病的種類的認識”,已被衛生部、各級行政機關和醫院普遍接受,指代每種病例所患疾病的第一診斷確定的疾病名稱。
那么,一個發現三十年的病還能算新病種嗎?
東南大學法學教授、衛生法學科領頭人張贊寧介紹說,我國現代漢語及醫學詞典對此并無明確解釋,各人各地理解均有不同。“據我考證,目前對新病種的理解是混亂的,沒有統一解釋。”
張贊寧將其歸納成三種:第一種是新發現的。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非典(SARS)從2003年到現在已有8年,但它相對其他甲乙型傳染病而言,也許在30年-50年后也仍可被稱為新病種,艾滋病也是這樣。“但我個人認為,新病種一般應以10年為限較好。”
第二種是原來未被列入,現在被列入了的病種。如手足口病,是個老病種,過去不認為是傳染病,但最近衛生部將其列入丙類傳染病進行管理。在傳染病這一領域,手足口病就是新病種。還有新修訂的《傳染病防治法》將原來丙類傳染病中的肺結核、新生兒破傷風、血吸蟲病調整為乙類傳染病,將原來乙類傳染病中的黑熱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傷寒調整為丙類傳染病。那么在乙類傳染病中,肺結核、新生兒破傷風、血吸蟲病就是作為新病種加入的。
第三種則是新認識的病種。有些疾病比較古老,但未被人們所認識,現在被醫界認識了,有的還被重新命名。如肉芽腫性小葉性乳腺炎,這種病過去就有,但人們對它沒有認識,將其統稱為“乳腺炎”,并作一般的乳腺炎治療。近30年人們對它才有所認識,將它從“乳腺炎”中分出來,所以它就是新病種。
即便是認可張贊寧的三種觀點,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新病種都能像非典一樣得到社會與醫學界乃至政府的高度重視。類似肉芽腫性乳腺炎這樣的新病種,面臨著醫院不愿意收、醫生不愿意治、新培養的醫學生不懂得治三個方面的難題。
醫院的“保守治療病”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家開始推行醫療市場化政策,要求醫院要重視經濟效益和經濟管理。直到2005年5月24日,衛生部下屬的《醫院報》頭版頭條刊出了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新明的一次最新講話,并冠以《市場化非醫改方向》的題目,醫改的方向才慢慢扭轉。
“盡管我們已經不再主張醫療市場化,但在醫療市場化政策的指導和影響下形成的醫院管理制度并沒有改變,且其危害正在持續和放大。” 山東省聊城大學法學院教授孔繁軍說。
張贊寧提出我國的醫療收費體制上存在重器械、重儀器、重藥品,輕知識、輕技術、輕勞動的“三輕三重”現象。一個病人到了醫院診療,掛號費、診療費、手術費往往收得很低,而藥品費、器械費、儀器使用費卻很貴。
這種弊病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拿不出醫院應該得到的利益,導致醫院向患者要,而這種機制使得醫患關系越來越糟糕,但政府短時間內確實又拿不出來這么多的錢。難呀!”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直言。
另外,由于當前醫患關系的緊張態勢,醫院針對一些較為復雜的疾病,通常采取“防衛性”治療措施(如保守治療,遵循所謂的醫學常規),不愿做帶有一定風險性的手術,以避免自身陷入醫療糾紛甚至醫療事故中去。江蘇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夏民認為這也是醫院管理制度存在的問題。
記者調查發現,很多肉芽腫性乳腺炎的患者都曾被醫生建議過進行“單純性乳房切除手術”,因為對于乳房疾病來講,那是最直接、最少風險的治療方法,而且列入醫療保險的報銷范圍。但如果使用新技術或藥品來治療,就會因該技術或藥品不在醫保目錄中而無法報銷。杜玉堂則認為,治療漿乳、 肉芽腫等乳腺疾病,是應當保留乳房的,即使切除了腺體也要保留乳頭乳暈,“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以后想鼓起來很容易。我們要強調的是為漿乳或肉芽腫犧牲整個乳房是不值得的,我不贊成做‘乳房單純切除術’,我知道全國各地有人在做,但我呼吁刀下留乳。”
利益預期較少導致的醫生缺乏
醫院畢竟只是接受病患的載體,最直接診病的還是醫生。
杜玉堂認為,即使醫生確診病人患了肉芽腫性乳腺炎,也不愿意治這樣的病。做手術時,劃開乳房表皮之前,里面的病灶如何沒辦法預測的,只能手術時根據病人的具體情況進行。所以手術常常需要三個小時,有的甚至長達五六個小時。而且手術后病情容易復發,因為只要有一點病灶未清除干凈這個病就會再發。復發的病人找回醫院,加劇醫患關系的緊張。所以,醫生、醫院都不愿意接收肉芽腫性乳腺炎病人。
杜玉堂將他的手術過程形容為“如履薄冰”。但是這樣的手術,據杜玉堂醫生說,他每做一次收入是一千元。
“在當前形式化的科研考核和以資歷為主要標準的職稱晉升制度下,醫師的科別選擇就有了包括個人發展在內的長遠利益和經濟效益為主的眼前利益的綜合考量的理由,”孔繁軍說。
醫生的職稱包括初級職稱(醫士、醫師/住院醫師)、中級職稱(主治醫師)、副高級職稱(副主任醫師)、正高級職稱(主任醫師)。一位正規醫學院本科畢業的學生的職稱之路是這樣的:完成五年的醫學本科之后到醫院進行一年的實習,申報執業醫師,在通過了全國統一的考試之后,第二年可獲得執業醫師證書,成為醫師;繼而,參加并通過全國英語考試和計算機考試,申報醫師資格,評審通過后獲得主治醫師職稱;五年后,發表三篇省級論文,參加兩項科技進步獎活動,再通過計算機考試和英語考試,可申報副主任醫師職稱,也就是高級職稱。
“職稱晉升和職務升遷的壓力,科研造假和論文抄襲替代了嚴謹的學術研習,因此,對新病種的忽略或漠視也就是自然的了,”孔繁軍說。而從眼前利益來看,“醫療美容、眼科、腦科、腫瘤科、皮膚科、性病、輔助生殖等科別利益水平高,專科醫師就更愿意關注,但像肉芽腫性乳腺炎這樣一些需要下大力氣研究而利益預期較小的,便很少有人涉足。”
缺乏癥的另一面是醫生的先天不足
盡管利益導向出現了失衡,但倘若更多的醫生能夠在正式進入行業之前,就選擇一些新病種作為學習、研究方向,顯然也不會在醫治新病種方面出現醫生匱乏的現象。可是,我國醫生培養制度卻存在著先天不足。
以杜玉堂為例,作為一名治療肉芽腫性乳腺炎的專家,他一開始也不知道如何治療這種病。
2002年,杜玉堂第一次看到這種病,而且發現醫生們總治不好它,作為一個治療乳腺疾病已經25年的醫生,他好奇了,開始泡圖書館、做筆記、畫手術圖,把全國關于這個病的病歷、論文字字句句研究了個遍。一研究就是五年。
閉關不出診、篇篇論文仔細琢磨、做統計病歷表……這樣的專注和探索在醫學界已經很少。
缺少了專注和研究精神,醫生們就很難認識到這種發病率不斷攀升的病。孔繁軍認為,醫生的培訓多是以師承方式進行,缺少必要的理論學習和研討。“由此造成培訓后的醫師在其后的自主從醫過程中,經驗型的模仿治療多,研究型的創新治療少,”那么,“新病種出現認識不足、誤診誤治也就不出奇了,”孔繁軍說。
不足癥一:基礎教育缺位
記者翻閱了一些醫學院的教材,發現很多教科書的版本還停留在10年前,甚至30年前,而醫學是“一個醫生如果5年不學習,將有30%的知識淘汰”的學科;醫學院的教學受傳統觀念影響,采用灌輸式的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缺乏研究、解決問題的能力,只會生搬課本里的條條框框。
正是這樣的醫學教育體制使得醫生認識不到肉芽腫性乳腺炎與其他普通乳腺炎的區別,誤診誤治,即使治不好病人,也沒有進一步研究。
對此,王岳提倡“基于問題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PBL,也稱做問題式學習)的教學方式。它強調把學習設置到復雜的、有意義的“疑難問題情景”中,通過老師與學生的合作來解決真正的問題,從而使學生學習隱含在問題背后的科學知識,形成解決問題的技能和自主學習的能力。“基于問題的學習”的關鍵是培養出具有實證精神和質疑、批判精神的“人”,而不是單純的灌輸“知識”。
即假設醫學院能夠在學習期間,就對一些新病種,進行針對性教學,顯然會直接影響他們日后的科別選擇。
另外,王岳認為在醫學教育中要凸顯職業教育的特點。在發達國家,醫學教育首先確立為職業教育,即在完成大學高等教育后針對有志于醫療服務的畢業生進行的重在培養職業能力的教育。學生報考醫學院時往往有非常明確、成熟的人生理想,他們選擇讀醫學院校實際上就是選擇了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為患者排憂解難,共同面臨生死的考驗。這種職業精神使醫生在其執業的過程中立足患者的利益,努力研究如何為患者治療。
事實上,從杜玉堂進入肉芽腫性乳腺炎這個領域的過程看,大多數醫學院的學生在這一階段并沒有專業的選擇性意識,使得對于類似肉芽腫性乳腺炎的新型、更為精專的疾病沒有針對性學習。 “我國的醫學教育僅僅針對高中生,其報考的學校和專業受到父母的較大影響乃至干預,”王岳對《方圓》記者說。
不足癥之二:醫學實踐的傾向性不夠
醫學是一門實踐學科,醫學院的學生必須經過實習才能畢業。而成為一名執業醫生的前提也是必需通過實踐技能考試。衛生部《醫師資格考試暫行辦法》規定,通過醫師資格考試評價申請醫師資格者是否具備執業所必須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這個考試包括了實踐技能考試和醫學綜合筆試,這足見對醫生實踐技能的重視。
但是在醫生培養的過程中,這種重視卻沒有其他配套制度來保證。張贊寧告訴記者,醫學院的實習時間安排過短,名義上有一年,實際上只有不到半年時間,因為這一年的實習還包括了寫畢業論文的時間和畢業生找工作的時間,而實習成績所占畢業生成績的比重過輕,一般只作參考成績考慮,幾乎沒有誰因為實習成績差而畢不了業。
“在不少醫療損害案件中,就是由于醫務人員缺乏實證精神,完全憑自己的主觀臆斷和經驗判斷草率作出診斷。這很可能會導致患者錯過最佳的治療時機,釀成終生的痛苦。”王岳說。
對此,孔繁軍總結道,要真正體現出醫學專業的實踐性特點,“是否可以用臨床觀察或病例調查等方式來替代畢業論文,實習教學與理論學習是否可以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等,都值得考慮。”
醫學教育中的問題使醫學院學生難有解決問題的研究精神,實踐技能培訓的種種缺陷又使他們缺乏動手能力,而這兩方面是醫生培養制度中最關鍵的兩個環節。
新病種的研究
是否需要上升到制度層面
我國2009年新修訂的《執業醫師法》規定,醫師在執業活動中應履行努力鉆研業務,更新知識,提高專業技術水平的義務。但該義務并沒有相關法律責任的規定。相反,從事醫學研究、學術交流,參加專業學術團體,參加專業培訓,接受繼續醫學教育,是醫師在執業活動中的權利規定。
也就是說,沒有哪個制度或者法規約束醫生對像肉芽腫性乳腺炎這樣的新病種進行研究。
孔繁軍也并不贊同以防患性的管理制度來約束醫生。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建立或完善應然性的引導制度,即讓醫生明白應該怎么做,可以怎么做,而不是過多地強調不能怎么做,即變防患性管理機制為鼓勵和引導性管理機制。要鼓勵醫生形成“向善”的思維定式,而不是“向錢”。但他也明確,這不僅需要一部法律的修改,而更多的是微觀層面上的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的是整個社會的變革。
在王岳看來,曾經醫生講究“懸壺濟世”、“仁心仁術”,現在則是不考量疾病自身或患者利益只立足自身利益最大化;更有甚者醫患雙方反目成仇、對簿公堂,也發展出職業“醫鬧”。 醫療法律關系源于委托行為。而委托行為往往具有人身依附性,即委托人與被委托人間的委托行為是建立在對對方人格信任基礎上的,如法諺所云:“無信任即無委托。”所以,在社會上,原本很難找到比醫患關系更應穩固、信任對方的法律關系了。但是這些年的臨床工作中,我們漠視、放縱醫院、醫生的種種逐利行為。最終的結果就是,醫患賴以和諧共存的信任基礎徹底被毀壞了。
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衛生部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孫東東就認為沒有必要上升到制度問題的層面,因為完全可以通過中華醫學會制定的指南來解決。“中華醫學會制定的指南是醫生手術的標準,醫生必須按這個方法來治,反之,沒有指南,醫生這么去做,病人可能會反過來告醫生超出技術標準操作、違反診療規范。”孫東東說。
孫東東對杜玉堂以手術方式治療肉芽腫性乳腺炎持審慎態度,認為必須經同行的專家鑒定之后才能評價,因為這個手術操作只有幾年時間,做過手術的病例也才兩百例,它可能的后果目前仍未顯現出來。“醫學需要很長的時間來觀察療效,但如果是成熟的技術,很快就能推廣開來。”
“其實在國外,醫生的自律最重要,制度其實對于沒有知識的人往往作用非常大,但是一旦進入專業領域,幾乎是社會外的世界。想想誰可以監督無影燈下腹腔內醫生的手呢?”在采訪的最后,王岳對記者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