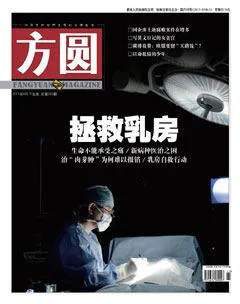上陣父子兵的法學家
大多數法學家的子女,似乎并沒有選擇這個充滿是非的職業
世襲制古來有之,老子皇帝、兒子太子,代代相傳家天下。但歷史總是驚人相似,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模式:開國皇帝英雄、末代皇帝昏聵,祖上的大好基業傳到實在平庸的一代,便亡了國。商場上也有子承父業、發揚廣大的,但多數都是“富不過三代”,家族生意要么零落凋敝,要么被迫成為非家族經營,更有敗家子,坐吃山空,淪落街頭。雖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遺傳基因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世易時移,也無法保證永遠的王侯將相。虎父犬子的例子,相信不用我舉,讀者也能信手拈來。
但是,環境對于人還是有影響的。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不但與老鼠的基因有關,還跟小老鼠所生長的環境有關。家庭環境對于每個人的成長都起著關鍵的作用,先天有利的條件至少能為這種職業傳承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且前代的資源積累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后代的擇業傾向。當前人創造的便利的條件已經為后人鋪平了道路時,后人的選擇和成功似乎都在情理之中了。例如,美國歷史上的亞當斯父子,父親是美國第二屆總統,兒子是第六屆總統,有這么偉大的父親在,好像不成功都很難。而布什父子更是現身說法的一個例子。不過,在法學家的歷史中,這樣上陣父子兵的事情,卻很少有人知道。
最著名的父子法學家可能就是馬克思,他的祖父、伯父、父親都是法學家,馬克思本人也在波恩大學、柏林大學攻讀多年法學。還有,德國的費爾巴哈父子都是著名的法學家。現代的著名人物則包括理查德·波斯納和其兒子埃里克·波斯納,后者跟他父親一樣,成為了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教授。還有三代都是法學教授的例子:賽耶(James Bradley Thayer)1873-1902年在哈佛大學法學院任教授,他的兒子后來成為該院的教授(1910-1915年),并當過主任,他的孫子也是該院教授(1935-1945年)。我們幾乎可以猜想到,當爺爺輩的賽耶和父親輩的賽耶把自己的法律圖書傳給小賽耶的時候,他們的目光中飽含了多少期許。對于小賽耶而言,這當然也是一條成本最小的成功之路。
我國的這種例子,我所知道的并不多。從近代來看,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學家伍廷芳和伍朝樞是不大為人所知的父子法學家。民法學教授佟柔的公子佟強在北大法學院任教,則可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個現代的例子。其他的就不知其詳了。蓋因中國法學研究之發展,本來時間就短,尚未有學術積累,一些老一輩的法學教授對于以法學為業也是心有余悸,故其子女從事法學教育和研究的,慎之又慎。
根據我的觀察,一個職業能通過家族傳承,表明了該職業的職業化程度。就像古代很多絕技,都只是傳兒不傳外,而現代家庭教育,也會影響到子女的職業傾向。如果法學是一個非常受人尊崇的職業,做父母的肯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子女,但是現在我發現的情況恰恰相反。大多數法學家的子女,似乎并沒有選擇這個充滿是非的職業,甚至家庭也不鼓勵選擇這個職業,他們便轉向了工程或者科學的研究。
因此,至少在目前來看,尚沒有產生這種父子法學家的環境。現在成名的中青年法學家,父輩都是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遭受過挫折的,他們的子女都是在“重理輕文”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于是,法學家成為了孤立的個案。這從另一個方面也反映了法學教授的職業化程度并不高。
現在中國的自然科學已經不乏大家,但是社會科學方面實在是后繼乏人。學術傳統的傳承就像子承父業一樣,總要老爸留下一些比較專業化的技能,而不是連他自己也捉摸不定的玄學。如果沒有深厚的學術積累以及進行這種積累的習慣,我們就如同踩在浮萍上,沒有成就感,也沒有安全感。當法學缺乏了研究的傳統,就變成了一項沒有激情的技術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