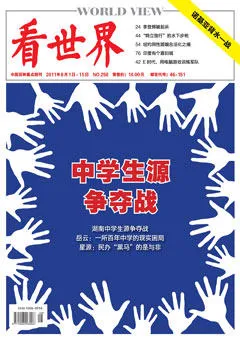史沫特萊的中國足跡
2011-12-29 00:00:00于則
看世界 2011年15期


“由于我的心靈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寧,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史沫特萊
“美國姑娘,赤色危險人物”
作為一位美國記者和作家,1892年出生的史沫特萊在她37歲那年寫出了她最為優秀,也最為出名的小說《大地的女兒》。
早在童年,她和家人搬到科羅拉多州的特立尼達,并目睹了1903年至1904年美國煤礦工人的罷工事件。這時她的心中,已經埋下了激進的種子。17歲那年,史沫特萊通過了全縣教師的考試,并在她家附近的農村學校任教一個學期。
后來她去了德國,她花了幾年時間在那里研究涉及各種左翼的問題。1929年,她完成了她的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然后踏上了去上海的路。
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等待被邀請前往延安。在這期間,駐守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5天以后,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之后,并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英語廣播,以評述西安事變的發展狀態。她的報道引起了不小的騷動,從此她被永久貼上了“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的標簽。甚至有人認為她是無賴。
美國報紙說:“她背后有龐大的軍隊”,“美國姑娘,赤色危險人物”,“美國婦女幫助中國人叛亂”。美聯社在一篇很長的背景介紹中,說“從前的一個美國農村姑娘將成為千萬黃皮膚人的實際上的‘白膚女皇’”。
延安使她興奮
1937年1月,史沫特萊正式接到共產黨的邀請訪問延安。她的公開身份是到前線去做戰地救護工作。
到達延安的當天晚上,史沫特萊便與兩位朋友一塊去見朱德將軍。史沫特萊在中國的幾年里,從報紙上讀到過太多有關朱德的消息。這些消息,對他的稱謂,并不那么好聽。因此,在史沫特萊最初的想象里,她將見到的朱德,一定是個“堅強英勇、脾氣暴躁的革命者”。
但她見到的朱德卻是“五十多歲了,相貌和藹可親,額角布滿皺紋。他看起來確像紅軍之父。他滿面春風,連連對我說歡迎,并向我伸出了雙手;我用雙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臉頰左右親了一下”。在后來,她與朱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并征得朱德的同意,撰寫了他的傳記。
在延安,史沫特萊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進行了多次交談,她的手提式打字機一直響到深夜。她給予毛澤東以高度評價;而她稱周恩來是一位學識淵博、閱歷深廣、毫不計較個人的安福尊榮、權利地位的卓越領導人。
在采訪和寫作之外,史沫特萊還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圖書管理員,負責擴展延安窯洞圖書館外文書籍。她努力工作以吸引外國記者來到延安,并發動過一場滅鼠運動。她的住處就出現了私人性質的娛樂晚會。有了留聲機和唱片,當然就少不了要跳交際舞。
據史沫特萊回憶,“有時候,我給毛澤東寫一個‘請即來一談’的便條,他很快就來了,手里提著一袋花生米。于是外國朋友引吭高歌,中國主人拍掌擊節,歌罷由中國主人們或唱歌或講古,窯洞滿座,談笑風生,一時成為樂事。”
史沫特萊回憶:“在延安的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人言可畏,群情側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時,我居然謝絕了他。他指責我怕事,說道:‘我同封建主義斗了半生,現在還不想罷休!’我只好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和他跳了一次……”
延安使她興奮,延安使她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她強烈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告訴她,她應該留在黨外,以便與在外面和國外做更多的工作。她聽后感到極為痛苦和傷心,放聲大哭起來……
軍旅中的史沫特萊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隨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萊在準備隨部隊開赴前線時,不慎從馬背上摔了下來,背部受傷,推遲了行期。10月,史沫特萊養好了傷,隨身攜帶了打字機、照相機和簡單的行李,赴八路軍抗敵前線采訪。她很快趕上了駐扎在太原的八路軍,然后到達北部山區的八路軍總司令部,成為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隨八路軍總部轉戰各地,史沫特萊與八路軍戰士同吃同住,她關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進了與他們的感情。史沫特萊與八路軍相處不到半年,便深深地愛上了這支部隊。她甚至說:“離開你們,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為了這支部隊,史沫特萊甚至于1938年到了漢口,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和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份,一面救護傷員和難民,一面報道中國抗戰,并向世界性組織呼吁救援。
在漢口,史沫特萊多次訪問美國大使館,向大使和武官介紹八路軍的活動。她多次接觸約翰·戴維斯、佛蘭克多恩、史迪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