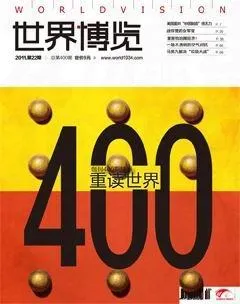主義下的婚姻和人生
上個月,李陽的外籍太太在微博上發布了被家暴后的照片,輿論一片嘩然,諸多譴責指向李陽。隨后李陽接受了采訪,其中一些言論令人驚訝,比如他承認結婚不是因為感情,而是“為了研究家庭教育”,甚至在柴靜問他怕不怕女兒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實驗品”時,李陽回答:“挺好啊,有好的實驗品和不好的實驗品……小白鼠不是拿來實驗的嗎?”
這些談話令大部分人感到氣憤。不過依我看,李陽雖無理,卻十分坦誠,他這些不中聽的話其實是不少人的心聲。大大咧咧承認為了研究家庭教育而結婚固然討厭,可全中國有多少姑娘不也是為了套房子才結婚的么?在她們心里,婚姻和房子必須是有牢固聯系的,就像李陽心中婚姻和研究教育也有必然聯系一樣。
同樣,直接說“我家孩子就是實驗品”當然挑戰大眾,可大眾里有多少是以朗朗父親為榜樣,逼孩子每天刻苦練琴6小時,試圖在中國幾百萬琴童里殺出一條血路?這些孩子只是沒明說的實驗品罷了。總的來說,大眾和李陽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剝削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為自己謀利。
李陽代表的價值觀,其實是非常流行的一種觀念,就是“唯有用論”。在以李陽為代表的部分人心里,世界上只有一種衡量標準:對我有用,或對我無用,其余沒有什么可尊重、值得仰望或需要忌憚的。比如學英語是“有用的”,因為英語學好了可以賺錢,而語言背后整個世界的文化和文明則是“無用的”,對賺錢沒有意義。
這種市儈到骨子里的價值觀可以稱為“極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這個詞翻譯得并不準確,梁文道認為應該翻譯成“效益主義”更好。“效益主義”追求盡可能地把利益最大化,僅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并無善惡上的不妥。但萬事就怕做過頭,一個人要是在利益增值上扎得太深,一切都以“對自己是否有利”為唯一標準時,什么法律道德、社會規則、他人權利,基本都是可以無視的。
只苛責李陽個人的道德水準沒什么意義,畢競他這種心態和社會的大環境有直接聯系。極端功利主義在這里既有深厚的土壤,又趕上了很好的時機——整個世界都在宣傳唯一的標準:成功,因為成功的人往往能跨過法制道德等無數道圍欄。而不成功的草根們,無論怎么小心翼翼都很難保住自己的利益。在這樣的恐慌下,人想不功利都難。這種大環境下產生扭曲的婚姻和家庭,并不算是多意外的事情。
“馬桶騎士”請注意/龍隱
一般人進了廁所,其他能干的事情就不多了。不過廁所是部分古今中外思想者的樂園。宋時有人“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歐陽修更說:
“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
在“廁讀”方面,作家亨利·米勒首屈一指。他確實在廁所里完成了一些名著的閱讀,而且堅持認為其中的一些作品,比如《尤利西斯》的妙處是在其他地方無法完全領悟的。米勒認為只有少量的書籍和雜志才適合廁所“待遇”,其中他挑出了《大西洋月刊》。他甚至告訴別人什么樣的廁所更適合閱讀:如果要閱讀《拉伯雷》,他建議找個簡陋的農村茅房:“在玉米地的茅房里,新月的銀色月光透著門縫照了進來。”
在以色列醫療機構工作的羅恩·紹烏爾最近了做了關于“廁讀習慣”最科學的一次研究嘗試,他收到了499份男男女女的完整調查問卷,年齡從18到65歲不等,其中有待業人員,也有學生、建筑工人和學者,一些來自農村,也有一些居住在城市里。超過一半的男性(64%)和41%的女性坦言自己經常在上廁所的時候讀書,而且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讀物就是“伸手可及的東西”,一般而言就是指報紙。
在豆瓣的“馬桶讀吧”小組,“馬桶騎士”們交流多年的廁所讀書經驗,討論在廁所最適合讀什么書、有何注意事項。有位“騎士”說:一是不宜讀“黃書”,因為這會引人走火入魔,產生其他沖動;二是最忌令人愛不釋手的通俗讀物,比如金庸的武俠小說。“俺第一次看《天龍八部》,一時大意帶入了廁所,結果‘廁所方一刻,世間已半天’,待清醒過來已如同中了‘十香軟筋散’,不但沒站起來,還一屁股栽進馬桶。”
當然了,對如廁讀書也有人語帶譏諷,清代學者郝懿行說,“入廁脫褲,手又攜卷,非惟太褻,亦苦甚忙,人即篤學,何至乃爾耶。”
紹烏爾的研究暗示,“廁讀者”更容易患上痔瘡,不過紹烏爾總結說,“廁讀”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它可以打發你的無聊,而且基本上是無害的。最重要的是,在那里絕對不會再有人在身旁喋喋不休或指揮你去干這干那,廁所是真正的清靜樂土啊。
(龍隱,出版工作者,現居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