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葡澳時(shí)期澳門社會(huì)治理的法團(tuán)主義模式
馬志達(dá)
(北京大學(xué) 政府管理學(xué)院,北京 100871)
論葡澳時(shí)期澳門社會(huì)治理的法團(tuán)主義模式
馬志達(dá)
(北京大學(xué) 政府管理學(xué)院,北京 100871)
近年來,研究澳門的學(xué)者用法團(tuán)主義理論對葡澳政府的管治進(jìn)行解釋,指出葡澳政府的管治模式實(shí)際上是法團(tuán)主義模式。①參見婁勝華:《轉(zhuǎn)型時(shí)期澳門社團(tuán)研究》,第9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一、葡澳時(shí)期法團(tuán)主義的實(shí)踐內(nèi)容與經(jīng)驗(yàn)
1849年葡督亞馬留將中國駐澳官員逐出澳門,澳門的管治權(quán)完全落入葡萄牙殖民者手中,葡萄牙開始在澳門實(shí)行殖民統(tǒng)治。但是,由于受語言文化、風(fēng)俗習(xí)慣等諸多差異的阻隔,葡澳殖民當(dāng)局對華人事務(wù)直接管治的努力遭受挫折,迫使葡澳政府轉(zhuǎn)而尋求間接方式來實(shí)現(xiàn)對華人事務(wù)的管理。葡澳當(dāng)局的間接管治模式可以稱做為“軟殖民體制”。“軟殖民體制”無法依靠自身力量和能力完成對一個(gè)多元異質(zhì)社會(huì)的嚴(yán)密控制,從而在政府與居民之間留下了大片管治空間或縫隙,需要一種體制外力量去填補(bǔ)。在澳門,這種體制外力量就是各種各樣的社團(tuán)組織。通過這種方式,澳門實(shí)現(xiàn)了葡澳當(dāng)局自上而下和社團(tuán)自治自下而上治理的有機(jī)結(jié)合,維護(hù)了社會(huì)秩序。
(一)供給部分公共品
長期以來,澳門實(shí)行自由港和自由市場經(jīng)濟(jì)政策,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向社會(huì)提供的公共產(chǎn)品和服務(wù)僅限于國防、司法秩序、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等極其有限的范圍,基本不介入社會(huì)民生事務(wù),并沒有提供基本社會(huì)保障與社會(huì)福利。為此,澳門許多華人社團(tuán)都致力于向市民或會(huì)員提供教育、醫(yī)療、賑濟(jì)等公共物品或準(zhǔn)公共物品,如同善堂、鏡湖醫(yī)院慈善會(huì)等社團(tuán)所提供的慈善、賑濟(jì)、醫(yī)療服務(wù);中華教育會(huì)、工聯(lián)、中華總商會(huì)、同善堂、鏡湖醫(yī)院慈善會(huì)等社團(tuán)所提供的“義學(xué)”與免費(fèi)或低收費(fèi)的教育服務(wù);街總、工聯(lián)、婦聯(lián)等社團(tuán)提供的社區(qū)服務(wù)、托兒服務(wù)、家庭服務(wù)、老人服務(wù)、臨屋服務(wù)等多項(xiàng)社會(huì)服務(wù),等等。直到1980年代,葡澳政府才開始大規(guī)模地進(jìn)入社會(huì)福利領(lǐng)域,建設(shè)公共設(shè)施,資助民間社團(tuán)發(fā)展社會(huì)化服務(wù),進(jìn)入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相互彌補(bǔ)提供公共服務(wù)的新階段。
(二)表達(dá)與維護(hù)會(huì)員利益
澳門許多社團(tuán)章程,哪怕是僅有極其簡單的條文,也會(huì)列有“會(huì)員權(quán)益保障”的內(nèi)容,如澳門各區(qū)街坊會(huì)的宗旨是“團(tuán)結(jié)坊眾,服務(wù)社群。發(fā)揚(yáng)人助自助精神,關(guān)心社會(huì),維護(hù)居民合法權(quán)益,辦好有關(guān)文康、福利等事業(yè)”②見《澳門街坊會(huì)簡介大綱》(未注明日期),該文件注明“街坊總會(huì)”宗旨與各區(qū)街坊會(huì)宗旨相同,查“街總”章程,雖無明確字樣,但含“權(quán)益保障”之意。。尋求社團(tuán)提供集體性的權(quán)益保障是生活在葡澳政府管治下的多數(shù)華人的共同選擇,開展會(huì)員以及相關(guān)人的權(quán)益保障成為澳門許多華人民間社團(tuán)的基本活動(dòng)。通過這種權(quán)益表達(dá)與維護(hù)活動(dòng),使得社團(tuán)可以成為凝聚不同階層利益的載體,實(shí)現(xiàn)利益維護(hù)的集體化,有助于利益協(xié)商機(jī)制的形成,避免社會(huì)原子化利益維護(hù)的散亂甚至對抗格局的出現(xiàn),從而實(shí)現(xiàn)政府對社會(huì)的有序控制。
(三)社會(huì)整合
葡澳時(shí)期,澳門大量的社會(huì)矛盾都是通過社團(tuán)予以化解,從而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有序發(fā)展。社會(huì)調(diào)解是澳門民間社團(tuán)社會(huì)整合功能的重要反映。在澳門,華人社團(tuán)承擔(dān)的社會(huì)調(diào)解涉域廣泛,個(gè)人的、家庭的、群體的、官民之間的,甚至介入中葡兩國之間的外交沖突。不同層次的社會(huì)矛盾與沖突可以由相應(yīng)層次的民間社團(tuán)調(diào)解。社團(tuán)內(nèi)部會(huì)員之間的糾紛通常可以在社團(tuán)內(nèi)得到協(xié)調(diào),相同利益群體內(nèi)不同利益主體間矛盾可以由功能區(qū)域內(nèi)社團(tuán)間相互協(xié)調(diào)裁判,不同社會(huì)利益群體之間的糾紛(如勞資糾紛等)可以由功能區(qū)域內(nèi)代表性社團(tuán)進(jìn)行調(diào)解,同樣,不同性質(zhì)的社會(huì)不穩(wěn)定根源可以由相應(yīng)社團(tuán)去化解。根源于貧困與災(zāi)害的,由慈善性社團(tuán)去化解;根源于現(xiàn)代化的,由現(xiàn)代性社團(tuán)(如行業(yè)性協(xié)會(huì)等)去化解;根源于社區(qū)發(fā)展的,由社區(qū)類社團(tuán)(如街坊會(huì))去化解;根源于合法性的,由代表性利益團(tuán)體去化解。①參見婁勝華:《轉(zhuǎn)型時(shí)期澳門社團(tuán)研究》,第339、318頁。
二、葡澳時(shí)期法團(tuán)主義治理模式的局限
在葡澳政府時(shí)期,政府與社團(tuán)的協(xié)商主要局限在政府與執(zhí)政盟友之間(即政府與核心功能性社團(tuán)之間)的聯(lián)盟協(xié)商,這就產(chǎn)生了協(xié)商在功能、政治與社會(huì)層面的局限性。在功能上,協(xié)商主要是對核心功能性社團(tuán)利益的協(xié)調(diào)與庇護(hù),是盟友之間的利益分肥;在政治上,協(xié)商主要體現(xiàn)為盟友交換,公民與邊緣社團(tuán)參與不足,民主性不高,削弱了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和對政府的信任度;在社會(huì)層面,政府是自上而下的權(quán)威主導(dǎo),社團(tuán)其實(shí)是政府的代理人與辦事機(jī)構(gòu),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dá)功能得不到發(fā)揮。
(一)民意回應(yīng)性不高
在葡澳政府時(shí)期,政府與社團(tuán)的關(guān)系是一種差序格局。政府與部分功能社團(tuán)結(jié)成執(zhí)政聯(lián)盟關(guān)系,功能性代表社團(tuán)是連接政府與社會(huì)成員的中介性社會(huì)單位,如工商界的中華總商會(huì)、勞工界的工聯(lián)、教育界的中華教育會(huì)等。在葡澳時(shí)期,政府與社團(tuán)的關(guān)系成為一種“蛛網(wǎng)結(jié)構(gòu)”。④參見婁勝華:《轉(zhuǎn)型時(shí)期澳門社團(tuán)研究》,第339、318頁。“蛛網(wǎng)結(jié)構(gòu)”實(shí)際上是一種權(quán)力與利益分配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的政府與社團(tuán)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中,政府對社團(tuán)的權(quán)力授予與利益輸送行為首先是在政府的功能性社團(tuán)等核心社團(tuán)進(jìn)行,其次才是次級(jí)功能性社團(tuán)等非核心社團(tuán)等組織,呈現(xiàn)出先后、層次、程度等的不同。這導(dǎo)致政府的地位授予與資源輸入在社團(tuán)間的不均衡分布,政府與社團(tuán)關(guān)系體現(xiàn)出“政府——核心社團(tuán)”的緊密聯(lián)系與“政府——核心社團(tuán)——非核心社團(tuán)”的松散或間接聯(lián)系。因此,政社合作局限在小范圍的親政府核心社團(tuán)協(xié)調(diào)與利益整合,而對于那些在政府與社團(tuán)關(guān)系“蛛網(wǎng)結(jié)構(gòu)”邊沿或外圍的社團(tuán)以及不為社團(tuán)所代表的大眾的利益,則被忽視或漠視。囿于這種差別化的交換關(guān)系,導(dǎo)致政府與社會(huì)的合作局限在功能性社團(tuán)間的利益協(xié)調(diào),不能反映社會(huì)公眾利益訴求,政府的民意回應(yīng)性較差。社團(tuán)越來越像政府機(jī)構(gòu)而顯得官僚化,社團(tuán)離政府越來越近而離社會(huì)越來越遠(yuǎn)。
在界別功能性社團(tuán)主導(dǎo)的政社格局中,政府的施政主要反映部分核心功能性社團(tuán)的利益與價(jià)值(甚至是這些社團(tuán)領(lǐng)導(dǎo)人的利益與偏好),而非主流民意,葡澳政府的公共政策的民意回應(yīng)性較弱。澳門的重大政策并不來自民眾、民意,澳門居民也不在政府中占據(jù)一席之地,更缺乏向政府表達(dá)意志的政府通道。這也導(dǎo)致澳門華人市民的政治意識(shí)和參與程度一直偏低,對政治體制的組織運(yùn)作關(guān)心和認(rèn)識(shí)不足,由此所導(dǎo)致的是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和疏離感。同時(shí),市民對政府的滿意度也不高,從而削弱了政府的行政合法性。
在回歸前澳門所做的一次社會(huì)調(diào)查中,澳門市民對葡澳政府的滿意程度僅為22%,而36%的市民則表示不滿。
因此,為提高政府施政的民意回應(yīng)性,法團(tuán)主義模式不應(yīng)是差序格局,應(yīng)該從社團(tuán)合作走向社會(huì)合作,使施政方針真正反映社會(huì)主流民意。
(二)削弱公民政治效能感
吸納華人富豪代表進(jìn)入政府,與其形成執(zhí)政聯(lián)盟關(guān)系,是葡澳當(dāng)局實(shí)行以華治華、葡華共治的治理策略。而華人代表為了維護(hù)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接受葡澳當(dāng)局的策略,采取合作的行為。華人參與澳門政治的過程呈現(xiàn)出從完全排除在外到個(gè)別性吸納、從有限的小規(guī)模參與到全體華人取得公民權(quán)的漸進(jìn)性特征。澳門華人精英代表呈現(xiàn)固化的趨勢,即一旦成為華人代表,將擁有越來越多的行政與組織資源,這些資源又進(jìn)一步固化其精英代表的角色。同時(shí),華人精英只能以社團(tuán)為渠道參與政治,不能以個(gè)人方式參與政務(wù)。這種以社會(huì)團(tuán)體為依托的政治吸納方式有效地保證了政治參與的秩序性,但不利于個(gè)人利益的多元化表達(dá)。調(diào)查顯示,在這種社團(tuán)聯(lián)盟政治的格局中,作為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受到嚴(yán)重的削弱,公民對影響政府信心不足,從而削弱了其民主意識(shí)與行動(dòng)能力。
1991年在澳門進(jìn)行的問卷調(diào)查(您覺得您有能力去影響澳門政府的決策嗎?)結(jié)果顯示,澳門人對他們能否影響政府決策完全沒有信心。這種對政府決策表示的無力感(powerlessness),明顯影響澳門人的實(shí)際政治行為,如對政治參與過于被動(dòng)及欠缺積極性。8年過后,澳門人的政治效能感改變不大,如表1所示。

表1 澳門人的政治效能感:您覺得您有能力去影響澳門政府的決策嗎?(%)
(三)降低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度
葡澳當(dāng)局的政社合作實(shí)行的是親疏有別的盟友合作,聽取的實(shí)際上是執(zhí)政聯(lián)盟社團(tuán)的利益訴求,施政方針反映的大多是聯(lián)盟社團(tuán)的利益與價(jià)值。對于社會(huì)公眾來說,這種行政過程可以通俗地歸納為“小圈子政治”或“圈內(nèi)人分肥”。對于這種圈內(nèi)人利益分配的機(jī)制來說,邊沿社團(tuán)和社會(huì)公眾既不滿也無可奈何,催生政府是少數(shù)人的政府的觀念,從而降低對政府的信任度。調(diào)查顯示,對于葡澳政府的信任度,只有三成的受訪者明確表示信任葡澳政府。①鐘庭耀、馬嘉莉、李博儀:《港澳兩地回歸前民情比較》,載吳志良、楊允中:《澳門2000》,第270頁,澳門基金會(huì)2005年版。
出于對葡澳政府的不信任以及缺乏進(jìn)入主流話語渠道的合法性機(jī)制,華人在政治的表達(dá)上處于沉默階段,首次立法會(huì)選舉共計(jì)登記選民3 647名,華人不及200人。正如該屆澳督李安道所言:“這個(gè)立法會(huì)的組織,基于各種不同的原因,仍未包括澳門社會(huì)的所有階層。”②載《市民日報(bào)》1976年7月16日第1版。(其實(shí)未包括的主要是華人社會(huì)。)到1980年的第二屆選舉,登記選民總數(shù)也僅有4 195人,約為澳門人口的1/8,參與率之低尤其是華人冷漠參與的事實(shí)說明澳門華人個(gè)體依然對政府持不信任態(tài)度或者遠(yuǎn)離政治,并未融入政治生活表達(dá)利益訴求。這說明,作為政府的代表的聯(lián)盟社團(tuán)沒有得到市民的政治信任以及社團(tuán)與市民間的互動(dòng)仍未能得到充分發(fā)展。其中一個(gè)問題是圈內(nèi)協(xié)商的封閉性減弱了決策的民主性,它只能促成圈內(nèi)人的商議與互動(dòng)。③婁勝華:《社團(tuán)與政府:策略性合作伙伴關(guān)系》,澳門日報(bào),2007-08-22。
信任感的缺失與社團(tuán)結(jié)構(gòu)及其利益調(diào)整的綜合作用,使聯(lián)盟社團(tuán)的社會(huì)協(xié)調(diào)能力大為下降,邊緣社團(tuán)的社會(huì)行動(dòng)不斷增加。新的利益關(guān)系與利益矛盾導(dǎo)致原來不同社團(tuán)之間緊密的政治合作關(guān)系出現(xiàn)調(diào)整與分化。
三、結(jié)語與討論
法團(tuán)主義的有效性與社團(tuán)的自主性、獨(dú)立性關(guān)聯(lián)密切。從一般意義上說,社團(tuán)等非營利組織的產(chǎn)生是社會(huì)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社會(huì)利益分化和社會(huì)民主推進(jìn)的必然結(jié)果。因?yàn)樯鐣?huì)利益分化和社會(huì)政治的民主化,必然會(huì)導(dǎo)致社會(huì)力量的上升,而非營利組織正是社會(huì)力量的重要載體。但是,在非營利組織發(fā)育和發(fā)展過程中,所在國家或地區(qū)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政治結(jié)構(gòu)對其組織功能的實(shí)現(xiàn)或發(fā)揮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在那些社會(huì)力量和社會(huì)自治傳統(tǒng)較強(qiáng)的國家或地區(qū),由于政府與社會(huì)的二元緊張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形成,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政治結(jié)構(gòu)有利于非營利組織的成長與發(fā)展,因而具有較強(qiáng)的獨(dú)立性,其志愿性、自治性和自決性也較強(qiáng)。在這些國家或地區(qū)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較為有效。
但是,葡澳時(shí)期的大多數(shù)功能性社團(tuán)受控于政府,在組織合法性、資金等方面對政府形成依賴,自身的獨(dú)立性較差。實(shí)際上,社團(tuán)功能呈現(xiàn)“擬政府化”的特征,并具有行政化色彩。社團(tuán)的行政化是指該組織行使的職能大多為政府職能的延伸或政府交辦的事務(wù),自身自主性和主動(dòng)性不夠;組織內(nèi)部的組織結(jié)構(gòu)等級(jí)制明顯,官僚化色彩濃厚;社團(tuán)與政府的關(guān)系為從屬關(guān)系,成為政府的“一條腿”。在這樣的政社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中,政府是社團(tuán)的上級(jí),社團(tuán)是政府的傳聲筒,這必然削弱社團(tuán)在會(huì)員甚至市民利益與價(jià)值表達(dá)的功能,導(dǎo)致片面追求迎合政府意志,而對基礎(chǔ)群眾的基本訴求和權(quán)利保障考慮不到,使公眾對社團(tuán)的滿意度和支持率降低,從而降低了法團(tuán)主義模式在當(dāng)時(shí)澳門社會(huì)整合上的有效性。
馬志達(dá)(1974—),男,廣東南海人,北京大學(xué)政府管理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
2011-04-01
C916
A
1000-5455(2011)03-0154-03
【責(zé)任編輯:于尚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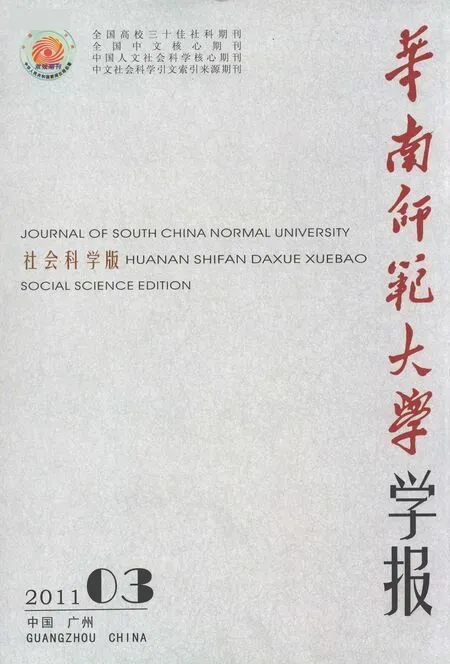 華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1年3期
華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1年3期
- 華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回歸后澳門學(xué)校體育課程的改革路向
- 流浪兒童社會(huì)支持網(wǎng)絡(luò)研究——基于廣東省少年兒童救助保護(hù)中心的考察
- 青少年網(wǎng)絡(luò)成癮研究現(xiàn)狀及未來展望
- 縱橫優(yōu)化模式下行政服務(wù)流程的逆向度選擇——佛山創(chuàng)新經(jīng)驗(yàn)的啟示
- 從政治動(dòng)員到制度建設(shè):珠三角一體化中的政府創(chuàng)新
- 東亞產(chǎn)業(yè)關(guān)聯(lián)與區(qū)域貨幣金融合作的進(jìn)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