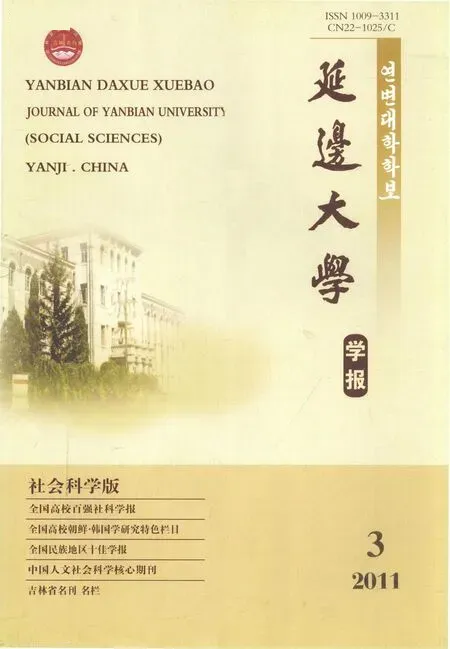論朝鮮朝后期家庭小說中父權家長形象的塑造
李 娟
(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吉林延吉133002)
在朝鮮朝后期的家庭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由兩大系列構成:一類是作為家庭支柱的男性形象系列,一類是作為家庭附庸的女性形象系列。在這兩類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作者表現出了在家庭生活中一個自然人因個體性別、家庭地位的不同,而使其個體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同處境以及因社會文化對性別個體的要求而產生的性別文化差異。這些形象包括了父子(女)、夫妻、妻妾、妾與妾、繼母與子女以及同父異母子女等相互間復雜的家庭內部的人際關系。而在這些形象中,父權家長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父權家長形象根植的宗法父權體制
父權家長形象的重要地位是和父權(夫權)在朝鮮朝時期的封建家庭中至高無上的權力有著密切的關系。朝鮮朝時期的社會也是和中國一樣,是一種封建宗法父權體制,這種體制集合了道德、法律、權力、欲望于一體。男性成員通過家庭婚姻、社會、政治、文化、教育和經濟等組織,在家中行使統治權力,對女性進行壓制。在宗法父權秩序中,男尊女卑,男外女內,男性以主體身份進入宗法體制,女性則被放置在邊緣地位之中,不是完全被排除在體制之外,而是收編在體制之內的邊緣位置上,置于婚姻家庭秩序之內。女性喪失主體自我的現象,在文化傳承上有其傳統性別規范的背景。由于朝鮮朝是家國同構、三位一體的宗法社會,因此,“父權家長”這個原型符號可以被擴展為家長、族長,甚至君主。作為一家之長的父親,實際上是擴大了性別與輩份的“父親”,族長實際上是指增加了族權,或許還有神權的“父親”;君主是指增加了君權的“父親”。所以,在有關家庭主題的敘事文學作品中,代表一家之長的“父權家長”形象,實際上既包含了父親,也包括了掌管家庭的丈夫。
朝鮮朝社會一直以儒家思想為正統,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朝鮮朝時期的儒家文化是一種父權家長制文化,它強調了一種對父權家長的絕對敬畏。因此,無論在父子(女)關系中,還是夫妻關系中,父權家長是處于絕對統治地位的,子女沒有獨立性和自主權,必須為父親而活。家庭的其他成員也必須遵從于父權的統治,服從于父權的權威。正如孔子反復強調的:“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父之道”。[1]也就是說,“孝”的核心是服從父母及長輩的意志,民間廣泛地在“孝”字后面加一個“順”字就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血緣倫理和社會倫理的雙重屏障,使得子女在感情和責任上均臣服于父親。“父親”作為專制家長,憑借舊家族制度和傳統觀念所賦予的權力,像君主一樣統治著屬于自己的“家庭王國”。專制家長們,不僅把握著整個家庭的經濟大權,而且還掌握著所有家庭成員的前途與命運。
作為中國儒家文化的傳承者,朝鮮朝后期家庭小說的作家們對“父權家長”的態度是復雜的。一方面,由于社會的變遷,人們對于家庭觀念的改變,使家庭關系面臨著變異和重構。另一方面,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兩班士子們,又存在著深深的“戀父情結”,傳統士大夫的觀念、責任感等,兩者的沖撞結果,使父親處在了中心的位置。原本“父權家長”在這些人的內心深處永遠是“家”的核心和代表,父權秩序是不可侵犯的,這就形成了:一方面是對父權家長形象的仰視,另一方面則是展現父權家長面對社會制度和文化沖擊之下的軟弱與無力。一家之長的地位被動搖,以父(或夫)為核心的傳統家庭模式被解構,與之相連的崇尚孝道的家庭倫理道德也被顛覆,而父權家長的存在,則成為關于“家”喻言的表述核心。
二、父權家長形象構建的家庭倫理觀念
在朝鮮朝時期人們的生命意識中,不僅認為家是生命的最高準則,一切必須服從家,一切必須為了家,而且認為在自然血緣的“家”中從父母,在社會血緣的“家”中臣于君王。在人們的意識中,血緣是不可選擇的、萬古不移的權威,家也就是不可舍棄與離異的生存依托。家是人的家,人是家中的人,被內化、被規定了,生命行為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家”。“家”是一個等級制的實體,這種等級觀念是由具體的親屬制度來實現的,與親屬稱謂系統相匹配的“五服制”推演到親屬之外,涵蓋整個社會的人際關系,形成了“五服社會”。人們特別看重人際間的血緣關系,人由血緣構成的等級是合理的、公平的,這樣就完成了對社會等級制度的接受。家庭中的“父”或“夫”是決定家庭成員命運的“圣旨”,每個人都在一個等級森嚴的家庭關系之中遵從忠孝觀念和禮法規定。“大家庭小社會”,大的家庭、家族儼然就是封建宗法社會的一個縮影。在宗法父權制的朝鮮朝倫理社會中,父權家長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作為以家庭生活為創作母題的家庭小說中,有關父權家長形象的塑造是極為豐富多彩的。在這類形象中,不少形象是作為觀念符號出現的,但角色的相同不等于性格的相同,大多數父權家長形象的塑造還是極具個體特性和文化意蘊的。
三、朝鮮朝后期家庭小說文本中的父權家長形象
產生于朝鮮朝后期的家庭小說,主要以《謝氏南征記》為發端,通過對家庭所負載的倫理道德、愛情、親情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揭示,形象地塑造了四類父權家長的形象。
(一)在矛盾中彷徨的家長
對內打理好家庭,對外效忠于國家的典型的家長形象,是朝鮮朝社會制度和儒家文化規范的理想家長。家長作為家庭權力的核心,應該處在家庭結構的中心點上以及深處矛盾與糾葛的原則立場中。但是在《謝氏南征記》中,卻描寫了一位儒家符號化人格與現實生活人情、人性相矛盾的家長形象。男主人公劉翰林是一位文采超群、有謙讓之德,同時重孝悌,做事慎重而且為人寬厚的儒家理想君子。他的文采和謙讓之德是通過他15歲在考取翰林編修后,上書皇上,請求再讀10年書后,再效忠皇上而交待的。對父親、姑媽等長輩的孝敬、孝順,體現了他儒家理想君子人格所遵從的倫理道德規范。但是,隨著故事的展開,在妻謝氏和妾喬氏之間發生家庭矛盾糾葛時,他卻是一個不辨是非、無能無奈的弱者形象。聽信妾喬氏的讒言,放縱喬氏使奸計陷害妻謝氏,并最終將妻子逐出家門,也招致自己被流放,差點遭暗算而死,弄得家破人亡。前后的對比較鮮明,明明是一個才德兼備、盡忠盡孝集于一身的理想君子形象,卻無力處理好家庭內部妻妾的矛盾紛爭,這里顯示出了“父權”在妾喬氏的積極“覺醒”與“反抗”中,漸漸失去其權威的一面,也變得無奈與無能了。
謝氏為了繼后嗣規勸丈夫劉翰林納妾時,劉翰林“疑其言或不誠,只是笑而不答”。后來謝氏將媒婆之言告訴翰林時,劉翰林卻說:“吾之置妾本不急,而夫人好意亦不可違,喬氏誠如此,宜娶來”。[2]結果劉翰林雖然很喜歡原配夫人謝氏,但是謝氏勸告其納妾繼后嗣的時候,裝作不得不接受的樣子。納妾的第一個目的是為了繼后嗣,但是劉翰林漸漸失去了聰明和重心,陷入到美妾——喬氏謀害謝氏的奸計之中。
喬氏的惡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剛剛嫁入到劉家的時候,曾受到劉家人的稱贊,并且受到劉翰林的寵愛,但是當謝氏也生下兒子之后,喬氏十分煩惱:“吾與彼容貌之美,無以加焉,而嫡妾之分顯殊矣。徒以我則生男彼則無子之故,能被丈夫厚待。彼今生子,而將為此家之主,我兒自然無用耳”。[2]由此可見,喬氏感到了危機,原本自己是出于繼后嗣的需要,被娶入劉家的,現在連繼后嗣的目的也被否定了,那今后自己的生存、自己所生兒子的處境……在當時嫡長子繼承制的朝鮮朝社會中,作為一個母親,一個沒有身份和多少家庭地位的妾,這些都是喬氏不得不去想、不得不去謀劃的。于是,為了自己,為了今后兒子在家中長子的地位,喬氏開始了自己罪惡計劃的實施。剛開始,喬氏在丈夫面前離間謝氏、陷害謝氏時,劉翰林還能清醒地認識到謝氏的賢淑,并且規勸喬氏:“……然性本柔順,必不害爾。爾無憂……”。結果在喬氏一次次奸計的“事實”面前,劉翰林的聰明也漸漸被蒙蔽,開始懷疑并遠離謝氏,最終逐出了賢德的妻子,并使自己也陷入苦難的境地。當所有的事實都擺在面前的時候,作為丈夫才開始反省自己,并慨嘆:怎么有臉去見自己的祖宗呢?內心儒家君子的理想人格形象又重新回到了現實,并占據了劉翰林的心。在劉翰林逐出謝氏之時,就是身邊的鄰居都慨嘆:“夫婦之際,豈不難哉!”文中雖然是鄰居們的感嘆,也是作者想要表達的觀點。這里面既有對妻子的要求,也有對丈夫的要求,謝氏是儒家理想妻子的典范,她不但為繼后嗣積極為丈夫求妾,不顧婆婆杜夫人的勸誡:“因一時的無子而納妾?妻妾是擾亂家中的根本,夫人怎么能自取禍害呢?這是萬萬不可的”。后來門客董清的出現,又使謝氏執意規勸丈夫:“要親君子而遠小人”。因此被皇陵廟娘娘稱之為:“與曹大家、孟德耀比肩”。劉翰林則不然,不僅惑于美色,還誤交匪人,導致幾乎家破人亡,作品中對此解釋為:“翰林亦君子之人,不幸早達,未及周知天下事理,天將降一時災禍以大警之”。最后,劉翰林從所有誤會中解脫,在重新獲取功名和名譽后,處罰了喬氏,找回了謝氏,一家團圓。可惜的是,在作品的結尾,劉翰林又納了許氏為妾,雖然又將許氏描寫為一位賢淑之女子,但劉翰林是否會吸取教訓,是否能真正處理好“一夫兩妻”的家庭生活秩序呢?
(二)害死子女的無能家長
這類父親的形象大多出現在朝鮮朝后期的繼母型家庭小說中。大多數都是由于前妻的過世,后娶進來的繼母和前妻子女之間的矛盾糾葛。
《薔花紅蓮傳》中描寫了一位恪守儒家倫理規范,缺乏對事實做出正確判斷的父親形象——裴武龍。平時對幼年喪母的前妻所生的兩個女兒偏愛有加,以致引起了繼母許氏的嫉妒。為了獲得丈夫對自己的愛、對自己所生兒子的愛,就開始謀劃著怎么除掉前妻所生的兩個女兒。當許氏的妒忌之心被裴武龍察覺到了之后,對于許氏的處理顯然是表現出一副封建家長的姿態,面色上很是不滿,并嚴聲告誡許氏說:“我們家本來很窮,是前妻張夫人從娘家帶來了很多財產,才使我們家變得富裕了,你現在豐裕的生活是得益與張夫人的恩惠,……而現在,你還要虐待她的兩個女兒,于情于理都難辭其咎。以后不許再這樣,應該倍加疼愛她們才是……”。[3]這些話沒有起到告誡和規勸的作用,反而使許氏心里覺得更加反感,背地里對兩個女兒的虐待也更變本加厲。
當許氏設計將剝去皮的老鼠放在女兒床上,誣陷女兒薔花懷孕墮胎之后,不知情的父親裴武龍在女兒出現了意外之后,態度陡然間大變。告訴許氏:“你看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能力我清楚,無論怎么處置我就不管了,你就看著辦吧!”從裴武龍的這番話和他的行動,我們看到了:一個兩班儒家教條的“君子”形象躍然紙上,一個重視體面和名譽的樣子頃刻間被刻畫了出來,不想調查,也不去了解情況,就拿出儒家禮法的規范去處罰自己的愛女。這時候,家門的顏面要比愛女的生命更加值得裴武龍去考慮,所以主動地讓后妻去處理這件事情。許氏也正中下懷,并在旁邊添油加醋地煽動:“我們裴氏家族雖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作為這村里的兩班,有這樣丟人的事,是家門的一大羞恥。如果這話泄露出去,不僅有辱家門,而且整個裴氏家族都抬不起頭來,他們三兄弟也會以獨身老死,怎么能讓這樣的事兒發生呢?”[3]裴武龍在聽完許氏的計劃之后,明明知道是要弄死薔花,但還是欺騙并命令薔花回姥姥家。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裴武龍的雙重人格:一方面作為父親一貫很愛兩個女兒,表現出慈父的一面;另一方面,在女兒出現了他意想不到的事故時,卻變成了一個全然不能夠明辨是非的父親,頃刻間露出了儒家“正人君子”的面目。也正因為如此,才被許氏窺見并利用。在這里慈愛的父親全然不見了,也不問問薔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把自己的女兒強硬地推向了死亡的境地。在薔花爭辯的時候,他還說:“你怎么能不聽父親的話,爭辯這么多呢,是要惹怒父親嗎?”
裴武龍比起“父親”要更加重視家門的體面和聲譽,他在這里表現出了回歸到封建父權家長的典型形象。為了家族家門連自己深愛的女兒也不會放過,并且連是非曲直都不問一句,就趕緊想草草了事,以免外傳有損家門聲譽。這一點證明了當時兩班社會的男性們,只重視體統而疏于把握事實真相的無能。是裴武龍的心腸軟弱,缺乏主體判斷能力,最終自己害死了疼愛有加的女兒。前妻的女兒之所以欣然接受死亡,是因為她把遵從父命視為孝,認為這是人倫之道。“百善孝為先”的孝悌觀一直主宰著朝鮮朝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作子女的要注重長幼尊卑,晚輩對長輩必須絕對服從。但作為父權統治者的家長們,并沒有意識到子女們的孝心,只想著維護社會的傳統道德理念,并將其作為人生的全部,而招致自己及其家庭悲劇的發生。雖說小說世界充滿了夸張和虛構,但從中還是能窺視出朝鮮朝時期文弱書生只重視體面和名份的觀念。
這種家長形象在《孔菊潘菊》、《金仁香傳》等作品中也大同小異地出現過,他們全都被塑造成了懦弱和沒有自我意識的男性家長形象。正是這種懦弱無能家長的存在,才促成了繼母對前妻子女發生施惡行為。
(三)囿于家庭倫理秩序的無奈家長
《月英娘子傳》中的家長崔熙圣,比起其他作品中的家長更值得關注。《月英娘子傳》中表現出的家庭矛盾與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崔熙圣娶妾不是為了后嗣生產,而是因御命不可違。在《月英娘子傳》中,第一夫人閔夫人,第二夫人胡夫人,她們倆和第三夫人鄭夫人的矛盾對立是作品的主要矛盾。
男主人公崔熙圣在盡孝與愛情方面存在著矛盾心理,遵從“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儒家理念,就必須遵從父母的意愿再納妾,但納妾又有悖于對閔夫人愛情的忠貞。更主要的是崔熙圣覺得再娶個夫人進來不是件妥當的事情,一定會鬧得家庭不和。但是又難于皇命不可違,必須迎娶御命之鄭夫人時,崔熙圣叫來兩位夫人,交待道:“我現在是不得不跟鄭小妾結婚,這應該說是我們家門的不幸。但是你們自己不要失去做人的本份,最大的原則是始終不要失去做人最起碼的禮數”。在這里作為家長的崔熙圣對即將發生的事情還是有一定的預見性的,這和作品開頭就交代的人物具有超凡的能力是相吻合的。所以崔熙圣預感到了以后可能出現的狀況,心里總是惴惴不安。
第三夫人鄭雪瑩仗著自己的權勢,不顧及在家中的尊卑位置,任意放肆地胡作非為。如果說《謝氏南征記》和《薔花紅蓮傳》中出現的矛盾,是對家長的愛情和作為父權家長權利的抗爭的矛盾,那么《月英娘子傳》中的矛盾卻是作為皇親的鄭雪瑩依仗著自己的家門背景,希望得到合理的待遇而產生的對家長對抗的矛盾。成婚后的鄭雪瑩嘆息自己在家庭中的處境,她認為崔熙圣輕視和責罵自己,是因為自己處在第三夫人的位置。“妾是皇后的親妹妹,怎么能違反朝廷風俗呢?妾的心跟柳花、梨花等同,郎君也敢蔑視!不是因為別的,而是讓我位居身份比自己低的女人之下,我不能忍受!這是我傷心地緣由”。[4]自己的身份比兩位夫人都高,但她卻沒有享受到作為真正妻子的合理待遇,心中感到不平。鄭雪瑩嬌蠻跋扈的行為,在生完兒子之后愈加囂張。在封建家庭中,妻子對丈夫的反抗,在當時的社會現實生活中是絕對不可容忍的。而這里的鄭夫人全然不顧及男尊女卑,直白地暴露了當時朝鮮朝社會的等級身份制和皇權御命。
在娶鄭氏之前就預見到將來會產生矛盾,在事情出現后,又能夠將事情擺在當面解決,行使作為家長的權力,嚴管輕舉妄動的鄭氏,顯示出了崔熙圣作為一家之主齊家的能力。但這里作為丈夫,儼如一家之長的“父親”般責罵自己的妻子,不是以丈夫愛的角度,去解決家庭中夫妻之間的問題,完全是一種靠父權家長權力來威懾自己的妻子,顯然處理的方式很難讓人接受,這是日后鄭氏將憤怒轉嫁給先前兩位夫人的原因所在。就在崔熙圣奔赴戰場的時候,家中發生了三位夫人的矛盾糾葛,妻妾矛盾激化,這是家禍產生的根源。這種戰爭的介入,使惡妾們驅逐和迫害正妻有了可乘之機,同時丈夫處理家庭問題的弱化,因為自己的離開也變得名正言順。當掌握著父家長權力的男性不在家時,家庭問題發生的同時也爆發了國家的戰爭。國家的危機和家庭的危機同時發生。當戰爭結束和男性回到家中時,家庭又恢復了往日的和平。這意味著如果家庭秩序和諧有序,那么國家秩序也會相應的和平,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家庭小說又把家庭問題向外擴大,延伸為社會、國家的問題。男性在此時,首先要把處理國家問題放在首位,體現了“忠君”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
丈夫在婚姻家庭中本應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朝鮮朝后期的國文家庭小說中,對丈夫們的描寫卻顯得弱化了。他們在家庭出現矛盾的時候往往沒了主見,對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或存在的重要性也沒有積極的覺悟。因此,丈夫們存在的價值在于取得富貴功名,而不是為了家庭、生活。丈夫們雖然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表現得很強勢,但對于與自己關系密切的妻妾或子女問題卻愛莫能助。
(四)期望獲得婚姻自主的家長
《淑英娘子傳》中塑造了一位愛情至上的家長——白善軍的形象,真實地將作為男性的情感與欲望暴露無余。
父母老年得子,生了白善軍,所以對他寵愛有加。因為有一天在夢中遇見了一位佳人淑英,并由此得了相思病。在作品中,女性(淑英)通過超現實的力量(以仙女的身份),積極尋找自己預定的姻緣,主動向男性(白善軍)坦白,約定三年后的姻緣。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這種做法應該是淑英(女)在誘惑善軍(男),并超越等級身份制度的束縛,對于淑英來說是具有女性自覺意識的。在朝鮮朝時期的小說中,女主人公的身份一般是很明確的,但淑英的身份并沒有明確的說明。善軍只是在夢里看見淑英以后,在不知道任何有關淑英的情況下,就愛上了淑英,并因相思而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父母想盡了所有的辦法,也未能治好兒子的病。看到善軍的樣子,淑英心里很不安,就又出現在夢里,背著天庭的規定,約善軍見面。善軍準備啟程時,父母再三勸阻,還是未能攔住善軍。善軍去與淑英約會,實際上已經超越了人間和天界的界限。白善軍有意與娘子結百年之好,不是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只是一個托夢而已,在現實看來,是很荒唐的。作品將白善軍設計成了一個純粹的愛情至上主義者。在朝鮮朝的封建社會中,對于將來要承擔家長職責的男性繼承人來說,善軍形象的塑造是完全缺乏維護家庭秩序和儒家倫理道德準則的。這里的所作所為,只是欲望沒有實現之前,心理驅使下的迫切需要。而且為了解決欲望的煎熬,侵犯了婢女月梅,以緩解對淑英的思念。白善軍對于月梅的態度,與其他古小說截然不同,白善軍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心理和生理欲望,她只是白善軍泄欲的工具而已。在其他的家庭小說中,娶妻或納妾是以繼后嗣為目的,起碼在家庭中給予一定的身份、地位,但月梅卻連作“妾”的名份都沒有。淑英的做法,也使自己變成了一個不貞的女人,違背了天規,被處罰回到人間,善軍將淑英領回了家。父親白公了解了這期間發生的所有事情,并沒有太多地責怪兒子,并默認了這樁婚事。在作品中,作為家長的父親——白公,對兒子這樁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默認,可以看出:父性的權威和“特權”在這里被打破了,作為父親對兒子的選擇和需要能夠理解,并給予尊重和關愛。宗法父權體制下的“父親”形象漸漸消失,而作為家庭成員之一的“父親”漸漸出現在讀者的視線里。但是作品中白公作為一家之長迎娶兒媳的過程卻被忽略了,畢竟父權家長的意識還深深地扎根在父親們的心中。善軍跟淑英結婚以后,只是沉迷于與娘子的愛情中,根本無心于學業,看到如此的樣子,白公很是痛心,無奈于對兒子的溺愛,也只能聽之任之。
白家也是屬于當時封建官僚的兩班家庭,父親白公對兒子的要求,也完全是按照儒家規范去要求的,只有科舉及第和考取功名,才能實現自身價值,延續家門的繁盛。而兒子善軍的想法只是追求自己的愛情,認為只要有娘子陪伴,過著舒心的日子就是最大的滿足。父子之間因價值觀的不同而產生了直接的對立。父親下令將白善軍送到京城參加科考,但善軍因想念娘子而中途轉回。白善軍的這一形象在當時的儒教社會里,絕對是一個不思進取、不能齊家治國的叛逆形象。作為男子大丈夫為求取功名,去參加科考,卻因為思念家中的妻子,而欲放棄考試的男人,從情感上來說應該是值得肯定的有情有義的好丈夫。但是在當時作為家門的繼承人,只有科考及第、立身揚名,才能勝任齊家立業,白善軍卻做出了讓父母傷心的舉動,在當時的宗法父權社會中,這是兒子對父母最大的“不孝”。
當他知道月梅使用計謀害死淑英后,逼迫月梅寫下供書,用刀砍斷了月梅的脖子。但是這件事情的發端是始于善軍的。善軍并不反省自己的行為,認定這只是月梅在作惡。而對于月梅心中的積怨、妒忌,月梅在八年中積蓄的恨,白善軍是意識不到的。在他的思想深處,一個婢女是不會有自己的主張的,她的一切行為都應該是以服從主人的意愿為終極目標。在這里白善軍根本沒把月梅看做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女人,而完全是自己家庭中的一件物品而已,可以隨意任自己使用。白善軍的形象有別于封建家長式的父權形象,雖然在婚姻愛情的選擇上走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縛,但是在其思想的深處還是深深地根植著父權家長對于家族成員的統治與支配的思想。
四、結語
父權是伴隨著父親的發現而興起的。父親身份的確立必然要求父權的出現來維護這種父親身份。而離開了父親身份,父權則無處容身。家庭倫理和社會倫理、父權和君權在儒家思想的演繹下,巧妙地聯結在一起,在封建社會及家庭生活中,一直占據著強勢的地位。但父權還是無法逃避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它在朝鮮朝后期也無法選擇地走向了下坡路。
在本文中,大家也許只能從行文中感覺到父權的漸行漸遠,其實父權的衰微就是這樣的一種趨勢。可能啟蒙運動和新思想并不能表現父權的衰微,只能看到整體有瓦解的趨勢。但是從女性主義理論中,從小說作品文本中,女性漸漸獨立的姿態上和女性覺醒的意識上,我們已經能夠清晰地看到父權、男權的漸漸遠去。
[1] 論語·學而篇[M].北京:中華書局,2007.
[2] [臺]林明德.韓國漢文小說全集:第7卷[M].漢城:韓國國學資料院,1999.9,14.
[3] 作者不詳.薔花紅蓮傳[A].古小說全集(13)[Z].漢城:仁川大學民族文化研究所東西文化研究院,1983.134,134.
[4] 作者不詳.月英娘子傳[A].古小說全集(4)[Z].漢城:亞細亞出版社,1976.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