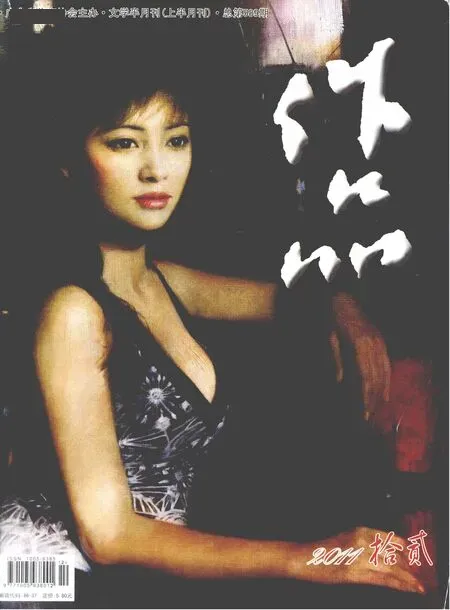所謂題材
數年前和作家李銳做過一次訪談,談到了文學的題材。他說:文學最好不以描述的對象來分類,諸如寫農民的、寫城市的。最好以文學的命題來分類,比如寫愛情的、寫悲劇的,等等。為什么我們不把美國的福克納歸入“寫農民的”行列,為什么他用英語寫了美國南方的農民,就不是“農村題材小說”?其實在這樣的分類后面,隱含了一種文學等級的劃分。小說的標準不在于你寫農民還是寫國王,寫鄉土還是寫城市,而在于你是否把農民或是國王、鄉土或是城市充分地做出了文學化的表達。
我們常常用寫作的題材來給作家作品歸類,這是一種敘述的方便,但局限也是明顯的。
近年來“歷史母題”長篇小說始終處于創作的亢奮狀態中。在有了多種歷史著作之后,為什么還要用文學來重新敘寫“歷史”?比如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寫戰爭創傷和對人類心靈的摧殘。哈金說,人們對其他國家的歷史是不關心的,但文學卻使這種傳播有了可能。在日本,原子彈爆炸后就誕生了《黑雨》等在世界上影響深遠的小說。
有價值的“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往往也是對通常所謂“歷史進程”的否認,對所謂大寫的歷史的否認。作家以一種個人化的視角,進行重新的思考,通過并非簡化、縮寫的個人的敘述,重新敘述歷史。而不僅僅是偉人、大事件的歷史。
我們曾經聽過讀過許多以神圣的標簽打扮過的“歷史”和文學,那樣的敘寫后來被證明是謊言。也是對真實和生命本相的淹沒。所有的諾言都無視生命。當文學借助具體的特定的一種歷史情景或歷史際遇,當文學把那些被無情泯滅的生命從歷史的諾言中打撈出來給人看,我們讀到的是對人類靈魂活動的力量或構成方式。
就如史鐵生曾經說,“從個人出發去追問普遍的人類困境”。
優秀的作品不以題材論,對于語言、對于小說形式的獨特創造,對人心的真切體察,通過這些,記錄一個時代的心靈,在這些事件已經過去的時候,仍然被閱讀,這才是好的文學。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遭遇了殘酷的解體和失敗,人們持續尋找著真理,但從內部到外部都遭遇到價值否定,這種中國人的精神處境,充滿了煎熬和混亂,也讓我們從文學中,看到了復雜和豐富。人對苦難的體驗,苦難對人性的煎熬,人性的光明與黑暗,人生的溫暖與悲涼,這些,也許是我們在電影、電視、流行歌曲、深度報道之外,還需要文學的某種理由。
文學是虛構的,但虛構的背后,永遠都有著作家本人的背影,他的故鄉,他的成長,他的靈魂深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