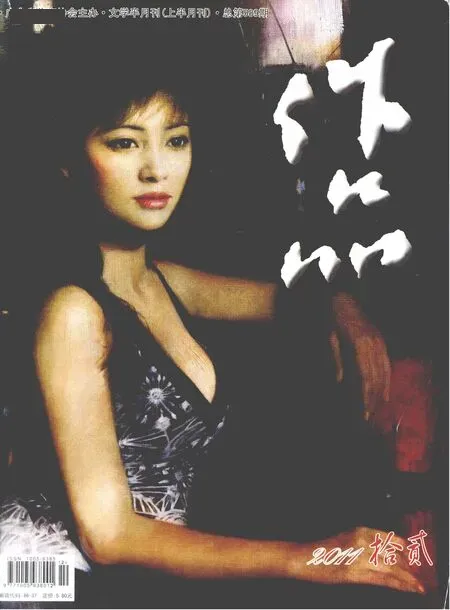站在那高高的布達拉宮

這是我第二次來布達拉宮了。前一次來是順訪,只在拉薩停留了一天,匆匆地在布達拉宮和大昭寺觀覽了一天,留下的只是宏偉、壯觀、精致、神秘的印象。今年來布達拉宮卻是專門的,來前還閱讀了一些有關西藏歷史與文化的著作,因為還要到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以及山南地區的桑耶寺等地去,想對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民俗風情有更多的了解。從西寧坐上赴拉薩的火車開始,我的心情就激動著,從格爾木開始,那巍峨的昆侖雪山、奔跑的藏羚羊和野兔,那平靜得像藍色綢緞般的措那湖,映入眼簾的一切都仿佛散發著西藏的氣息。晚上到達拉薩,從火車站去賓館的路上,司機又專程繞路途徑了布達拉宮廣場,夜色里布達拉宮如一幅宏大的油畫,懸掛在湛藍色的天空下,依然是那么雄壯而肅穆。
現在我就踏上了登覽布達拉宮的階梯了。
拉薩秋天的氣候就如南方的五月,說變就變。剛進布達拉宮東門時,呼啦啦下了一場暴雨,強勁的風雨撕扯著衣服和還來不及完全撐開的雨傘,讓人猝不及防,生出深秋的涼意。但不到十分鐘,當我爬到宮墻上升不到30米處的無字碑時,卻又是烈日當空,汗水刷刷地流下來了。
“無字碑”是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時大管家桑結嘉措立的,為的是紀念他修建布達拉宮的功勞。布達拉宮始建于唐代,是松贊干布為迎娶文成公主時的創意之作。我后來去過位于山南地區的雍布拉康,那里是松贊干布的第一座宮殿,其實規模很小,建于一座不大起眼的小山上,才知道布達拉宮就是仿雍布拉康而在拉薩的山上修建起來的。經歷過許多的時間,布達拉宮建建停停,也不斷被兵火毀壞,而只有到清朝的五世達賴喇嘛時,才最大規模的修建起來。而這期間,五世達賴喇嘛花力最多,而他最得力的管家桑結嘉措則是最強有力的執行者與監管者。站在無字碑前,我在想,這桑結嘉措也是夠大膽的,表面上看他不想居功自傲,但骨子里卻透露出一種高傲與野心。他模仿武則天在自己的陵墓前立無字碑,表明自己的功勞將流芳千古,可供后人作無限的評價,碑看似無字卻有聲,仿佛在述說著桑結嘉措功勞蓋世的豐功偉績;碑看似低調,實則是高調昭示桑結嘉措意欲全權治理西藏的野心。如果是真正的低調,桑結嘉措根本就不要去立碑,有道是是非在于歷史的洗刷,功績在于人的口碑,公道自在人心。或許正是這樣的高調,桑結嘉措敢于在五世達賴喇嘛圓寂之后將密不宣喪的秘密保留15年,也敢于將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雪藏15年,終于釀造了他自己被殺戮、倉央嘉措也最終被廢黜繼而失蹤的悲劇。
從無字碑往上五六百米,就開始進入布達拉宮的宮殿里。布達拉宮不愧是世界上最高也最精致與金碧輝煌的宗教宮殿。步入它的核心殿堂以及主殿堂前供演藏戲的廣場,你會產生一種宏大的心靈震撼。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宮殿,廣場內,似乎還回響著當年三世、四世、五世乃至六世達賴們觀看藏戲和舉行盛大佛教儀式的鑼鈸聲和法號聲。那粗獷的腳步聲、呼喊聲仿佛還透過地上的磚石反射到城垣上,回蕩在我的耳邊。
供奉若干老達賴喇嘛的靈塔殿是游人流連得最久的地方了。這不僅僅是它需要上好幾層樓逐層觀看,更重要的是這里保留著諸多的秘密,存在著諸多的疑問。隨著導游的講解,我就進入了那歷史的謎團,并漸漸拉開了對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探尋。
在靈塔殿里,供奉最大的當然是五世達賴喇嘛的靈塔了,因為他使西藏雪域的各種宗教統一于佛教這一教派,而且還理順了西藏與清王朝之間的友好關系,他不遠萬里到達北京朝覲,不僅得到了清朝皇帝的獎賞,也得到了全西藏僧俗的擁戴。故他的靈塔在所有的達賴靈塔中是最大最高的,用的黃金、寶石裝飾也是最多的。他的功勞在歷代達賴喇嘛中最大,何況布達拉宮也是在他的主政下大規模改造與建筑的,盡管他還等不到它的完全竣工就圓寂了,但他自己為自己包括他的心腹管家桑結嘉措所造的靈塔當然也就是最大的了。
但一座座靈塔尋訪下來,唯獨不見有六世達賴喇嘛的靈塔。他去哪兒了呢?是不是因為他在布達拉宮時邊當達賴又當談情說愛的浪子詩人而不合適于給他建塔?還是因為他被罷黜后押送北京途中流落失蹤于青海湖而無法收集到他的靈骨而不適合給他建塔呢?導游講解到此處時雖舉了幾種說法,但并無定論,這沒有六世達賴靈塔的迷總還是纏繞在我的心頭。
其實,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之所以沒有靈塔,根源在于他不是一個神,而是一個人,他的一生都在神與人之間的關系里纏繞著,糾結著。布達拉宮是要供奉神的,要供奉一個完美無缺的佛在人間的替代者。而制造神的操縱者與制造人的操縱者,始作俑者都是桑結嘉措。是他,為了實現他的政治野心,讓倉央嘉措被認定為轉世靈童之后還讓倉央嘉措流落在民間,從而使得倉央嘉措更多地接觸了民間,也在少年時就過早地愛上了他的情人瑪吉阿米,說到底,這顆愛的種子也算因為桑結嘉措留下的自由空間而得以播下的。也還是他,在倉央嘉措已可以理政的時候,他拒絕了倉央嘉措學習政務的要求,從而封殺了聰慧無比的倉央嘉措可以發揮他政治才能的機會。桑結嘉措心里清楚,倉央嘉措早已過了他的上一任達賴十五歲就可以理政并且可以創造超人政績的年齡,桑結嘉措只不過是舍不得這誘人的權力,舍不得這可以實現宏大政治野心的機會。也正是在這種無望的時刻,倉央嘉措決心不再做神而做人了,也就是說不再做政治的傀儡而做回他自己了。依仗他的聰明才智,他完全可以當好一個政治家,他有敢于擔當的精神,也有敢于奉獻的勇氣。事實證明這一點,在西藏僧眾需要的時候,他毅然斬斷了情緣,潛心當他的活佛;在他最后被押解出拉薩時,僧人們為保護他,將他留在哲蚌寺內而與蒙古軍隊抵抗。為了避免流血,他從哲蚌寺勇敢走出,跟隨蒙古軍隊而去。這就是當之無愧的活佛啊!他不愧是西藏僧眾心中擁戴的法王啊!這些絕不是一個只會寫情詩的偽活佛、浪蕩子所能做得到的。
當然,作為詩人的活佛,倉央嘉措自有他性格懦弱的一面,面對桑結的霸道無理,他反抗了,據理力爭了,但結果卻逼迫他不得不走向了“放蕩”的一面。他偷偷出宮去喝酒了,去會情人了,也大膽地去寫情詩了,那也是他反抗桑結嘉措的另一面。他不惜損害他自己的形象,就是要破壞桑結嘉措只把他當政治傀儡的目的。這就正如魏晉時期的名士一樣,為反抗虛偽的禮教,不得不以放浪形骸的行為去表達自己的奇行獨性一樣。倉央嘉措也正是這樣一個獨立特行的人,桑結嘉措管得越嚴,規勸得越多,他就恰恰要反其道而行之。
有人說倉央嘉措是政治斗爭的犧牲品,他的悲劇是一場政治惡斗所釀成的。從表面上看,這的確如此,因為當時的西藏確實存在著桑結嘉措與清代政府統治西藏的蒙古拉藏汗之間的明爭暗斗。在這場斗爭中,倉央嘉措是被動的,甚至是被瞞騙的。但是,倉央嘉措又并非是完全被動的,一旦他知道他不過成為了桑結嘉措手中的一張牌,一個政權的幌子和影子之后,他毅然作出了他的選擇——與桑結嘉措的不合作。他心里十分清楚他作出這種選擇的后果。他知道,這不是桑結嘉措拋棄他,而是他要徹底拋棄桑結嘉措,他要破壞桑結嘉措的政治陰謀,要讓桑結嘉措的政治野心落空。在做神、做傀儡與做人之間,他寧愿做一回真正的人。
倉央嘉措畢竟是做了一回人,而且還做了偉大的情人,也是偉大的詩人。他的詩道出了許多人想說而未能說出的哲理,像那種“最好不相見,便可不相戀;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最好不相伴,便可不相欠;最好不相愛,便可不相棄;最好不相對,便可不相會;最好不相誤,便可不相負;最好不相許,便可不相續;最好不相依,便可不相偎;最好不相遇,便可不相聚;但曾相見便相知,相見何如不見時”的詩句,沒有刻骨銘心的愛過體驗過,又怎能創造出如此讓人讀后難以忘懷的詩句呢?
而在西藏僧侶及民眾的心目中,倉央嘉措又是怎樣的人呢?僧侶們從維護宗教莊嚴的角度,他們為倉央嘉措的風流辯護,甚至認為他“天天有人作伴,從來未曾獨眠;雖有女子在旁,從來沒有沾染”,他的行為不羈不檢,即便是不守戒規,沉溺女色,不過是“迷失菩提”而已。甚至還有人認為他的放蕩是修行過程中的必經之道哩!這也難怪,因為在藏傳佛教的密宗當中,就有歡喜佛的極樂境界,女性代表著“智慧”(般若),男性代表著“方便”,二者都代表著人類的創造活力,男女雙修融為一體才可達到極樂涅槃之境界。而在一般的民眾眼中,六世達賴喇嘛根本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深愛他們的活佛,也由衷地體諒他們的活佛:
活佛倉央嘉措,
別怪他風流放蕩,
他所尋求的,
和我們沒有兩樣!
也正是如此,布達拉宮中雖沒有六世達賴喇嘛的靈塔,卻有他的塑像,這塑像擺在哪兒呢?擺在長壽殿里。倉央嘉措竟然成為長壽的象征!這究竟是指他的創造活力寓示著長壽呢,還是指他的精神永垂不朽呢?可能兩者都有。當然,布達拉宮的管理者為了不找麻煩,只塑了倉央嘉措少年時的塑像,那純潔慈善、安祥淡定的面容的確讓人觀之動容。
從布達拉宮山上下來,人們都要去八廓街尋找那個名叫“瑪吉阿米”的小酒館,似乎在那里人們才可以找尋到倉央嘉措的痕跡,因為那里曾經是倉央嘉措與他的情人瑪吉阿米的天堂。而那天,我卻沒有去。我以為,那個小酒館只不過是倉央嘉措的表象,那個小酒館怎么能代表倉央嘉措的全部呢?在那里,人們除了加強了對倉央嘉措是一個酒鬼,是一個放蕩子的印象之外,還能得到什么呢?實際上,理解了倉央嘉措的處境,了解到倉央嘉措的心路歷程,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倉央嘉措是一個敢于叛逆、獨立特行有著自我選擇意志的強者,是一個敢愛敢恨、敢于擔當的宗教領袖,也是一個敢于坦露心胸、有著無限激情與文學創造才能的智慧詩人。惟其如此,后來的人們才帶著美好的期待為他編造了更完美的結局,也帶著對他才情與智慧的崇敬將許多民間創造的情詩加到了他的身上。有人說倉央嘉措在青海湖失蹤之后,又游歷了西藏乃至印度的許多地方,最終在蒙古的阿拉善停留下來,成為那里受人尊敬的活佛,并在那里圓寂。有人甚至說當時的阿拉善王妃與他有著深深的友誼與情誼,一生都崇拜著他的智慧和為人。后來的民眾都在傳頌著他的情詩,同時又把許多情詩依托在他身上而加以傳揚,比如那首著名的《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那一世》,據考就不是他的作品。這說明什么呢?這只能說明,倉央嘉措是人民的活佛,也是人民的詩人。他雖然沒有五世達賴喇嘛那樣的豐功偉績,也沒有五世達賴那樣雄偉的靈塔,但他的才情,他的創造力,他的為人,他的精神卻永遠銘刻在民眾的心里。他的形象絕不在那小小的酒館里,而是永遠地站在那高高的布達拉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