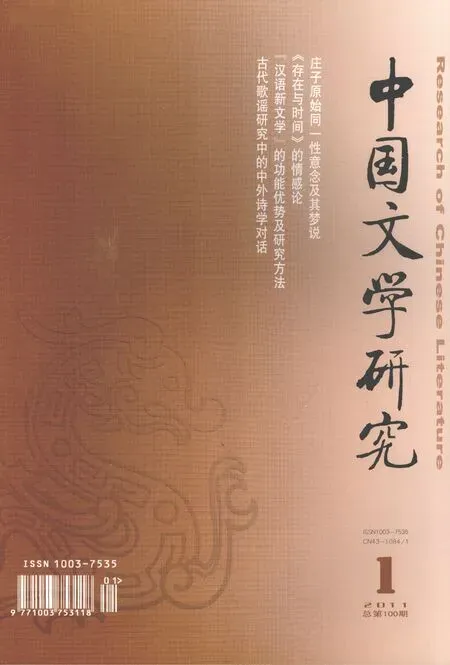論魯迅小說中的賤民話語
2011-11-19 21:27:50朱崇科
中國文學研究
2011年1期
關鍵詞:小說
朱崇科
(中山大學中文系 廣東 廣州 510275)
魯迅先生曾經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提及,“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而實際上,他在小說(本文所用魯迅小說版本出自金隱銘校勘《魯迅小說全編》插圖本,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如下引用,只標頁碼)實踐中的確也向“不幸的人們”傾注了相當復雜的感情,即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粗略梳理相關研究,我們不難發現,論者更多的是從小說主人公的身份歸屬加以處理:比如小知識分子、農民(游民)、婦女等等。這樣的操作固然有利于增益我們對上述歸納的了解和認知,但對于“不幸的人們”的判定卻似乎仍有“盲人摸象”之嫌,而實際上,“不幸的人們”指涉各異,畢竟,現實人生中,“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爾斯泰語)。
話語分析和賤民(subaltern)理論的巧妙結合其實給我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痛恨理論或者對以西方文論詮釋中國問題的做法過敏者似乎找到了殺戮和撻伐的標的,而在我看來,“賤民話語”之于魯迅小說卻是相當有意味而且頗具針對性的問題意識,如果我們對它重新加以界定的話。
“賤民”這個概念,或許更容易為人所知的是印度社會中的“不可接觸的人”階層。〔1〕而相關研究也是相當著名,那就是由印度拓展而日益國際化的“賤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比如其代表學者之一的古哈(Ranajit Guha)在《賤民研究》第一卷的序言中說,該學派致力于促進南亞研究中賤民問題的研究和討論。……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