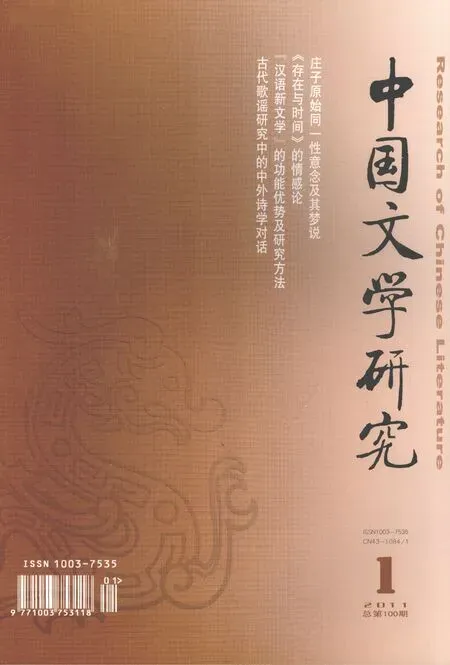隱喻·主題·記憶
——論張愛(ài)玲小說(shuō)的政治敘事
張文東
(東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 吉林 長(zhǎng)春 130024)
在現(xiàn)實(shí)的意義上,任何寫(xiě)作都是“體制”下的寫(xiě)作,都必須依從于某種現(xiàn)實(shí)政治結(jié)構(gòu)及其話(huà)語(yǔ)機(jī)制,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也不例外,雖然她始終都在申辯自己的寫(xiě)作是完全脫離政治的〔1〕,但事實(shí)并非如此。與所有人一樣,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也是一種政治敘事,其政治話(huà)語(yǔ)雖有“隱喻”、“主題”與“記憶”等敘事樣式的不同,但卻始終貫穿在她各個(gè)時(shí)期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當(dāng)中。
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從1943年5月的《沉香屑:第一爐香》,到1976年寫(xiě)完卻出版于2009年初的《小團(tuán)圓》,雖幾經(jīng)擱淺,亦斷斷續(xù)續(xù)幾十年〔2〕。一直以來(lái),受夏志清的影響,人們常以《秧歌》和《赤地之戀》為分界線(xiàn)來(lái)思考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歷程,將其分為三個(gè)時(shí)期,即“上海時(shí)期(《傳奇》)”、“香港時(shí)期(《秧歌》和《赤地之戀》)”、“美國(guó)時(shí)期(《怨女》和《半生緣》等)”〔3〕,甚至更愿意將“上海→香港→上海→香港”看作是“張愛(ài)玲寫(xiě)作的循環(huán)之旅”,以證明“香港時(shí)期”的里程碑意義〔4〕。但實(shí)際上這種具有鮮明“政治意味”的“地域性”劃分,恰因?qū)Α跋愀蹠r(shí)期”的“偏重”而成為一個(gè)“偽題”。在我看來(lái),“上海時(shí)期”如果是以“淪陷時(shí)期”來(lái)標(biāo)示的話(huà)應(yīng)可確定,因?yàn)椤秱髌妗穾缀跏俏ㄒ坏摹?〕;“美國(guó)時(shí)期”也可以,因?yàn)槠陂g間或幾部“記憶性”文本的書(shū)寫(xiě),以及在“惘然的回憶”中不斷改寫(xiě)的文本,都具有相同或相通的品格;但是唯獨(dú)“香港時(shí)期”不能單獨(dú)劃分出來(lái),因?yàn)榫驮诖饲安痪玫?950年3月至1952年1月間的“上海時(shí)期”里,張愛(ài)玲還有《十八春》與《小艾》兩部小說(shuō)——盡管和她到香港之后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在“政治情緒”上完全相左,但在“迎合”某種現(xiàn)實(shí)政治的“政治敘事”意義上卻完全取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