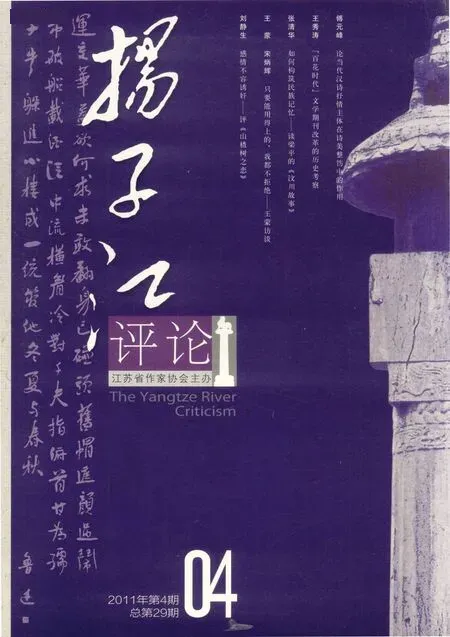弋舟小說《懷雨人》管窺
邵振國
弋舟的中篇小說《懷雨人》(見《人民文學》2011年第3期)是一篇先鋒性很強的現代小說。
此前弋舟發表過的許多中短篇亦具有這種“現代”品質,拙文準備提及的另一篇《把我們掛在單杠上》(見《山花》2008年第8期),即是這種品質的佳作。
《懷雨人》寫了這樣一個人,名叫潘侯,與其大學同學李林,即第一人稱的敘述者“我”,被給予那樣一種“受監護”與“監護人”的關系。之所以形成這種關系,是因為潘侯的大腦有別于“正常人”,具體說,就是他沒有正常人的“方向感”,走路會碰樹撞墻,生活和就學不能自理。然而他又是一個智力超強、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能在“十秒鐘內運算出七十二的四次方”,是個學哲學的。第一面見到學中文的李林時,他會發問“你從哪里來?”如同蘇格拉底對于“人”的拷問。當對方回答“西安人啊”而引發他由大唐建都地“細數唐朝近三百年的歷代帝王”,即是說他很了解“人的歷史”。這種人因一部翻譯影片而得名叫做“雨人”。
我稱贊這篇作品所溢出的光彩斑駁的藝術優長,有三點是我感觸頗深的:小說人物豐滿的個性、復雜性和鮮活的質感;語言敘事的藝術張力,即能夠經得住閱讀想象的“拉拽”;作品內容和蘊含能夠訴諸形式的表現。
潘侯這個人,在我看來不亞于薩特小說《惡心》中的安東納·洛根丁,其細節的豐滿和表現力,也強于洛根丁在街上想拾起的“那張紙”,被踐踏弄污粘滿泥濘的紙,或在咖啡店聽那“沒有旋律,只有音符不知疲倦地跳動”的音樂。潘侯的相關細節有意味而沒有意念化,是那樣充足地發自性格深處。譬如潘侯在學校操場上鍛煉,那種“摧枯拉朽的狂奔”,讓我們能夠直觀到“他始終在妄圖自己決定一些事”,并體驗到他身心的那種自由的愿望,覺出他“宛如一個嬰兒般的令人疼惜”,再看這塊操場,確實“成為了一片蒼涼無際的荒原”。
弋舟細膩精致地描寫了潘侯由一個沒有“方向感”的生活低能兒一步步走向“正常”,所經受的自我約束和壓抑、種種“碰壁”的情節和精神變化的過程,其中有他“躲在鋪上瑟瑟發抖,喉嚨深處發出詭譎的喘息聲”,也有他在一只“黑殼筆記本”內記錄下的他對于社會人際的看法,能作為“一些人在塵世走過這么一遭的佐證”的東西,還有他的一次可謂純凈真摯的戀愛和他形而上的愛情觀。盡管那個學物理的“永遠深諳物質守恒的女生”朱莉,不避諱說她愛的就是“潘家這棵大樹”,但潘侯對她依舊不改癡情,在那個“白菜豆腐”的小飯館“虛擬”她的存在,為她擺上碗筷,給她搛菜。因為潘侯認為:她愛我,我才愛她,那不是愛情。愛情不是兩個人的事,而是一個人能夠做的和應該做的事。當他的“監護人”李林勸他明白,朱莉愛你的什么?他卻只回答“我愛她”。那么你愛她的什么?潘侯回答:“身體。”李林說,身體是人人都有的共性,你怎么不去愛別人或所有的她們?潘侯說:“是的,我愛她們。”上述細節不僅賦予潘侯“泛性愛”的人性哲思,而且形而上地給出他純凈透明的心靈天地。所以其中還有他那樣的精神之旅——走向那座“廢棄了的天主教堂”。這片神的廢墟就是潘侯的領地!潘侯只有在這里不再碰壁撞墻,行走不會再遇到任何障礙物,他眼前的路徑條分縷析,他還牽著李林的手,像是成為李林的“監護人”和向導。因為這里沒有人們故意擺放在宿舍中間的椅子、水瓶,乃至“絆馬索”之類。他在這里能夠縱情朗誦阿赫瑪托娃大段的詩歌,還帶著他的女友來這里幽會。
弋舟運用這些細節不僅使小說人物個性豐滿,還讓整體情節蘊含渾厚、寓意深邃。就在他不斷走向“正常”的時候,他也就不再是他自己了。他“出色的空間感成功地繞過了這一切陷阱”,但是他“反而喪失了那種明快的披荊斬棘的虎虎生氣”。弋舟給了他一個又由“正常”返回的精彩書寫!一個晚間,他帶著女友朱莉來這里,就是在這塊神的廢墟,他的女友被四個強徒糟蹋了。他卻依照“正常人”教誨的“自為”的規則逃逸了。
情節接下來即是他離開學校、離開家庭,乃至與這個世界訣別。弋舟寫朱莉這個人,也不是單向度的,她恰是在她實惠的夢想破滅后,說出“我愛他!”從她的病榻枕下取出那本黑殼筆記本,遞給了李林。因為李林在弋舟的人物設置上就是潘侯的另一面或說就是同一個人,如同歌德筆下的靡菲斯特之與浮士德。那筆記本的扉頁上寫的幾行獻詞,不僅是遭難后的朱莉所愛的、認同的,它更是李林的精神的同構:“我總是向著堅硬撞去/有一天我撞向了你/從此世界打開了一道柔軟的縫隙”……
是的,李林這個人鮮活生動,顯得更有分量。他舉起左手于眼角邊向潘侯示意:“向左!向左!將自己拽出肉體”,那也是對他自己精神的召喚。末了在搜尋潘侯行蹤時,他還是用這個動作,放逐了他的逃逸。他不僅伴著潘侯的肉體奔跑,還陪著潘侯精神苦痛的思考,他時常會想起自己少年時喂養的那條因吃了死老鼠而死的小狗。他會因為自己曾制止潘侯這樣那樣,而感到懊悔和自責,他會感覺到潘侯“那喘息經過努力壓抑后,蠕動著,像窨井下涌動的暗流”。小說最為精彩的就是末尾“放逐逃逸”,弋舟把兩顆靈魂的對視無言地寫到了骨血里,的確讓我們看到數十年后“校門口潘侯留下的那只足印”,“有時我趁著四下無人,就會將自己的一只腳踏入那個足印。”
我們說,《懷雨人》的敘事較完美地訴諸了形式的表現,李林對于潘侯表面的對立、骨血里的契合,構成這一形式的內部結構,我們是從李林身上看到“這個上帝遴選出來的孩子終獲全勝,他活在時間的褶皺之外,不受歲月的撥弄”。用敘事者李林的話說:“我那想象中的紅色鉛筆一路向左、向左地拐出去。我想知道在紅色鉛筆的箭頭抵達終點之前,是否會有那么一個瞬間與潘侯的步履重合在一起。”
這讓我想到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即是那種整體的象征性的訴諸形式的書寫!弋舟最后的筆墨說:“我只有以這樣的方式結束我的回憶:不過將一切寫成了一篇寓言。”但是這不是“寓言”,而是藝術本該如此,一個真正有才華的作家把他所想說的訴諸了形式。美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伯瑞德·貝瑞孫在談海明威作品時說:“真正的藝術家既不象征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藝術作品都散發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
在這個意義上,我要提到弋舟另一篇小說《把我們掛在單杠上》。它敘述的是一老一少通過中國古典詩歌的傳授和學習而對于“掛單杠”的理喻。這個“掛”就是把人體像折疊馬扎一樣地折成另一副樣子,不管它的痛苦與艱難,而它是人對于自己身體的自主和自由的選擇!這篇作品非常感人,我以為它與《懷雨人》是同一個意味蘊含。它藝術地表現出:人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能自主,須經歷那樣的艱難困苦,遭受非議和攻擊。尤其那個小學五年級的學生挨打的時候,反襯出“人體的自主”已蕩然無存了!但是司馬教授在一個沒有別人的夜晚,終如愿以償地把自己掛在了單杠上!他喜悅溢于言表地吟著:“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
我以為該作亦是海明威式的訴諸形式的書寫,因此才能給予我們這樣深刻痛切的對于人類命運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