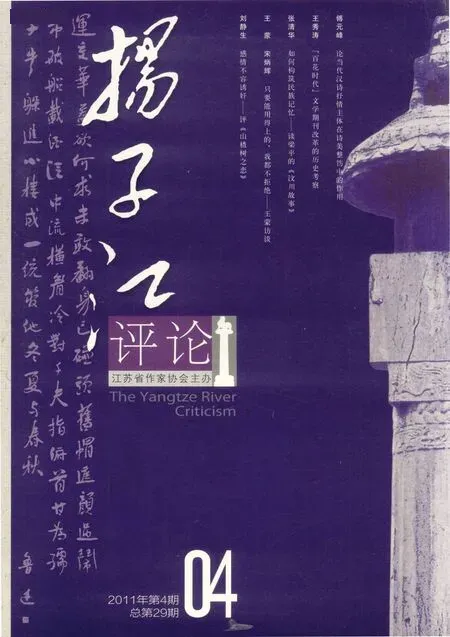“百花時代”文學(xué)期刊改革的歷史考察
王秀濤
1949年以后文學(xué)期刊的格局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同人刊物和商業(yè)刊物逐漸被取消,“過去一小伙人掌握了一個刊物(既是所謂同人刊物)”的辦刊方法“已經(jīng)過時了”,原因在于“我們應(yīng)該明白我們已經(jīng)處于另外一個嶄新的時代了。我們已經(jīng)是主人,國家和人民需要我們的刊物能擔(dān)當(dāng)起思想領(lǐng)導(dǎo)領(lǐng)域里的問題,一切生活中新思想和舊觀念的交戰(zhàn)的問題”。①文學(xué)期刊的定位與職能被定于一端,其辦刊思路與管理辦法也存在著政治化、行政化的特征。1956年“雙百”方針的實施在一定時期內(nèi)改變了文學(xué)期刊的狀況,其調(diào)整的方向與以往截然不同。中國作協(xié)還在11月召開了文學(xué)期刊工作會議,意在推動文學(xué)期刊的改革,并提出了可以創(chuàng)辦同人刊物等以往不可能提出的主張。這一時期的文學(xué)期刊調(diào)整無疑是十七年文學(xué)期刊發(fā)展的重要現(xiàn)象,但這一現(xiàn)象還未得到學(xué)界的全面研究,回顧、總結(jié)這一段歷史,能夠還原“十七年”文學(xué)期刊發(fā)展歷程的復(fù)雜性,豐富我們對文學(xué)與政治的關(guān)系等重要問題的認(rèn)識。
一
文學(xué)期刊的改革是1949年后文學(xué)期刊越來越僵化、走向極端的一種反應(yīng)。因此,一旦環(huán)境允許,作家、編輯就開始表達(dá)不滿和改革的要求,而“雙百”方針的提出無疑為文學(xué)期刊調(diào)整也營造了寬松的文學(xué)環(huán)境。1956年被許多人認(rèn)為是文學(xué)藝術(shù)的“春天”,有學(xué)者把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這一段時間稱為“百花時代”,這種環(huán)境的形成為期刊調(diào)整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1949年以后文學(xué)期刊大多以機關(guān)刊物的形式存在,以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標(biāo)準(zhǔn),它被視為“我們的喉舌”、“我們與群眾聯(lián)系的最密切的工具”,“最集中表現(xiàn)我們文藝工作部門領(lǐng)導(dǎo)思想的機關(guān),是文藝戰(zhàn)線的司令臺”。這種政治定位使文學(xué)刊物擔(dān)負(fù)著進行意識形態(tài)宣傳和政治思想斗爭的任務(wù),所刊發(fā)的言論“就代表了整個運動的原則性標(biāo)準(zhǔn)”,編輯部人員“就不應(yīng)該是一個普通的看稿人或集稿人。他們就應(yīng)該具有高度的明確的思想性,最能判斷是非輕重,敢于負(fù)責(zé)地表明擁護什么,鼓吹什么,宣傳什么和反對什么,而且是熱烈地?fù)碜o和堅決的反對”。②
為了明確文學(xué)期刊的這種職能,發(fā)揮其配合政治的工具作用,文藝界掀起過一次期刊的調(diào)整運動。1951年11月20日全國文聯(lián)常務(wù)委員會擴大會議通過了關(guān)于調(diào)整北京文藝刊物的決定。調(diào)整的原因是這些刊物不能達(dá)到“有明確的戰(zhàn)斗目標(biāo),強烈的思想內(nèi)容、生活內(nèi)容和群眾化的風(fēng)格,成為文藝事業(yè)的不斷的革新者”的要求。這次調(diào)整按照“少而精”的原則,著重加強《文藝報》、《人民文學(xué)》、《說說唱唱》,停止出版《人民戲劇》、《新戲曲》、《人民音樂》、《民間文藝集刊》,《新電影》停刊,加強《大眾電影》。③全國文聯(lián)對地方文藝刊物的改進問題也很關(guān)注,不但在《文藝報》上刊發(fā)多篇文章進行探討,而且全國文聯(lián)研究室還專門進行調(diào)查研究,撰文對地方文藝刊物的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文章認(rèn)為地方文藝刊物存在著“無領(lǐng)導(dǎo)無計劃的自流現(xiàn)象”,刊物之間“缺乏適當(dāng)?shù)姆止ぁ保胺结槻幻鞔_,未能面向本區(qū)群眾,貫徹通俗化、大眾化的方針”,因此“必須進行適當(dāng)?shù)恼{(diào)整”,并提出“刊物的方針和讀者對象必須明確”,“與當(dāng)?shù)厝罕姸窢幘o密結(jié)合”等進行期刊調(diào)整的意見。④
1951年11月的文藝界整風(fēng)運動進一步促進了文學(xué)刊物的調(diào)整運動,在11月24日的北京文藝界整風(fēng)學(xué)習(xí)大會上,丁玲指出了當(dāng)時文學(xué)期刊存在的問題,譬如“思想性不夠,任務(wù)不明確、目標(biāo)不明確”,“刊物的負(fù)責(zé)者沒有足夠的責(zé)任感”,“缺乏自我批評,也害怕批評”,“個別的刊物還有小集團的傾向”,“在思想上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群眾思想斗爭的實際”等,號召文學(xué)期刊“為提高我們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戰(zhàn)斗性而斗爭”。⑤在此次文藝整風(fēng)過程中,各文學(xué)期刊都進行了內(nèi)部的思想檢查。《人民文學(xué)》編輯部就認(rèn)為,“必須通過這次學(xué)習(xí),改造我們的工作,使《人民文學(xué)》成為真正貫徹工人階級思想領(lǐng)導(dǎo)和貫徹毛澤東的文藝路線的、和群眾保持密切聯(lián)系的、勇敢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也就是說,真正符合今天人民需要的文藝刊物”⑥。文藝整風(fēng)后,全國文聯(lián)常務(wù)委員會的擴大會議通過的關(guān)于調(diào)整北京文藝刊物的決定“已得到基本的實現(xiàn)”,“《文藝報》、《人民文學(xué)》的工作,已有所加強。《劇本》和《歌曲》的出版,適應(yīng)了群眾的需要。但所有刊物都還未完全實現(xiàn)調(diào)整刊物決定所規(guī)定的任務(wù),還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還要繼續(xù)加強和提高”。⑦
此次文學(xué)期刊的調(diào)整在某種程度上達(dá)到了預(yù)定的目標(biāo),譬如有人說,“自從地方文藝刊物的方針、對象、任務(wù)逐步明確了以后,許多地方文藝刊物出現(xiàn)了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得到了當(dāng)?shù)厝罕姷臍g迎,擴大和加深了文藝作品的宣傳教育作用”⑧。但這種“進步”卻對文學(xué)期刊造成了進一步的約束,譬如河南的《翻身文藝》“本來充滿著各種各樣的內(nèi)容和形式”,“后來省里辦了《河南大眾報》、《河南青年》、《新河南婦女》等報刊,為了實行分工,這個刊物便以供應(yīng)群眾演唱材料、供應(yīng)農(nóng)村劇團劇本為主要任務(wù)”,實行分工的結(jié)果是“來稿公式化、概念化,水平提不高,組織不來好稿”,刊物的發(fā)行量“降低得很厲害,最高印數(shù)是五萬份,最近一期只印了六千七百多份”。⑨而中央級的《人民文學(xué)》和《文藝報》在加強了思想性和戰(zhàn)斗性后,“看一看情況,真是空虛的很,一個《人民文學(xué)》,都苦于沒有文章,一個《報》,也是七拼八湊,這中間又急于以棍子征服人或甚至殺人,做盡了壞事,你看,這能成什么氣候?”⑩
1956年召開的文學(xué)期刊工作會議的目的就在于改變文學(xué)期刊的現(xiàn)狀,中國作協(xié)對此次會議進行了長時間的準(zhǔn)備。據(jù)負(fù)責(zé)籌備此次會議的郭小川在日記中記載,早在4月份中國作協(xié)就準(zhǔn)備召開編輯工作會議?,此后郭小川多次在日記中提到作協(xié)書記處會議討論過此次會議的召開。郭小川還于9月份赴上海、武漢等地訪問作家和編輯,并與文學(xué)期刊編輯進行座談,為文學(xué)期刊編輯工作會議做準(zhǔn)備。從編輯和作家的發(fā)言來看,都對文學(xué)期刊的現(xiàn)狀表達(dá)了不滿,反映了當(dāng)時文學(xué)期刊存在的問題。一是刊物內(nèi)容千篇一律,譬如“文章千篇一律,什么題材都寫成小說,‘人往高處走’,過去《人民文學(xué)》形式狹窄,一般作者也競相學(xué)習(xí)。劍拔弩張、盛氣凌人的多,流暢的少;思想抄襲,模仿性大”;“反映舊社會的東西太少”;“《人民文學(xué)》的詩都是一樣,都是新疆蒙古,四行一節(jié),幾下子一搞,有些膽怯了”;“《文藝報》一發(fā)表趣味就差不多”;“學(xué)校一般同學(xué)對《文藝月報》意見最大,都是應(yīng)景文章,長期都是如此”。二是刊物缺乏自身的風(fēng)格,定位不明確。有人指出,“刊物的方針性質(zhì)不明確,要創(chuàng)造出風(fēng)格不易。甚至不同意,看法不一致。究竟是全國性,還是地方性?”“以后報刊應(yīng)想辦法發(fā)揮每個人的個性和風(fēng)格。以后把門打開,不要前篇一律”。三是編輯思想上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的問題。有人反映,“檢查刊物,脫離政治是對的,但認(rèn)為重視藝術(shù)也是不對的,政治也是硬性配合政治,為工農(nóng)兵就是登工農(nóng)兵作品”;“現(xiàn)在把題材和形式絕對起來。把特寫絕對化,時代感和時代‘趕’。訂計劃時反映工業(yè)、農(nóng)業(yè)各多少篇也是不對的”。“作者經(jīng)常按編輯要求寫稿,逐漸就摸到了脾氣”,需要“減少機關(guān)化,增加社會化”。?郭小川此次外出訪問座談的內(nèi)容也成為召開編輯工作會議的重要參考資料,經(jīng)過整理后成為“后來在會上通過的《編輯會議紀(jì)要》,也是周揚、茅盾等人講話的一個重要依據(jù)和參考資料”?。
文學(xué)期刊存在的諸多弊端,使得文學(xué)期刊的調(diào)整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同時1956年“雙百”方針的提出則使得期刊的調(diào)整具備了可能性。早在1956年年初召開的知識分子工作會議對知識分子相關(guān)政策的改變,已經(jīng)預(yù)示著中國共產(chǎn)黨對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控制的放松。文藝界在2月份召開的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以及3月份召開的全國青年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會議,都意在改變此前文藝界的沉悶現(xiàn)象,消除知識分子因胡風(fēng)事件造成的心理壓力,這也是1956年進行文藝調(diào)整的重要開端。文學(xué)期刊編輯工作會議就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下進行籌備的。
“雙百”方針的提出無疑是1956年文藝界進行文藝調(diào)整的最重要的推動力。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即將建立的時候,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jǐn)U大會議上就《論十大關(guān)系》的討論做總結(jié)發(fā)言,提出“藝術(shù)上的百花齊放,學(xué)術(shù)上的百家爭鳴,應(yīng)該成為我們的方針”?。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懷仁堂向科學(xué)界、理論界、文藝界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陸定一提出,“要使文學(xué)藝術(shù)和科學(xué)工作得到繁榮的發(fā)展,必須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并認(rèn)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和科學(xué)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在編輯工作會議召開之前,《人民文學(xué)》已經(jīng)做出了調(diào)整和變革,這為編輯工作會議和其他文學(xué)刊物的調(diào)整做了示范。1956年秋秦兆陽就制定了《人民文學(xué)改進計劃要點》,主張“在文藝思想上,以現(xiàn)實主義為宗旨,但在發(fā)表作品時,應(yīng)注意兼收其他流派有現(xiàn)實性和積極意義的好的作品”;“以提高質(zhì)量,樹立刊物的獨特風(fēng)格,為今后改進的中心問題”;“藝術(shù)性與思想性并重,不因政治標(biāo)準(zhǔn)而忽略或降低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但在具有特殊性的作品面前,可根據(jù)具體情況靈活掌握”;“提倡嚴(yán)正地正視現(xiàn)實,勇政地干預(yù)生活,以及對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性的追求”等共計18條。?秦兆陽的這些計劃代表了他革新《人民文學(xué)》的指導(dǎo)原則,在他主持下,《人民文學(xué)》發(fā)表了一批“干預(yù)生活”的作品,從1956年5月開始陸續(xù)發(fā)表《爬在旗桿上的人》、《本報內(nèi)部消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揭露現(xiàn)實生活矛盾的作品。同時《人民文學(xué)》還發(fā)表針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存在的問題和矛盾以及探討文學(xué)規(guī)律的論文,譬如秦兆陽署名何直的論文《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以及“文藝短論”和“創(chuàng)作談”欄目上的文章。
可以說,政治環(huán)境的寬松,《人民文學(xué)》的表率以及文藝界所形成的共識使得文學(xué)期刊的調(diào)整運動具備了必要的條件,而1956年11月份召開的文學(xué)期刊編輯工作會議則為其提供了政策基礎(chǔ)、理論基礎(chǔ)以及調(diào)整的方向、方法等具體指導(dǎo)。
二
1956年11月21日文學(xué)期刊編輯工作會議開幕,“在一開始,就確定這次會議的中心內(nèi)容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且按照周揚的主張,“這次會議也要徹底地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會議不做報告,也不做結(jié)論,大家把意見發(fā)表了,也就完了”?。因此此次會議也與以往不同,“在會議的開頭,沒有工作方面的總的報告;只是由作家協(xié)會的三位副主席在會議上作了具體內(nèi)容不同的啟發(fā)性發(fā)言。會議首先放手讓大家充分地、暢所欲言地提出問題,談出自己對問題的看法、意見,對各個有關(guān)方面的批評、建議。由于各個刊物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會議在最后也沒有做出總的決議,而是將大家的討論當(dāng)中對一些重要問題所取得的共同意見,寫成一個‘全國文學(xué)期刊編輯工作會議紀(jì)要’,供各文學(xué)團體、各文學(xué)期刊編輯部結(jié)合各自的具體情況參考執(zhí)行”?。
會議于12月1日結(jié)束,對于學(xué)期刊的改革形成了一致的意見,認(rèn)為要真正貫徹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必須大膽放手,敢于在刊物上發(fā)表各種不同的見解,開展自由論爭;發(fā)表多種多樣形式的作品,并且促使各種文藝形式得以發(fā)展;敢于干預(yù)生活,發(fā)表批評現(xiàn)實生活中的缺點的作品;要辦好一個刊物,必須要求每個刊物各自有著鮮明的主張,鮮明的民族風(fēng)格和地方色彩。會議提出了幾項新的措施:從1957年1月起,全國各個文學(xué)期刊一律取消機關(guān)刊物的名義;文藝團體對所屬刊物只作原則方針上的領(lǐng)導(dǎo),不干涉其日常編輯工作;全國各個刊物之間沒有指導(dǎo)或領(lǐng)導(dǎo)關(guān)系,彼此都可以相互批評;每個刊物都要有一個團結(jié)的有創(chuàng)造性的編輯部,要充滿著學(xué)術(shù)上的自由論辯的空氣和嚴(yán)肅的工作作風(fēng);?各刊物之間去掉那種不成文的指導(dǎo)或領(lǐng)導(dǎo)的關(guān)系,大家平等,展開相互間的批評和競賽;一律實行企業(yè)化的管理方法。刊物不能自給的部分,由國家補貼。作家協(xié)會所辦的已經(jīng)有了較大影響的刊物,實行定期自給,在不能完全自給的時期,實行計劃虧損辦法。?
此次會議無疑為文學(xué)期刊的改革準(zhǔn)備了政策基礎(chǔ),推動了1957年的期刊改革運動。一方面,新創(chuàng)刊的刊物大量出現(xiàn),不下十?dāng)?shù)種,如《詩刊》、《星星》、《新港》、《收獲》、《延河》、《雨花》、《東海》、《園地》等等;另一方面,為了擺脫刊物的行政化色彩,突出自身特色,在會議前后出現(xiàn)了期刊改名的潮流。《山東文藝》更名為《前哨》,《山西文學(xué)》更名為《火花》,《西南文藝》更名為《紅巖》,《貴州文藝》更名為《山花》,《河北文藝》更名為《蜜蜂》,《湖南文藝》更名為《新苗》等等。?更名當(dāng)然并不是改變名字那么簡單,體現(xiàn)了刊物追求改變、體現(xiàn)自身獨特性的意圖。譬如“為適應(yīng)文學(xué)藝術(shù)事業(yè)繁榮和發(fā)展的需要”,1957年1月《甘肅文藝》更名為《隴花》,編者指出:“從今年起,《甘肅文藝》改為《隴花》,隴是甘肅的簡稱,從字義上講,隴是地里的塄坎,花是象征著‘百花齊放’的意思。那么《隴花》這個刊名,包含著兩種意思,它是我們甘肅省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的園地,這里將培養(yǎng)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幼苗,在這個園地里,將開放出甘肅省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花朵。我們歡迎各種形式,各種內(nèi)容的作品‘百花齊放’,只要是‘花’就培育它,使其開放。”?
改變審稿、選稿和組稿的標(biāo)準(zhǔn)是大多數(shù)文學(xué)期刊改革的重要思路。1957年創(chuàng)刊的《星星》在第一期上就發(fā)表這樣的主張:“我們歡迎各種不同流派的詩歌。現(xiàn)實主義的歡迎!浪漫主義的也歡迎!”“我們歡迎各種不同風(fēng)格的詩歌。‘大江東去’歡迎!‘曉風(fēng)殘月’也歡迎!”《星星》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了有關(guān)愛情的詩《吻》、《收獲期的情話》、《大學(xué)生戀歌》、《湖上情歌》以及《草木篇》等。《人民文學(xué)》推出7月特大號,刊發(fā)李國文的《改選》、宗璞的《紅豆》等小說,穆旦、汪靜之、康白情的詩歌,以及沈從文、啟明的散文。沈從文的《跑龍?zhí)住肥恰度嗣裎膶W(xué)》專門組稿而來的。?1957年創(chuàng)刊的《詩刊》在組稿方面也同樣如此,據(jù)呂劍回憶,“創(chuàng)刊之初,在團結(jié)各派詩人以及組稿方面,都企圖開拓出一個新的局面。我們首先發(fā)表了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這首詩的構(gòu)思及其表現(xiàn)手法,當(dāng)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公劉的《遲開的薔薇》,就是冒著風(fēng)險發(fā)出的,那時‘愛情’在文藝作品中是個禁區(qū),我們既請張光年評論郭沫若,也約陳夢家來讀徐志摩,徐這個題目一直是犯忌的,除了關(guān)心新人之外,正如徐遲為呂亮耕詩集作的序中所說,我們也還想打撈一下‘沉船’”?。
文學(xué)期刊的改革還體現(xiàn)在期刊的管理和體制的變革方面。一方面期刊極力淡化行政化色彩。《詩刊》創(chuàng)刊時編輯部無一人是黨員,其編輯制度也極力維護編輯部的獨立性:“堅持質(zhì)量第一,決不盲目崇拜名人,也不輕視無名小輩。在編排目錄時,根據(jù)內(nèi)容質(zhì)量而不是根據(jù)作者名氣來確定先后順序。在稿件處理中,不論對著名詩人或文藝界主要領(lǐng)導(dǎo)推薦來的作品,只要質(zhì)量不夠,就提出意見與之商改或婉退,甚至還曾大膽退過詩壇巨匠郭老的詩作。”?有文學(xué)期刊編輯在回顧自己所編刊物未改革前的狀況時說,“我們的刊物在改版之前,有一個時期還規(guī)定了各種題材在每期刊物上所占的百分比,甚至為此降格以求;為了配合政治任務(wù),編輯人員每逢2、5、8、11月擬定下季選題時,都先到黨委了解下一季度的中心工作”。但他認(rèn)為文學(xué)期刊會議后各地方文學(xué)期刊仍然缺乏個性,原因就在于“刊物機關(guān)化,是刊物缺乏個性的主要根源”。他主張“黨委對于刊物的領(lǐng)導(dǎo),主要是多關(guān)心、多研究、多指導(dǎo),而不是多動手。如果具體到審稿、看大樣都管,這只會抓了眉毛,丟了辮子。刊物編輯部的事,原則上由刊物自己管,黨委和文聯(lián)可以委托一兩個人負(fù)責(zé)刊物領(lǐng)導(dǎo)工作,刊物的內(nèi)容、風(fēng)格……由他們?nèi)ゴ_定”。?可以說,去行政化是當(dāng)時文學(xué)期刊的普遍追求。
許多文學(xué)期刊都進行了這種去行政化的嘗試,因此在“反右”斗爭中這種行為遭到強烈批判。“他們把省市委宣傳部對刊物的領(lǐng)導(dǎo)叫做‘干涉’,并且動輒就叫囂起來,這不應(yīng)該‘干涉’,那不應(yīng)該‘干涉’;干涉幾乎成了他們的‘口頭禪’。他們說什么‘刊物應(yīng)該獨立自主’,‘發(fā)揮編輯部的創(chuàng)造性、積極性’。”《新苗》主編、民盟盟員魏猛克遭到批判,認(rèn)為他“在整風(fēng)開始的時候,就趁機把《新苗》‘獨立自主’起來了。他非法剝奪了原來編委會的職權(quán),把黨員和進步的編委拒之于門外,有關(guān)編輯部的許多重要問題(如編輯方針、體制、分工等),既不向黨委匯報,也不召開編委會研究討論,而由這個右派主編獨斷獨行”。?雖然這些政治批判難免夸大其詞,但從批判中不難看出文學(xué)期刊在刊物管理和體制方面做出的革新。
1957年還興起了出版同人刊物的嘗試。周揚在文學(xué)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可以創(chuàng)辦同仁刊物。1957年5月周揚在文章中重申了這一觀點,“辦成圈子較小的同人刊物,當(dāng)然也可以”?,這無疑激發(fā)了文學(xué)界創(chuàng)辦同人刊物的興趣。據(jù)敏澤回憶,“唐因、唐達(dá)成建議我們可以一起辦一個文學(xué)上堅持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同人刊物,希望我能跟陳涌講一下。陳涌表示,如果雪峰參加他可以參加”?。郭小川本人也曾經(jīng)有過辦同仁刊物的打算,他在“文革”時期的自我批判中說,“我自己還想自己辦一個同人刊物,這所謂同人,不僅包括李興華、楊犁、蘇中、涂光群、楊志一這些人,而且還想拉林默涵、樓適夷等等一起辦,后來因為林默涵從文藝黑線的全局考慮認(rèn)為不需要,而應(yīng)集中力量辦好已有的反黨喉舌如《文藝報》等等,才沒有辦出來”?。劉紹堂和友人也有過創(chuàng)辦同仁刊物的打算,據(jù)他回憶,“黨中央宣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激動人心,形勢大好,李岸熱情沸騰,倡議仿照蘇聯(lián)模式,籌辦一個全國性的青年文學(xué)刊物,刊名和蘇聯(lián)的一樣,叫《青春》。他要求我擔(dān)任主編,唯熙和他擔(dān)任副主編,雜志實行股東制,每股一千元。我接近上層,認(rèn)為不會允許創(chuàng)辦同仁刊物雜志,李岸要我試探一下”?。
據(jù)“反右”時期的批判文章看,全國出版同仁刊物的舉動還有很多,譬如“以韓秋夫為首的右派集團,打算在篡奪《青海湖》不得手以后,即創(chuàng)辦一個販賣資產(chǎn)階級的文藝觀點和低級趣味的‘同人刊物’——《夜鶯之友》,來和《青海湖》唱對臺戲。在貴州省,以錢革、楊守達(dá)為首的右派集團,準(zhǔn)備出版同人刊物——《文學(xué)青年》”?。
這幾次創(chuàng)辦同人刊物的嘗試并無付諸實踐,江蘇作家創(chuàng)辦的《探求者》雜志則起草了《章程》和《宣言》。據(jù)陸文夫回憶,1957年6月6日他和方之、葉至誠、高曉聲一起“決定創(chuàng)辦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國文壇上創(chuàng)造一個流派。經(jīng)過一番熱烈討論之后,便由高曉聲起草了一個‘啟事’,闡明《探求者》的政治見解和藝術(shù)主張;由我起草了組織‘章程’,并四處發(fā)展同人,拖人落水”?。陸文夫起草的《探求者文學(xué)月刊社章程》提出,“本月刊系同人合辦之刊物,用以宣揚我們的政治見解與藝術(shù)主張”;“大膽干預(yù)生活,對當(dāng)前的文藝現(xiàn)狀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創(chuàng)作方法也應(yīng)該多種多樣”。高曉聲起草的《探求者文學(xué)月刊社啟事》則表示“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shù)傾向;我們把編輯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來源就靠同人,我們將在雜志上鮮明地表現(xiàn)出我們的藝術(shù)風(fēng)貌……我們不承認(rèn)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是最好的創(chuàng)作方法,更不承認(rèn)這是唯一的方法”。?隨著形勢惡化和“反右”斗爭的開始,《探求者》未能創(chuàng)辦但依然遭到批判,其《章程》、《宣言》也成為對他們進行批判的依據(jù)。
期刊工作會議為期刊改革指明了方向,其決策也為期刊改革提供了政策保證,但之所以能夠引發(fā)如此大規(guī)模的期刊改革嘗試,也說明1949年以后文學(xué)期刊制度存在的弊端,其審稿、組稿等制度制約了文學(xué)發(fā)展的多樣化,尤其是文學(xué)期刊作為機關(guān)刊物的行政化色彩也造成了期刊管理上的缺陷。
三
期刊改革是“雙百”方針的產(chǎn)物,就像呂劍所說的,“如果沒有一九五六年的氣候,就不會有《詩刊》,《詩刊》的創(chuàng)刊曾經(jīng)被看做是一個吉兆,是文藝界擺脫束縛,走向舒暢的信號”?。可以說1956年到1957年的文藝調(diào)整和期刊改革是特殊政治時期的產(chǎn)物,一旦政策有變,這些改革和調(diào)整的合法性就會喪失。而且就是在“雙百”方針時期,文藝調(diào)整也不是毫無限度的,同樣要受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約,對政治正確的堅持也是首要的條件。
因“雙百”方針?biāo)纬傻摹鞍倩〞r代”只是相對而言的,因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本身是有底線的,毛澤東就提出過判斷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政治標(biāo)準(zhǔn),并指出“這六條政治標(biāo)準(zhǔn)對于任何科學(xué)藝術(shù)活動都是適用的”?。標(biāo)準(zhǔn)的制定意味著并不是任何主張和改革都能夠被接受,“毒草”只能被批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樣要堅持必要的政治標(biāo)準(zhǔn),因此文學(xué)期刊工作會議主張改革的同時也形成了這樣的意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絕對不是要我們把思想斗爭的旗幟收起來,而且要把它舉得更高。我們的刊物必須站在先進的立場、黨的立場上成為宣傳先進思想、先進事物、先進藝術(shù)的陣地。既然是‘爭鳴’,就必須‘爭’,通過說理的而不是粗暴方式,在刊物上對落后思想、落后事物、落后藝術(shù)進行斗爭。”?
在貫徹“雙百”方針的過程中,文藝界內(nèi)部很多人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持一種擔(dān)憂和謹(jǐn)慎的態(tài)度。在文學(xué)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上,與會代表對會議的決議大都表示擁護,但《萌芽》主編哈華則表達(dá)了不同的意見,他認(rèn)為“這樣搞下去沒人堅持黨的文藝路線了。我們辦個《萌芽》,就是想堅持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執(zhí)行文學(xué)期刊改革的編輯在進行變革時也大都以政治安全作為考慮因素。主持《人民文學(xué)》的秦兆陽雖然對刊物進行了很大的改革,但其在此次會議上的言論反倒顯得有些保守,他認(rèn)為辦刊物只能“大同而小異”,大同即“為社會主義事業(yè),為人民服務(wù),毛主席的方針,這些都是同的,如果這些東西不同,那就是根本的不同。又如昨天周揚同志講的跟唯心主義進行戰(zhàn)斗,這是應(yīng)該同的,雖然我們的刊物可以發(fā)表唯心主義的東西,但我們的心里的想法和實際上的做法都是相同的”。他認(rèn)為刊物的風(fēng)格、特點不是主要問題,最主要的是“我們刊物所擔(dān)負(fù)的任務(wù)。我們要教育讀者,至少要引起他們動腦筋,而要引起他們動腦筋,我們得有本錢。我們不是為風(fēng)格而風(fēng)格,我們是為了讀者,為了提高讀者的水平,我們得給他們東西,這是刊物的最主要的任務(wù)”。?秦兆陽在“文革”后回憶自己的編輯生涯時,也頗為自豪地說,“凡我主持編輯的刊物,從未忽視文學(xué)與政治關(guān)系以及文學(xué)本身的特點,總是力求掌穩(wěn)方向,不為文藝思潮復(fù)雜多變的奇風(fēng)怪雨所動”,“凡我經(jīng)手的稿件,無不字斟句酌地注意思想藝術(shù)的社會效果”。?有人研究認(rèn)為,秦兆陽在主持《人民文學(xué)》改革期間“流露出革命理想主義者的真誠”,所刊發(fā)的干預(yù)小說也“以矛盾的面貌出現(xiàn),而不能走向徹底”,“無論是版面安排或者推薦語,都不脫一種總體的框架:對政治性的認(rèn)同和確認(rèn)”。?
文藝界內(nèi)部對“雙百”方針的態(tài)度也是復(fù)雜的,尤其是一些地方行政領(lǐng)導(dǎo)對這一方針并不完全贊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文藝界的調(diào)整和期刊的改革。1957年1月7日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四人發(fā)表《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認(rèn)為由于提倡百花齊放,“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越來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當(dāng)前重大政治斗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務(wù)事、兒女情、驚險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寫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驚天動地的解放斗爭、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說、戲劇、詩歌,因此,使文學(xué)藝術(shù)的戰(zhàn)斗性減弱了,時代的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沉了,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光輝在文學(xué)藝術(shù)這面鏡子里光彩暗淡了”。陳沂也發(fā)表了《文藝雜談》,同樣擔(dān)心由于“雙百”方針的執(zhí)行造成文藝界的混亂。針對這種狀況,1957年l月18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強調(diào),“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志認(rèn)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嗚方針很不理解”?。同時表示,“也許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為黨為國,但意見是不對的”?。此后不久,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批評總政治部文化部長陳沂,指責(zé)他在《學(xué)習(xí)》雜志上發(fā)表的《文藝雜談》是阻礙鳴放,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diào)。?但毛澤東的意見卻在傳達(dá)時出現(xiàn)了反差,“這次書記會議以后,不少省市傳達(dá)時說:毛主席是肯定四人文章,說他們是為黨為國。許多省市報刊轉(zhuǎn)載了陳其通等四人文章,有的加按語肯定,并配發(fā)擁護文字。有的地方還開座談會擁護四人文章并檢討本地區(qū)1956年文藝工作中的‘文字’。這可能是未聽懂毛澤東的講話,同時也反映了當(dāng)時許多人同四人文章有共鳴”?。
1957年創(chuàng)刊的《星星》的遭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dāng)時期刊改革所經(jīng)受的政治壓力和阻力。《星星》創(chuàng)刊號因發(fā)表情詩《吻》,“被《四川日報》上一位署名‘春生’的批評家,在題為《百花齊放與死鼠亂拋》的一篇文章里面,斥之為‘色情’的作品,并認(rèn)為《星星》把黨的‘百花齊放’文藝方針,搞成了‘死鼠亂拋’”。《星星》編輯部為此寫了反批評文章,但被《四川日報》壓住不發(fā),因為寫《百花齊放與死鼠亂拋》的“春生”是省委宣傳部分管文藝的副部長李亞群。據(jù)石天河回憶,“我們堅持按‘百家爭鳴’的原則,應(yīng)該容許反批評。報社不發(fā),我們就準(zhǔn)備自行印發(fā)。這就引發(fā)了一場大禍。四川文聯(lián)領(lǐng)導(dǎo)以‘機關(guān)大會’的形式,對我和流沙河、儲一天、陳謙等人,進行了壓制性的批判,并給了我‘停職反省’的處分”。后來因毛主席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對《星星》和《草木篇》的問題說過一些話,才撤銷了對石天河等人的處分。?
雖然“雙百”方針的執(zhí)行使得文學(xué)環(huán)境得到了一些改觀,但文學(xué)期刊的根本性變革也是不允許出現(xiàn)的,因此同仁刊物的創(chuàng)辦大多是一種設(shè)想,并且遭到一些具有政治敏感的老作家的勸阻,他們憑借政治經(jīng)驗意識到辦同人刊物的政治風(fēng)險。譬如劉紹堂為籌劃創(chuàng)辦同仁刊物《青春》曾向康濯、邵荃麟尋求意見,“我首先聽取康濯同志對創(chuàng)辦《青春》的意見,康濯同志勸我慎重;我又找當(dāng)時的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邵荃麟同志請教,荃麟同志極力勸阻。于是我叫維熙轉(zhuǎn)告李岸,辦刊一事不妥,便回鄉(xiāng)了”?。陸文夫、方之在籌劃創(chuàng)辦《探求者》雜志期間曾向巴金詢問意見,據(jù)巴金回憶,“我覺得他們太單純,因為我已感覺到氣候在變化,我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雜志’,放棄他們‘探求’的打算”?。而敏澤等中國作協(xié)內(nèi)部工作人員在籌辦同人刊物時更是小心翼翼,據(jù)敏澤回憶,“當(dāng)時,為了避免被人抓把柄,決定群眾一個都不吸收,唐因是黨員,唐達(dá)成和我是共青團員,這樣做是免得別人說搞非黨的活動。我們只是口頭上簡單地商量過,雪峰和我都問過(郭)小川,周揚的話算不算數(shù),如果算數(shù),時機成熟就辦”?。可見在經(jīng)歷過政治風(fēng)雨的老作家看來,文藝政策具有不確定性,既使眼下政策允許的事情也并不見得具有可以實施的合法性基礎(chǔ)。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給黨內(nèi)高級干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jīng)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這是為什么》,“反右”斗爭開始。文藝界的調(diào)整和文學(xué)期刊的變革都被視為反黨行為。《人民文學(xué)》被認(rèn)為是“代表了修正主義的創(chuàng)作逆流,革新特大號變成了‘毒草專號’。中國作家協(xié)會很快編印出來供內(nèi)部閱讀的一本厚厚的《人民文學(xué)》毒草集,集中理論方面,除收秦兆陽的《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還收入了近半年以來,包括5、6、7期《人民文學(xué)》發(fā)表的很多評論、雜文,有李清泉用筆名寫的批評社會上右派的雜文、編后記和筆者及編輯部其他編輯寫的短論和雜文等。作品則赫然收入了李國文、宗璞等剛發(fā)表的新作”。文學(xué)期刊上“毒草”的出現(xiàn)被認(rèn)為是期刊編輯的政治責(zé)任,譬如李希凡在批判《本報內(nèi)部消息》等作品時認(rèn)為,《人民文學(xué)》是這類作品“代銷的市場”,他認(rèn)為《在橋梁工地上》發(fā)表,“受到《文藝報》、《人民文學(xué)》等捧場之后,劉賓雁才敢于寫《本報內(nèi)部消息》這樣露骨的反動作品,自從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報刊的贊揚之后,所謂‘揭露生活的陰暗面’,和歌頌黃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現(xiàn)了”;“只是《本報內(nèi)部消息》一篇,《人民文學(xué)》1956年6月號的‘編者的話’,就費去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專門推薦這篇有著露骨的反黨目的的特寫,誰能說編輯部沒有它的態(tài)度呢?并且直到最近他們還在繼續(xù)推薦《改選》、《紅豆》這樣的毒草和莠草,卻看不到他們對于放出的毒草,作過任何嚴(yán)肅負(fù)責(zé)的交代”。
文學(xué)期刊的改革被看做是篡奪文學(xué)領(lǐng)導(dǎo)權(quán)的行為,《文藝報》在刊發(fā)的批判文章中就指出,“根據(jù)報刊所揭發(fā)的材料看來,在全國范圍內(nèi),好多文藝刊物都被右派分子篡奪了領(lǐng)導(dǎo)權(quán),篡改了刊物的政治方向,只是輕重程度不同罷了,這種情況大體上可分為如下三類:一、右派篡奪了領(lǐng)導(dǎo)權(quán)并在編輯部內(nèi)占優(yōu)勢地位的有:《江淮文學(xué)》、《芒種》、《星星》;二、右派把持了刊物的而偷運毒草的有:《新苗》、《長江文藝》、《熱風(fēng)》、《東海》、《蜜蜂》;三、沒有被右派分子篡奪去領(lǐng)導(dǎo)權(quán)但有右派分子活動的,這就比較多一些,不必列舉”。
文學(xué)編輯和籌辦同人刊物的作家也難逃嚴(yán)厲的政治懲罰。1957年6月24日到7月8日,《文藝報》陸續(xù)舉行了5次全體人員大會,“展開了嚴(yán)肅的自我批評和尖銳的斗爭”,會議“揭露黨員唐因、唐達(dá)成等人對黨的領(lǐng)導(dǎo)抱有嚴(yán)重的對抗情緒。他們要求大鳴大放,實質(zhì)上是要把文藝報辦成資產(chǎn)階級的‘自由論壇’,唐達(dá)成要求編委會‘敲作家協(xié)會的大門’……同時有的編輯為了拒絕黨和作協(xié)的領(lǐng)導(dǎo),竟然提出文藝報編輯部應(yīng)該‘六親不認(rèn)’的荒謬論調(diào)”。籌辦《探求者》的方之、高曉聲等人也遭到嚴(yán)厲的政治打擊,《探求者》的“啟事”和“章程”被認(rèn)為是“一個在文藝領(lǐng)域中的系統(tǒng)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lǐng)”。“反右”斗爭使大批編輯被打為右派,“當(dāng)時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幾個刊物,沒有一個不被認(rèn)為是犯了嚴(yán)重的右傾錯誤,它們的主要負(fù)責(zé)人(主編、副主編、編委、編輯部主任),絕大多數(shù)不是被錯化為‘右派’,就是受到‘留黨察看’、‘嚴(yán)重警告’等黨紀(jì)處分”。
結(jié) 語
文學(xué)期刊改革最后以失敗而告終,文學(xué)期刊不但沒能達(dá)到改進的目的,反而在辦刊思路上更加倒退。在“反右”斗爭的震懾下,報刊方針和編輯行為更加保守,各地文學(xué)期刊被重新調(diào)整。中國作協(xié)書記處為改革刊物提出了“明確方向,加強領(lǐng)導(dǎo)、縮短戰(zhàn)線,充實力量”的改進刊物工作的方針,同時“為集中力量辦好刊物”,決定從1958年起將《文藝學(xué)習(xí)》與《人民文學(xué)》合并,將《文藝報》改為以文學(xué)評論為主的社會、政治、文學(xué)、藝術(shù)評論的半月刊。并指示所屬各刊物按照上述方針切實改進工作。這次改革的目的顯然是為了糾正此前改革所犯的錯誤,“改組后的《人民文學(xué)》,將糾正過去一個時期內(nèi)所犯的修正主義錯誤,同時接受《文藝學(xué)習(xí)》一度把青年讀者引入右傾迷途的教訓(xùn),真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文學(xué)刊物”。文學(xué)期刊改革的失敗可以說是“十七年”的文學(xué)體制的必然結(jié)果,其改革的限度和對必要的政治標(biāo)準(zhǔn)的堅守也是社會主義文學(xué)作為“工具”文學(xué)所具有的特征。雖然這一時期的期刊改革對此前文學(xué)期刊的弊端有一定的糾偏作用,但根本性的變革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改革的目的仍然是為社會主義制度服務(wù),在文學(xué)體制的根本特征無法變革的條件下,期刊改革只能是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的調(diào)整。
【注釋】
①丁玲:《為加強我們刊物的思想性、戰(zhàn)斗性而斗爭》,《文藝報》第五卷第4期。
②丁玲:《為加強我們刊物的思想性、戰(zhàn)斗性而斗爭》,《文藝報》第五卷第4期。
③《全國文聯(lián)關(guān)于調(diào)整北京文藝刊物的決定》,《文藝報》第五卷第4期。
④《關(guān)于地方文藝刊物改進的一些問題》,《文藝報》第四卷第6期。
⑤丁玲:《為加強我們刊物的思想性、戰(zhàn)斗性而斗爭》,《文藝報》第五卷第4期。
⑥《人民文學(xué)》編輯部:《文藝整風(fēng)學(xué)習(xí)和我們的編輯工作》,《文藝報》1952年第2期。
⑦《北京文藝界整風(fēng)學(xué)習(xí)基本情況》,《文藝報》1952年第15期。
⑧劉金鋒:《地方文藝刊物的幾個問題》,《文藝報》1953年第9期。
⑨《對地方文藝刊物的意見》,《文藝報》1953年第7期。
⑩胡風(fēng):《致王元化》,《胡風(fēng)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頁。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8卷,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頁。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1卷,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279頁。
?郭小川:《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檢查、受批判、再檢查》,《郭小川全集》第12卷,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頁。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頁。
?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人民日報》1956 年 6 月 13 日。
?張光年:《好一個“改進計劃”! 》,《人民文學(xué)》1958 年第 4 期。
?郭小川:《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檢查、受批判、再檢查》,《郭小川全集》第12卷,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頁。
?郭小川:《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檢查、受批判、再檢查》,《郭小川全集》第12卷,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頁。
?《辦好文學(xué)期刊,促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報》1956 年第 23 期。
?《文學(xué)期刊編輯工作會議,要求認(rèn)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人民日報》1956年12月4日。
?《辦好文學(xué)期刊,促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報》1956 年第 23 期。
?參見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頁。
?《風(fēng)雨47載,輝煌400期——〈飛天〉沿革》,《飛天》1997年第8期。
?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頁。
?呂劍:《未完的回憶》,《詩刊》1976 年第 1 期。
?白婉清:《〈詩刊〉憶舊思今》,《詩刊》1997 年第 1 期。。
?李汗:《文藝刊物需要“個性解放”》,《文藝報》1957 年第 9 期。
?朱樹鑫:《決不允許右派分子篡奪文藝刊物》,《文藝報》1957年第24期。
?周揚:《解答幾個關(guān)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幾個問題》,《周揚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5年版,第510頁。
?敏澤、李世濤:《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敏澤先生訪談錄》,《文藝研究》2003年第2期。
?郭小川:《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檢查、受批判、再檢查》,《郭小川全集》第12卷,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209頁。
?劉紹堂:《哭苦命的李岸兄》,《我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原農(nóng)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頁。
?朱樹鑫:《決不允許右派分子篡奪文學(xué)刊物》,《文藝報》1957年第24期。
?陸文夫:《又送高曉聲》,《收獲》1999 年第 5 期。
?《“探求者:月刊社的章程和啟事》,《雨花》1957 年第 10 期。
?呂劍:《未完的回憶》,《詩刊》1976 年第 1 期。
?毛澤東:《關(guān)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3頁。
?《辦好文學(xué)期刊,促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報》1956 年第 23 期。
?黎之:《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宣傳工作會議”》,《文壇風(fēng)云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頁。
?秦兆陽:《在全國文學(xué)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上的發(fā)言》,《文學(xué)探路集》,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171頁。
?秦兆陽:《一個老編輯的嘮叨》,《舉起這杯熱酒》,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頁。
?李紅強:《〈人民文學(xué)〉十七年》,當(dāng)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1頁。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頁。
?黎之:《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宣傳工作會議”》,《文壇風(fēng)云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頁。
?黎白:《回顧總政創(chuàng)作室反右派運動》,牛漢、鄧九平主編《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jīng)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頁。
?黎之:《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宣傳工作會議”》,《文壇風(fēng)云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頁。
?石天河:《回首何堪說逝川———從反胡風(fēng)到〈星星〉詩禍》,《新文學(xué)史料》2002年第4期。
?劉紹堂:《哭苦命的李岸兄》,《我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原農(nóng)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頁。
?巴金:《悼方之同志》,《上海文學(xué)》1980 年第 1 期。
?敏澤、李世濤:《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敏澤先生訪談錄》,《文藝研究》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