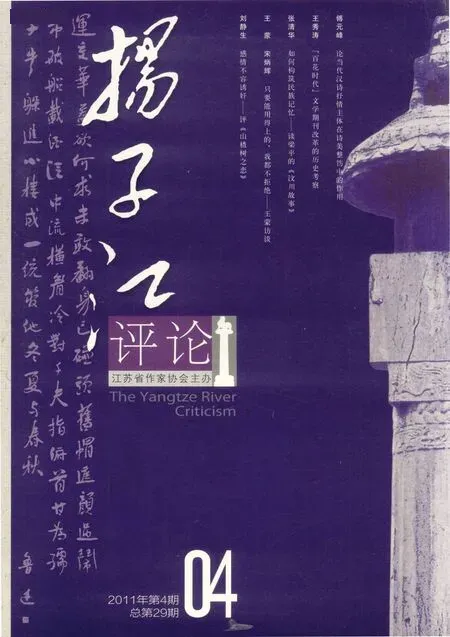新世紀中國現實的審美想象——2010年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掃描
張麗軍
六六的長篇新作《心術》(《收獲》2010年第4期),依舊是直面有“熱度”、有“難度”的社會問題——“醫患矛盾”。小說以一家上海三甲醫院里顱外科醫生們的工作情狀、生活困惑、情感糾葛、醫患紛爭為藝術表現內容,詳盡披露了醫生與病人、醫生與社會、醫生和醫生、醫生和護士之間的鮮為人知而又復雜難言的多元關系。小說的藝術形式新穎獨到,六六用“網絡論壇”、“私人日記”、六六“自述”等各類文學表現形態,寫出了醫生不為人知的苦衷:“醫鬧”蠻橫的報復,病人對醫生的無奈“防備”,醫患關系的緊張和沖突,醫生自身的精神危機,價值抉擇間的思想較量,醫德高風的艱難維護。正如小說中顱外科的老主任所言,不光要有精湛完美的醫術技巧,更要有治病救人、懸壺濟世的高風“心術”,這才是一個合格的醫生。小說精心刻畫了幾個醫生形象,他們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感立體鮮明、生動可感,富含生活氣息和現實維度。老主任的高尚醫德讓人敬仰贊許,大師兄雖然醫術高超,但面對女兒的命懸一線卻無能為力。二師兄出身“名門”卻沒有架子,他的愛憎分明能逞一時之快也為他帶來不少麻煩,他對少年病人賴月金的一腔關懷顯示了他內心的溫柔和敏感。“美小護”體貼入微、善解人意,她和二師兄最后的喜結良緣,證明了他們終究“逃不出”醫生和護士間的微妙、曖昧的情感“關系”。傳奇人物李主任的“安撫病人”的病患理論,平凡簡潔卻讓普通醫生難以望其項背。性格高傲的“孤美人”在身患絕癥之后茅塞頓開,從孤傲、陰冷的陰影里走出,笑對最后人生,醫生李剛對病人女兒的“自作多情”使讀者在捧腹之余也有一絲苦澀。《心術》的文學表述雖然立足醫院,卻沒有為這方寸之地所局限。貫穿小說始終的是那一句話:信仰、希望和愛是人最寶貴的東西。或許因為有了堅貞不渝的精神信仰,人才能在挫折、困難、打擊、不幸、失敗面前屢敗屢戰,高蹈前行;或許心存愛和希望,社會的文明進步、精神提升才會不至于如“空中樓閣”那樣虛妄飄渺。
謝湘寧的中篇小說《記者》(《小說林》2010年第4期)所直接言說的內容,有著強烈的社會現實性、批判性。小說描寫了作為報社的“頭牌記者”劉依然,在去采訪昊天集團——一家大型國有企業——時的內心掙扎、思想斗爭、情感困惑,把一個信奉職業道德、恪守記者信仰的女性形象,逼真細膩地展現了出來。對于昊天集團以及它的“老總”李大中,是正面報道企業的扭虧為盈、蒸蒸日上,是負面揭露集團內部管理人員的貪污腐敗、集團領導的奢華淫逸、國有資產的無形流失,還是鼓起勇氣報道集團職工的生活困難、下崗上訪?面對報社總編以退為進的“高壓姿態”,李大中周到妥帖的行程安排和順理成章的隱秘行賄,辦公室主任周龍的“美男計”,加上劉依然家庭矛盾的愈演愈烈,整個小說在極小的敘述空間里,把社會現實問題、感情問題、國有企業的管理問題、人性問題、良知問題都以高超的藝術表達,理性、客觀、條分縷析地予以觀察予以展開。小說的人文批判和良知洞察真有“四兩撥千斤”的不凡氣魄。故事結尾出人意料:采訪稿件被周龍力阻退回,李大中東窗事發鋃鐺入獄,報社沒有“虛假報道”因禍得福,劉依然又有了一次“出差采訪”的機會。小說可謂直擊社會現實痼疾,直面當下諸種不正之風,立意尖銳犀利,價值判斷鮮明有力,敘述視角也稱得上別出心裁。此外,在藝術人物的營造上也是可圈可點:精明能干的周龍、頗有鐵腕手段的李大中、庸俗透頂的丈夫馬杰、深謀遠慮的報社總編、一身正氣的退休老干部,都令人印象深刻,難以忘懷。
趙竹青的《火車頭》(《當代》2010年第4期)對“群眾性事件”的藝術展示不僅需要精湛高超的藝術匠心,也是對作家寫作使命、寫作良知、寫作勇氣的某種考驗。《火車頭》不僅機智靈活地表現了“群眾性事件”這樣敏感的甚至有禁忌色彩的特殊題材,而且沒有簡單地止于道德義憤的渲染和空疏的議論吶喊。而是從一個隱蔽側面入手,圍繞秋老八這樣一個有些“地痞”色彩的人物,以他追求下崗女工尤碧華為故事主線,用絲絲入扣的敘事探索編織起了嚴謹合理的情節框架。秋老八本是塔山鎢礦的一名火車司機,與尤碧華還有她的丈夫是同事,更是好朋友。然而尤碧華的丈夫,在一次意外中不幸地死于秋老八之手,兩家的關系走向冷淡。隨著塔山鎢礦的改制、企業效益的下滑、國企改革的失敗,尤碧華下崗了,秋老八的妻子也棄他而去。秋老八和尤碧華這一對“冤家”,在灰色的、艱難的生活里,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糾葛:秋老八想娶尤碧華好好地照顧母女二人,尤碧華卻因為丈夫之死心里的創傷始終未能痊愈。直到秋老八開著“火車頭”為了鎢礦工人的利益鼓動群眾“鬧事”,他們之間的情感堅冰才慢慢消融。此時,秋老八卻被公安人員帶走了。在情感表達上,小說既有溫情脈脈的人性關懷,又有冷峻甚至痛苦的人文反思。作者的追求正義的人文訴求、渴望公平的呢喃絮語、審視黑暗的嚴厲姿態、書寫底層的熾熱抱負,讓人肅然,也使人動容。
羅偉章的中篇小說《窄門》(《人民文學》2010年第9期)的藝術追求和人文探索都極為成功。小說在舒緩有致、平靜無波的敘述背后,逐漸地掩藏、醞釀、積累高密度的敘事勢能,直到最后的瞬間“爆發”,真可謂驚心動魄,精彩不凡,讓讀者的心靈受到較為密集的強烈震撼之后,也暗暗贊嘆作者新穎獨到的敘事才具。小數內在紋理構造得精致豐厚,幾近天衣無縫。鰥夫林光華在兒女事業有成之后,以獨守礦山為樂事,怡然自得地與山水樹木相依為伴。孰料在一幫牌友的挑唆帶動之下,他漸漸地迷上了茶館喝茶、打牌的消遣日子,陰差陽錯般地愛上了名為茶館服務員實為“暗娼”的張慶秋。然而,一個是年近花甲的鰥夫老人,一個是不滿三十的青春少婦,生理和年齡的錯位、生活方式的隔閡、情感溝通的代溝,使兩人漸生怨隙。隨著兒媳張紋的出軌、兒子林川精神的崩潰,林光華的心理在失控后,為給兒子報仇,也為給自己泄恨,在一個山洞“溫柔”地殺死了“暗娼”張慶秋。小說背后思考的社會問題極為嚴肅深沉,作者探尋孤寡老人因為生活孤獨、苦悶、親情缺席、交流貧乏所帶來的可怕后果和灰色現實。小說的敘述內容立意鮮明,社會擔當深廣明確,藝術細節真實生動,人物形象立體復雜,值得大家一睹為快。
魏微作為七零后作家中較具特色的、代表性作家,近幾年來的創作探索一直呈現著扎實、平穩的藝術發展勢頭,《鄉村、窮親戚和愛情》、《化妝》、《大老鄭的女人》這些代表性文本都能折射魏微細膩、敏感、飄逸、唯美、詩性的內心體悟,溫情默默的文字性格也讓她的小說更具獨特的氣質。相對而言,中篇小說《沿河村紀事》(《收獲》2010年第4期)之于魏微以往的小說創作,有明顯的“斷裂”、“轉型”之跡。魏微的凝視、觀察的文學視野亦顯得開闊、豐滿起來,表現、思考的文學中心亦發生了由“內到外”的飛躍。小說以曾經僻遠貧困的南方小村——“沿河村”為審視點,以見證人、記錄人、參與者的多重文化身份,用浪漫、豪放、粗獷的新鮮筆致摹寫了沿河村人從窮變富、由弱到強、從“軍人”到“商人”、從保守閉塞走向改革新潮的多維性的社會轉變。作者也敏銳地嗅到了改革帶來的悄然“歷史遺忘”,曾經振奮人心的理想主義、集體主義已經蕩然無存,沒有絲毫蹤影;原先的“逃稅軍車”也已銹跡斑斑,成為沒有人理睬的寂寞“文物”。沿河村的人們也從一種“瘋狂”進入了另一種“瘋狂”,村民的“集體癔癥”仍然驚心動魄地上演著、燃燒著。這到底是歷史的巨大倒退,還是時代的痛苦進步?魏微的文學關懷、社會審視以小見大,氣度不凡,小說敘事跳躍起伏又疏密得當,作者對人心善惡的變遷考察,對理想主義的人文挽歌式的憑吊留戀,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別致拷問,富有較高的情感深度和卓越的思想力量。
鐵凝的短篇小說《春風夜》(《北京文學》2010年第9期),有著對卑微底層純真情感的由衷贊嘆和深情理解,也有對城市文明規則的嚴厲審視。小說把敘事鏡頭對準一對農民工夫婦——俞小荷和王大學,他們兩人,一位是為人洗衣做飯、恪盡職守的保姆,一個是常年“以車為家”的長途司機。雖然夫婦倆彼此謀面相互“溫存”的機會少得可憐,但他們依然彼此以樸實本真、溫暖感人的情感方式關懷著對方掛念著彼此,依然有尊嚴地活著、有尊嚴地愛著。某種程度上,“春風旅館”象征著森嚴的城市文明秩序,對夫妻二人有些許排斥和拒絕,他們反而用純一感人的情感力量,溫暖著冷漠無情的都市倫理。鐵凝在有意無意間用輕盈從容的文學書寫思考厚重嚴苛的社會真實,在孜孜以求地構建著溫馨動人的情感王國,達到了一種震撼人心的審美標高,營造了一座溫潤社會的精神之塔。
阿袁的《顧博士的婚姻經濟學》(《十月》2010年第4期)寫出了大學校園諸位高校教師的復雜人際之爭,也道盡了“儒林世界”里多樣的人情百態。小說從顧博士夫婦來師大試講,夫妻間的差別讓其他教授浮想聯翩寫起,細細道來,顧博士跌宕起伏、妙趣百般的幾段情事傳聞,在幾近諷刺調侃之余,也有苦澀無奈的輕微嘆息。顧博士先后與外語系的系花沈南、小師妹姜緋緋“拍拖”戀愛,兩位美女幾乎都“招架不住”顧博士“婚姻經濟學”的精打細算,無果而終。而“丑小鴨”陳小美沒有愛逛街購物、吃零食的“惡嗜”,讓顧言的錢包不再“膽戰心驚”,而她的一雙巧手里的廚藝更是讓顧博士眼界大開嘆為觀止,陳小美完美地符合顧博士的實惠、世俗、經濟的“婚姻經濟學”。小說敘事輕盈飄逸,人物形象的刻畫飽滿生動,顧博士、陳小美、中文系主任陳季子、孤傲刻薄的教授俞非、愛嚼舌頭的姚麗絹、落魄可笑的卜教授、自作多情的學生鮑敏,都在支撐著小說探索現實的力度深度。小說最后,顧博士的婚姻經濟學竟“風靡”師大。博士、教授這些象牙塔里的“天之驕子”們,本應該安心從容地扎根學術獻身教育。然而,在阿袁的筆下我們看到的是,偷窺別人隱私、飛短流長于小道消息、精于投機專營的不學無術之徒,小說頗有幾絲《圍城》嬉笑怒罵的美學遺風。
雖然的《何氏眼科》(《黃河文學》2010年第8期)中的何大夫經營眼科門診,擅長做雙眼皮手術,收價合理,對真正的病人,手術費可以讓步。小說講一個身高只有一米二的女子做雙眼皮的故事,這個面容嬌好的女子氣質高雅,從容淡定,臉上布滿光輝,甚至讓何大夫心神蕩漾。普通人追求美麗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一個殘疾女子獲得美麗后感激的道謝意義更為深重,結尾處尤其耐人尋味。美麗并非表面而是生存的狀態,卑微還是崇高都是自我的選擇,唯有心胸開闊,從容淡定而又不盲從時尚,才會擁有美麗的人生。小說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張力,飽含溫情。戴善奎的《劫后人家》(《四川文學》2010年第9期)是一篇對震后生活深切關注和透視的作品。小說沒有大幅描寫震后那滿目瘡痍的場景,而著眼于災區人民積極開展自救的過程。他們不僅在廢墟上打造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也在內心重筑起一片愈加澄澈和堅固的精神家園。郭震海的《一株莊稼》(《山西文學》2010年第9期)從生活中取材,描寫現實,揭露弊端,將村子中最好的土地修建避暑山莊,年輕人積極支持,而老憨在村里成為孤獨者,郁郁而終。山莊建成后,村民們不用種地,女人們可以成為服務生、清潔工,男人們則成為保安,原來明晃晃的鋤頭生銹了,犁鏵成了山莊的展覽品,又一個金秋時,老憨低矮的墳頭上長了一株莊稼,孤獨而健壯,傳說中最后的一株莊稼,表現了作家對當今生活的深切關注和深刻洞察。
劉慶邦的短篇小說素來有著較高的文學特色,他本人也有中國當代的“短篇小說之王”的美譽。劉慶邦《丹青索》(《北京文學》2010年第9期)以類似白描般的細節刻畫,為讀者精彩地描繪了一位落魄藝術家的黯淡面影。主人公索國欣年輕時是一名美術教師,退休后他的畫興不減,以“畫什么都行”當起了業余畫家。機緣巧合間,畫商老桂的無意中建議,使他以專畫打鬼的“鐘馗”謀得了一絲自信。索國欣甚至還以每張畫一百元的“高價”,批給畫商老桂,竟也利潤不菲。然而“事業”的“成功”,無法維持支離破碎的家庭生活:他妻子整日以“筑長城”為“主業”,女兒索曉明則成了吸毒的“癮君子”。他最后也在妻子、女兒的蠱惑下由“藝術家”墮落成了“藝術生產者”,最終“把鐘馗這個打鬼的神仙,畫成了被打的鬼”,他的“生意”也隨之沒了市場。索國欣的“杰作”——鐘馗畫像,頗有強烈豐富的隱喻之意,它既喻示著“人不人鬼不鬼”的世道社會,也暗示出鬼魅叢生的人心鏡像。小說的敘述語言冷靜理性,故事結構清晰曉暢,情節構思精妙新穎,文章到處涌動著劉慶邦深刻濃郁的文學憂慮和道德拷問。鄧學義的《生意經》(《山西文學》2010年第9期)講述的是新時代的支書兼村長關興林,面對村里經濟條件提升而人與人之間越來越遠的新農村的典型問題而煩惱,小說圍繞村里的一尊關公仗刀立像由鬧鬼到鬧神展開故事情節。作者從現實中取材,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生動的神仙崇拜、大仙下凡的圖畫,沒有曲折動人的情節,沒有慷慨激昂的格調,小智慧隱藏在平凡的生活中,發人深省。陳紙的《剛果的羊》(《四川文學》2010年第9期)中,來自剛果的種羊“望旺”未如期使身邊的母羊懷上羊仔,于是開始了它的治病之旅。非科班出身,有著雜七雜八背景和荒唐見解的幾位“專家”在這一過程中丑態百出,最后卻歪打正著……作者在敘事過程中帶有鮮明的批判和諷刺意味,充滿了智慧和幽默,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中的荒誕性和悲劇性。
邱華棟的《交叉跑動》(《延河》2010年第8期)講述的是兩個故事,兩個主人公,看似毫不相干的兩個人最后相遇。故事情節交叉進行,而他們心靈深處對復仇的渴望和壓抑卻不期然間相遇。彭克強的童年從“文革”開始,他的父親有著如火的革命激情,白日將毛主席像章別在額頭上,鮮血直流卻在人群的歡呼聲中驕傲地走著,夜晚激情無處宣泄,彭克強母親的身體便成了他父親最好的宣泄品。哥哥彭克威是個小混混頭領,九歲時就可以為吃雞肉,卡住雞脖子將雞殘忍的殺死。妹妹生下來便身體弱,皮膚透明般。“文革”后,父親過著平凡的生活,不久便意外死去,之后,母親便有些瘋癲,哥哥成為彭克強的老師,在夜晚帶他翻上房檐教會他如何才是真正的成長為一個男人。第二個主人公名叫韋克堅,從農村考上大學,成績優異卻依然無法融入大學的生活。他決心走政治“紅道”得到組織的認可。他前后遇到三個女孩子,卻無一例外遭到嘲笑愚弄和輕視,慘痛的經歷讓他面對招搖過市的戀人們心生怨恨,內心壓抑渴望釋放。在新疆的一個夜總會,受過傷的韋志堅希望會有好運氣,他發現了美麗的熱娜古麗,此時,心中積蓄了滿滿復仇之火的彭克強向他們走來,命運就這樣交叉,為了美麗的熱娜古麗,彭克強殺死了韋志堅,殺死了木胡塔爾。小說的敘事手法獨特,語言表達精準,深刻揭示了“文革”前后被時代壓抑的人們的精神狀態。所謂交叉跑動,并不僅僅是故事情節的交叉進行,更重要的是主人公精神壓抑和人性扭曲的相似性造成一種交叉。小說自始至終被一種悲涼的基調所包圍,主人公的成長是一種被動的成長,一種由父及兄,由兄及弟的暴虐相傳,又或是一種由被玩弄后種下的仇恨繼而畸形的成長過程。作者塑造了極端個性化的主人公,向現實發出深沉的拷問,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力作。
朱山坡《逃亡路上的壞天氣》中(《上海文學》第10期),“我”、黑狗、臭卵,一個“貪污犯”、一個“犯了命案”、一個“得罪黑社會”,三個人逃亡去緬甸。小說開篇便設置了如此驚心動魄的活動環境,中間時隱約已經出現了政治陰謀,在逃亡過程中遇到大風雪,司徒市長對裝著一百萬箱子百般重視,后被兩個同伴搶去,在小女孩格桑冒著生命危險的幫助下奪回箱子,竟然發現箱子里裝的是妻子給自己準備的衣物。這種突然的變化讓小說在跌宕起伏中給人以深思。小女孩格桑的出現為整個故事增添了別樣的味道,丑惡中增添了美和純潔的愛,使小說有了人性的溫暖,小說由此得到升華。最后作者筆鋒一轉,整個故事竟然是荒唐的陰謀。人物逃亡過程中的心理過程,懺悔和悔恨,糾結到釋然,一切順理成章,毫無矯揉造作之感。既是荒唐的陰謀,更是溫柔的諷刺。
王祥夫《三坊》(《天涯》第5期)。三坊,一個因盛產麻糖而泛著甜味兒的小鎮,一個在城市化進程中被吞沒的犧牲品。拉麻糖的小人物糖五那原本悠閑恬靜的生活消隱在鋼筋、水泥之中。小說極其簡短,卻足以將這種家園的變遷、人物命運的起伏和人物心靈的嬗變刻畫的淋漓盡致。鄉村傳統的文化和生存方式在城市化的沖擊下消隱、瓦解、崩潰,而依附于傳統家園生存的底層小民的失落感也昭然若揭。這其中的郁悶和糾結是不言而喻的。
葛芳的《枯魚泣》(《朔方》第 10期),開篇寫“那魚真是瘋了”。魚的意象貫穿全文,三哥身體之外有另一個自己,作者將錦鯉魚附在另一個三哥身上,用魚最初的沖動象征三哥內心的膨脹和騷動,自己暢游在精神世界中,在一方閣樓里練書法、作畫,在漫天星斗下聽風的吟唱、花的蒂落,聽見孤獨的落葉飛時靈魂不安的苦澀聲,夜深人靜時,寂寞的流淚。這樣一個精神的唯美主義者,像鯉魚跳躍式的奔跑,很不安分,一方面是文學熏陶下的高潔,一方面是夜總會小姐的迷情。三哥是個矛盾復合體,老實的讓人聽不出撒謊,衣冠楚楚卻隱藏不了他內心對美和真的崇尚,生活的困境也不能阻止他苦中作樂,調侃人生。三哥渴望魚死網破似的愛情,渴望驚濤駭浪,腦海中一半是潔凈無塵的湖水,一半是激情和迷亂。小說整體的氛圍是神秘而玄妙,用冰冷的湖水和炙熱的火焰體現主人公的矛盾糾結,細膩精致的敘述讓人隱隱作痛。
劉曉珍《翁婿的戰爭》(《北京文學》第10期)。一場岳丈與女婿之間的沒有硝煙的戰爭,一場為了錢與權展開的較量。姐夫這樣一個無錢無權的小人物將升官發財寄希望于與姐姐這場功利的婚姻。在此,婚姻不再是責任與關愛,而成為金錢和權力的宿營地。作品為我們揭示了利益和欲望驅使下人與人之間那赤裸裸的功利關系,利用與被利用成為至高無上的處事法則。小說具有鮮明的現實批判性和指向性,感情隨物質的貧瘠豐盛而忽高忽低,這樣功利的婚戀觀所帶來的幸福又是怎樣的幸福?
楊鳳喜《一步之遙》(《星火》第10期)這篇小說,敘述城市互不相識的鄰居慢慢熟識,又因為對丈夫與女鄰居的猜忌而結束友誼,平靜的敘述中充滿著溫情的力量,矛盾沖突中彰顯疏遠的無奈和猶疑。最后滴下的淚水表露了女主人公對友誼的不舍和留戀,但為了自己平靜而安穩的生活,放棄純真的友誼。作者截取生活的真實小片段,從愛情和友情出發,為讀者闡釋了現代城市生活的封閉,人情的自私與冷暖。
當掉入現實的漩渦的時候,再也無法自拔,主人公只能任憑無形的力量擺布,使讀者仿佛看到主人公的面貌一點點的扭曲、變形,最后歸于魔鬼之列。王宗坤的小說《無法終止》(《百花洲》第10期)中最精致的是他的對人物心理描寫的刻畫,如開篇寫主人公因為嫖娼被抓到公安局,走出公安局時的慌張,作者描寫得很精到,“猛然跨進出租車,迅速地把車窗玻璃往上搖,外面的世界隔絕了,出租車內立刻就充滿了一種甜兮兮的味道,這種味道讓我產生了一種逃離的快感。”“再一次感受到車流人流排泄出來的聲音和色彩,我的情緒不再像剛才那樣外化,一股濃濁的世間氣息就如同強心劑注入了我的身體。”先是心理極度恐慌、膽怯,生怕別人看穿了什么,眼神陰霾遮蔽,而后現實生活的氣息賜予了他自以為是的資本,融入它們,一切罪惡仿佛都消失不見了,當權力地位仍在時,閑言碎語也不過是一場風信子的問候。同時小說描寫了主人公從逐漸掌握官場訣竅的過程,直至將自己身心交出,將羞恥心一點點剝離殆盡,人性的光芒在主人公身上變成了義無反顧和大義凜然的作惡,可悲至極。小說中現實的爾虞我詐、光怪陸離,主人公在無可奈何中醉生夢死,在鮮亮背后是濃重,是人生存的卑微和無奈。作者用痛快淋漓的敘述筆法,透射了掉入漩渦的悲戚和無法終止的人生,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品。
李治邦《尋找出路》(《青島文學》第10期)。小說塑造了鮮明的英雄人物李出路,英雄的光輝只在每次奮不顧身的救火后社會的褒揚,而在生活中英雄沒有光輝,妻子埋怨,老人生病沒錢交住院費,壓力的背后隱藏著英雄的無奈,為現實生活所迫,最終決定轉業。將小說引向高潮的是他的副隊長,與李出路的轉業相反,副隊長試圖賄賂過他好多次,他的妻子希望他成為立功的英雄,李出路厭惡地對他說,我不走,你也當不上我的隊長。而現實是副隊長佩服他的英雄氣概,想幫他渡過金錢的難關。在李出路罵他忘恩負義時,得到副隊長犧牲的消息,原因是副隊長不像他一樣能夠找到出路,被憋死在火海中。什么是出路?轉業意味著現實生活的富足,卻同時意味著信仰和理想的缺失。小說對李出路夢境的描寫傳達了他的內心選擇,夢中妻子帶他走出火海,走出來后看到一片大花園,孩子在花園里玩耍。小說采用夢境和現實結合的筆法,刻畫了英雄的掙扎、反抗直至順從,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發人深省。
中躍的《炒地皮》(《廣州文藝》第10期),以戲謔卻沉重的筆調,諷刺性地道出了當今知識分子的困境和文化界的尷尬處境。身為作家的中躍對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的把握游刃有余。文中那個叫中躍的主人公似乎是作者本人,又似乎是許多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小說家,因為他也在渴望著名利;但是他卻又有知識分子的那份清高:無法和樸克等熱衷于“炒地皮“的牌城大學的知識分子們徹底地同流,看不慣學生們棄講座而觀看”炒地皮“的行為。嚴峻的現實拷問與濃烈的警示意義交織:這種尷尬的心態與尷尬的處境鮮活的展現了當今文化界陽光背后的一些陰影,與同時刊登的那篇《三十如狼》相比,這篇小說也對當今高等教育狀況起了一種警示作用。另外,作者用了牌城大學、麻將城、草雞毛報社等戲謔性的語詞使文本的寓意更加鮮明。
夏天敏的《泛滿泡沫的河流》(《長城》2010年第6期)描述對財富的渴望毀掉了曾經美麗的河流,毀掉了曾經拙樸善良的少年,毀掉了曾經執著過的夢想。作者以其憂民的心態深切地關注著農民的生存和精神狀況,并有著深深的焦慮感和絕望感。文中故事發生地的高原河曾經有魚有龜,高原河畔曾經有一個拘謹沉靜、純真寬厚、重情重義、充滿生活情趣的高原少年尤小偉。但是生活的困窘與世態的炎涼使尤小偉遭受了屈辱與磨難,他的心靈開始扭曲,他決計以成為富人的方式來報復給過他屈辱的人,報復這個不公的社會。尤小偉犧牲親人,犧牲友情,犧牲曾經養活過自己的土地,不擇手段地辦起果汁廠,他的發財夢圓了,而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也湮沒在發財夢中。文中的“我”的角色是多重的,既是一個敘述者,又是看著尤小偉變化的審視者,還是尤小偉人性蛻變的參與者。作為一個審視者,“我”的理智是清醒的,對尤小偉的變化充滿著一個知識分子的痛苦與焦慮;作為一個參與者,我對清清的河流變成泛滿泡沫的河流是有責任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向利益作了妥協,所以在面對尤小偉所做的一切時會迷茫。小說中的生活是凡俗化的,語言練達深邃,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作者在小說中傾注了他對地域文化的特殊感情,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和特有的文化觀念關照著農民艱難的生存困境,關照著困境之下人性的變異。
肖彭的《北京戶口》(《星火》2010年第6期),以近乎殘忍的筆法勾勒出一個有失公正的社會和生存世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外國對我們這些孩子都敞開大門歡迎,為什么北京作為我們的首都,我們居住了十幾年的家,卻把我們拒之門外?”小說結尾處主人公那扣人心弦的追問令人無言以對。一紙戶口阻礙了升學、就業、戀愛等所有生活的方方面面。北京戶口的缺失給這些“外來戶”帶來了物質財富的憑空喪失,更剝奪了底層小民做人的權利和尊嚴。然而不公正的何止是政策,更在于那無常的人生際遇。主人公苦苦籌來的巨額“戶口遷移費”換來的卻是詐騙犯的落網以及警察的到來。作者將筆觸對準當下的普通小民和社會熱點問題,無疑具有強烈的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悲憤的情緒貫穿小說始末。作者似有意為作品安上了一個光明的尾巴。不久的將來,政策也許會變,局面也許會扭轉,但應如何去審視和安撫那些之前為一紙戶口付出巨大代價和犧牲的弱勢群體?在這一點上,小說無疑具有了審視過去和拷問人心的力量。
光盤的《洞的消失》(《上海文學》2010年第11期),圍繞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的“洞”,講述了三個故事。前兩個故事——“村民”和“攝影家”的故事圍繞小說中真實出現的“洞”這樣一個實體展開,而“畫家”的故事題目為“洞之外”,是關于“虛”的洞的敘述。小說給人以強烈的震撼,最突出的是心理刻畫。面對突然出現的“洞”,村民們恐慌、焦灼、逃災的心理刻畫得淋漓盡致,各家在屋前屋后挖地洞,以逃避災難的來臨,小說并沒有批判農民的愚昧和封建,為了防止即將到來的災難,團結一致,向祖先祈禱歲歲平安,這一切只為了描寫普通人面對災難的無力感。“攝影家”們對洞的離奇消失,得出了“不正常的現象預示著災難的到來,這不是迷信,而是科學預測”的結論,同樣突出的也是心理刻畫,面對家人和同事的不理解,認為他們得了心理疾病,就如同魯迅筆下的“狂人”與“正常人”,各執一詞。一個鄉村,一個城市,一個用迷信的方法解釋,一個用科學解釋,最后都歸結于人類對災難到來時的無助和恐慌。第三個故事,作者借由不被世人接受的畫家“妖”之口,嘲諷地產開發商,更表明了藝術家應該有關注現實、批判現實的職責。“站在洞口我們永遠也看不到洞里的世界”,“妖”有洞察世事的眼光,不被世人接受卻用心生活。三個故事緊密相連,虛與實相結合,“洞之外”看似不相關的故事卻道出主題,生活的哲學既審美又審丑。突出的心理描寫、巧妙的構思、新穎的結構、深層的寓意、靈魂的書寫,使得小說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宗利華有成熟的小小說寫作謀略,在情節設置和人物塑造方面都是一個高手。《香樹街104號》(《時代文學》2010年第11期)是他香樹街系列小說的一篇。小樂和小滿,一個小說家,一個詩人,詩人和小說家的身份令他們與現實世界產生一定距離,而這種距離更容易使他們看透現實并明晰丑惡的真相,兩人在香樹街的生活就是一個不斷發現真相的過程。小說情節具有一種內在的張力,在不斷跳動著的節奏中,人物命運有了曲折變化,人格的扭曲和人性火花的碰撞也展現了出來,因而可讀性較強。宗利華對造成人格扭曲的生存環境和社會原因有著清醒的認識并充滿了批判性。文中對小滿和小俊這兩個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是別具一格的,筆端充滿了悲憫和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