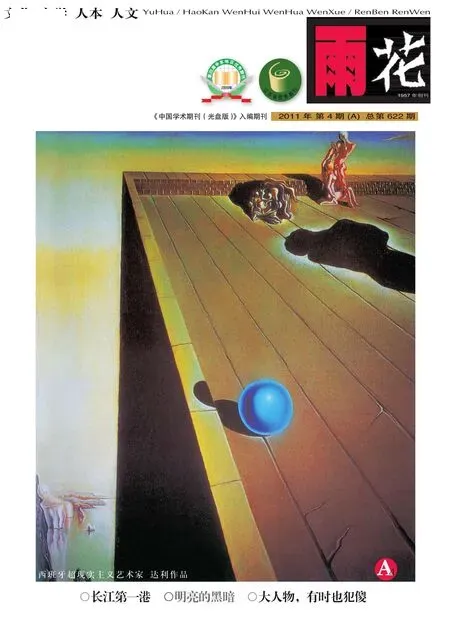明亮的黑暗
● 王 往
明亮的黑暗
● 王 往

21歲那年我流浪到了棲霞鎮,自此認識了陳哥。
那天中午我從鐵路上下來,去天橋南邊的廢品收購站賣道釘,一個瘸子在執磅。過磅后,他叫把道釘扔到廢鐵堆的最里面。這些道釘是從舊枕木上拔下來的,我偷偷藏在草叢里了,按規定是要上繳的。
“這是從鐵路上搞來的吧?鐵路上的東西私家收購站不允許收的,你自己也要當心。”
瘸子給我開了票,叫我去老板那兒拿錢。他的字十分工整,小數點后面的“0”圓得像一顆水珠。
我問他:“老板在哪?”他說老板在打麻將,你不認識嗎?我說不認識。他打量著我,說:“你才來棲霞?”我說我在鐵路上做工。他說:“哦,這是你搞的外快,我幫你去拿錢,你等一下。”
他去拿錢了,我看著磅秤旁邊散落的舊書本,就翻了起來。
他回來了,我還在翻書。
他把錢給我,說:“你找,多找幾本。”
我找了幾本比較新的雜志,問他要多少錢。
“不要錢,你拿走吧。”他笑著說,“我也常常從這里找些有用的東西。”
他又上下打量著我,問:“你在鐵路上做什么工?多少錢一個月?”
我告訴他,在鐵路上做的是拆除舊軌道和清理水溝的雜活,工錢是論天給的,8塊錢一天,不干活時沒有錢。他說,我知道了,你不是正式的鐵路工人,正式的鐵路工人都穿藍色工作服,你是民工,沒有人家的待遇高。他問我,你可不可以來棲霞街做生意?
他讓我跟他出去,指著墻上繃著的牛皮、狗皮、羊皮說:“收購皮毛很賺錢,我告訴你到哪里去收購。”
他又指著墻根攤著的鵝毛、鴨毛說:“還有這些羽毛,也可以收購,都很賺錢,比你做工強多了,你還有時間看書。”
提到看書,我來了興趣,在鐵路上和工友們住集體宿舍,實在是吵鬧。可是我沒做過收購的生意,加上這是陌生的地方,我哪里敢。
我說:“我回去想一想。”
他大概站累了,將一只手撐在那條瘸了的腿上,說:“你不要想了,肯定比你做工劃算,你要是想做的話,就找我。”
一連下了幾天雨,鐵路上干不了活,從收購站拿的幾本舊雜志也看完了,很是無聊。其間,因為工友借了我的雜志看,上廁所時順便當手紙撕了幾頁,還和人家吵了一架,其他工友并不向著我說話,他們嘲笑我是書呆子。我想寫一些東西,也不得安心。他們總在我寫作時,湊過來看幾句,帶著不屑的神情,丟下一兩句譏諷,讓我面紅耳赤愣在那兒。我決定離開鐵路,去找那個瘸子。
我到收購站時,沒有看見瘸子。看著墻上繃著的獸皮,聞著腥臊的怪味,我又想離去。一個中年男人從收購站里出來,問我有沒有貨賣,我說沒有,想找那個執磅的大哥。
一個賣破爛的男人過來了,中年人指著我對那人說:“瘸子要帶徒弟了,小偷要帶徒弟了。”
那男人看著我,嘿嘿笑著:“你要跟瘸子學手藝?”
我搖搖頭,不知道他為什么說瘸子是小偷。
我離開收購站,打算去街上瞎逛,沒走幾步,就碰上了瘸子。他問我有什么事,我說瞎逛的。他說:“你不想做生意嗎?”我嘆著氣,猶豫著。
“你先到我住處玩玩,我們好好聊聊。”他說。然后,他問我姓什么,我說姓王。他買了一個西瓜,讓我跟他走。他說他姓陳,棲霞街上人都叫他獨腿大俠。
他停下來,拍著自己那條瘸腿說:“我說給你,你不要害怕,我是小偷,不過我不偷熟人的,棲霞街上人我從來不偷,我都到南京偷。”
我說:“我以為你在收購站做工呢。”
他說,他那天是找不著人打牌,才幫魯老板執磅的。他和魯老板是親戚,魯老板的老婆是他的堂妹,他們對他放心。
他一個人住著三間瓦房,還帶后院,后院里還有一間平房,他說是廚房。房間和后院都非常整潔,房間里還掛著寫有古詩的條幅。
“這些字都是我寫的。”他說。
“啊——”他竟然會書法?我雖然說不上他書法的好壞,可是想到他說自己是小偷,我驚嘆了。
“沒事的時候,我喜歡寫毛筆字。”他似乎沒注意我的驚奇,把臥室的門打開,指著寫字臺上的幾本字帖和鋪著的白紙說,“我閑下來就寫毛筆字。這些字帖是從收購站的舊書里找來的。”
他的臥室真可以叫一塵不染,床上的被子疊得方方正正,被單的角都平平整整。寫字臺上還放著一盆水仙,葉子綠得像在雨中一樣。
他把西瓜洗了,剖開,給了我一瓣,叫我把西瓜籽吐到他鋪著的報紙上。
我慢慢地吃著西瓜,心里想著他怎么會說自己是小偷。
他告訴我,他這個房子租金是120塊一個月,棲霞街的外來人沒有一個舍得住這么大房子的,有人要和他合租,他不愿意。
“你來了,就住西間。”他說,“我不要你出錢。”
我說自己不會做生意,他說他帶我去屠宰戶那里,讓他們把皮貨賣給我。
我說:“你不是喜歡安靜嗎?”
他笑起來:“我看你喜歡看書,才想叫你和我住的,喜歡看書的人不會太吵鬧。”
陳哥起得很早,他說早上的公交車人多,“生意”好。一般情況下,他午飯前后就回到棲霞街了。回來后,他就找人打牌。他不和做小買賣的人打,都找有錢的主兒,比如收購站老板老魯,販豬的常老板,還有華菱香——一個運輸老板的老婆。他常常找不著打牌的人,因為他贏的時候多,人家懷疑他會偷牌。
“你偷不偷牌呢?”我問他。
他說:“我不偷,他們打牌都一心想贏錢,我是當作玩的,和練毛筆字一樣都是為了好玩,玩就是玩,偷牌還有什么樂趣。我要么直接偷錢,這是手藝。”
陳哥很為自己有這門“手藝”驕傲。他說這些年從沒失過手,除了棲霞街人知道他以偷為業,南京城里的警察碰都沒碰過他。
“你是用刀片劃人家的包,還是調包的方法?”我問他。
他說:“我從不用刀片劃人家的包,也不調包,我就直接解人家的紐扣,或者拉開包鏈,用手指夾出來。”
他把雙手伸開給我看,手指白而細長,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的前端都有硬而平滑的印痕。他說,主要是用這三根指頭。我這才想起他的中指平時為什么總是微微弓起。我問他,你解紐扣和拉拉鏈的速度一定很快吧?他說也不一定,要看具體情況,就像寫毛筆字一樣,要有輕重緩急,寫出字來才有力又有形,才能給人一氣呵成的感覺,關鍵是要保持鎮靜,要把人家的錢想作是你的,就不緊張了。
“再怎么想,畢竟不是自己的,怎么就不緊張了呢?”我想不通。
他說:“錢在他那兒是錢,在我這兒也是錢,不過挪個地方罷了,對國家來說,錢的總數并沒有少啊,有什么想不通的。”
他說完,得意地笑了。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房間里寫詩,他進來了,坐在我旁邊看了起來。
他說:“你真奇怪。”
他念著我詩中的兩行:家是一把無法攜帶的雨傘/離開她注定要經受風雨,然后說:“這句子好奇怪,你會寫奇怪的句子。你是怎么想出來的?”
我說:“突然間就冒出來的。”
他說:“奇怪奇怪。你以前也寫過嗎?”
我說寫過,然后把包里的一個剪貼薄拿給他看。
他說:“我拿我房間慢慢看。”
第二天早上,他沒有去南京“做生意”,他說看了一夜詩,發現了好多奇怪的句子,興奮得睡不著,上午要補個覺。
中午,我回來時,他已經做好了飯,還買了一瓶好酒。他說我聽說寫詩的都愛喝酒,你多喝點酒,再寫一些奇怪的句子給我看。我說我不喜歡喝酒,詩也要靜下來才寫。他哈哈大笑起來:“小王,你還記得我們剛認識那天的事嗎?”
我說:“記得,你讓我做生意的。”
他說:“不是說這個。你那天從鐵路上下來,滿身油污,褲腿撕開了,就用鐵絲纏著,你看到書時的眼神啊,就像多少天沒吃飯的人看到了包子,我就覺得你很有意思,跟我一樣喜歡尋開心,可是我沒想到你會寫出這么奇怪的句子。”
我說:“我也沒想到你會書法。”
我會寫詩的事讓陳哥傳遍了棲霞街。
房東老黃來收房租時,陳哥說:“老黃,跟我住的小王會寫詩呢。”老黃“哦”了一聲,一邊忙著寫收據,一邊說:“他不是收皮貨的嗎?”
陳哥說:“老黃,你不信嗎?不信,我把他的詩拿給你看。”
老黃敷衍著:“下次下次。”
我去老魯的廢品站賣皮貨,老魯把我收來的皮貨攤在地上,看了看說:“收皮貨你還寫詩,今天這皮貨成色差多了,是不是把眼睛熬壞啦,看走眼了?”
老魯給了我一個很低的價錢。
還有一次,老丁家的兩個孫子把我叫住了,說有鴨毛要賣給我。我停下自行車,老丁的大孫子拿著一根雞毛對我晃著:“瘸子說你會寫詩,你把詩拿來,我就把鴨毛給你。”然后哈哈笑著,跑了。
我對陳哥說:“陳哥,別跟人家說我會寫詩。”
“這有什么,你怕誰?”他說,“棲霞街除了你誰會寫奇怪的句子!”
我說:“我不愿讓人知道。”
他說:“我寫毛筆字我就不怕人說,明天我要把我的書法拿去賣,你看我的!”
第二天晚上我回來,他把我帶到他房間說:“你看看,我寫的書法都讓我賣了,五塊錢一幅,賣了八九十塊。”
幾天后,老魯家出貨,讓我去幫工,我在捆扎報紙時,發現陳哥扔在那里的書法,我才知道他說了謊。
棲霞街的人背后都叫陳哥“瘸子”,也有當面叫的,陳哥并不介意。但是老魯的七八歲的兒子魯小波叫他“瘸子”,他就很生氣。老魯的兒子應該叫他舅舅,可他只是偶爾叫他舅舅,比如九蘋在場時。
一天晚上,陳哥打牌回來對我說他和華菱香睡覺了。
我說:“不會吧,你吹的。”
他說:“華菱香和我們打牌,她在桌底下,先用鞋底碰我,我讓開了,后來她又脫了鞋子,光著腳踩我腳面。打了牌之后,我就到她家去了。”
我問:“你給她錢了?”
他說:“我沒給,她也沒要,就說要和我好。”
第二天早上,他問我想不想買些書,他可以從南京給我帶。我說暫時不想,手頭還有書看。
晚上我賣了皮貨,經過一個報刊亭,買了兩本雜志帶了回去。吃了晚飯,我給了他一本。
“陳哥,你看看,不錯的。”他說:“我要練字,你自己看吧,我過會再看。”
我回自己房間看書了,他卻又突然闖進來,把書扔到我床上,說:“我給你買書,你不要,你的書我也不看!”
“我知道你為什么不讓我給你買書,因為我是小偷!”他大聲叫喊著,“你瞧不起我,我是小偷!”
我放下書,站起來:“陳哥,你聽我說……”
“我不聽你說。你為什么說華菱香是跟我要了錢才睡覺的,因為我是瘸子!瘸子不配有女人!”
“陳哥……怪我,我不應該隨便說……”
“我不聽,明天我就上外地去了,你做你的生意。”
陳哥走后一個星期才回來。他拉我去飯店吃飯,說估計我在家也舍不得吃好的,要補一補。點了菜后,他問我那幾天有沒有寫出奇怪的句子,我說一句也沒有寫,心情也不好。他說,全怪他朝我亂發火,叫我別計較。
我問他:“這幾天,你上哪兒去了?”
他說:“回了一趟老家,陪老娘了,女兒也天天纏著,可愛極了。”接著,他就把女兒跟他去逛公園、釣魚的事繪聲繪色講了一遍。講完了,又問我:“你想沒想出奇怪的句子?”
我說:“鞋子里的故鄉蹲在路邊/聽著他鄉的歌謠,你覺得這句子怎么樣?”
他讓我再念一遍,問我:“是你剛剛想出來的?”
我說:“你走以后,我也很想家,剛才聽你說了回家的感受,就想出了這個句子。”
“奇怪奇怪,故鄉是穿在鞋子里的,想想還真是這個味道,可是只有你想得出。”他說。
“你快把它記下來。”
下雨的時候,我們都不出去。陳哥會做幾樣菜,他一個人在廚房忙著,不讓我幫手,說我做這些事做不好,理個韭菜也理不干凈。
我就坐在客廳,看門前的杏樹、櫻桃和芭蕉,看雨水在樹干上無聲地流淌。門前還有一個池塘,平時是一汪黑水,河邊遍布垃圾,但是雨水濺起的水花是白色的,幾只鴨子安靜地游動著,竟然也有一絲情趣。
吃了飯,陳哥去練字,我則要睡一會兒。醒來時,再坐到客廳,看著雨中的一切。看著看著,我流下淚水。
陳哥從房間出來,見到我流淚,就重新回去練字,隨后去準備下一餐飯。
天漸漸黑了,他也坐到客廳,看著門外的景色。
他問我為什么不讓他和別人說我會寫詩。我說,我也不知道這是什么樣心理,我高中畢業后,在家寫詩就常常受到父母責罵,說我不務正業。我還給他講了這樣一件事:我晚上愛散步,村里人是沒有散步的習慣的,覺得我很怪,他們的東西丟了竟然懷疑是我偷的,甚至還有人說我會偷看女人洗澡。有一次,派出所半夜來把我抓去,說有人報案,賊從他家窗子翻進去偷走了一筆錢,懷疑是我。
“村里人不知道你會寫奇怪的句子?”他問我。
“有一些人知道,不過他們認為這個沒用,認為我是怪人。”
他嘆了口氣,又笑起來:“你也會恨我吧,我讓一個詩人去收皮貨,和屠宰戶打交道,這有些不可思議啊。”
我說:“收皮貨有什么不好,比在鐵路上掙錢多多了,還有時間看書。再說,我哪稱得上詩人……”
他問我:“想到什么奇怪的句子沒有?”
我說:“雨水中的芭蕉/等著宋朝的黃昏。”
他跟著我念:“雨水中的芭蕉/等著宋朝的黃昏。”然后自言自語:“宋朝的黃昏,奇怪,奇怪的句子,宋朝的黃昏是什么樣子……”
閑下來時,我會把寫的詩投稿。我把通訊地址設在老秋的小賣鋪,來了樣報,總是陳哥先拿到。他沒事就去老秋那兒問,老秋不煩他,因為他經常從老秋那兒買些日用雜品。他拿了信件,就到處拿給別人看,說小王真的會寫詩,我不騙你們。
我叫他不要拿給別人看,他怎么也不聽。
我們相處了三年多,因為一件意外的事,他離開了棲霞街。
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來,臉上帶著傷。他告訴我派出所一個警察的老婆在街上被人偷去了6000塊錢,這個警察就帶人把他從牌桌上抓走了,狠狠打了一頓,叫他招。他說自己從不在棲霞街偷東西,怎么打都不承認。警察沒辦法,對他說,先放你回去,三天之內拿出6000塊錢交到我手上,不然就將你另一條腿也廢了,趕出棲霞街。
他讓我立即搬家,還說已經給我找好了房子,他怕自己走后,那個警察遷怒于我。
我當晚就搬了家,他也收拾了包裹。
他問我:“你寫了那么多奇怪的句子,能不能為我寫一句?”
我說:“會的,不過還沒想出來。”
他說:“我暫時不會走遠,三天以后我再來。”
第二天,警察到我們原來住的地方來搜查,陳哥早不見了。聽別人說,那個打他的警察家里遭到了報復,小偷不知道是如何潛入房間的,把存折和一塊手表偷走了,走時還將門上的鎖孔都被噴上了膠水。
第四天凌晨,陳哥來找我了。我開了門,只見他像一幅剪紙一樣站在黑暗里。我又高興又緊張。他說這幾天他住在麒麟鎮,馬上要到上海去,問我為他寫了奇怪的句子沒有,我說這幾天提心吊膽的,什么也沒有寫出來。
天蒙蒙亮了,他讓我用自行車送他去棲霞火車站。
到了車站,他說:“小王,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問他什么事,他笑著說:“華菱香和我沒有感情,每次睡覺都要我120塊錢。”
他又說:“其實,我沒有母親,她比父親死得還早,我也沒有女兒,我想抱養一個,可人家都嫌我是瘸子,怕孩子跟了我受罪。”
我更加難過了,覺得他的身子突然間變得非常單薄。
他又說:“其實,我從來不懂你的詩,也不懂那些奇怪的句子,只是覺得喜歡,喜歡……”
我的眼睛濕潤了,一句話從大腦中閃出,我說:“在困難的火焰上,你抱著明亮的黑暗。”
他驚喜地問我:“這是不是你為我寫的奇怪的句子?”
我點點頭。
“在困難的火焰上,你抱著明亮的黑暗。”他一個字一個字念著,然后說:“我終于等到你為我寫的句子了。不過,你也是這樣的吧?”
我點點頭,我發覺他是懂得這句子的含義的。
這時候,腳下顫動起來,火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