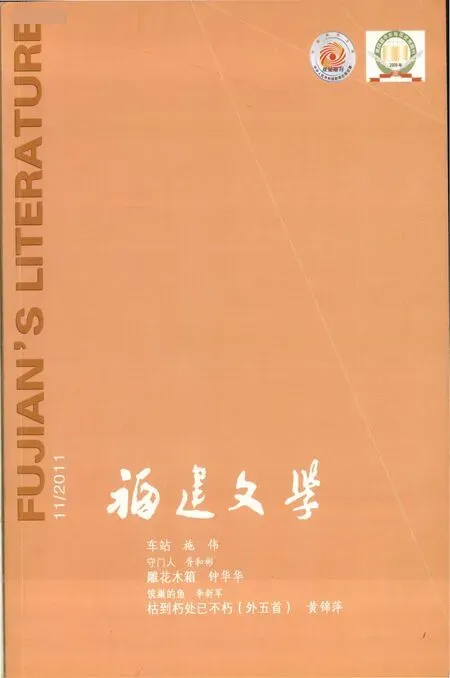他讓后工業時代變得柔軟——讀哈雷詩集《零點過后》
戴冠青

當我們在后工業時代的水泥叢林中左沖右突,感覺靈魂越來越累,心兒越來越老,可是,能安頓靈魂的詩意家園似乎越來越遠,能撫平心靈皺紋的自然之風也總是遙不可及時,我讀到了哈雷的詩。
哈雷的詩里有嘶鳴的蟋蟀,有低唱的秋水;有麻雀的眼神,有老杉的年輪;有“一夜塘前月色/舞動清秋”(《秋天的樹》),有“柔軟的草葉豐茂的雨季豐饒寧靜的土地”(《苔樹》);有“像手指”“像風”“像音樂般撫摸我的心”的“那樹條上的茸芽”(《故園春來》),有“高高的巖壁上”,像“長長的、像清潔的飄帶/就這么長年掛在你的胸前/有限地舞動 那曼妙的音階/潺潺垂落在無限歲月中”的瀑布(《瀑布》);還有“以愛的無畏,投向你”的愛情島(《愛情島》)和“站在土屋前等著她的心上人”的“很老的乳娘”(《村莊》)……
這些美麗而又憂傷的意象,喚起了我們久遠的記憶。它們曾經是那么真實,那么親近,在我們赤著腳四處追逐嬉戲的童年的田野,在我們無數次從潛意識里浮現出來的迷人的夢境,在我們背著行囊風塵仆仆地徜徉在遠山遠水的風景。但在后工業時代的浮躁和焦慮中,許多人已經淡忘了,視而不見了,或者顧不上了。這讓我們惆悵和無奈。但是今天,哈雷的詩讓我們驚喜。他悄悄地拾掇著這些美好的意象,把它們珍藏在《零點過后》的詩匣中,讓每一個讀者一打開就會感受到一陣撲面而來的清新的風,領略到一個動人的唯美的意境,如《秋天的樹》:
“行走在秋天里的兩條道路/都通往荷塘,而坡上/一株翠綠的樹/在另一個時間意象出現之前/開始懷舊//喘息是從內部開始的/秋水之上,風把樹葉握得更緊/而殘荷還在江南掙扎著/松軟的身軀/垂落了最初的誓言//有些聲音將季節撕開一條裂痕/要讓黃葉將它覆蓋/就像睡夢想要覆蓋記憶/我和你來到山道上,觸摸落霞的體溫/秋心變得感動//你依在邊上的影子更加清晰/草色彌漫的臉上/傳遞著一瞬濃似一瞬的秋意/酒過千觴,回望眼,一夜塘前月色/舞動清秋”
一棵懷舊的樹,一株柔軟的殘荷,一塘淡淡的月色,一瞬濃濃的秋意,就這樣把我們那顆被世俗和功利煎熬得快要硬化的心浸潤得酥酥的軟軟的,變得感性、純真和懷舊。
不僅如此,哈雷的詩更以一種憂傷的悲憫抒寫,帶給我們一份久違的感動。他為被草遮埋的小路而悲哀:“這條小路被草遮埋了/像睡在荒野上的細小的孩子/無法躲開來自山口的風,還有雨水/沖襲著他悲哀的記憶/更為悲哀的是,一整個冬天里/沒有落葉和飛雪的記憶/沒有凜冽的冰凌的記憶”(《從冬天的小路回來》)他為受傷的老杉而悲憤:“它碰撞到了狂野的天風/卻把根扎得更緊/它讓烏鴉在枝頭經營 攀援的花/恣意纏繞著開放/稀疏的葉片拍打著云朵/時空遠隔的心映照星辰/因為它讓所有的斧手顫栗/還因為它是老杉 依然/長出新生的綠芽”(《老杉》)他為果實的掉落而牽掛:“當風帶來了秋聲/鴿子成群飛去,我的世界充滿了別離的苦戀/生命如果可以這樣送達/我愿意把自己風干,然后從枝頭/跌落在地”(《悲情英雄》)在哈雷的世界中,不管是小路,還是老杉;不管是樹的果實,還是輪回的季節,都是一種生命的形式,都有一份悲憫的情懷。于是,生命的殘缺,生命的受傷,生命的失落,在他的審美觀照中,便染上了一種獨特的憂傷,這份憂傷讓我們讀出了一種呵護生命的渴求和希冀,讓我們心疼,更讓我們感動。
更耐人咀嚼的是,哈雷的憂傷還蘊藉著一種反思的力量和批判的精神。在這些美麗的詩句中,我們讀到了情感的力度和審美的深度。最喜歡那首《村莊》:“七步,和曹植的詩一起/走進我的童年的村莊/一座石磨壓成的村莊/扁扁的村莊 福州往東兩百公里/有廊橋跨過河面/木杵敲在青石板上/水車在不遠處轉動……”在這首詩中,哈雷深情的抒寫先是把我們帶進了他的村莊,跨過河面的廊橋,敲在青石板上的木杵,在不遠處轉動的水車,裊裊飄蕩的炊煙,馱著柴禾的農夫,站在土屋前等著心上人的乳娘,無一不美得讓人心疼。然而,當這個美麗的村莊被開發成了景區,當成千上萬的觀光客涌進景區戲耍照相時,那純粹的原生態的美麗卻再也不見了。這種對審美錯位的揭示,對純樸美的呼喚,對原生態被破壞的譴責,在哈雷這些動人的詩句中被表現得蘊藉而感傷,字里行間涌動的人文力量讓我們回味再三反復咀嚼。
哈雷是一個資深詩人,上大學時就開始寫詩。那時他很年輕,渾身洋溢著激情,情懷里涌動著浪漫,詩中更是充滿了理想和追求。后來他去編刊物和報紙,曾經有一度停止了歌唱,直到三年前他又開始寫詩。他自己曾說:“我的詩歌創作一度斷層:2007年5月我在鼓嶺腳下一片飛流直落的瀑布面前重新找回了靈感,14年來未曾寫詩,突然這一天內心有了沖動的渴求。我至今依然可以感到那個瞬間帶給我奇妙的感覺,是真正詩歌意義上的一次神性的交匯,這種瞬間觸動,就像米沃什說的那樣:給我一個莎士比亞的瞬間,是神來之筆。”(《哈雷論詩》)是的,十四年的蟄伏,帶來的是一次非凡的超越。在這本《零點過后》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他詩藝的精進,“和過去不同的是,我開始敘事,開始用名詞和動詞寫作。一方面想讓詩歌變得含混,在意義的層面上游移不定,而另一方面又被那些難以捉摸和不斷自我構造的東西所誘惑;一方面對清晰、柔美、簡潔、有力的語句充滿了渴望,另一方面更加迷戀那種跳躍的、通透的語言,并能為此獲得欣喜若狂”,更看到了他在審美上的自覺。他已經不再僅僅迷戀于浪漫的傾訴和理想的傳達。他開始更理性地審視我們當下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更深入地思考生命的存在方式,從而更獨特地傳達他的審美發現和情感把握。
于是,在這個堅硬的后工業時代,哈雷力圖用自己獨特的詩意傳達把它變得柔軟。他曾在《柔柔的……》的這首詩中寫道:
我第一次聽到浪的聲音/在你的懷里呢喃著/海上的帆船遠去了如飄向天際的紙鳶/沙灘延伸出的臂膀/像金色的夢裹著我/感動的心/柔柔的……//秋陽中傳來你的聲音/愛語纏繞在綠樹花影之中/音樂灑落的小徑上,十月的歌/穿過了島嶼,奏響了龐大的鋼琴/青藤和老樹都仰起飛花的笑臉/吟詠的心/柔柔的……//我的步履在傾斜的坡道上慢了下來/那許多現實和不現實的想法/全都放下了,只想著一個人,一叢三角梅/一只相隔不遠的小船/然后全都把這些裝進今夜的詩句里/思念的心/柔柔的……
就在詩人“柔柔的”的吟詠中,我們的心開始變得柔軟,變得溫情,變得善解人意。于是我們明白了,在這個硬朗的世界里,我們不僅要懂得奔跑,還要懂得減速;不僅要懂得開發,還要懂得守望;不僅要懂得別離,還要懂得思念;不僅要懂得“許多現實和不現實的想法”,還要懂得“一個人,一叢三角梅/一只相隔不遠的小船”。
就這樣,哈雷用自己獨特的審美認知和動人的詩意傳達,讓這個世界的一切生命從此變得柔軟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