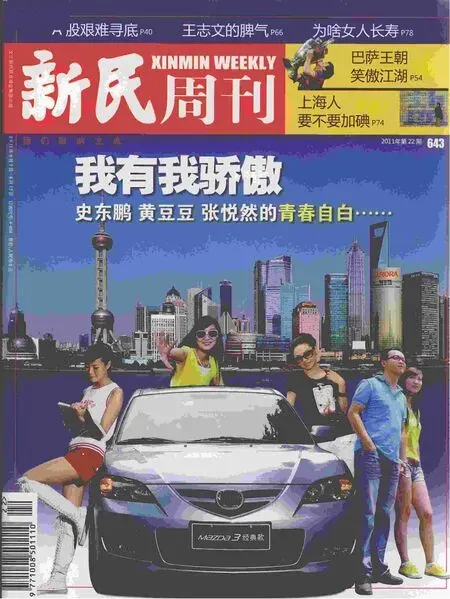暴力執法必須改變
王琳
2011年5月,輿論焦點再次透過個案集中到城管執法體制。上一次是崔英杰案,這一次是夏俊峰案。在近年來的重大網絡輿情事件中,多數都是從個案發端,由“鏡中我”情緒激發公民圍觀,最后落到體制病灶。該慶幸的是,孫志剛事件終結了收容遣送制度,趙作海冤案催生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體制的完善乃至革新,很多時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我們也看到,“躲貓貓”及之后數十起看守所在押人員非正常死亡事件,并未促進看守所與偵查機關的分離;崔英杰案及前后無法計數的“小販大戰城管”事件,同樣未促進城管執法體制的深層改變。
作為遵循“不告不理”原則的法院,它的審判對象只能是檢察機關指控的“夏俊峰涉嫌故意殺人案”。依現行法律,夏俊峰有免予死刑的空間。從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材料來看,得到共識的事實是:城管街頭執法時曾與夏發生沖突,在城管辦公室內雙方有爭吵,夏在城管辦公室內有刺殺行為并造成后果。在此基礎上,法官對爭議事實多處“選擇性失明”,才有了“依法判處死刑”的裁斷。例如,辯方提供了6名證人證言,證明城管執法人員在街頭執法中毆打了夏俊峰。但無論是一審還是二審,6名證人均未被獲準出庭。主審法官苗某的解釋是,庭審中,這些材料均進行了宣讀;6名證人證言和當事人夏俊峰口供矛盾,所以未予采信。夏的上述口供是有利于控方的,這時,法院選擇采信。而夏俊峰還稱,在城管辦公室他“被毆打后,亂劃傷刺中的被害人”。很明顯,這份口供是有利于被告的,此時法院卻不采信。主審法官解釋稱:“夏俊峰與兩個城管在辦公室里究竟發生了什么,沒有充分的證據和證人來證明。”
重證據不輕信口供,是刑訴法上明文規定的證據規則之一;死刑案件應排除一切合理懷疑,也為最高司法機關所反復強調。如果夏俊峰在城管辦公室內未被侵害,他身上的傷從何而來?夏俊峰明顯較3名被害人矮小,又為何要在城管的地盤、對多名執法人員主動展開攻擊?
執法沖突引發的這場殺人慘案,被害人不該死,被告亦不該死,該死的其實是城管暴力執法機制。于社會轉型期出現的城市管理亂象背后,有著復雜的社會根源。行政相對人與城管之間的暴力相向,已經很難去考證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但從依法行政的視角來觀察,城管暴力執法經不起合法性考量。各地城管局的設立,源于行政執罰的日益成“難”以及“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管理理念。行政機關本無城管局,所有行政執法部門實則都是城市管理部門。在“帕金森定律”這一“官場病”的影響之下,各行政執法部門紛紛選擇了趨利避害,在保留了許可、審批等文案工作的同時,將大量繁瑣而艱苦的外勤及難以執罰的處罰權甩手扔給了城管部門集中行使。其結果,城管局只罰不管,原相應的管理部門又因為“執罰權”的讓渡也疏于管理,使得城市管理在“管”字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真空。站在執法前線的城管人員因此成了矛盾的焦點,進而成為許多市民深惡痛絕的對象。
城管局“執罰權”的來源也大可質疑。在國家層面,迄今仍無一部規范城管的法律出臺。依《行政處罰法》第十六條雖明確,“國務院或者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國務院本身并沒有決定城管執法權,國務院也沒有授權任何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決定由城管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這種由地方政府或地方人大超越立法權限,對行政執法罰私相授予的做法實則與“法治”相去甚遠。
有銳意改革者曾想以“媽媽城管”、“碩士城管”、“溫柔執法”等舉措,來糾正城管的“妖魔化形象”。這些城管新政的共同命運,均擺脫不了熱熱鬧鬧開場、冷冷清清落幕的結局。因為城管之所以存在,正在于原有的職能部門(衛生、城建等)不暴力。暴力執法實是城管的宿命。如果城管執法人員也不愿暴力執法了,城管部門一定會再聘請一批城管執法協勤人員,來實施暴力。可嘆的是,這一現象正在發生。
當暴力與執法聯姻,且將目標定格在為維護其生存權而抗爭的小攤販身上時,暴力抗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城管暴力執法模式不根本改變,崔英杰案之后有夏俊峰,夏俊峰案之后還會新的“崔英杰”和“夏俊峰”。終結這一流血沖突,并不在對夏俊峰的死刑判決,而在對暴力執法的死刑判決。(作者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