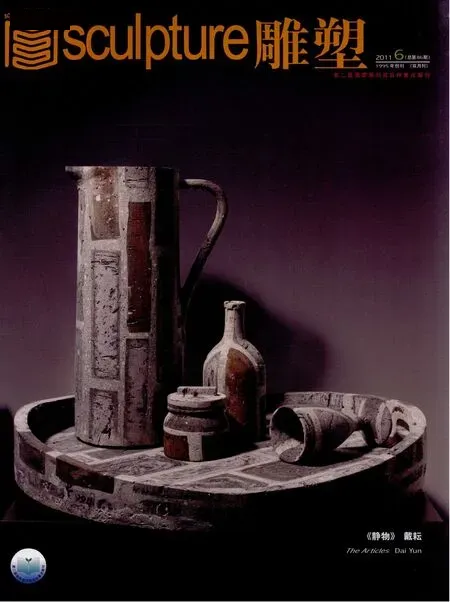穿越時空,穿越記憶——雅尼斯·庫奈里斯訪談
■ 黃篤 翻譯:郝志蓉 by Huang Du,t ranslater:Michel le Coudray
黃篤:庫奈里斯先生,據我所知,您早年在希臘渡過,曾親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希臘內戰,這兩場戰爭進行了大約10年之久。您大約于1956年移居羅馬,進入美術學院學習。但我想了解,您從希臘去羅馬的原因是什么?
雅尼斯·庫奈里斯:當一個人18歲的時候選擇是很單純的。坐上火車,就去了意大利。這不是很麻煩。但我在意大利遇到了一些藝術家,我們一起努力創造了一種帶有批判性的藝術語言,這才是重要之處。
實際上,我一直在歐洲藝術圈內。而早年意大利的經歷開始使我形成了自己的藝術觀,這至今對我仍至關重要。是的,我出生于希臘,并親歷過戰爭,所有這些經歷對我的人生來說都是重要的。但是,我在意大利找到了一種邏輯和一種語言。而作為藝術家,我又認為自己誕生在意大利。所以,我覺得意大利比希臘對我而言更親近。


黃篤:1960年,您在羅馬的Tartaruga畫廊展出的作品《無題》。作品由“數字”“字母”“箭頭”和其它符號組成。它們背后的觀念是什么?
雅尼斯·庫奈里斯: 1960年,我有幸在Tarta ruga畫廊舉辦了首次展覽。我當時非常年輕,還是美術學院的一名學生。重要的是,這些對我來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繪畫,有我的房子墻壁那么大的尺寸。我把一張張紙貼到墻上,從一面墻貼到下一面墻,墻與墻之間不留縫隙。由此,尺寸已與空間銜接起來,因為它們的大小取決于空間。
于是就有了一種節奏的嘗試,這些紙張就像音樂中的音符。實際上,我的確在吟誦它們。意大利曾產生了一位舉足輕重的詩人朱塞佩·翁嘉雷蒂,他的富于節奏感和隱逸感的詩影響了我。他的詩歌散發著古羅馬赫爾墨斯主義。(赫爾墨斯主義或西方的赫爾墨斯傳統是一套基于希臘化的埃及偽經作品的哲學和宗教信仰。這些作品據說是赫爾墨斯· 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秘密教義,他是埃及智慧之神圖特和希臘赫爾墨斯融合的化身。西方神秘宗教傳統深受這些信仰的影響。這些信仰在文藝復興時期亦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可以說,我的早期作品創作于1959年和1963年間。1960年,我的作品首次在Tartaruga畫廊展出。從一開始,“空間”就在我的作品中占據了中心位置。
黃篤:在1967年,您似乎開始放棄繪畫,而轉向裝置。在一個叫L’Attico的新畫廊中,您展出了一些裝置作品,它們包含了三種要素:涂有清漆的鐵板結構夾控著棉花、四個鐵制容器盛有土和仙人掌、涂有清漆的鐵板上的棲木伴有活的鸚鵡。什么原因使您從二維創作轉向三維裝置作品,甚至包括作品中對動物的使用?
雅尼斯·庫奈里斯: 這些早期作品已經產生了空間問題或對空間的憂慮。我從未認為這些作品是繪畫,也就更談不上從二維轉向三維。從一開始,我就沒有企圖做畫。它們不是“畫”上的,而是“貼”在表面上的。所以,對我來說,數字、字母與鸚鵡等的作品之間沒有什么明顯的界限。看數字、字母作品的人“解讀”作品。然后,第二步是面對于鸚鵡的作品,觀眾不再解讀了,而是鸚鵡對這位觀眾說話。因此,在我看來,鸚鵡更像是作品的一種延伸,而不是作品方向的改變。
這些作品的確是在當時那樣一個重要的政治時刻問世了。材料通過自身的重量得到呈現也在觀念中體現了出來。例如,所謂的“煤”,煤確有其重量,因為重量是作品存在的條件。同樣,它還表明了一種流動性,即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如此以來,我們開始一邊旅行,一邊創作。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創作作品”。這也是“這類作品自由”的組成部分。因此,它不僅僅局限于工作室的創作,更多的是與場合、關系、聯系和諸如此類的事相關聯。

黃篤:1969年,您在那不勒斯的盧西奧·阿梅里奧(Lucio Amelio)畫廊展出了一件多媒體裝置作品,其上下垂掛的8個金屬天平上盛有咖啡粉。這件作品的核心觀念是什么?您所用的媒介與情況、語境或經濟狀況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雅尼斯·庫奈里斯: 顯然,當時并不存在經濟方面的問題。重要的一點是它與藝術家的作用有更多的關聯。我們正在尋求更多自由,例如,我將小的固體乙醇片放在一塊鐵板貨架上,一旦點燃生命很短暫,僅僅3分鐘就消失了。這件作品在那不勒斯舉辦的一個展覽中展出。所以,這些作品既不僅僅是幻覺,亦非烏托邦,而是蘊涵著意識。尤為重要的是,我們主要的問題是創造一個更強大的藝術家形象,這已經是政治了。藝術家是作品的核心。

黃篤:那么,您的意思是想在材料中找到能量及其轉化的過程嗎?
雅尼斯·庫奈里斯: 許多是關于能量的。當時就有這樣巨大的能量。藝術家擁有能量,他們一直在發現和體驗。我并不喜歡用“正在體驗”這個詞,我其實是一個很保守的人,根本不是一個有實驗性的人。我的作品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東西,而不是一個實驗品。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黃篤:現在,我有一個頗為迷惑的問題。1969年以前,您的一些作品中已使用了動物。而在1969年,當您將12匹馬拉進羅馬的L’Attico畫廊時,并非毫無緣由,而是遵循著自己的藝術邏輯。然而,眾所周知,在20世紀60年代末,意大利精神病學家弗蘭科·巴薩格利亞提出了“民主的精神病療法”的思想,并在都靈的戈里齊亞建了一家精神病院。當時的想法是要打破醫院界限。因為這種醫院在功能上一直是把精神錯亂的人規定、限制和禁錮在某一固定空間。巴薩格利亞的思想就在于要解放或開放醫院,以建立患者與人、社群乃至社會的交往。
顯然,您的這件作品像杜尚的作品一樣具有顛覆性。因此,我想知道,您于1969年展出的12匹馬的作品是否與“打破醫院界限”的思想有關聯。倘若與其思想無關,那么,該作品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呢?
雅尼斯·庫奈里斯: 對我來說,重要的不只是將12匹馬牽入畫廊,而是將它們拴在畫廊四壁,并界定了眼睛平視高度的空間周長。也就是在1969年,我還在巴黎一家畫廊創作了一件類似的作品,是一個環繞畫廊墻壁燃燒煤氣的裝置(注:用金屬管以吊鉤的方法懸掛著噴射的火焰,地上放著煤氣罐)。所以,畫廊空間被以戲劇藝術(d ramm atu rgia)的要素所利用和發揮,如此這般獨特效果和姿態,從卡拉瓦喬直到現在, 像意大利許多藝術大師那樣,“戲劇性”在作品中至關重要。


黃篤:那么,您的意思是這一作品與傳統意大利作品有關,是嗎?
雅尼斯·庫奈里斯: 可以說,戲劇性一直是這類意大利傳統的條件,像畢加索的繪畫《格爾尼卡》也遵循了這一傳統。
黃篤:我要回到您于1973年創作的有火的作品。“貧窮藝術”強調即興事件、偶發事件和不可預知的理念。這些理念是否受 “游牧”思想影響?在您之前,有像路西奧·馮塔納、皮耶羅·曼佐尼和阿爾伯托·布里這樣的藝術家,比如:布里也在其作品中用火。您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與這些藝術家有關嗎?
雅尼斯·庫奈里斯: 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基于元素間的某種辯證關系,如:火與鐵(就是這種辯證關系)。因此,這種矛盾或爭斗存在于感受力(火)和結構(鐵)之間。而在煤、金屬、鸚鵡等作品亦可看到感受力和結構之間的類似關系。因此,材料之間也有這種的對話。只有如此,感受力才會變得更強大。作品不是“被再現”,而是要“被呈現”。所以,它是一種姿態,速度也非常快。重要的是不要再現,而要一種直接的姿態。此外,馬就有類似的直接影響。
現在,回到您剛提的第二個問題。是的,馮塔納、布里、翁貝托·波丘尼,我們是同屬一個家族血脈。但不僅僅是他們,還有像杰克遜·波洛克、烏姆博托·波丘尼和許多其他的藝術家都在我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關于游牧,上世紀80年代羅馬曾有過一場大爭論。我從沒有把自己視為游牧者。在我看來,詩人蘭波也不是游牧者。然而,如果我不是游牧者,那我的確是一個旅行者。我去過很多地方。在我的靈魂深處,我是一個游客。我希望自己是一個能與人溝通的,思辨之人。例如,如果我來中國,我想把某些東西帶到中國,也能從中國帶走某些東西。我是那類浪漫之人。

黃篤:從某種意義上說,您是烏托邦式的藝術家。
雅尼斯·庫奈里斯: 當然,藝術家不得不烏托邦式。
黃篤:剛才您提到您的作品和傳統藝術之間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看,“貧窮藝術”的藝術家不同于未來主義的藝術家。例如,米開朗基羅·皮斯特雷多和您本人的作品都非常尊重歷史和傳統價值,而未來主義的藝術家對傳統則頗多微詞。您在1984年曾寫過一篇文章,文中寫道“沒有歷史感,便很難作畫。”您如何看待歷史意識和現代觀念之間的關系?
雅尼斯·庫奈里斯: 在我看來,波丘尼的《行走的人》(1913年,銅雕,《空間中連續性的獨特形式》)讓人聯想到希臘雕塑《勝利女神》(Nikedi Samotracia)。未來主義的藝術家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運動有密切關系,他們是介入者(in terven tisti)。他們頌揚現代,憎惡傳統。這就是未來主義。(未來主義是一場藝術和社會的運動,20世紀初起源于意大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意大利現象。不過,類似的運動也同時在俄國、英國和其它國家發生。未來主義者運用任何藝術媒介進行實踐,涉及繪畫、雕塑、陶瓷、平面設計、工業設計、室內設計、戲劇、電影、服裝、紡織、文學、音樂、建筑甚至美食)。
我是屬于接近二戰結束的一代,也是帶有戰后問題的最后一批藝術家。未來主義的藝術家創作深陷一種“頌揚戰爭”之情。之后,未來主義和“貧窮藝術”的藝術家一起目睹了戰爭的終結,我們出現了如羅伯托·羅西里尼和維托里奧·德·西卡的電影,他們的電影恢復了戲劇,同時也恢復了傳統,使意大利人回想起了苦難。很顯然,曼佐尼創作的《大便:意大利制造》表明,他并不是一個未來主義者。

黃篤:這個時期意大利產生了新現實主義電影運動,包括德·西卡、羅西里尼、安東尼奧尼和費里尼。我的問題是,如果新現實主義電影和“貧窮藝術”的確存在關聯,那它們之間是什么關聯呢?
雅尼斯·庫奈里斯: 羅西里尼和德·西卡等是那個時期的大知識分子。他們積極應對意大利人的戰后問題及其損失。他們在社會和文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是我們的大師。
我相信,關于“貧窮藝術”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建構并找到了呈現我們作品的方法,這種語言的命運就是向世界開放,決不能局限于意大利本土。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貧窮藝術”是歐洲人提出來的,用于辯證地對抗美國人提出的“極簡主義”和“波普藝術”。1969年,哈羅德·史澤曼策劃了一個重要展覽《當態度變為形式》,匯集了來自美國和歐洲的藝術家。從此以后,雙方開始了一場大對抗。上個世紀70年代,亦有其他許多展覽發生,將美國和歐洲藝術家匯集一堂,包括德國的博伊斯和一群嚴肅的意大利藝術家,他們現在仍在努力創作。所以,這個目標,也是我們冒險的出發點,與我們所談論的(包括戰爭、新現實主義、布里、馮塔納等)都有關。
黃篤:另一個問題是切蘭(Celant)先生在1967年寫的《貧窮藝術》一書中提到了意大利藝術家馬里奧·梅茲、您、鮑里尼和皮諾內,還包括德國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荷蘭藝術家迪貝茨以及美國極簡主義藝術家卡爾·安德烈和理查德·塞拉。他把這些藝術家都納入“貧窮藝術”的范疇。您對他的觀點有何看法?
雅尼斯·庫奈里斯: 很難將這些藝術家放在一起。例如,卡爾·安德烈是一位令我敬佩的藝術家,但他絕然不同。他教條,而我們卻不。而藝術家理查德·朗的觀念更接近于“貧窮藝術”,因為他具有同樣的流動性。
黃篤:切蘭在一篇文章中把“貧窮藝術”的藝術家形容成游擊隊員。一個特別的問題是關于馬里奧·梅茲于1968年創作的《靜坐》和1969年創作的《干什么?》。這些作品與當時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如1968年法國五月暴亂)有關嗎?
雅尼斯·庫奈里斯: 我不能替馬里奧·梅茲回答有關問題,但我認為曼佐尼的《大便:意大利制造》確與政治有關。我還認為俄羅斯藝術家馬列維奇的繪畫也與政治有關,因為他的黑色方塊的確是與民粹主義的對立。
今天對我而言,我喜歡德拉克洛瓦的繪畫《摩洛哥的猶太婚禮》(1839)。我喜歡這位來自法國巴黎的藝術家的想法。他去了阿爾及利亞,受邀請到一所房子里,那里正舉辦這個猶太人的婚禮,于是,他創作了這幅畫。我覺得這幅畫畫得很美。德拉克洛瓦畫這幅畫時,這種自由是一種很新的事物。對我來說,今天仍然很新,因為仍有同樣的旅游精神,充滿著文化的匯集與交流。
黃篤:1992年,您在德國的施瓦本格明德(Schwabisch Gmund)創作了大型裝置,豎起一個36米高的T字形木架裝置,從上端垂吊下一個巨大的裝有老家具的麻袋。這件作品的觀念是什么?
雅尼斯·庫奈里斯: (以天主教堂為背景)這件作品的尺寸與教堂成比例,在教堂的前面安放著那件雕塑作品,如此的安放將這件作品與教堂并置于同樣重要的位置。說到觀念,這是一個沉重的觀念。它來自于文藝復興早期藝術家多那泰羅的雕塑《圣·喬瓦尼的頭》,左手托著、展示著頭,一個非常明確的舉動告知 “我做的事,我負責!”要不是在德國,我絕不會創作這件作品。
我非常喜歡德國,我在德國(杜塞爾多夫美術學院)教過8年書。德國對我一直都很重要,也許甚至比意大利還重要。
黃篤:我們談一談1989年在巴黎的《大地魔術師》展覽吧。您對該展覽的見解很有趣,因為您的觀點與我之前的理解完全不同。在您看來,這個展覽的意義或真正價值到底是什么?
雅尼斯·庫奈里斯: 康斯坦丁·布朗庫西住在慕尼黑。他決定離開慕尼黑去巴黎,后來他留在了巴黎。我很贊同藝術家決定自己的命運,而非由別人決定。這恰恰是我提到畢加索的作品《阿維農的少女》時想要表達的意思,因為由此可看出藝術家革命性態度的端倪。

黃篤:這是您第一次來到中國。您已去過很多地方,像云南、北京、上海。您對中國的印象怎么樣?
雅尼斯·庫奈里斯: 我所看到的都很美。人們都很有禮貌,很樂觀。中國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國家。
黃篤:我知道您此次中國之行是準備一個項目。能否告知一二?
雅尼斯·庫奈里斯: 我的第一個項目就是看中國,它迄今為止是如此奇妙。不管怎樣說,我正在中國創作一系列作品,希望能在中國展出這些作品。
黃篤:這些作品是按部就班地創作還是為某一特殊場景而創作呢?
雅尼斯·庫奈里斯: 兼而有之。例如,一些作品是在北京的一家工廠里創作,運輸工作已準備就緒。接下來,我正在著手根據空間的情況創作一些作品。
黃篤:那么,我們衷心祝您在中國的藝術項目大獲成功。由于采訪時間較長,感謝您的耐心和慷慨。
雅尼斯·庫奈里斯: 不用客氣。我將很快回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