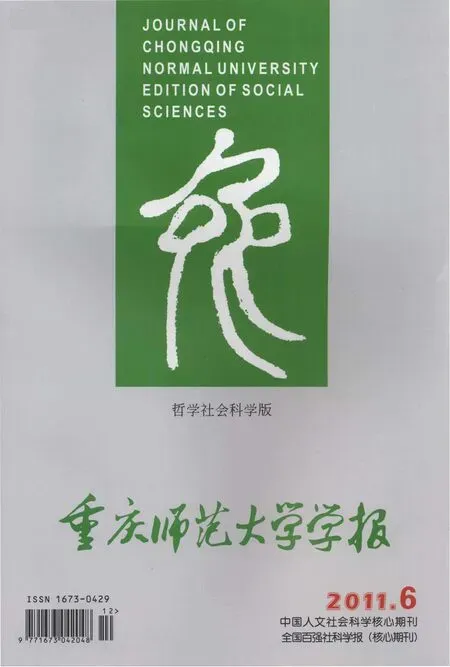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對“啯嚕”的嚴厲鎮壓與社會恐慌
龔義龍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 400015)
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對“啯嚕”的嚴厲鎮壓與社會恐慌
龔義龍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 400015)
乾隆中后期,四川及其周邊地區“啯嚕”活動頻繁,已經嚴重地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清政府下決心鏟除“啯嚕”這一黑社會組織。但是,清政府面對著這一困境:將真正的“啯嚕”與被懷疑為“啯嚕”者、被裹脅入“啯嚕”者區別開來,以打擊真正的“啯嚕”,而不致造成大的社會恐慌。而事實上,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幾乎是辦不到的。“啯嚕”鎮壓活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會恐慌,后果很嚴重。
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啯嚕”;嚴厲鎮壓;社會恐慌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對清代巴蜀“啯嚕”及相關問題已經作了比較廣泛的研究。拙文將既有學術探討概括為哥老會與“啯嚕”的淵源、“啯嚕”的起源與發展、“啯嚕”的性質與基本群眾等幾個方面。在既有研究基礎上,本人曾對“啯嚕”的基本群眾、“啯嚕”的日常活動、“啯嚕”產生的社會根源作過一些學術探討。[1]隨著對《清代巴縣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三省邊防備覽》深入研究,本人對清代巴蜀“啯嚕”的認識進一步加深,擬在此對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對“啯嚕”嚴厲鎮壓及其帶來的社會恐慌進行分析。
“啯嚕”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社會邊緣群體”,因此,在“社會邊緣群體”(包括竊賊、乞丐、川江水手等)數量龐大的清代巴蜀,要想鏟除作為黑社會組織性質的“啯嚕”,勢必會牽涉到被懷疑為“啯嚕”者、被裹挾入“啯嚕”者,進而造成較大的社會恐慌。
在清代巴蜀“啯嚕”這一社會群體中,真正的“啯嚕”無疑具有黑社會性質。不管是從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從而對清朝統治構成間接的威脅,還是其活動的直接目的就是顛覆大清政權,依據《大清律例》,這部分“啯嚕”都該遭到鎮壓。但是,被官府認為具有“啯嚕”嫌疑的,還有誘賭、哄騙的川江水手,形跡可疑、行色匆匆的過路人,乃至小偷小摸的乞丐。而成群結伙的“啯嚕”中,還裹脅有乞丐、水手及其他失業者,這就使得“啯嚕”這個社會群體的成份變得十分復雜。
然而,“啯嚕”這一“社會邊緣群體”從最初三五成群,發展成為有組織的匪徒,經歷了一個過程。清政府對“啯嚕”的認識,以及對“啯嚕”的政策變化也相應地發生著變化。
一、清政府對“啯嚕”的最初認識
雖然在雍正年間、乾隆初年,“啯嚕”活動已成為危害多省的社會問題,但是,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深居宮闈的乾隆皇帝,以及“啯嚕”活動頻繁地區(包括湖廣、貴州、四川、陜西等省)的封疆大吏,對“啯嚕”的認識仍然表現得懵懂無知。該年7月7日乾隆皇帝發出上諭:“此等匪徒,聚集多人,搶劫拒捕,甚屬可惡,斷不可不盡法處治。著再傳諭各督撫加緊搜捕,并遵照前奉諭旨,將拿獲各犯嚴刑訊問,其因何聚集?所謀何事?”[2]7月14日,湖廣總督舒常奏折也附和著乾隆皇帝的困惑:“‘啯匪’來歷為何?因何聚集?意欲何為?”[3]
當然,這并不是說清廷朝野對“啯嚕”的認識盡皆如此顢頇。事實上,有些人對“啯嚕”還是早有認識的。
乾隆三年(1738),李厚望調任重慶已經接觸“啯嚕”案件。先是,四川有“啯嚕”者,皆流民惡少,強悍嗜斗,動成大獄,而重慶為甚,積案幾當通省之半。厚望至,閱其牘,嘆曰“此皆無知犯法者也”。于是,“核其毆抵者上之,得省釋者數百人”。[4]
乾隆八年(1743)10月,四川巡撫紀山奏稱:“川省數年來,有湖廣、江西、陜西、廣東等省外來無業之人,學習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兇刀,肆行鄉鎮,號曰‘啯嚕子’。”[5]
乾隆九年(1744),御史柴潮生奏稱:“四川一省,人稀地廣,近年以來,四方游民多入川覓食,始則力田就佃,無異土居,后則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強悍者,儼然為流民渠帥,土語號為‘啯嚕’,其下流民聽其指使,凡為‘啯嚕’者,又各聯聲勢,相互應援。”[6]
這就是說,早在乾隆初年,重慶府官員李厚望已處理了大量“啯嚕”案,四川巡撫紀山、御史柴潮生等也先后上奏,指出“啯嚕”的基本來源正是數年來“湖廣、江西、陜西、廣東等省外來無業之人”。這些人又“勾引本省不肖奸棍”。最初,這些人“力田就佃,無異土居”,后來“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學習拳棍,并能符水架刑”,“三五成群,身佩兇刀,肆行鄉鎮”,“桀黠強悍者,儼然為流民渠帥”,而其下流民聽其指使。各股“啯嚕”之間相互聯絡,壯大聲勢。顯然,“啯嚕”的所作所為已經嚴重擾亂了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但此時,官府仍然將“啯嚕”案作為一般案件對待。
二、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加大對“啯嚕”追剿的力度
乾隆中期發生了幾個震驚朝野的事件,乾隆三十六年(1771)山東王倫起義、乾隆三十三年(1768)“叫魂”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蘇四十三”起義。這些使得乾隆皇帝的神經繃得更緊。歷次上諭透露出,乾隆皇帝與封疆大吏們似乎已經開始懷疑“啯嚕”具有顛覆大清政權的性質,因而對“啯嚕”追剿的力度明顯加大。
乾隆四十六年(1781)7月30日,四川提督成德奏折指出,若任“啯嚕”猖獗下去,恐怕會釀成王倫、蘇四十三之禍。成德奏道:“匪徒敢于百十成群到處搶劫拒捕,若不即行擒獲,盡絕根株,即可釀成王倫、蘇四十三之事。竊查川省啯匪多系各處無籍游民,素無恒業,向來不過同伙三五人各處游蕩,或于偏僻鄉村臨時行強搶劫行旅,一有稟報即嚴拿究懲,今竟敢百十成群,到處搶劫拒捕,實屬罪大惡極。”[7]鑒于“啯嚕”活動可能引起較大范圍的社會騷亂,清政府對“啯嚕”采取了嚴厲追剿的措施。
乾隆中后期,各級官府屢次發出嚴查“啯嚕”的“安民告示”。這表明,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啯嚕”這個社會群體已成為中國社會一個嚴重的禍患,令清政府及老百姓大傷腦筋。
乾隆四十二年(1777)4月《重慶府下行各縣牌文》曰:“案奉臬憲檄發查拿啯匪告示,當經本府照樣刊刻板片,檄飭各屬經書赴轅請領印發在案。”[8](105)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頒布《從重懲治川省啯匪專條》,《專條》稱:“四川地廣民稀,山路僻遠,最易藏奸。各處無籍游民,蟻聚烏合,結伙成群,久為商旅地方之大害。是以另立川省啯匪專條,從重懲治。”[8](106)
據此,乾隆四十七年(1782)3月15日,巴縣頒布《嚴懲啯匪新例》。《新例》稱:“照得士農工商,各有恒業,醫卜星相,并可營生。此外,或樵或采,或雇或傭,皆堪自食其力,不致坐困饑寒。即或命之不辰,窮餓而死,當屬清白良民,得以保全首領,何苦喪心易志,竟為啯匪,搶奪傷人,身負大惡之名,死作無頭之鬼。……為此,示仰縣屬居民人等知悉。嗣后咸宜恪遵法紀,各守恒業,寧使饑寒迫身,切不可流入匪類。所有奉到新例列后。計開:一、川省啯匪在曠野攔搶,未經傷人之案,除數在三人以下者,發煙瘴充軍。一、四人以上至九人者,不分首從,俱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均面剌‘外遣’二字。如有脫逃,拿獲即行正法。但傷人者,即將傷人之犯擬絞監候,入于秋審情實。一、數至十人以上,無論傷人與否,為首擬斬立決,為縱擬絞監候,仍入秋審情實。被脅同行者,發遣為奴。其中倘有殺人奪犯傷差等事,有一人于此,即照場市搶劫之例,將首伙各犯,分別斬梟絞決監候。”[8](107-108)
清朝各級官府的“勸告”不可謂不是苦口婆心,“懲治條例”不可謂不嚴厲,卻還是有人鋌而走險,流為“啯嚕”。這說明,根治“啯嚕”僅僅停留在勸諭層面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為此,在頒布“懲治條例”的同時,清政府在湖南、湖北、貴州、四川、陜西等省開始了對“啯嚕”更嚴酷的追剿。但是,要剿滅行蹤不定、跪譎多端、為害多省的“啯嚕”談何容易!
乾隆四十六年(1781)8月9日,四川總督文綬即指出,要剿滅“啯嚕”存在著很大的難度,“川省啯匪到處游蕩,乘間搶劫,其蹤跡本無一定,此處查拿則逃往彼處,非止重慶、夔州地方為然”。“啯嚕”“白日綹竊為紅線,黑夜偷竊為黑線,此皆匪類之市語。其首伙、名姓、排行率皆變易無常,即同時同案之犯,所供本伙姓名、籍貫亦各不相同,且有一人數名,皆非真名實姓,并拿獲到案又另捏供姓名者,必彼此質認始知某甲即系某乙,總屬鬼蜮伎倆”。[9]到處游蕩,蹤跡無定,白日綹竊,黑夜偷竊,這是查拿“啯嚕”的一大難題。而“啯嚕”的成員不用真實姓名,或一個人用數個名字,也使得緝捕不易。
更為重要的是,“啯嚕”動輒“聚至百人之多,執持器械,拒傷兵役,且攜帶鳥槍、軍器”[10](26)。“啯嚕”已經成為一股股有組織的武裝團伙,剿滅這些為害多端的“啯嚕”實為十分困難的事情。更何況,“啯嚕”始則結伙行強,繼而聞拿四散,或偽裝為水手,推橈寄食,或化為乞丐,沿途行乞,計圖漏網。[11]
另文有述,每一伙“啯嚕”或糾結一處,或將乞丐、稚童之類也卷入團伙,更是加大了剿滅和區分“啯嚕”的難度。文綬即稱,“啯嚕”若在“沿途遇有匪類,即漸相糾結,并誘脅乞丐、童稚一路隨行,希圖人眾難拿,逃往外省躲避,或散入各川傭工,及沿途兵役截拿急迫,復力拒圖脫”。“現在嚴訊已獲各犯,均供實因四處截捕嚴拿,竄避山林,沿途遇有匪類,即漸相糾結,并誘脅乞丐、童稚一路隨行,希圖人眾難拿,逃往外省躲避,或散入各川傭工,及沿途兵役截拿急迫,復力拒圖脫”。[12]
剿滅“啯嚕”的難度越大,“啯嚕”的社會危害越大,清政府越是急于將之剿滅。文綬的奏折、乾隆的諭旨似乎都表明了對“啯嚕”應“務求根誅,永絕后患”。文綬奏稱:“川省無籍游民平日不務生計,每多搶竊之事。自軍需竣后(按指大小金川之役結束后),外省無業之人充夫覓食者亦多,當經分別編查押逐。其為匪犯案者,俱隨時嚴拿獲究。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辦獲搶奪劫竊及拒捕傷人等案,計題咨梟斬絞決發遣各犯,每年一百數十名至二百數十名不等。近以梁山、墊江等縣各報有搶奪刃傷事主、鄉保之案,臣以啯匪黨類本多,流害靡已,必須搜捕凈盡,大加懲創,方可永除擾害。”[12](32)乾隆諭旨,“湖廣、貴州各省若不特派大員專司擒捕,不足以專責成”,即派湖廣提督李國梁挑選本標精兵壯丁300名,先由湖北至湖南、貴州一帶,會同各該督撫實力搜捕凈盡,毋使一名漏網。若此三省,目今已無賊匪,則竟往四川交界處會同文綬將川省啯匪一體搜捕凈盡。李國梁接旨,與參將蔡鵬、守備李麟勛各帶兵丁100名,分三路擒捕啯嚕,一由湖南永綏各地方,無論城市荒村、叢箐峻嶺之處,密行沿途搜捕;一由湖南屬之澧州、湖北屬之宜都、宜昌前赴施南一帶地方督率搜捕,與四川督臣文綬商辦督捕,務期凈盡。[13](24)
三、嚴厲鎮壓與社會恐慌
事實上,乾隆中期,“啯嚕”已成為有組織的團伙,其活動地點不一,各自的頭目、成員各異,故而難以將某一股“啯嚕”活動的來龍去脈弄清楚,我們只能將官府對“啯嚕”搜捕、嚴懲,“啯嚕”對抗、逃竄的一般情形展示出來。
在大江渡口攔截,交界地方設卡堵擒,在各地四處搜捕,成為清政府緝拿“啯嚕”的重要方式。四川總督文綬即令在各大江渡口攔截,各交界地方設卡堵擒,又令在巴縣、長壽、墊江、梁山、合州、大竹等地四處搜捕。最后在合州等處生擒“啯嚕”一百余名(一次擒獲80余名,一次擒獲23名)。[14]
但是,在官府強有力追捕之下,“啯嚕”往往竄逃于各省之間,這就增加了追剿的難度。為此,乾隆皇帝下旨各省會合追捕,并力搜剿。7月9日劉墉奏稱,“川黔二省會合追捕,并力搜捕,以凈余孽。即使湘與川黔接壤各處并無‘啯嚕’蹤跡,仍然要嚴密防范截拿,不敢少懈”。[15]由于各省會同追剿,“啯嚕”日有報獲。仍咨會各鄰省交界一體防范盤緝,不難悉就殲除。7月24日四川總督文綬奏稱,已獲匪犯業有80余名。[16]盡管川省緝拿頗有成效,但在強有力的打擊之下,“啯嚕”紛紛逃逸川省,竄入別省。一方面,乾隆皇帝斥責文綬辦事不力,另一方面嚴行申斥文綬親身前往督率擒捕。同時諭令李國梁帶兵先由湖北至湖南、貴州一帶搜捕,如三省已無賊匪,即往四川交界處所,將四川“啯匪”搜捕凈盡。[17]
當然,有些“啯嚕”并不逃出川省,而是在當地高山密林處就近藏身。針對這種情況,追剿的官兵就需要深入各山林箐搜查、殲捕“啯嚕”。[16]
在強有力的追剿之下,被打散的“啯嚕”可能混跡于各廠做工,或混跡于水手、乞丐之中,或被鄉村農戶雇為傭工。為防止“啯嚕”漏網,官府嚴飭所屬多派兵役,于山僻村莊、水陸要隘搜查截捕,并飭各該廠員將各廠砂丁、背夫新來面生可疑之人,及重慶、夔州船行關口經過官商船只橈夫嚴加盤查。其各鄉村收割雇工,向本有薦引保人及自備之鐮刀、扁擔等物可以查察,令地方官嚴飭鄉保實力稽查。又,匪黨中查有家室親屬者,恐其潛回藏隱,亦責成原籍地方官及保鄰人等嚴密搜擒,不使混匿。采取這項措施,成效顯著。7月27日文綬奏稱,先后拿獲“啯嚕”90余名。[18]
對于“啯嚕”的懲治,依照《大清律例》,不分首從,凡幫同拒捕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聞,即并拒捕而隨行為匪者,亦當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本著這一原則,清政府對捕獲的“啯嚕”進行了嚴厲懲治。據8月25日、9月7日,舒常奏折,“啯嚕”頭目彭家桂、傅開太、吳榮三犯被處決梟示,王興國、皮麻子被發給伊犁給厄魯特為奴。[11]據7月5日、8月4日文綬奏折,胡范年等9犯分別梟示正法。首犯劉胡子、廖豬販子、朱大漢以及同伙張小滿速辦示眾。[19]據8月9日文綬奏折,經嚴督搜捕,擒獲121名,其中,劉胡子即劉繡、廖豬販子即廖榮系拿獲各“啯匪”供出之首犯,還有兇犯江老七等20名,俱在梁山、墊江一帶拿獲。當將劉胡子即劉繡、廖豬販子即廖榮二犯凌遲處死,仍梟首遍傳各處示眾。[20]據8月25日、9月7日舒常奏折,將嚴正綱、張和尚處決梟示,葉士明、李宏春、鄒開太,雖屬被脅隨行,止于背包,匪徒搶劫時并未動手助勢,但既入匪黨,亦難輕縱,應發遣伊犁給厄魯特為奴,照例刺字。[11]據10月22日舒常奏折,朱玉、孫達包子一伙隨同已經正法之王三豹幫搶分贓,實屬同惡相濟,將二犯處決梟示。劉添貴、王文鳳、匡陽泰三犯,雖被脅從,為日無幾,并未助陣分贓,但既入匪黨,亦難輕宥,應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至王大富并非黃大富,張元保并非“啯嚕”。李老七、吳魁應一并遞籍安插。周潮盈隨同拒捕各匪,助勢分贓,實屬同惡相濟,擬將周潮盈處決梟示;劉玉彩、王成忠、胡添才雖被脅從,并沒有助勢分贓,但既入匪黨,亦難輕宥,應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張守仁雖非“啯嚕”,而行竊多案,仍歸案嚴辦;至雙瞽之李宗瑤同何錦堂、胡大昌、楊又高、楊名高,被李維高挾嫌妄扳,應與向周潮盈口角成隙之鄧成德概行省釋。[21]從上述對各“啯嚕”案犯的懲治可以看出,清政府對已危及政權穩定的“啯嚕”采取了極其嚴酷的鎮壓措施,而且對于首犯、脅從者的懲治政策是有區別的。
由于官府的嚴厲鎮壓,輾轉奔逃、分散藏匿成為“啯嚕”首要的避難辦法。7月9日,劉墉的一道奏折就指出,一伙“啯嚕”由貴州仁懷竄回川省之江津、綦江邊界地方,分散潛藏。[15]對于較為強勢的“啯嚕”股匪而言,甚至會私立棚頭,拒捕傷差。匪首劉老十、毛老九等七八十人,因查拿緊急,由四川竄逃貴州、湖廣,復回川境。其余竄入湖廣、貴州者百余人及七八十人不等。私立棚頭,拒捕傷差。[22]劉胡子、廖豬販子供認,最初與胡范年等搶奪,并在合州拒捕,后因胡范年等逃散被獲,該犯等復為首,結伙逃往太平,竄入楚、黔等省,沿途糾眾,屢次搶奪拒捕,殺傷兵役。[20]
也有“啯嚕”易名改裝,行乞僻鄉。趙得相一伙,除擒獲及格殺外,其余匪徒零星逃逸,或潛匿山箐,或易名改裝,求乞鄉僻。[16]還有“啯嚕”充夫混跡。文綬奏稱,“啯嚕”節經搜截擒獲,已星散逃匿,續報盤獲匪黨,每止兩三同逃,并無結聚抗拿之處。川省到處皆山林僻徑,既易竄匿,又或冒入銅鉛鹽廠及官商船只,充夫混跡。目下山田稻田均獲豐收,秋糧遍野,鄉農雇人收割或借托傭工寄跡覓食,均未可知。至前此查拿各匪,由川省自東壤界逃往楚省,轉入黔省,由川省東南界竄回,經官兵追截捕獲,追至墊江縣一帶,沿途陸續逃散。[18]
綜上所述,清政府對“啯嚕”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過程,乾隆前期清政府對“啯嚕”基本上是作為一般案件處理的,但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叫魂”案、“王倫起義”、“蘇四十三起義”等事件發生之后,清政府的神經繃得更緊。考慮到“啯嚕”猖獗嚴重地擾亂了社會秩序,特別是擔心“啯嚕”活動會直接針對清政府的統治,乾隆中后期,清政府明顯地加大了對“啯嚕”追剿的力度。在清政府嚴酷的鎮壓之下,“啯嚕”或者輾轉奔逃,或者混跡于乞丐、水手之中,或者遁入廠礦、農戶傭工,而清政府對“啯嚕”務盡根誅的追剿,無疑會導致追剿范圍擴大化,從而導致社會恐慌。
[1]龔義龍.清代巴蜀“啯嚕”始源探析[J].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
[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七日著四川湖廣等督撫迅速搜捕啯嚕毋存姑息上諭[J].歷史檔案,1991,(1).
[3]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湖廣總督舒常等為已將續獲啯嚕皮麻子等飛飭解省事奏片[J].歷史檔案,1991,(1).
[4]向楚等修纂.巴縣志[Z].卷九.官師下.民國二十八年刻本.
[5]清高宗實錄[Z].卷203.中華書局,1985.
[6]嘉慶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四川總督勒保奏.錄副奏折[Z].
[7]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四川提督成德為報赴川省搜緝鄰水一帶啯嚕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2).
[8]清代巴縣檔案匯編[Z].乾隆卷.檔案出版社,1991.
[9]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九日四川總督文綬為報實力搜捕啯嚕務期無枉無縱事奏片[J].歷史檔案,1991,(2).
[10]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三日湖南巡撫劉墉為啯嚕進入貴州并湖南偵緝截拿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1).
[11]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湖廣總督舒常等為報審訊續獲啯嚕嚴正綱等奏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七日湖廣總督舒常為報審訊定擬所獲啯嚕嚴正綱等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2).
[1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四川總督文綬為報前后拿獲啯嚕并仍四路緝捕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1).
[13]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湖廣提督李國梁為報欽奉上諭起程督捕啯嚕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2).
[14]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四川總督文綬為報擒獲啯嚕劉老十等并已抵川東督捕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五日四川總督文綬為報追捕啯嚕并嚴辦已獲胡范年等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1).
[15]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九日湖南巡撫劉墉為復貴州拿獲啯嚕鐘鳳鳴并湖南雖無匪蹤仍行嚴防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1).
[16]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四川總督文綬為報已將續獲啯嚕趙得相等處死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2).
[17]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湖廣提督李國梁為報遵旨赴川省搜拿啯嚕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2).
[18]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四川總督文綬為報嚴密搜捕川東啯嚕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2).
[19]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四川總督文綬為報擒獲啯嚕劉老十等并已抵川東督捕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五日四川總督文綬為報追捕啯嚕并嚴辦已獲胡范年等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1).
[20]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九日四川總督文綬為復報先后拿獲啯嚕并飭各屬文武查拿搜捕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2).
[21]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湖廣總督舒常等為報審定擬辦啯嚕周朝盈等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2).
[22]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八日湖廣總督舒常等為復嚴密擒拿川省啯嚕事奏折[J].歷史檔案,1991,(1).
The Qing Government’Severe Suppression to“Guolu”and Social Panic in the Late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
Gong Yilong
(China Three Gorges Museum,Chongqing400015,China)
In the late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Guolu”exercised actively in Sichua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and it has seriously disturbed the normal social order,so the Qing government determined to eradicate“Guolu”-the triad society.However,the Qing government faced with the dilemma:in order to crack down on the real“Guolu”,without causing major social panic,the real“Guolu”,the suspected“Guolu”,and those who have been inducted into the“Guolu”should be distinguished.In fact,this was almost impossible to realize under the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Severe repressing“Guolu”inevitable resulted in social panic,and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severe.
in the late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the Qing government“Guolu”;severe suppression; social panic
K24
A
1673-0429(2011)06-0082-05
2011-09-09
龔義龍(1968—),男,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博士。研究方向:區域社會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