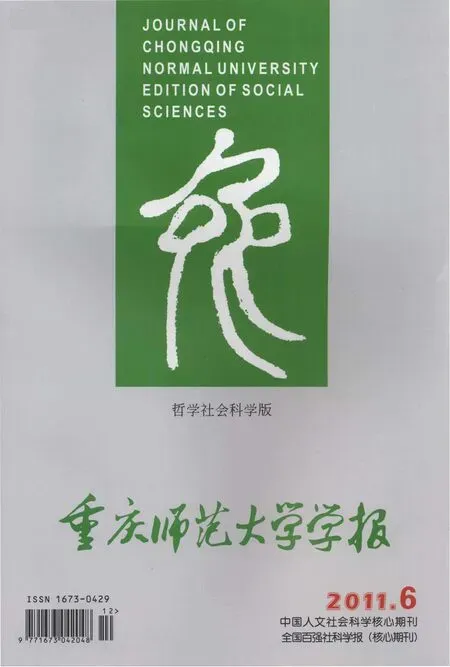附帶民事訴訟限制賠償范圍的反思與矯正——兼論附帶民事訴訟“執行難”的解決對策
鄔硯
(重慶沙坪壩區人民法院,重慶400030)
附帶民事訴訟限制賠償范圍的反思與矯正
——兼論附帶民事訴訟“執行難”的解決對策
鄔硯
(重慶沙坪壩區人民法院,重慶400030)
現行民事訴訟制度在確定賠償數額時,不判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和精神損害撫慰金,并將適當考慮被告人賠償能力作為一項原則。但前者無法回避舉證責任的困難性、賠償能力的不確定性、裁判結果的不公正性、審執交織的不合邏輯性等明顯缺陷;后者抹煞了公法與私法的區別,違背了責任聚合的處理規則,違背了“舉輕明重”的法律原理,在邏輯上與現行法律相沖突,且忽略了精神損害賠償的調整功能。故附帶民事訴訟限制賠償范圍缺乏合理性,應“堅持強勢意義上的平等對待”,與普通民事訴訟的賠償標準保持一致。其執行難的問題可以通過建立偵查階段的財產保全制度、完善賠償與量刑相結合的制度、建立民事賠償執行與刑罰執行相結合的制度、建立監獄代償制度、建立國家救助制度等方式予以克服。
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執行難
為節約訴訟資源、提高訴訟效率,刑訴法設計了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以解決因犯罪行為導致的民事賠償問題。但是,從現行法律規定及司法實踐來看,與普通民事訴訟相比,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過于狹窄,不但形成了與普通民事訴訟各行其是的二元賠償格局,而且出現了“小傷害大賠償、大傷害小賠償”的倒掛現象,導致該制度飽受詬病。基于此,本文對附帶民事訴訟限制賠償范圍的相關理由進行反思,并立足于統一賠償標準的思路,提出解決附帶民事訴訟執行難的具體建議。
一、現狀:附帶民事訴訟與普通民事訴訟在賠償范圍上存在顯著差異
(一)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受到嚴格限制
無論在立法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均受到嚴格限制,遠小于普通民事訴訟,就加害人而言,厚此薄彼的現象十分明顯。
1.精神損害賠償。在普通民事訴訟中,根據《民法通則》第120條、《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的規定,受害人有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但在附帶民事訴訟中,根據《刑事訴訟法》第77條第一款、《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1條第二款、《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的規定,被害人無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2.殘疾賠償金與死亡賠償金。在普通民事訴訟中,根據《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7條的規定,受害人或其近親屬有權請求獲得殘疾賠償金與死亡賠償金。在附帶民事訴訟中,這二者均被排除在賠償范圍之外。根據該司法解釋制定者的解釋,在確定殘疾賠償金與死亡賠償金的性質時,分別采納“勞動能力喪失說”與“繼承喪失說”,認定二者均屬于“對未來收入損失的賠償”。[1](310、357)據此,二者均屬于間接的物質損失。而《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2條將賠償范圍限定為“因犯罪行為已經遭受的實際損失和必然遭受的損失”,因此,2006年“第五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明確指出:“確定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數額,應當以犯罪行為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失為依據,死亡補償費不能作為人民法院確定賠償數額的根據。”(此為最高人民法院姜興長副院長在會議上的總結發言,鑒于發言人的職位與發言的場合,我們有理由相信,該觀點具有官方性質,系審判實務中的主流觀點。)由于殘疾賠償金與死亡賠償金同屬于間接損失,在死亡賠償金被明確排除的情況下,實踐中,基于“相同問題相同處理”的認識,殘疾賠償金也往往被排除在賠償范圍之外。對此,有人稱:“附帶民事訴訟不判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失費,簡稱‘三不賠’。”[2]
3.賠償能力。在普通民事訴訟中,除確定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時需考慮被告的賠償能力外,在確定其他賠償責任時,被告的賠償能力對賠償范圍沒有任何影響。但在附帶民事訴訟中,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的“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了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應當掌握的幾項原則,其中之一就是要適當考慮被告人的賠償能力。在2006年的“第五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適當考慮被告人的賠償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姜興長副院長的總結發言)再次作為一項指導原則得到重申。
(二)附帶民事訴訟限制賠償范圍的理由
同為損害賠償之訴,為什么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要小于普通民事訴訟?對此,贊同者主要持以下兩個理由:
1.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目前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多數公民(特別是大多數犯罪人)經濟能力還很有限,即使法律修改允許附帶民事訴訟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即使法院作出精神損害賠償的判決,最終當事人也難以得到實際賠償,看似符合法理的規定在實踐中不過是看得見、摸不著的‘空中樓閣’。”[3]“對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權利保護,不能完全依賴于一份執行難度很大的判決書,沒有充分有效保障的權利并無任何實質意義。”[4]“在被害人物質損失都難以得到充分賠償的情況下,再增加賠償精神損失沒有實際意義。不能把判決和執行簡單割裂開來。對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權利保護,不能完全依賴于一份沒有執行可能的判決書。”[5]綜合起來,持這一觀點的人主張,由于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判決高額的賠償責任對受害人而言沒有實質意義。這可謂“賠償能力論”中的“受害人論”。
此外,還有人指出,由于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判決高額的賠償責任反而會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第一,站在法院工作的角度,“無論是在內地法院還是沿海法院,無論是基層法院還是中高級法院,附帶民事訴訟難以兌現成為急需解決的難題”[2],即執行難。第二,“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空判’愈來愈嚴重,業已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上訪、申訴等加劇,被害人轉化為加害人的報復性犯罪的出現等,不一而足。”[6]以上,可謂“賠償能力論”中的“社會論”。
2.避免重復評價。有人主張,“從理論上,犯罪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損害,通過確定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判處其一定的刑罰,本身就是對被害人的一種撫慰。”[7]還有人認為,“在確定刑罰的過程中,犯罪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害程度已經作為重要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如再進行精神損害賠償,就有重復評價之嫌。”[4]
二、反思:附帶民事訴訟限制賠償范圍的不合理性
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指出:“法必須根據正義的要求來提升自我的本質,而正義則需要法的原則(即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普遍性。”附帶民事訴訟限制賠償范圍,從而構建不同于普通民事訴訟的賠償標準,在裁判結論上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差別對待,這種做法是否具有合理性呢?
(一)“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論”之反思
的確,絕大多數暴力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所以在實踐中,“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度加大、結案絕對數減少”[8]。但是,因為沒錢,所以不賠或少賠,站在被告人的角度來看,頗有點“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味道。實際上,無論在制度層面上以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為由限制賠償責任,還是在實踐層面上根據被告人的賠償能力確定賠償責任,均存在明顯缺陷。
第一,舉證責任的困難性。要根據賠償能力確定賠償責任,就必須查清被告人的財產狀況。但應當由誰承擔舉證責任?從理論上講,有三種選擇:一是要求受害人承擔舉證責任。但是,要求受害人舉證是否符合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受害人作為已經受到傷害的個人,能否查清并證明他人的財產狀況?二是要求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但是,被告人往往已被采取強制措施,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況下如何完成舉證責任?而且,被告人舉證證明的財產越多,則其承擔的責任越大,被告人為自身利益計,必然選擇不舉證或少舉證,因此,被告人的舉證如何能成為裁判的依據?三是要求法院依職權調查。但是,對法院而言,“這項工作像民事執行工作查清被執行人有無執行能力一樣艱巨。”[9]
第二,賠償能力的不確定性。姑且不論沒有發現被告人有賠償能力并不等于其一定沒有賠償能力,即使查清了判決時被告人的財產狀況,但人的一生是不斷創造財富的一生,被告人的賠償能力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被告人現在沒有賠償能力,并不表示以后沒有賠償能力。
第三,裁判結果的不公平性。首先,“如果個人應當永遠對其所犯的罪行負責,那么當他是犯罪的受害者時,他也應當永遠得到犯罪給他造成的損失的賠償。”[10](284)如果以被告人的賠償能力作為依據,不同的受害人面對同樣的損害,就會因為被告人賠償能力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賠償,這對受害人顯然是不公平的;其次,站在被告人的立場,如果被告人的財產是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獲得的,那么,要求有錢的被告人承擔更大的賠償責任,對積極勞動的被告人是不公平的。此外,從法的指引功能來看,這一邏輯是否意味著對積極創造財富行為的否定,是否意味著資本的“原罪”?
第四,審執交織的不合邏輯性。審判權與執行權具有不同的職能,審判要解決的問題是應否承擔賠償責任,在多大的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即責任承擔問題;執行是將判決確定的賠償責任予以落實,即責任履行問題。因此,判不判、判多判少是判決的問題,能不能賠是執行的問題,如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或暫時沒有執行能力,可以依法裁定終結執行或中止執行。從審判流程來看,審判在前,執行在后,因此,應當是審判決定執行,而非執行決定審判。根據賠償能力確定賠償責任的觀點,既混淆了審判權與執行權的職能,也忽略了審判與執行的先后順序。
此外,“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論”還存在一個顯見的缺陷。即雖然大部分刑事案件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但并不排除個別案件的被告人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如沈陽的“劉涌案”,分別發生在上海淮海路、重慶永川區的寶馬傷人案,杭州富家子弟飆車撞人案,被告人及其近親屬均具有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責任能力。由于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大都相對“貧窮”,使得這些富有的被告人承擔的賠償責任,比普通民事訴訟中并不富有的被告承擔的賠償責任更小,這種結果顯然超出了制度設計的合理性。
(二)“雙重評價論”辨析
“雙重評價”的觀點系站在國家本位主義的立場,但是,“在公訴案件中強調社會普遍利益的維護,強調公訴機關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卻多少忽略了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視了被害人的獨特要求。”[11](56)并且,在理論上是難以自洽的。
第一,抹煞了公法與私法的區別。“刑事訴訟可以說是一種‘公權訴訟’,其目的在于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往往與國家的憲政秩序聯系在一起。而附帶民事訴訟可以說是維護民事主體私人利益的‘私權訴訟’,目的主要在于解決民事糾紛,維護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的民事權益,往往與國家的憲政秩序沒有直接的聯系。”[12]因此,國家對于犯罪的處罰,雖然對受害人的確具有一定的精神撫慰作用,但這種意義上的精神撫慰與以金錢賠償為特征的精神撫慰是兩種完全不同類型的行為。前者是一種公權性質的行為,其目的在于維護整個社會發展所必需的秩序和保護所有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后者作為被害人對于犯罪行為所造成損失的賠償要求,是一種私權性質的行為,其目的在于實現經濟上的賠償。鑒于公法與私法在保護目的、責任性質上的不同,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是國家法律對犯罪行為作出的評價,不能由此抵消被害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損害,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第二,違背了責任聚合的處理規則。“所謂責任聚合,亦稱請求權聚合,是指同一法律事實基于法律的規定以及損害后果的多重性,而應當使責任人向權利人承擔多種內容不同的法律責任的形態。”[13]在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嚴重侵害公民人身財產權益的情況下,由于侵權法與刑法構成一個權利保障的多層次體系,由此導致被告人“既構成民事侵權,也同時構成了刑事犯罪,從而產生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聚合”[13]。對于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聚合的處理規則,“前者是通過賠償之方式對受害人之補償,后者是通過刑罰之方式對公民的人身權利之維護以保障符合統治者利益的社會秩序安寧,兩種責任的基本目的不同。依據法律之規定,加害人除應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以外,還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這兩種法律責任不可相互吸收、抵銷或者替代。”[14](104)因此,《侵權責任法》第4條第1款明確規定:“侵權人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的,不影響依法承擔侵權責任。”所以“雙重評價”的觀點,以刑事責任吸收民事責任,有違責任聚合的處理規則。
第三,違背了“舉輕明重”的法律原理。民事案件允許被害人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損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權造成的損害程度深,如毀人容貌的故意傷害、強奸、侮辱、誹謗等犯罪行為造成的精神痛苦,往往會伴隨受害人一生。舉輕以明重,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當然有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所以臺灣高等法院在“白曉燕命案”中,判決被告人陳進興給付失去愛女白曉燕的白冰冰高達17130萬元的精神撫慰金。以“重復評價”為由否定被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從法理來看,違背了根據“舉輕以明重”得出的當然解釋結論,將導致因輕微的民事侵權對被侵權人的賠償(包括精神損害賠償)比因犯罪而由被告人承擔賠償救濟更為充分的倒掛現象;從情理來看,難以想象一個婦女的名譽權受到侵害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損失,而被強奸卻沒有此項權利。
第四,在邏輯上與現行法律相沖突。“重復評價”的觀點認為,由于精神損害程度已經被作為量刑情節考慮,所以如判決精神損害賠償,則會構成重復評價。如果按照該邏輯進行推理,對于財產犯罪所造成的物質損失,被害人也不得要求被告人進行賠償,因為立法者也在法定刑的設置中考慮了財產損失的程度。但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77條的規定,因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應當得到賠償。因此,“重復評價”的觀點與現行法律的邏輯沖突顯而易見。
第五,對精神損害賠償的功能認識錯誤。精神損害賠償,有調整之功能,有撫慰之功能,亦有懲罰之功能。就其調整功能而言,“金錢無從購買‘同樣’之‘非痛苦’以填補損害事故所引生之痛苦,僅止乎購買或可購買‘他樣’舒適、方便或樂趣等享受用以掩蓋損害事故所引生之痛苦。”[15](311)也即是說,“通過金錢來使受害人獲得一些樂趣、享受等精神利益,從而間接消除其精神痛苦。”[16]判處被告人刑罰,雖然對被告人進行了懲罰,但不能另行創造舒適、方便或樂趣等享受,因此,不能實現對被害人精神痛苦的調整,不能取代精神損害賠償。
三、矯正:統一賠償范圍并有效化解“執行難”
正如哈耶克所言:“沒有什么不平等的現象會象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一樣導致如此大的怨恨。其他不平等的現象之所以不像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那樣引發極大的怨恨,只是因為它們被認為不是人為的結果。”[17]而通過法律對犯罪行為進行規制,明顯帶有規制人(包括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的主觀意愿,規制的結果顯屬“人為的結果”。所以,為了不致引發社會的“怨恨”,無論是在立法的層面還是司法的層面,“在沒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均應當堅持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18]
現行附帶民事訴訟制度采取限制賠償范圍的做法,形成與普通民事訴訟分庭抗議的二元賠償格局,人為制造了“相同損害不同賠償”的不平等結果。然而,如前所述,其限制賠償范圍的種種理由均不成立,更不足以構成“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所以,這一做法不但“割裂了民事法適用的統一性和確定性”[19],更重要的是,使得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因限制賠償范圍導致的“經濟上的不平等”而飽受詬病。所以,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應當與普通民事訴訟保持一致。當然,附帶民事訴訟本就存在執行難的問題,如判決更高金額的賠償,執行難度必然更大。但是,普通民事訴訟中亦存在執行難的問題,卻并未成為限制普通民事訴訟賠償范圍的理由。從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來看,立法的選擇是通過豐富執行手段、強化執行力度來緩解執行中存在的各種阻礙。同理,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執行難也不應成為剝奪受害人求償權的理由,妥善而正當的解決對策應是通過多種手段化解執行難。
(一)建立偵查階段的財產保全制度
現行法律僅規定了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有權進行財產保全,未規定在偵查、檢察階段的財產保全問題,導致被告人財產在偵查、檢察階段處于“三不管”的真空狀態,以至被告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差”轉移、隱匿、變賣財產。因此,應當完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財產保全制度,將財產控制時間提前,在刑事偵查期間即可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保全措施,對被告人的財產進行有效控制。在操作上,有兩種路徑可供選擇:一是賦予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財產保全權,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根據受害人的申請實施財產保全;二是仍由法院進行財產保全,在偵查、檢察階段,受害人即可向財產所在地的法院申請財產保全。
(二)完善賠償與量刑相結合的制度
實踐表明,在附帶民事訴訟中,“調解協議基本得到及時履行,社會效果較好”。[20]所以,調解不失為化解執行難的妥善途徑。但由于雙方對立情緒嚴重,且被告人缺乏賠償能力,因此調解有很大難度,必須通過有效手段來促成調解。賠償與量刑相結合即屬促成調解的有效手段之一。所謂賠償與量刑相結合,是指將被告人履行民事賠償責任的情況作為確定刑罰的酌定情節。從理論上來說,這一制度“兼顧了被害人、被告人和國家三方面,充分發揮了三方面的作用,有益于社會關系的和諧發展。通過這一程序,被害人能夠與被告人就賠償展開博弈,以獲得滿意的經濟賠償和精神撫慰,從而彌補因犯罪而遭受的損失;被告人獲得了彌補犯罪行為、承擔社會責任的機會,實現了減輕刑罰的目的;國家從追訴犯罪人科以刑罰的目的轉變為以恢復社會關系、平抑矛盾為最終目的。”[21]
第一,將賠償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激勵被告方積極賠償。這一做法已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如《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等。在適用上,一方面,在被告人或其家屬作出賠償后可減輕刑罰,即刑事責任部分轉化為民事責任;另一方面,如被告人客觀上有能力履行賠償責任,但惡意逃避、拒絕履行義務的,可酌情從重處罰,即民事責任部分轉化為刑事責任。通過定罪壓力,來逼迫有能力賠償者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有效保障受害人的權益。正如楊宇冠教授所說:“這種從輕不會超過量刑幅度,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22]
第二,應擴大賠償主體的范圍,“自愿代為賠償的范圍可由近親屬延伸至任何愿提供擔保的案外人。”[23]由于被告人往往賠償能力有限,且被限制人身自由,無法籌集資金,難以履行賠償責任,如將賠償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不僅被告人愿意盡力賠償,而且被告人的家屬、親友也愿為其籌集賠償資金。”[19]因此,在調解時,應盡量吸納被告人的家屬、朋友參加,通過家屬朋友代為履行,解決被告人賠償能力不足的問題。
(三)建立民事賠償執行與刑罰執行相結合的制度
所謂民事賠償執行與刑罰執行相結合,是指將被告人履行附帶民事賠償的情況作為減刑、假釋的酌定因素。這一制度,在法理上與將賠償與量刑相結合大致相當,可以起到激勵被告人積極履行賠償義務的作用。當然,被告人履行附帶民事賠償的情況只是確定減刑、假釋的參考因素,而非充分必要條件。
(四)建立監獄代償制度
所謂監獄代償制度,即如受害人未能獲得充分賠償的,則由監獄將被告人在監獄服刑期間的勞動所得的一部分支付給被害人。
站在比較法的角度進行考察,法國監獄法規定,已決犯勞動收入的1/6應作為保證勞役金,用作司法費用和受害人的賠償;1/6應作為儲蓄勞役金,在釋放時發給罪犯,供其在回歸社會初期、暫時沒有合法收入階段用作生活費用。意大利監獄法規定,罪犯勞動報酬的30%要上交救濟和扶助受害人基金。德國監獄法規定,罪犯的勞動所得一部分交社會保險金,一部分用作受害人的賠償金,并留足罪犯回歸社會后4周的生活費。日本監獄法規定,應將罪犯勞動所得的一部分用作對受害人的賠償費用。巴西的刑罰執行法規定,罪犯的勞動所得主要用于以下目的:一是賠償法院認定的犯罪造成的損失,二是幫助罪犯家屬,三是罪犯零用,四是補償國家為維持罪犯的生活所支付的費用,余下部分在出獄時發給本人。[24](127)
上述國家的監獄制度體現出兩個共同點:一是應將被告人勞動所得的一部分用作對受害人的賠償費用;二是不能將被告人的勞動所得全部用于對受害人的賠償,應為被告人留一部分作基本生活之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可以此為基本架構,建立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監獄代償制度。
(五)建立國家救助制度
所謂國家救助制度,是指當受害人因無法從加害人處獲得充分賠償而導致生活陷入困境時,由國家給予適當經濟補償的制度。在被告人無力賠償的情況下,由國家進行救助,其實質是國家福利政策的延伸,“一方面可以解決被害人暫時的生活困難,幫助他們走出生活困境,安撫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心靈”[25],另一方面可以消除群眾對法律制度的不信任感,維護、鞏固司法的地位。最高法院在《關于進一步加強刑事審判工作的決定》中,也提出“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
實行國家救助,必須注意以下問題:第一,國家救助的資金來源。不解決資金來源問題,國家救助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一般認為,資金來源有三:一是罰沒款,包括對被告人處以的罰金、沒收的犯罪所得與非法財物、沒收的保釋金等,必要時,行政罰沒款亦可包含其中;二是國家財政專項撥款;三是吸納社會捐贈。第二,申請國家救助的條件。國家補償不是一種陽光普照式的公共福利,取得補償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首先,應要求“被告人賠償前置”。“犯罪人對其行為責任的承擔永遠是第一位的,國家的補償是第二位的。”[26]因此,只有在受害人不能從被告人處獲得賠償或獲得賠償不足時,才可以申請國家賠償。其次,只有當受害人因不能從被告人處獲得賠償或獲得的賠償不足額,并導致其生活陷入困境時,才能要求獲得國家救助。第三,國家救助的期限。國家救助應堅持“救急不救貧”的原則,救助期限可設定為一年,使被害人有一年的時間生產自救,或申請社會救助。第四,權利轉移。受害人獲得救助后,應當將其在所獲救助的范圍內對被告人的債權轉移給國家,使國家依法享有對被告人進行追償的權利,從而避免被救助人雙重得利或被告人不當免責。
應當看到,國家救助制度是囿于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狀況的過渡政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終究會被完備的社會保障機制所取代。
以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構成重復評價為由,限制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不構成“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違背了憲法規定的平等原則。就此問題,站在立法論的層面,應當修改現行法律規定,要求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與普通民事訴訟保持一致,對受害人實行平等對待;站在解釋論的層面,雖然精神損害賠償由于司法解釋的明文規定無法納入賠償范圍,但是,應當將殘疾賠償金與死亡賠償金解釋為“必然遭受的損失”,從而納入賠償范圍,并應摒棄將“被告人賠償能力”作為確定賠償金額的參考因素。同時,鑒于大多數被告人的責任能力有限,應通過建立偵查階段的財產保全制度、完善賠償與量刑相結合的制度、建立民事賠償執行與刑罰執行相結合的制度、建立監獄代償制度、建立國家救助制度等方式,為受害人提供充分的保障措施與救濟渠道。
[1] 黃松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2] 劉青峰.何以刑事附帶民事判決幾乎不能執行[J].法制資訊,2008,(2).
[3] 李洪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若干爭議問題研究[J].法制資訊,2008,(2).
[4] 邢四文.附帶不是完全取代——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標準和范圍之辯[J].法制資訊,2008,(2).
[5] 最高法將發布司法解釋,統一刑附民訴訟賠償標準[N].法制日報,2008-08-14.
[6] 高遙生.聚焦刑事附帶民事訴訟[J].法制資訊,2008,(2).
[7] (轉引自)曲新久.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公權與私權的協調[J].法學,2003,(8).
[8]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面臨的司法困境及其解決對策的調研報告[J].法律適用,2007,(7).
[9] 高遙生.完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五點考慮[J].法制資訊,2008,(2).
[10] 恩李科·菲利.犯罪社會學[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
[11] 龍宗智.相對合理主義[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12] 江偉,范躍如.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機制研究[J].法商研究,2005,(4).
[13] 利明.論責任聚合[A].判解研究[C],2003年第2輯.轉引自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4270.
[14] 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15] 曾世雄.損害賠償法原理[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16] 林鏡蘭.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探討[J].法制與社會,2006,(8).
[17] 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M].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轉引自李鵬.論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價值及本土化.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2925&page=2.
[18] 王軼.民法價值判斷問題的實體性論證規則——以中國民法學的學術實踐為背景[J].中國社會科學,2004,(6).
[19] 肖建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內在沖突與協調[J].法學研究,2001,(6).
[20] 薛劍祥.刑事自訴和附帶民事訴訟中的調解適用[J].華東刑事司法評論:第八卷.
[21] 薛少林.“以賠代刑”的理性思考:刑罰和賠償互易制度[A].司法解決糾紛的對策與機制·全國法院第十九屆學術研討會獲獎論文集[C].
[22] 羅智勇,王敏.加強刑事訴訟中被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中澳刑事被害人保護問題研討會”觀點摘要[J].人民法院報,2008-08-14.
[23] 楊立新.性暴力犯罪受害人可否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問題[DB/OL].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 id=12948.
[24] 儲槐植.外國監獄制度概要[M].法律出版社,2001.
[25] 陳衛東.在“中澳刑事被害人保護問題研討會”上的發言[N].法制日報,2008-06-23.。
[26] 彭鳳蓮,陳旭玲.情理與法的沖突:呼喚刑事附帶民事的公費輔助補償[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6,(1).
Introspection and Remediation of Incidental Civil’Limit of Compensation
Wu Yan
(People’s Court of Shapingba District,Chongqing 400030,China)
when confirm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the present civil action systems don’t consider the death compensation,disability compensation and spirit of solatium,but take the solvency margin of defendant into account.The former has obvious defect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burden of proof,uncertainty of solvency margin,unfairness of referee results,illogicality of review and implementation,etc.while the latter obliterat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violates the processing rules of responsibility aggregation,conflicts with the present laws logically,and neglects the adjustment of spirit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So the incidental civil’limit of compensation lacks rationality and should stay the same with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common civil action.The difficulty in enforcement can be resolved by establishing the property preservation systems,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compens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enalty,building the system of civil compensation and criminal penalty,setting up the system of prison compensatory and the system of national salvation,etc.
incidental civil;limit of compensation;difficulty in enforcement
D925
A
1673-0429(2011)06-0109-07
2011-10-20
鄔硯(1976—),男,法律碩士,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