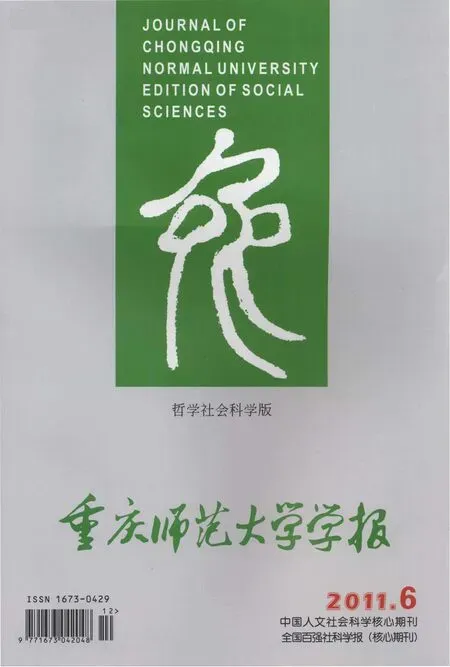再論1930年代“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之爭
歐孟宏
(湖南理工學院 文學院,湖南 岳陽 414006)
再論1930年代“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之爭
歐孟宏
(湖南理工學院 文學院,湖南 岳陽 414006)
1933—1935年,中國電影界出現了一場引人注目的“軟”、“硬”電影之爭。這次論爭在左翼電影批評家與軟性電影論者之間展開,涉及到電影藝術的本質、內容與形式、藝術性與傾向性、批評的基準等問題,其產生的根源在于雙方政治立場、文學與藝術觀念以及電影觀念等方面的巨大差異。這場論爭對于我們全面了解左翼電影理論與批評、軟性電影理論與批評、左翼文藝理論及新感覺派的文藝觀都提供了有力的參照和依據。
“軟”、“硬”電影之爭;軟性電影觀;電影理論與批評
1933—1935年,中國電影界出現了一場引人注目的電影之爭,這次論爭主要是在左翼電影批評家羅浮(夏衍)、唐納、塵無、魯思等人與強調電影的藝術形式和娛樂功能的劉吶鷗、黃嘉謨、穆時英、江兼霞等人之間展開的。它是左翼文藝家與“自由人”、“第三種人”之間的論爭在電影領域里的延伸。這場電影論爭最初是因為劉吶鷗在其創辦的《現代電影》雜志上發表《中國電影描寫的深度問題》、《關于作者的態度》等文章之后而引發的。而“軟性電影論”的正式提出,是稍后黃嘉謨在《現代電影》上發表的《硬性影片與軟性影片》一文。他在文中認為“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給心靈坐的沙發椅”。事實上,盡管劉吶鷗、黃嘉謨、穆時英、江兼霞等人都攻擊過左翼電影,但他們攻擊的程度與所采用的基準皆有所不同,比如劉吶鷗以藝術價值為基準,而黃嘉謨則以娛樂價值為準繩。而在左翼電影批評人士的回擊中,上述這些人的觀點被冠以“純藝術論”、“純粹電影題材論”、“美的觀照態度論”和“冰淇淋論”而統稱為“軟性電影論”。
一、對軟性電影觀的重新檢視
為了更為準確地把握這場所謂的“軟”、“硬”電影之爭,筆者將這場論爭中軟性電影論者的主要觀點重新進行了一番檢視。
早在1932年7月1日至10月8日,劉吶鷗就在《電影周報》第2、3、6、7、8、9、10、15期上發表了《影片藝術論》一文,其主要觀點如下:(一)關于電影的本質。劉吶鷗認為:“影片藝術是以表現一切人間的生活形式和內容而訴諸人們的感情為目的,但其描寫手段卻單用一只開麥拉和一個收音機。”“影戲是動作的藝術,影戲的內容應該盛入動作表現的形式里。”由此可以看出,劉吶鷗將視覺表現視為電影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質。(二)從上面的電影本質觀出發,劉吶鷗認為“織接”是電影藝術的生命。劉吶鷗所說的“織接”不單指具體的剪接工作,還包括整個影片的蒙太奇思維和總體構想。(三)對蘇聯“電影眼睛”學派和歐洲先鋒電影運動從藝術角度加以述評,指出其優點與不足,強調應當正確運用電影特性來創造電影美。(四)文學是電影的一個重要藝術元素。劉吶鷗認為,字幕和文學的敘事方法對于豐富電影的畫面內容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他同時也指出電影和文學畢竟是不同的兩種藝術,其表現形式和方法有著本質的區別,如果在銀幕上一味搬用文學要素,顯然是有害的。
從《影片藝術論》一文來看,在蘇聯蒙太奇學派和歐洲先鋒電影的影響下,劉吶鷗對電影的認識主要是從電影所特有的物質手段出發來論述電影的表現手法和形式特征,進而證明電影是一門獨特的藝術。這表明劉吶鷗的電影理論從一開始就將電影的藝術性擺在首位,這與西方早期電影理論頗為相似。
在《中國電影描寫的深度問題》(載1933年4月6日《現代電影》第1卷第3期)一文中,劉吶鷗開門見山地指出:“在一個藝術作品里,它的‘怎么樣地描寫著’的問題常常是比它的‘描寫著什么’的問題更重要的。”[1](158)他批評國產電影最大的毛病是內容偏重主義,而不把豐富的內容純用電影的手法描繪出來給人看。劉吶鷗認為影藝是沿著由興味而藝術、由藝術而技巧的途徑而走的,視覺要素的具象化是一部影片形式上的最后決定者。在此文中,劉吶鷗認為暴露片當然可以做,因為它是題材中的又一方面,但他反對那些技巧不完熟、描寫不夠的暴露片,將其視為畸形兒。在《論取材——我們需要純粹電影作者》、《關于作者的態度》、《電影節奏簡論》、《開麥拉機構——位置角度機能論》(分別載于《現代電影》第4期、第5期、第6期、第7期)等文章中,劉吶鷗進一步強調一切作者藝術家一定要以“美的觀照態度”“處理材料,整理事實而完成他的創作”。在《電影的形式美的探求》(載《萬象》第1期)中,劉吶鷗更是明白無誤地指出:“在一般藝術上形式,即表現方法,卻比主題,即內容更重要。”“一部影片的藝術上成功與否,卻與意識形態少有關系。”
概括起來講,劉吶鷗的基本觀點就是將技巧的運用與形式的創造視為電影創作的根本,他認為發展國產電影的關鍵,不在于主題內容的改造和革新,而在于形式技巧的完善和提高。
黃嘉謨在《電影之色素與毒素》(載1933年10月1日《現代電影》第1卷第5期)一文中批評國產電影現狀時說:“好好的銀幕,無端給這么多主義盤踞著,大家互相占取宣傳的方地,把那些單純的為求肉體娛樂精神慰安的無辜觀眾,像填鴨一般地,當他們張開口望著銀幕時,便出人不意的把‘主義’灌輸下去。”他要求拋棄一切含有宣傳作用的素料,重新恢復第八藝術的純真的表現,讓每個人用他的技巧自由地去發展。
在《硬性影片與軟性影片》(載1933年12月1日《現代電影》第1卷第6期)一文中,黃嘉謨首先就明確指出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給心靈坐的沙發椅,它本來是軟片制成的。接下來,他批評中國電影卻由軟片變成了硬片,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左傾意識在作怪。黃嘉謨還認為革命口號題材的影片因為其干燥而生硬的說教使得觀眾進電影院的興趣大減。黃嘉謨進而提出:“電影是軟片,所以應該是軟性的。”
在《軟性電影與說教電影》(載1934年6月28日7月2—4日《晨報》“每日電影”)一文中,黃嘉謨認為說教派主張應在電影里散布主義的宣傳,這無論如何是斷送國產影片的一種方法。他還認為,如果抹殺電影應有的娛樂性,便會失去觀眾,完全失去電影的效用。在批判左翼電影理論之后,黃嘉謨指出中國影業惟有走上純影藝而接觸到現實生活的“正路”,才有開始繁榮的一日。
從黃嘉謨的這幾篇文章來看,他盡管也與劉吶鷗一樣堅持“純影藝”的藝術主張,但他更側重于強調電影的娛樂價值。
江兼霞在《關于影評人》(載1934年12月20日《現代演劇》第1期)一文中認為,電影如果離開了電影藝術,縱使能達到教育的使命,那也不過是枯澀的教材、拙劣的幻燈影片而已。以此作為依據,他說:“影片制造,電影批評,必須先從它的藝術的成就、技術問題入手,內容是其次的。”[2]
1935年,穆時英針對左翼影評人提出的電影批評的基準問題發表了《電影批評底基礎問題》一文。在這篇文章中,穆時英批判了魯思的庸俗社會學電影本質觀以及形式與內容相統一的機械論。穆時英認為,要解決電影批評的基礎問題,首先必須明確藝術的一般本質和電影的特性。為此,他指出:“藝術是人格對于客觀存在的現實底情緒的認識,把這認識表現并傳達出來,以求引起其他人格對于同一的客觀存在的現實獲得同一的情緒認識底手段。”“電影借助膠片、演員、攝影師、導演及腳本所共同構成的畫面以表現作者的情緒。”接下來,穆時英探討了電影作品的內容、傾向性與形式三者之間的關系,認為它們是三位一體的統一物,互相決定,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在上述基礎上,穆時英進而指出電影作品的傾向性與藝術性、社會價值與藝術價值四者之間也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藝術價值并不是電影作品的全部價值。最后,穆時英才提出了電影作品的評價基準應該為:電影作品是具有二重價值的,產生于它的傾向性的社會價值和藝術性的藝術價值。影評人不能機械地拿它的社會價值,也不能單純地拿它的藝術價值來做評價基準,而要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看,才能決定其評價。[3]
從《電影批評底基礎問題》這篇文章來看,穆時英并不是劉吶鷗和江兼霞那樣的藝術至上主義者,他是從情感方面來揭示藝術的本質進而觸及到電影的特性的。他對左翼電影理論的電影藝術本質論、內容與形式統一的一元論并沒有全盤否定,而只是揭示左翼影評人在電影理論方面所犯的庸俗社會學和機械唯物論錯誤。事實上這對于糾正左翼電影理論的某些偏頗是非常有益的。但在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文化環境下,穆時英的這一很有見地的文章并沒有引起左翼電影理論人士的深刻反省,反而使得左翼影評人士與他之間的論戰進一步升級。先是有魯思還擊穆時英的長達萬余言的《論電影批評底基準問題》,之后有塵無的《論穆時英的電影批評底基礎》以及史枚(唐納)的《答客問——關于電影批評的基準問題及其他》等文章,均對穆時英展開了猛烈的批判。
為了應對左翼影評人的責難,穆時英又寫下了一篇長達4萬字的理論文章《電影藝術防御戰——斥掮著“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招牌者》,該文從1935年8月11日至9月10日在上海《晨報》連載。從這篇文章來看,由于穆時英對康德、尼采、叔本華等西方哲學家以及馬克思、普列漢諾夫、布哈林等人的哲學觀和文藝思想都有所涉獵,因此他不僅能夠指出左翼影評人在哲學觀和文藝思想上的庸俗社會學與機械唯物論的缺陷,也能為自己的觀點找到理論依據。穆時英在這篇長文中批判和論述了九個問題,其觀點大致如下:(1)偽現實主義的本體。穆時英認為,左翼影評人的主觀認識與客觀歷史行程一致論、藝術反映客觀現實論、客觀反映的正確程度決定藝術價值論都是偽現實主義,因為他們只強調了辯證唯物論里邊的機械論傾向,只抓住了“存在決定思維”這個原則,而忽略了其余重要的、詳細的規定。(2)思維與存在。穆時英認為,一切思維導源于存在,這是存在決定思維這個公式的第一義。他批判左翼影評人只知機械地套用“存在決定思維”這一名言,而沒有真正理解它。(3)主觀與客觀中間的距離。穆時英認為,在思維中存在著的現實與在客觀中存在著的現實是不能不有著若干距離的差異的,現實認識是一個無限的過程。(4)文化的意義。穆時英認為左翼電影論者只知道解釋藝術和一般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基礎,而完全忽略了文化的積極的方面。(5)藝術的本質。穆時英認為,就一般意義來看,藝術是反映主觀的工具,而不是表現現實的工具。(6)藝術的思想與情緒。穆時英認為藝術是人格對于客觀存在的情緒的感應,此感應的表現與傳達,以求引起其他人格對于同一的客觀存在引起同一的情緒感應的手段。(7)藝術的終極的使命。穆時英認為,一切藝術都是生存斗爭的反映與鼓吹。(8)內容與形式。穆時英明確表示他并不否定內容決定形式這一定律,他只是批判左翼電影論者曲解了內容決定形式這一定律。穆時英借用安海姆的電影理論論述了電影中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系。在此,穆時英重申了他在《電影批評底基礎問題》一文中確立的電影批評基準。(9)批評底路。穆時英認為電影藝術作品的批評與電影藝術作品的創造同樣是理論的實踐的最基本的一部分,其重要性絕不在作品創造之下。
對于穆時英的這篇重要理論文章,無論是魯思后來在《影評憶舊》中回憶“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之爭,還是程季華所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對‘軟性電影’分子的斗爭”這一章節中均未提及,即便到目前為止的諸多關于“軟硬之爭”的學術論文中,也很少有人提及穆時英的這篇文章。其實,穆時英的《電影批評底基礎問題》、《電影藝術防御戰——斥掮著“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招牌者》這兩篇文章對于我們理解“軟硬之爭”的性質與雙方的理論缺陷有著重要意義。如果說劉吶鷗、黃嘉謨、江兼霞等藝術至上主義者在電影本質觀和批評觀上與左翼電影理論發生根本對立的話,穆時英的電影理論則更多的是對左翼電影理論的一些偏頗加以矯正。事實求是的說,盡管穆時英的電影理論也存在缺陷,但他以其深厚的哲學根底和文學藝術修為作為基礎,對電影的認識比左翼影評人顯然更為深刻。
二、“軟”、“硬”電影之爭的幾個焦點問題辨析
從現有文獻來看,“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雙方爭論的幾個焦點問題如下。
1.電影藝術的本質
對藝術本質的認識歷來是藝術理論中的一個最基本最關鍵的問題。而電影既帶有文化產品的商業性,同時又是一門藝術,因此不論是左翼影評人士還是軟性電影論者,均無法繞開電影藝術的本質這一核心問題。正因為這樣,電影藝術的本質問題首先成為了他們雙方論戰的焦點。在《清算軟性電影論》一文中,唐納充分認識到了電影首先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具有商業性,同時它也是一種藝術。唐納接下來談到了藝術的本質。他說:“藝術是社會的現象。社會的基礎物質的經濟結構,經濟——階級——階級心理——藝術,這就是藝術的一元論的概念。”[4]塵無也認為,藝術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它是借著形象而思維的。[5]同樣地,魯思對電影之本質的認識也沒有跳出上述兩者的窠臼。他說:“影藝是社會現象的一種,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的一種表現,即社會人類的意識形態的反映;更本質地說,它是某一種方式,反映客觀存在的現實。”[6]在《論電影批評底基準問題》一文中,魯思又對藝術的本質作出了如下概括:“藝術是由直接的存在底形象反映客觀現實,它絕不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直接的現象)上,這是不可能的。它必得闡明事物底規律性與必然性,由個別的現象來說明普遍的現象,由部分的東西來解釋整個的東西,這是藝術的特質和任務。”[7]事實上,魯思對影藝本質的認識與他對藝術本質的認識并無什么不同。總的說來,左翼影評人是在藝術與社會現實的關系上來認識電影的本質的。
軟性論者的電影本質觀中,劉吶鷗是從電影藝術的特性來理解電影的本質的。他認為:第一,動作是電影藝術成立的第一要素,富于暗示性,最能使它的意義給人明白;第二,電影是科學(光化學、工學)和藝術結婚的混血兒。[8]黃嘉謨則將娛樂性視為電影的本質,他直言不諱地說:“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給心靈坐的沙發椅。”而穆時英是從情感方面來探討藝術的本質的,他說:“藝術是人格對于客觀存在的現實底情緒的認識,把這認識表現并傳達出來,以求引起其他人格對于同一的客觀存在的現實獲得同一的情緒認識底手段。”“這樣的藝術底本質,當然也是電影作品底本質;它和別種藝術底不同,只是工具的不同,文學作品借文字,繪畫借顏料,雕刻借石膏,音樂借音符和樂器,電影則借膠片、演員、攝影師、導演及腳本所共同構成的畫面以表現作者的情緒。”[9]比較起來,軟性論者中的劉吶鷗、穆時英等人的電影本質觀顯然比左翼影評人更有說服力,因為他們的電影本質觀更能反映出電影藝術的某些重要特性。而左翼影評人盡管能夠準確地揭示出電影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但將之作為電影的本質則顯得機械而形而上學。更為欠缺的是,他們將藝術的本質與電影的本質混為一談,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
2.內容與形式
劉吶鷗在《中國電影描寫的深度問題》中指責國產電影最大的毛病是“內容偏重主義”:“內容重,描寫過淺,于是形式便全部被壓倒了。全體現出catalogue(目錄)式,好像只許翻翻目錄,給你想象他內容的豐富,而不把豐富的內容純用電影的手法描繪出來給人看”,“可是在技巧未完熟之前的內容過多癥卻是極其危險的。因為他是頭重體輕的畸形兒”。江兼霞則認為影片制造、電影批評,必須先從它的藝術的成就、技術問題入手,內容是其次的。他指責中國電影每一張新片開映,總有“意識正確”的影評人在檢查它的成績:內容是否空虛,意識是否模糊等等。黃嘉謨批評那些革命口號題材的影片表面上看來都是革命性的,前進的,奮斗的,聳聽而又夸大的,但其內質卻空虛和貧血,勉強而淺薄。相比之下,穆時英對左翼影評人的內容與形式統一的一元論并未加以全盤否定,而只是批判他們在這一問題上所犯的簡單機械唯物論錯誤。
為了反擊軟性電影論者的批評,左翼影評人異口同聲地堅持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一元論。唐納在《清算軟性電影論》一文中指出:“藝術的內容與形式,只在理論的探討的方便上才被分割,實際上這是不可分離的。”但唐納同時申明他絕不反對新內容要求新形式的創造。然而,他片面而武斷地認為:“軟性論者所謂形式的創造,絕不是和新內容適合的形式。從他們的根本反對新內容,更可以知道他們所謂創造形式,實際上就是使觀眾不去積極支持新生電影而已。”事實上,軟性論者并沒有簡單地全盤否定新內容,即便是特別推崇形式美感的藝術至上主義者劉吶鷗,也認為暴露片當然可以做,因為它是題材中的又一方面,他只是反對那些技巧不完熟、描寫不夠的暴露片,將其視為畸形兒。至于唐納認為軟性論者所謂創造形式是為了使觀眾不去積極支持新生電影就更是毫無根據的猜測了。羅浮(夏衍)在《“告訴你吧”——所謂軟性電影的正體》一文中認為,在藝術史上,作品的形式與內容,始終是內容占優位性的。他說:“史上不知道有多少的作家,在形式上極不完整,極端粗獷,有時甚至于文字的通順都不能做到,可是只因為在他們的心靈有了強烈的內容,而博得了不朽的聲譽。”塵無在《清算劉吶鷗的理論》一文中說:“‘形式是內容決定的’!怎樣的內容一定會要怎樣的形式來表現;怎樣的形式是只合表現怎樣的內容。”魯思在《駁斥江兼霞的〈關于影評人〉》一文中說:“形式與內容構成不可分的統一,對立的統一;形式是內容的范疇,內容是決定形式的。”當然,他同時也承認當時的新的電影批評也有著缺點,就是影評人把內容的檢討看得太重,比較地忽略了電影的技巧。因此,魯思說:“新的電影批評,不該忽略那些歐美電影的技巧,因為新生的電影是要繼承這已發展了的優秀的技巧,而更加徹底地把新的內容統一起來。”[6]
左翼影評人堅持電影的內容與形式的一元論有其特定的理論淵源。中國左翼文藝理論界長久以來一直堅持內容決定形式,內容與形式應該相互統一在一起的觀點。這種觀點的來源主要是受到了蘇俄的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列夫派”、“崗位派”以及日本藏原惟人新寫實主義等左翼文藝理論的影響。
不容否認,軟性電影論者在對待電影的內容與形式方面的確存在著拔高形式的意義而貶低內容作用的傾向,尤其是劉吶鷗的所謂“美的觀照”、“視覺要素的具象化”等理論更是完全離開內容而孤立地談形式。事實上,軟性電影論者的形式主義傾向也有其特定的中外文藝思潮背景。比如劉吶鷗、穆時英是當時上海新感覺派的主將,他們深受日本新感覺派和西方現代派文藝思想的影響。日本新感覺派作家池谷信三郎說:“藝術上最重要的首先是形式,其次是感想,再次是思想。”[10](92)川端康成曾說:“沒有新表現,就沒有新文藝。”[10](92)在這些文藝觀的影響下,劉吶鷗和穆時英重視電影藝術的形式美乃是一種必然。而與此同時,歐洲大陸的先鋒電影運動以及愛因漢姆等人的電影理論對劉吶鷗等人藝術至上的電影觀的形成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由劉吶鷗、黃嘉謨等人創辦的《現代電影》本身就是以介紹中外電影的知識動態和理論為宗旨,對世界各主要電影大國的創作情況都比較了解。因此,軟性電影論者重視電影的藝術形式可以說是緊跟了世界電影發展的大趨勢,這是應該加以肯定的。問題在于,軟性電影論者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國難當頭和社會矛盾異常尖銳的時刻,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軟性電影論者這種忽視對社會現實的揭露而重在追求藝術形式的唯美主義傾向顯得不合時宜。尤其是黃嘉謨等人對電影娛樂功能的大力鼓吹明顯地有悖于時代精神。這必然會引起左翼影評人士的不滿和憤慨,因此,雙方的論戰將不可避免。
3.藝術性與傾向性
左翼影評人對作品內容的高度重視使他們必然將作品的傾向性擺在首位,而藝術性則為其次;加上當時的左翼電影理論界人士將電影視為一種宣傳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工具,因此,左翼影評人特別強調電影的階級性,重視作家的世界觀。唐納認為,根本沒有不帶傾向性的藝術家,根本沒有純客觀的“美的觀照態度”,每個藝術家都有派別。[11]塵無認為,世界上沒有沒有主觀的客觀作品,藝術價值和政治價值是辨證統一的。[5]魯思亦認為,“藝術性”與“傾向性”兩者根本就不應該割裂開來。[6]當然,話也說回來,左翼電影批評盡管以電影的意識形態批評為重點,但也并未完全忽視電影的藝術技巧批評。
左翼影評人士對作品傾向性的強調遭到了軟性電影論者不同程度的批判。黃嘉謨指責中國電影界“主義學說,樣樣搜羅。放著純正的藝術不理,而去采用什么主義,什么化,什么派”[12]。他在《硬性影片與軟性影片》一文中認為,目前中國影片之所以由軟片變成硬片完全是左傾的“意識論”在作怪。[13]黃嘉謨并不否認“電影也是最普遍的教育和宣傳的利器”,但他同時也說:“但并不能說每部影片都是教育和宣傳的利器。都要負‘說教’‘填鴨’的責任。”“至于反帝反封建,當然是一般影界從業員的熱切愿望,但是我們主張應該量力而為。電影從業員所做的反帝反封建的步驟,決不能比政治力和社會運動力更加進步。”[14]江兼霞則非常明確地說:“要使中國電影進入與外片抗爭的地位,必須丟開了所謂‘意識’的圈套,而在編劇、導演、表演上,竭力去作電影之藝術上的各方面的研究,然后才可以走入正軌。同時,影評人假如是真心的效忠于中國電影的話,也該著重影片之藝術的批判,而不必只是空談意識。”[15]相比之下,穆時英在作品的藝術性和傾向性之間的關系上論述得更為具體也更為深刻(見前文所述)。
從雙方的觀點來看,左翼影評對作品傾向性的強調對于促使當時的中國電影從武俠神怪片與家庭倫理片的狹小圈子里擺脫出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一批所謂“現實的題材”與“前進的意識”的反帝反封建影片出現在銀幕上,徹底地改變了中國電影的走向。但左翼影評人這種過于注重“意識”而忽視“技巧”的傾向使得他們常常先入為主地以階級觀念或民族意識來作為衡量一部影片價值高低的首要標準,遮蔽了一些思想意識不左傾而藝術價值較高的電影作品。更為嚴重的是,為了迎合左翼影評人的“意識”要求,不少影片出現了在銀幕上“鬧意識”的情況。它們要么人為地制造階級對立情節,要么在銀幕上喊空洞的革命口號,要么在影片結尾加一個光明的尾巴,從而影響了作品內容的合理與完整,藝術性當然也就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其實,即便是左翼影評人,他們對于“意識”的理解也各有千秋,其中大部分人在談“意識”時顯得空泛而充滿說教意味,并不能正確指導電影創作,當然也很難真正使觀眾受到啟示。
在廣大農村出現災荒與破產、城市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小市民生活貧困、民族危機日益緊迫等社會現實面前,軟性論者卻在電影的傾向性與藝術性之間更重視后者,這使他們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所以一些左翼影評人說他們“是和敗北主義、親敵主義相一致的”,“是文化侵略的清道夫”。事實上,在對待藝術性與傾向性的問題上,除了黃嘉謨和江兼霞態度偏激地全盤否定國產影片的左傾意識而主張電影的娛樂性與藝術性之外,劉吶鷗和穆時英并未否定作品的傾向性。穆時英的小說集《南北集》就帶有明顯的普羅文學傾向,而劉吶鷗的小說集《都市風景線》對城市中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予以了揭露和批判,對無產階級新生力量進行了暗示。他們在電影上之所以更加強調藝術性,是因為他們是以藝術家的立場來看待電影的。如果說劉吶鷗的電影理論完全是探討電影的藝術形式而忽略其傾向性的話,穆時英則以深厚的哲學和文藝理論為基礎,詳細探討了電影作品的內容、傾向性與形式三者之間的關系,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他說:“內容既然是和客觀現實對立并適應的,通過了人類意識底情緒認識的主觀現實,它自始就不得不包含傾向性。”“傾向性是作品內容必然地包含了的元素,然而傾向性卻不是內容本身。”“形式愈能表現內容,愈能加強傾向性,作品底組織機能便愈發展,它底藝術性便愈豐富,它底藝術價值便愈高。”[9]從上述觀點可以看出,穆時英完全承認一切藝術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傾向性,這與左翼電影理論并無分歧,他所批判的是那種只片面追求影片內容的思想傾向性而不講究影片的藝術形式創造的意識形態電影批評,將其稱為“偽現實主義”。
4.批評的基準問題
關于批評的基準問題,軟性論者談得比較少。江兼霞認為:“影片制造,電影批評,必須先從它的藝術的成就、技術問題入手,內容是其次的。”“影評人如果是真心的效忠于中國電影的話,也該著重于影片之藝術的批判,而不必只是空談意識。”[15]穆時英則在《電影批評底基礎問題》一文中專門談到了“電影作品底評價基準”這一問題。穆時英認為:“電影作品是具有二重價值的,產生于它底傾向性的社會價值和產生于它底藝術性的藝術價值。影評人不能機械地拿它底社會價值,也不能單純地拿它底藝術價值來做它底評價基準。而要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看,才能決定其評價。”[3]從江兼霞和穆時英的觀點來看,他們對于電影批評的基準顯然有些差異。江兼霞認為電影批評應以藝術與技巧為重點,而穆時英認為電影批評應該立足于挖掘作品的社會價值和藝術價值,兩者不可偏廢。由此觀之,穆時英的電影批評基準更為合理。
與軟性論者相比,左翼影評人對電影批評的基準盡管論述得比較多,但立場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唐納在《清算軟性電影論》一文中說:“科學的電影批評應該是看作品的是不是表現客觀社會的真實。”“作品是不是表現客觀現實的真實,是和作家的世界觀分不開的。”[4]這樣一來,唐納很自然地就把意識形態批評作為了電影批評的基準。羅浮(夏衍)在《“告訴你吧”——所謂軟性電影的正體》中指出文化——藝術批評者的批評基準應該是“‘作品是否在進步的立場反映著社會的真實’,而決不在作品的外貌是否華奢與完整”[16]。塵無在《清算劉吶鷗的理論》一文中指出:“一個作品的藝術價值的判定,是在他反映現實的客觀的真實性的程度,而所謂真實性,就是這一個社會中的主導的必然的內在。”[5]魯思在《論電影批評底基準問題》一文中也明確說道:“影藝作品的價值,在于這作品反映客觀現實,正確到了怎樣的程度,才是決定影藝作品底唯一的客觀價值。所以電影批評底基準問題的原則,是電影藝術地表現社會的真實。”[4]從夏衍、塵無、魯思等人對電影批評基準的論述來看,他們與唐納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以意識形態作為電影批評的主要基準,有的人甚至認為作品藝術價值的高低也是由它反映客觀現實的程度決定的。
三、對“軟”、“硬”電影之爭的批判與反思
“軟”、“硬”電影的這場論爭,是由于雙方在政治立場、文學與藝術觀念以及電影觀念等方面存在著根本的差異。
左翼影評人很多都是左聯作家,有的人還是中共黨員,他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上來看待國產電影的,自然要求電影作為宣傳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因此,他們將作品的傾向性和教育性作為衡量一部作品價值高低的標準。同時,像唐納、魯思、王塵無等左翼影評人士都是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他們主要是以從蘇聯和日本借鑒過來的左翼文藝理論作為依據來展開電影批評的,他們自身缺乏深厚的藝術素養,因而在電影批評中不免出現重思想性而輕藝術性的弊病。
而軟性電影論者大多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上層社會人士,他們對現實社會的看法顯然不可能與左翼人士一致。而像他們中的劉吶鷗和穆時英,是當時海派中一個重要文學流派——新感覺派的主將,二人在描繪上海都市景觀上取得了相當高的藝術成就。因此,軟性論者的政治立場和藝術觀念決定了他們的電影觀顯然會以藝術性作為基點。
本來,雙方的眾多差異導致他們的電影觀念產生分歧是很正常的,如果雙方能夠以寬容的態度容納對方,就不致于在論爭中出現斷章取義、故意曲解甚至于加以人身攻擊的狀況。問題在于,左翼影評人采用宗派主義的方式,試圖以他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來奪取電影批評的話語領導權,使電影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目標服務。因此,他們勢必難以容忍軟性電影論者在理論觀點上對自己加以非難和指責。而軟性論者作為現代上海大眾文化的代言人,他們一直是將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品和娛樂工具來看待的,很多國產電影的左傾觀念和電影評論界的重意識而輕藝術的主流使得他們不得不起來表示不滿。于是,雙方借助一些報刊雜志在電影話語權方面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左翼以工農大眾的代言人自居,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為武器,試圖將國產電影的創作方向和批評標準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軟性論者的電影主張與上海現代大都會的商業消費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對于電影的藝術性或者娛樂性的強調,完全是為了追求個體的生命自由。在當時的上海,文化消費的主體畢竟還是以現代新市民階層為主,小資產階級、商人和作為社會中間階層的市民職員群體(包括律師、工程師、會計師、教師、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構成了電影消費的主體。這些人需要在下班之后進電影院松弛自己緊張的神經。因而,軟性電影理論的出現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社會基礎。但是,歷史的錯位,主要是一個時代性問題。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下,軟性論者主張電影躲進藝術的象牙之塔,或者借助電影來獲得快感而置民族危機與社會矛盾于不顧的論調,顯然有悖于時代的要求,他們既與國民政府當局倡導的新生活教育運動的精神相違背,又與激進的左翼革命思想背道而馳,因而最終只能處于話語的邊緣,失去了他們本來應有的位置。
就意義來看,不論這場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之爭的最終結果如何,軟性電影理論對左翼電影批評在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上的偏頗與缺陷進行了有力的匡正和補救,他們的電影理論與批評更接近了電影的本質。可惜的是,由于當時特定的左傾政治環境和左翼影評人士的急功近利,軟性論者的這些頗有價值的觀點并沒有被左翼影評人士所接受。而左翼影評人士通過這場電影論爭捍衛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左翼電影批評存在的合法性進行了有力的辯護。但不容置疑的是,左翼影評人士在一些重大的藝術(當然包括電影在內)理論問題上存在著機械化、簡單化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左翼影評人士在與軟性論者論爭的過程中表現出明顯的宗派主義和上綱上線將學術問題政治化的不良傾向,給建國后的電影批評帶來了消極的影響。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意識形態的獨白性原則”(即“一元論的原則”)具有如下弊端:它強化等級制,企圖壓制一切非權威力量。它扼殺創造潛力、窒息蓬勃的生機,它導致單一性、片面性、簡單化、僵化。它是培育教條主義的溫床。[17](482)
總的看來,這次軟硬電影之爭不僅使中國電影界對于電影的一些重大問題有了非常明確的認識,而且雙方爭論的問題已經超越了電影的范疇而擴展到了藝術領域,甚至于包括哲學的一般性認識問題。雙方在論戰中發揮得非常出色,精彩論述層出不窮,不僅使自身的電影理論素養得到穩步提高,也極大地提升了中國電影理論的整體水平,形成了中國電影理論發展的第一個高峰。一句話,這場長達三年的電影論爭對于我們全面了解左翼電影理論與批評、軟性電影理論與批評、左翼文藝理論及新感覺派的文藝觀都提供了有力的參照和依據。
[1] 丁亞平.百年中國電影理論文選[C].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
[2] 江兼霞.關于影評人[J].現代演劇,第1期(1934年12月20日).
[3] 穆時英.電影批評底基礎問題[N].晨報·每日電影,1935年2月7日—3月3日.
[4] 唐納.清算軟性電影論[N].晨報·每日電影,1934年6月15日—27日.
[5] 塵無.清算劉吶鷗的理論[N].晨報·每日電影,1934年8月21日.
[6] 魯思.駁斥江兼霞的《關于影評人》[J].現代演劇,第1期(1934年12月20日).
[7] 魯思.論電影批評底基準問題[N].民報·影譚,1935年3月1日—9日.
[8] 劉吶鷗.中國電影描寫的深度問題[J].現代電影,第1卷第3期(1933年4月6日).
[9] 穆時英.電影批評底基礎問題[N].晨報·每日電影,1935年2月7日—3月3日.
[10] 黃獻文.對三十年代“軟性電影論爭”的重新檢視[J].電影藝術,2002,(3).
[11] 唐納.清算軟性電影論[N].晨報·每日電影,1934年6月15日—27日。
[12] 嘉謨.電影之色素與毒素[J].現代電影,第1卷第5期(1933年10月1日).
[13] 黃嘉謨.硬性影片與軟性影片[J].現代電影,第1卷第6期(1933年12月1日).
[14] 嘉謨.軟性電影與說教電影[N].晨報·每日電影,1934年6月28日,7月2—4日.
[15] 江兼霞.關于影評人[J].現代演劇,第1期(1934年12月20日).
[16] 羅浮.“告訴你吧”——所謂軟性電影的正體[N].大晚報·火炬,1934年6月21日.
[17] 馬新國.西方文論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The Dispute Between“Soft Film”and“Hard Film”in the 1930s
Ou Menghong
(College of Arts,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nan,Yueyang414006,China)
in the 1930s,there was a noticeable dispute between“soft”and“hard”film in the filmdom.
This dispute was between“the Left”film critics and the“soft film”critics,touched the nature of film arts,content and form,artistry and tendentiousness,and the criterion of criticism,etc.This dispute offered powerful reference for us to totally understand“the Left”films’theory and criticism,“soft film”theory and criticism,“the Left”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and the new sensation concept.
the dispute between“soft film”and“hard film”;the views of“soft film”;theory and criticism of films
J9
A
1673-0429(2011)06-0013-08
2011-10-20
歐孟宏(1976—),男,湖南理工學院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戲劇影視文學。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1932—1937年中國左翼電影研究”(項目批準號: 10YJC76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