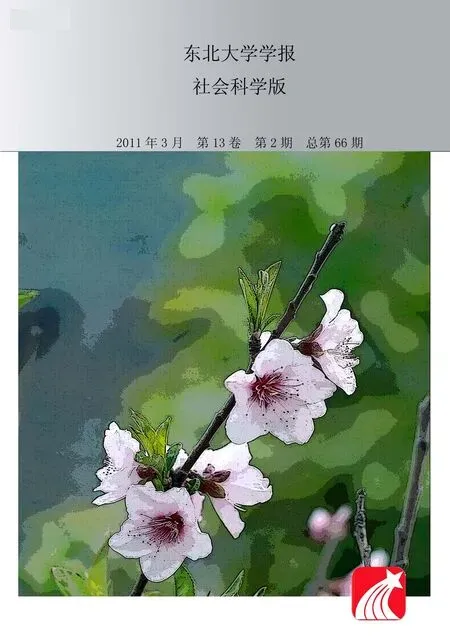“應該”和規范的邏輯前提
楊 松
(廈門大學哲學系,福建廈門 361005)
我們知道,不管是技術規范還是社會規范,在使用語言文字進行表達時都必須使用某些邏輯算子,以體現其對行為的指示功能。“應該”就是人們表達規范時最常用的邏輯算子之一。我們經常通過說“應該如此這般”來要求被規范的對象做到規約的內容。不過,在我們使用“應該”來表達規范的時候,還須要考察一下規范的邏輯前提,指出規范存在的合邏輯性問題,并且力圖通過這種考察說明,“應該”與規范的邏輯前提之間的密切關系。
一、規范存在的邏輯前提
“規范是調控人們行為的、由某種精神力量或物質力量來支持的、具有不同程度之普適性的指示或指示系統。”[1]那么,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規范要能夠產生,必須具備什么樣的條件”。這里涉及規范存在的邏輯前提問題,即要說明規范何以存在的可能性。我們認為,規范存在的邏輯前提至少存在以下兩點:
第一,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是充滿各種可能性的世界,因此針對某個問題存在各種選擇。我們發現,不管是技術規范還是社會規范,都是對某種行為選擇的引導。從直觀層面上說,存在的基本選擇是關于“是否”的選擇。比如我們說:“應該孝敬父母。”這里存在的選項至少有兩個,即孝敬父母和不孝敬父母,規范在這里的作用是將行為者的選擇引導到符合我們日常人倫要求上來(至于為什么要選擇孝敬父母是因為規范本身具有符合人的某種價值取向的特性,符合人們趨利避害、趨樂避苦的內在目的性[1])。另外我們不一定僅僅在“是否”層面上作出選擇,因為“是否”的選擇首先建立在二重語值的基礎上,事實上我們生活中不只是存在二重語值。僅僅在最基本的“是否”層面上的選擇往往不提供更多的信息。例如我們存在這樣的規范:“應該說真話!”當然,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在“說真話”和“不說真話”之間作出選擇引導的一種規范,但是事實上,這個規范的選擇域不僅僅是存在“是否”二重語值中的,而是存在“說真話”、“不說話”和“說假話”這樣的三重語值。單純地認為“應該說真話”僅僅是關于“是否”層面上的判斷,不能將其實際存在的選擇域表現出來,也不能說明該規范實際上要引導出的所有可能的選擇。所以,當人們提出“應該說真話”這一規范時,實際上是因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說真話”、“不說話”和“說假話”三種選擇,所以該規范判斷實質上是引導人們在三種行為中進行選擇:人們首先可以任意選擇是否要說話,其次在選擇“說話”的情況下,該規范就接著引導人們在“說真話”和“說假話”之間選擇。
因此,既然我們生活的世界存在至少兩種、有時候更多的選擇,那么我們行為的途徑就不是唯一的,而是存在各種可能性。正如在購買蘋果時,如果只有一個蘋果,那么我們根本無從選擇,只能說就買這一個;但是當面對一大堆蘋果可供我們選擇的時候,那么買任何一個蘋果都是有可能的。這時候就需要一種指導,告訴我們選擇什么樣的蘋果。同樣,正是在現實生活中存在各種各樣不同的選擇,我們才有制定規范的必要。如果我們實際上對一切事物的安排僅僅只有一種可供選擇的行為,那么面臨的將是唯一的行為方式,就沒有制定規范以引導選擇的必要。可見,規范存在也就須要預設“多”而非“一”,也正是因為現實生活中存在“多”,所以在多樣化的選項面前,我們要在選擇之前進行比較,判斷孰優孰劣,最終形成關于行為的指示(即“規范”)。“在‘自古華山一條道’的宿命中,人的任何行為均無所謂優劣、善惡,正是在‘條條大路通羅馬’的背景下,不同道路的選擇才有了優劣善惡之別。選擇的本體基礎是可能性空間,它反映在人身上即自由。”[2]當然,這里強調的自由不是單純的人身自由,還包括意志自由,由此引出規范存在的另一個邏輯前提。
第二,我們在面對各種可能存在的選擇時,可以自由地作出決定。盡管我們面前的道路是多樣的,存在各種不同的選項,但是如果我們并非具有自由意志,而是如同被線控制的木偶一般,一直都是身不由己,沒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選擇的可能,那么人們就沒有必要制定規范。因為,規范就是要在人們面對各種選擇的時候,通過某種精神力量或者物質力量的支持來要求人們選擇規范本身所倡導的道路,是對人們自由意志的某種限制。拿上面買蘋果的例子來說,正是因為我們在面對大量的蘋果的同時,可以自由地進行選擇,我們才可能訴諸某種指導,希望從“多”中選擇“一”。如果事先我們已經被命令必須買顏色發青的蘋果,那么就沒有必要在面對這些五花八門的蘋果時猶豫不決,更不需要別人指點哪種蘋果才是好的,直接買青蘋果就可以了。我們同樣可以看見,在法律上,對精神病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自由意志,對于他們來說根本不能對面前的道路自由地選擇,由于精神錯亂,只能被迫作出身不由己的決定,在他們受精神疾病控制的時候,規范是不存在的,因此就不存在所謂“違規”的情形。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為什么規范都是要引導人的行為選擇,因為對于自然界來說不存在自由意志,沒有進行規約的必要,我們可以規定士兵每天應該幾點起床,但是一般沒有辦法規定向日葵應該幾點開花。
另外,對于規范來說,它事先預設了這樣一個前提:如果我們的意志有所不同的話,對行為的選擇是不一樣的。如果人們不管在面對多種選擇的時候擁有何等自由的意志,最終的選擇都只能是某一個確定的行為的話,規范也依然沒有存在的必要。對此最極端的表現就是一種宿命論的觀點,即認為不管我們如何自由地選擇,事情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即通過作出“不管我如何意愿,最終都……”這樣的陳述來否認不同選擇的可能性。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意志有所不同的話,總會有不同的行為表現。在買蘋果的時候,如果沒有受到強迫,在自由決定的時候,人們總是會選擇是否買這一個蘋果,做出的行為總是不同----存在買和不買兩種不同的行為。這就表明,如果我們在實際生活中都是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來決定的,選擇后的行為總是有所不同,即我們選擇的事情會發生,而不選擇的行為不會發生。這里我們暫且將行為的結果擱置不看,就是說即使做A和不做A的結果都是導致X的發生,但是我們畢竟在行為上是有所不同的,我們對是否做A予以選擇。而規范恰恰是以行為為調整對象的指示系統,它是通過對不同行為的優劣、善惡判斷來引導人們的選擇。如果在病人垂危的時候,無論醫生竭盡全力搶救卻未能成功還是放任病人不管,最終都難免導致病人的死亡,我們是否可以說既然兩種行為的結果都是一樣的,那么它們之間不存在什么不同,選擇其中的哪種行為是無關緊要的呢?顯然不能!其次,不同行為總是會導致不同的結果,因為一個原因往往會產生多個結果,在某一個結果上也許是相同的,但是在其他方面總是會有所不同,而這種不同最集中體現在價值維度上。因此綜合看來總是存在結果善惡的不同,而規范正是在對這種不同結果的價值判斷的基礎上制定出選擇的標準。我們經常說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所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因此,盡管病人最終都是要死亡的,但是醫生的救死扶傷和見死不救顯然在價值結果上看是不同的,所以醫生的職業規范的存在有其必要性。
二、“應該”、選擇與自由意志
我們已經指出,規范存在的邏輯前提之一就是有不同選項的存在,接下來規范須要作出的就是對選擇的引導,告訴我們在面對眾多的選項時,究竟要選擇哪一個或者不要選擇哪一個。
進行選擇的前提是對各種選項進行比較,而比較就必須涉及某個標準的問題。我們一般不會在一堆老鼠中進行選擇,因為盡管世界上存在許多老鼠,但是我們的目的并不指向它們,所以完全沒有必要在一堆老鼠中比較孰優孰劣。因此,如果事物完全和我們的目的沒有關系,那么我們絕對不會對它們表示關心,更不會制定某個標準以提供比較。一旦某類事物同我們的某些目的之間有聯系,那么我們就會對這些事物制定選擇的標準。比如盡管對于我們一般人來說,老鼠不是我們需求的,所以亦不會討論我們選擇什么樣的老鼠的問題,但是對于科學家來說,為了滿足實驗的需要,不得不在作為試驗品的老鼠中制定標準,選擇某些特定種類的老鼠(例如實驗中經常出現的小白鼠)。因此,“我們有時候知道或可以想象得出存在這樣一些實際情形,在這些情形中,我們或別人不得不在各種標本之間作出選擇,只有在這時,我們才會給某一類對象設定標準,才會與另一種標本相對而言來談論一種標本的優點,才會使用有關它們的價值詞”[3]。同樣,正是在對各種選項的比較中,我們從自身的目的出發(即價值取向)制定出選擇的標準,才得出某些行為比較好、某些行為比較惡的結論,才能形成對行為進行具體引導的規范。
那么,在面對眾多的選項時,我們在什么情況下才會通過使用“應該”來引導選擇呢?
假設我們現在面臨四種行為:A、B、C和D,其中根據我們的價值訴求,得出這樣的結論:做A、B和C不違背我們的價值取向,即它們具有價值非負向,而D則和我們的價值取向背道而馳,是價值負向的。那么我們首先把A、B、C和D進行區分,將D選項用一個禁止性規范予以排除:“不應該(禁止)做D”。下面,我們在A、B和C三個選項之間進行比較和選擇,產生如下兩種情況:
第一,A、B和C在同等程度上符合我們的選擇標準,任何一個都不比另外兩個更讓我們滿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A、B和C當中的任何一個的選擇都是正確的,而且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一定要選擇三項當中的某一項,即我們只能說:“你可以選擇A,也可以選擇B,當然一樣可以選擇C,而且你的任何一個選擇都是正確的,但是沒有一個行為是你應該做的”。也就是說,盡管我們一定要在A、B和C當中進行選擇,但沒有義務必須選擇其中的某一個。因此,這時候人們表達規范所運用的邏輯算子是“可以”。可見,“可以”是在眾多選項中的弱選擇,對各個選項沒有強制。
第二,在A、B和C三種行為中,經過比較我們發現A比B和C更加符合標準,是最佳的一種選擇,因此這時候A就成為我們在三種行為中必須選擇的一項,于是我們說:“應該做A”。這時候,對于B和C來說盡管它們是價值正向的,但是由于存在更加符合我們的選擇標準的選項A,所以對A的選擇反而成為我們目前唯一正確的行為。因此,“應該”所表達出的規范實際上賦予我們一種義務,要求我們必須做到所規定的內容,它是在眾多行為選項中的強選擇,對某個特定的選項具有強制性。20世紀西方元倫理學的開創者摩爾對“應該”的問題看得尤其清楚,他說:“在我們所面臨的選擇中,如果不存在幾種同時同等正確的行為,而只有一種正確行為,那么我們應該采取的當然就是這種行為”[4]。
因此,對于“應該做A”這樣的規范來說至少傳達兩個信息:
首先,“應該”做的行為是“好的”或者說是“正確的”,受到的是肯定性的評價,它在各種可能存在的選項中具有符合某種標準的不可替代性。
其次,“應該”的行為必須是唯一的,因為“應該”一詞具有排他性。如果說“我們應該做X”,那么X必然是唯一最符合我們制定的標準的行為。如果存在行為Y或者Z可以同樣地符合預先存在的行為標準的話,那么X就不是我們應該做的行為,因為做Y或者Z完全可以替代X獲得相同的肯定性的評價。當存在X、Y、Z三種同樣符合要求的行為時,那么做任何一種行為都是正確的,但是沒有一種行為是應該做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使用的邏輯算子是“可以”,我們說“你可以做X,也可以不做X”。由于“應該”和“可以”之間存在這種區分,所以導致形成的規范類型也不相同。在使用“應該”和“不應該(禁止)”時,由于面臨的選項是我們必須做或者不做的,所以我們可以把這類規范統一稱為義務性規范。而對于使用“可以”的規范形式,由于存在相當的各種選擇,所以對任何一種行為的選擇都是可以的,我們把選擇的權利歸屬于當事人,因此稱之為權利性規范[5]。
對于“應該”和對選項的選擇之間的聯系,我們已經作了比較詳細的分析,但是還須要進一步注意一個問題:“應該”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有關于如何選擇,而且涉及對意志的控制。由于我們的意志是自由的,在選擇的時候沒有被教唆和掌控,所以對任何一個選項的選擇都是可能的,這時候通過“應該如何”表現出來的規范體現了對自由意志引導下的自由行為的限制,要求行為者不能隨心所欲地任意而為,而必須做“應該”引導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應該”的存在,也意味著對人們自由意志的肯定。在上面的例子中,根據對A、B、C和D的比較,我們固然知道最好的行為是選擇A行為,但是如果我們說“應該做A”,不僅因為A在與其他行為比較后具有優越性,而且還在于我們本來可以在四種行為中作出任意選擇。假設我們沒有自由的意志,注定受控制要做A,那么盡管A是最好的行為,但是我們不能再說“應該做A”了,因為我們根本不具有不做A的可能性,A是我們必然的行為,而其他選項基本等于消失,因此也不存在比較的可能性,選擇更加無從談起。或者我們的意志不是被決定的,而是隨機分配的,同樣對A、B、C、D四種行為的選擇就是隨機的,選擇任何一種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這仍然不是我們意志自由的表現,因為我們意志自由表現在我們對意志的可控制性,能夠自由決定做什么,隨機分配的意志同樣不能被我們掌握,通過“應該”規范行為的目的仍然不能實現。因此強調意志自由在“應該”的研究中是具有巨大意義的,一旦在社會生活中形成“應該如何”的規范時,我們始終應該意識到,這雖然是在限制選擇,但卻是對人的自由意志的確認。
三、選項和自由意志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在面對一系列選項的時候,只有最符合我們從自身目的出發而制定的標準的行為才是我們唯一應該做的,通過規范表達出來就是“應該如何”。不過,現實情況往往不如我們想象得那么簡單,因為選項盡管是存在的,但是我們究竟應該把哪些選項列入選擇范圍呢?
在國外,一些學者之間存在“可能主義”(possibilism)和“現實主義”(actualism)的不同觀點。事實上,“可能主義”正是我們日常在考慮哪些內容可以列入選擇范圍時經常會采用的觀點。它是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我們所應該做的行為是在一系列我們可能面臨的所有相關選項中最好的。而“現實主義”則這樣認為:我們應該做的就是在現實中能夠做的事情當中最好的行為。兩者在實踐中是存在分歧的,我們可以通過下面的例子來說明雙方的分歧:
瓊斯開車跟在一輛行駛很慢的卡車后面要穿過一個隧道,而且在隧道里改變車道是違法的,瓊斯如果這么做了就會破壞交通。然而,也許是她沒有意識到這是違法的,或者是她很匆忙,她打算駛入超車道里。如果她改道卻不加速,那么隧道里的交通會因此比她改道并且加速受到更嚴重的破壞。如果她加速卻不改道,那么她的汽車就會和卡車相撞[6]。
在這個例子里面,瓊斯究竟應該怎么做?她是否應該加速?可能主義認為,考慮到所有的可能性,瓊斯面前存在如下的幾個選項:第一,不加速并且不變更車道;第二,變更車道并且加速;第三,變更車道但是不加速;第四,不變更車道但是加速。現在,要想知道瓊斯應該怎么做,只要比較這四個選項就可以了:通過比較,人們發現,第一個選項最大程度地符合了人們的價值要求,因此第一種行為就是“應該的”。但是對于現實主義者來說,當前的選項并沒有可能主義者所提出的那么多,因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情況就是瓊斯已然要換車道,所以根本不存在上述的第一種和第四種選項,只有中間的兩種選項擺在她的面前,通過比較,第二種選項才是“應該的”。現實主義強調,對于瓊斯來說,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她已經是一定要變道的,因此她所要求得到的建議就是在她變道的情況下,究竟應該加速還是不加速。誠然,現實主義者也承認,對于瓊斯來說最好的行為就是既不加速也不改變車道,但是在現實條件下,“應該”所解決的必須是當下的而不是理想狀態下的問題。我們已經知道瓊斯要變更車道,因此在此時瓊斯面臨的選項只有中間的兩個,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于她來說最應該做的行為當然是加速[7]。
事實上,現實主義和可能主義都承認,在各種選項中,“應該”是指最符合人們目的的,雙方爭論的焦點并不在于如何來選擇,而是在于可供選擇的選項究竟是什么。現實主義認為,選項的設定應該從當前所處的情況出發,充分了解我們現實已經做了什么,然后在此基礎上確定目前面臨的選項,從而在這些現實的選項中確定何者為“應該”。由于瓊斯是一定要變更車道的,這是我們確定當前選項的基礎,所以完全沒有必要考慮到如果不變更車道會怎么選,當前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加速。但是對于可能主義來說,我們不僅要考慮在目前情況下的選項,而且要窮盡所有可能存在的選項,在這所有選項中予以比較,考慮何者為“應該”。可能主義不一味地接受當前的現實狀況,而是考慮在理想狀況下,所有可能存在的選項。在現實中,瓊斯固然已經變道,但是僅僅考慮現實選項從而確定“應該”是不準確的,“應該”只能從對所有可能選項的比較中誕生。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可能主義和現實主義對“應該”的功能理解是不同的。“應該”一詞存在兩種基本功能:首先是情態動詞或者關系謂詞(其本身又是價值詞)來連接主詞部分和謂詞部分;其次是作為建議的算子引導一個具體的建議[8]。現實主義強調選項的現實性主要是因為在當前的情況下,討論如果瓊斯變道和如果瓊斯不變道只是理論上的可能,現實情況是瓊斯變道了,我們考慮她是否應該加速的問題。因此,當現實主義說“瓊斯應該加速”的時候,其實是在當前情況下把“應該”看做一個引導建議內容的算子,告訴她目前應該怎么做。從可能主義的觀點來看,“應該”是對全部情況進行羅列以后挑出的最符合選擇標準的選項的表達,“應該”的用法不是說提供什么現實的建議,而是指出理想狀態下的最優選擇,這時候的“應該”是一個價值詞。從某種程度上說,可能主義是一種對現實主義的“秋后算賬”,它往往表達“本應該”的含義。事實上,現實主義者也看到他們和可能主義不是完全對立的,雙方存在可調和性,所以現實主義者杰克遜(Frank Jackson)和帕格特(Robert Pargetter)說:“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否應該做某事的答案,那只要看看目前所包含的一系列行為和如果不做的話,他會怎樣來取而代之;如果你想要知道在后來的某段時間里是否應該做某事,就要審視那時可能存在的所有相關的行為”[7]。
不過在討論完現實主義和可能主義的爭論之后,我們關于選項的確定仍然還存在一個事關意志自由的問題,因為雖然不管可能主義還是現實主義都承認我們面前選項的存在,但是如何知道什么才是我們的選項呢?杰克遜等人舉例說,如果我今晚要去朋友家參加一個宴會,我現在很猶豫要不要開車前往,因為一旦我在宴會上喝醉了,那么酒后駕車顯然是違法的。但是如果我能夠克制住自己,堅持在宴會中滴酒不沾,那么開車去然后開車回來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那么,現在的我究竟應該開車前往嗎[7]?
這里我們須要考慮一下,面臨的選項究竟是什么。將選項最大化,我們得到的選項有:第一,開車前往并且沒有喝酒;第二,開車前往但是后來喝酒了;第三,沒有開車前往而且沒有喝酒;第四,沒有開車前往而且后來喝酒了。顯然,這里不應該的事情就是第二條,其他情況都是允許的。不過,現在我作為赴宴者要問的是,我是否應該開車去?可能主義回答也許是除了第二種情況,其他情況都是允許的。現實主義的回答必然說這取決于現在你自己決定要不要喝酒了,我可以告訴你當面臨喝酒情況和不喝酒情況下的建議。因此,這里是否要開車取決于我對自己是否會喝酒的認識,而且一旦我確定我是否要喝酒,那么面臨的選項就會被固定下來,“是否應該開車前往”的問題也可以得到合理地解答。因此,選項的確定受到我是否具有自由意志的影響,只有我能夠自由地決定自己會不會喝酒,才能決定擺在面前的選項究竟是什么。杰克遜等人要我們設想,如果不是我,而是我的一個朋友要去參加宴會,向我征求意見是否應該開車前往,我如何能夠幫助他確立當前的選項呢?因為我根本沒有辦法確定他是否會喝酒,只能給出“如果……,那么……”的語句來概述他在不同的情況下應該干什么,并且指出唯一禁止的行為是開車前往但是后來喝酒。不過他一定會抱怨說我在問你該不該開車,不是在問“如果……”的情況下我應該怎么辦,這時我怎么可能幫助他確定選項?我不具有決定他是否會喝酒的能力,這完全不取決于我而取決于我的朋友,因此我不能給出現實主義視野下的建議。反之,如果我自問我是否應該開車前往的時候,只要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就完全可以探索出面臨的選項。可見,“應該”的行為就是當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確定選項之后,通過比較選項得出的最符合人們要求的行為。
參考文獻:
[1] 徐夢秋. 規范何以可能[J]. 學術月刊,2002(7):56-59.
[2] 周建漳. 歷史及其理解和解釋[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60.
[3] 理查德·麥爾文·黑爾. 道德語言[M]. 萬俊人,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22.
[4] 喬治·愛德華·穆爾. 倫理學[M]. 戴楊毅,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16.
[5] 徐夢秋. 規范的類型和功能[J]. 哲學動態,2006(6):10-11.
[6] Goldman H S. Doing the Best One Can[M]∥Values and Morals. Holland: Reidel,1978:186.
[7] Jackson F,Pargetter R. Oughts,Options,and Actualism[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86,95(2):233-255.
[8] Williams R L. Ought,and Logical Form[J]. Analysis,1987,47(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