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顛覆:《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shí)代》的后殖民解讀
顏曉川,馮 溢
(東北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遼寧沈陽 110819)
2003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得主J.M.庫切是典型的后殖民作家。他的小說一貫的主題就是關(guān)注主流話語之下的個(gè)人敘述,關(guān)注被壓迫者的痛楚與心路歷程,努力發(fā)掘被歷史宏大敘述所掩蓋的個(gè)人歷史,進(jìn)而反思殖民者的“自我”與邊緣化的“他者”之間的關(guān)系。《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shí)代》就是其中一部檢視殖民關(guān)系、抵制殖民主義的力作。故事以20世紀(jì)80年代的南非內(nèi)戰(zhàn)為背景,講述了一個(gè)卑微的生命在充滿戰(zhàn)爭、軍隊(duì)和種族隔離的社會中苦苦掙扎,渴望尋找生命綠洲的故事。天生弱智但心地單純的黑人園丁邁克爾·K與母親相依為命,他打算帶著患病的母親離開充滿戰(zhàn)亂的開普敦,到鄉(xiāng)村去過寧靜的生活。在顛沛流離的途中母親離世,K獨(dú)自漂流在路上。在政府、軍隊(duì)等各種殘暴勢力的壓迫和驅(qū)趕下,他失去了身份,失去了話語,一次又一次被投入營地,無法逃離受他人掌控的命運(yùn)。但他的逃離之心并未因此改變,最后逃入了空無一人的深山,過著動物般的原始生活,卻也因此達(dá)到了某種程度的自由。作品的主人公邁克爾·K是個(gè)謎一般的人物,他智力殘缺、沉默不語、離群索居。庫切如此再現(xiàn)殖民地他者形象卻并非出于白人固有的種族偏見,而是庫切特有的敘事策略:保持他者的他者性,從而展示權(quán)力系統(tǒng)的運(yùn)作過程,揭示敘述背后的霸權(quán)話語來顛覆和解構(gòu)政治權(quán)威。諾貝爾獎(jiǎng)授獎(jiǎng)詞精辟地評價(jià)這部作品:“小說描述了一個(gè)小人物的精神困境,他逃離了日益嚴(yán)峻的動亂和將要降臨的故事,卻陷入無所欲求的冷漠,并呈現(xiàn)對權(quán)力邏輯的否定狀態(tài)。”[1]228同庫切的其他作品中的被壓迫者一樣,邁克爾·K的沉默是壓倒一切的力量,令人窒息,然而恰恰是從這種沉默中顯示出一道真理的曙光,抵抗并顛覆了殖民話語與政治權(quán)威。
《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shí)代》表現(xiàn)的是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最為猖獗的時(shí)代。種族隔離制度的核心是“自我與他者”對立的二元論的復(fù)雜的意識形態(tài)。艾勒克·博埃默在《殖民與后殖民文學(xué)》中指出:“后殖民理論家們將殖民地的人民稱之為‘殖民地的他者’ (colonial other),或徑直稱為‘他者’(other)。‘他者’這個(gè)概念,主要是根據(jù)黑格爾和薩特的定義:它指主導(dǎo)性主體之外的一個(gè)不熟悉的對立面或否定因素,因?yàn)樗拇嬖?主體的權(quán)威才得以界定。”[2]即自我身份的建構(gòu)依賴于對他者的否定。
在逃亡途中,由于身體狀況很差,邁克爾被送往一家康復(fù)營地,在那里K遇到了醫(yī)官。許多批評家把這個(gè)人物看做是白人的代表,醫(yī)官對邁克爾·K的態(tài)度像許多南非白人對待有色人種的態(tài)度一樣非常矛盾。他照料K,使他恢復(fù)健康,是希望“有朝一日他就能夠重新加入營地生活,有機(jī)會穿過跑道來回大步走,喊口號,向國旗敬禮,并且練習(xí)挖坑再把它填上”[1]62。這里顯示出殖民主義的目的:幫助被殖民的他者是為了他們能夠“喊口號,向國旗敬禮”,換句話說,就是為帝國服務(wù)。正是由于這個(gè)原因,醫(yī)官才竭力保全K的性命,在慈善的名義下,殖民得以繼續(xù)。醫(yī)官虛假的、偽善的、家長式的作風(fēng)同白人話語中白人的“使命感”一脈相承。白種人把非白人想象為未開化的、沒受過教育的人,把他們看成不會自己走路的孩子,需要成人(白人)的監(jiān)護(hù),白人肩負(fù)著“拯救他者”的“使命與責(zé)任”,這反映出白人盛氣凌人的掌控欲望。在庫切的另一部小說《福》(又譯《仇敵》)中的敘述者蘇珊·巴頓對星期五也表現(xiàn)出這種家長式的態(tài)度。當(dāng)船來接他們?nèi)タ唆斔鞯男u,蘇珊堅(jiān)持把星期五也帶上:“我請你把你的人再派到岸上去,因?yàn)樾瞧谖宀恢皇莻€(gè)奴隸,更是一個(gè)孩子,這是我們的責(zé)任,不能把他自己留在孤島上,這比讓他去死更糟糕”[3]39。實(shí)際上,白人殖民者的所謂責(zé)任只是花言巧語的托辭,以遮掩鎮(zhèn)壓被殖民者之實(shí)。
醫(yī)官“好意”要恢復(fù)邁克爾·K的聲音,這樣K就不至于在歷史上“默默無聞”,而醫(yī)官掌控的欲望隱藏得更深。“談?wù)劙?邁克爾斯,……否則的話你就會白過一輩子,根本沒人注意你。……讓你的聲音被人聽到,講講你的故事!”[1]171然而,邁克爾沒有回應(yīng)醫(yī)官的“好意”----“為什么對我大驚小怪呢,為什么我這么重要?”醫(yī)官的話語反映出殖民者的焦慮,他想要迫使K去屈服他的掌控意愿,他和蘇珊·巴頓幫助星期五恢復(fù)發(fā)聲一樣:“我告訴自己同星期五講話,去教他走出黑暗與沉默,但是那是真相嗎?有時(shí)仁慈離我而去,我使用語言是用最簡便的方法讓他屈從我的意志。”[3]60同樣,醫(yī)官要把K帶回到語言世界的努力實(shí)際上也是讓K屈服于他的意志。如果K說出他的故事,似乎他的身份認(rèn)同問題給他帶來的痛苦就都可以解決了。因此,醫(yī)官要“使你(K)的生活有些內(nèi)容”實(shí)際上是在要求他作為主人的身份有些內(nèi)容。然而,K看破了“好意”的面具,他頑固地保持沉默,醫(yī)官的身份認(rèn)同因此受到威脅。只要醫(yī)官不能把K整合到自己的故事中,他主人的身份就是不合法的,他存在的意義就是令人生疑的。Michael Marais在《帝國的詮釋》一文中對于庫切作品中的沉默的作用,闡釋了相同的觀點(diǎn):“由于他們的(權(quán)威者的)統(tǒng)治地位取決于他(被統(tǒng)治者)對于他們的主人地位的承認(rèn),他的沉默否定了他們的地位,而且因?yàn)樗麄兊纳矸菀赃@個(gè)地位為前提條件,因而他的沉默挑戰(zhàn)著他們的現(xiàn)實(shí)”[4]75。沉默具有積極的意義,變成了反抗權(quán)威的力量。從這個(gè)角度說,沉默便不是屈從于他人話語的表示,而是他者所具有的反抗策略,這樣就可質(zhì)疑統(tǒng)治者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因此,盡管醫(yī)官再三勸說K講話,K就是保持沉默,以這種形式抗拒當(dāng)權(quán)者對他掌控的企圖。
話語實(shí)際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壓制邊緣意識形態(tài)的場所,人類的語言就是在不同的權(quán)力斗爭中建立起來的,被社會使用的話語其實(shí)是奪得統(tǒng)治地位的力量的話語,相反的話語則遭到壓制,不同的話語被排擠,在話語存在的地方就存在著權(quán)力展示。歷史的敘事即是權(quán)力的展示。新歷史主義的著名理論家海登·懷特認(rèn)為,歷史其實(shí)是像文學(xué)一樣,是一種敘事,“事實(shí)上,敘述始終是,而且仍然是歷史書寫的主導(dǎo)模式”[5]。庫切提出“歷史是將意義強(qiáng)加于時(shí)間和事件之上,但那時(shí)間和意義實(shí)際上是語言,它們是語言”[6]。庫切明確意識到在歷史的描述中意識形態(tài)被編碼入語言:
“歷史并非現(xiàn)實(shí):歷史是一種話語,小說也是一種話語,是另外一種話語。不可避免地,在我們的文化中,歷史將以不同程度的力量,試圖占據(jù)首位,宣稱自己是一種主人的話語形式;而像我這樣的人們也就不可避免地宣稱歷史只是人們彼此講述的故事。”[7]
歷史因?yàn)槠鋽⑹鲂圆粌H不可能體現(xiàn)真實(shí)和真理,而且往往成為擁有權(quán)力的人以歷史之名壓迫異己的手段。因此庫切把建構(gòu)歷史看做是暴力的敘事,一種暴力的再現(xiàn)。歷史暴力的再現(xiàn)模式表現(xiàn)在承認(rèn)同者,排除他者。因此,為了不再重蹈“建構(gòu)歷史”的覆轍,庫切用沉默去再現(xiàn)他者。他的小說總是呈現(xiàn)出“再現(xiàn)無力”,對他者的拒絕再現(xiàn)或無力再現(xiàn)即是對“歷史暴力的再現(xiàn)模式”的挑戰(zhàn)。歷史再現(xiàn)模式是通過把他者故意降低為客體而否定了他者的差異性。通過寫作的行為,作家可以敘事再現(xiàn)的形式反復(fù)地進(jìn)行歷史再現(xiàn)的暴力,因?yàn)楣P的力量同歷史的權(quán)威相似,如果敘事再現(xiàn)也是基于原來的社會關(guān)系,文學(xué)就變成了歷史話語的重復(fù)。
如果沒有了語言,否定的意義就無法建構(gòu)起來。失語的他者不能為自己言說,自我就無法進(jìn)入他者的經(jīng)驗(yàn),K的語言缺失像一道墻一樣把K同他人用語言去獲得權(quán)力的愿望隔絕開來。醫(yī)官無法理解K,他不僅不能通過語言了解K,他的多舌使得K的他者性變得更加顯著,K的意思卻越發(fā)讓人難以捉摸了。醫(yī)官越是想搞清K的意思,K就滑得越遠(yuǎn),所以醫(yī)官把K稱為“一個(gè)了不起的逃跑藝術(shù)家”[1]203。醫(yī)官努力描述K的故事,通過言語捏造K存在的意義,他是想把K納入語言系統(tǒng),剝奪K的實(shí)質(zhì)內(nèi)容。貫穿于這部小說始終,醫(yī)官所做的就是通過語言讓K的存在變得有意義,給K“一些內(nèi)容”,這樣他就不會默默地死去,并被埋在跑馬場的某個(gè)角落的不知名的坑中[1]186。然而,語言并不能給K任何內(nèi)容,也不能為其創(chuàng)造任何意義,因?yàn)镵已經(jīng)超越語言的媒介,而他的存在也超越了語言的否定。與醫(yī)官不同,K不依賴語言去交流,也不需要語言去建構(gòu)他的存在。
庫切認(rèn)為,文學(xué)的責(zé)任在于恢復(fù)他者的他者性。他在小說中致力于讓缺席的他者浮出歷史水面,讓不可見者重新可見,因?yàn)槌聊推茡p的軀體已經(jīng)作為無聲的語言為他筆下星期五、維庫埃爾、邁克爾·K等被壓迫者言說。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反抗力量,是拒絕納入權(quán)力話語體系的一個(gè)表征。因此,再現(xiàn)沉默----他者最顯著的特征,事實(shí)上起到了“尊重他者,為他者負(fù)責(zé)”的作用。庫切雖然不能使用他者的內(nèi)部語言為他者言說,但對自己使用的語言權(quán)威進(jìn)行顛覆的行為本身,對他者建構(gòu)文化的自我意識具有重大意義。
在邁克爾·K的時(shí)代,個(gè)體身份遠(yuǎn)沒有一個(gè)人在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社會身份和地位重要。這是一個(gè)沒有人可以選擇是否可以在此生活的時(shí)代,沒有可能全然蔑視歷史的桎梏。然而邁克爾·K把自己貶低到如蠕蟲一樣的生存狀態(tài),通過這種生存方式,至少可以逃避“掉進(jìn)歷史的大鍋”[1]185。正如邁克爾·K在小說結(jié)尾處所想:“我已經(jīng)逃離了那些營地;也許,如果我躺得位置很低,我也能逃過人們的博愛。”[1]219《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shí)代》暗示著總有一個(gè)角落可以躲開歷史的范疇,在那里生活以自由的旋律流淌。
在后殖民文學(xué)中,大多數(shù)作家認(rèn)為自己的責(zé)任是肯定并恢復(fù)他者聲音的價(jià)值,這樣他者就可以同藉由語言建立起的權(quán)威和壓迫作斗爭,再現(xiàn)他者的唯一方法就是賦予他說話的權(quán)利,即使這意味著使用殖民者的語言。所以“為了能夠進(jìn)入政治領(lǐng)域,把語言作為一種政治武器來改造和使用是極其必要的”[4]73。在這個(gè)意義上說,沉默就變成了他人語言的被動的犧牲品。然而,庫切的策略“同大多數(shù)后殖民作家所傳達(dá)的感覺都不同”[4]73。因?yàn)檎y(tǒng)語言是殖民者慣用的壓迫工具,反抗殖民統(tǒng)治的第一步就是對正統(tǒng)語言的棄置、顛覆與瓦解。他者一旦使用殖民者的語言來重塑自我,便失去了帝國界限之外的身份,再次把自我納入到帝國話語中來。在庫切對沉默他者的再現(xiàn)中,賦予沉默以力量:沉默是他者保持他者身份以抵抗西方同化的手段。盡管沉默在表面上使得他者在“正統(tǒng)的”“權(quán)威的”語言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卻是對正統(tǒng)語言的棄置,起到了保持他者的他者性的作用,沉默變成了抵制殖民者語言的手段。邁克爾·K超越語言而存在,語言的缺乏幫助K逃脫外在的壓迫。“K令人難以捉摸的另一面即是他的沉默,沉默既是被剝奪公民權(quán)的標(biāo)志,也是抵抗的表現(xiàn)形式。”[8]庫切沒有引用他者的聲音來反抗權(quán)威,而是把沉默作為一種消極抵抗。支配性與否定性總是與語言相連。K的沉默,同《福》中的星期五和《等待野蠻人》中那個(gè)蠻族姑娘的沉默一樣,充滿了不能言說的故事。“這些人不能說話或拒絕說仇敵的語言,但他們的沉默就好像千萬人在一起的吶喊。”[9]正如《福》中蘇珊·巴頓所觀察到的:“在每個(gè)故事中都有沉默,一切視線被遮蔽,一切話語沒說出口,直到我們說出沒被說出口的話,我們才進(jìn)入故事的中心。”[3]141換句話說,承認(rèn)他者的非語言存在是理解整個(gè)人類故事的關(guān)鍵。因此,在南非語境中,邁克爾·K的沉默被賦予了抵抗的政治意義,他的沉默是逃避主導(dǎo)話語的策略,也是抵制殖民者語言的策略。邁克爾·K的沉默“塑造出一個(gè)機(jī)警的、不斷被邊緣化的敘述主體,他靈巧地穿過權(quán)力的縫隙,保持了他民族的完整性,但卻并沒有大聲呼吁統(tǒng)治者的包容,也沒有夸大他自己的合法性和正統(tǒng)性”[10]。
庫切意識到抵抗帝國話語的方法并不是通過給予他者一種聲音作為“政治武器”來創(chuàng)造一個(gè)反對的力量,因?yàn)檫@樣做,他者仍然被放在權(quán)力話語結(jié)構(gòu)之中。正如賽義德所說:“如果權(quán)力用于壓迫,用于宰制,用于操縱,那么任何抵抗權(quán)力的東西都不能在道德上與權(quán)力處于平等的地位,不能簡單地成為抵抗權(quán)力的武器,抵抗不能與權(quán)力勢均力敵。”[11]因此庫切對于權(quán)力抵抗的觀念,不是要賦予他者另外一種聲音,創(chuàng)造一個(gè)“勢均力敵”的權(quán)力,而是對于權(quán)力的讓渡。K不是用語言而是用沉默去抵抗,才能瓦解和顛覆語言系統(tǒng)的界限與規(guī)則。沉默并不是言說的缺席或言說的無能,而是另外一種語言,像音樂一樣,是替代有聲語言可行的選擇。邁克爾·K的沉默含義豐富。我們可以從敘事者的描述中看到他有自己的思想(他是一個(gè)園丁),有自己的判斷(是去參加游擊隊(duì)還是留下來侍弄花園),有自己的幻想(使得荒蕪的農(nóng)場重新繁榮起來)。他的故事是所有南非黑人的故事----他們的故事非常宏大,遠(yuǎn)非官方正式語言所能傳達(dá)。盡管邁克爾·K不能用語言表達(dá)自己,但他可以像星期五一樣用音樂和舞蹈的“符號”表達(dá)自己。“他(星期五)只用音樂和舞蹈表達(dá)自己,對于言語來說,他的言語就像叫喊。”[3]142這就是星期五同世界交流、訴說他的故事的方式。“用藝術(shù)的方法,他的真實(shí)的故事才能被聽到。”[3]118通過藝術(shù)的方法,我們才能夠接近星期五,也只有用藝術(shù)的方法我們才能看清邁克爾·K的本性。
“藝術(shù)”是解讀K的關(guān)鍵。邁克爾·K的園藝也是一門藝術(shù),他以這門藝術(shù)手段靜靜地同外界交流,通過耕種土地,K表現(xiàn)了自我也發(fā)現(xiàn)了自我。我們須要去傾聽他的沉默,去關(guān)注他的園藝意涵----K表達(dá)自我的符號藝術(shù)。在無處不在的語言暴力中,藝術(shù)為沉默的人們提供了表達(dá)自我的出口。盡管他們沉默不語,星期五的音樂與舞蹈、邁克爾·K的園藝藝術(shù)繼續(xù)以自我的方式發(fā)出聲音,敘說他們自己的故事。
邁克爾·K對政治壓迫的抵抗不僅展現(xiàn)在他的沉默中,而且展現(xiàn)在他的園藝中。在《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shí)代》這部小說中,K與土地的聯(lián)系意味著自然是被壓迫者恢復(fù)自我和獨(dú)立性的地方。土地對于邁克爾·K來說具有多重象征意義:首先,土地是母親形象的象征。在土地中K可以獲得一種歸屬感:“我要住在這里,他想到:我要永遠(yuǎn)住在這里。這里是我母親和姥姥生活過的地方。”[1]122其次,在自然與文明截然相反的兩極,自然是人們可以逃避所謂“人類文明”的地方。在南非社會,自然界是K得以逃避被奴役的厄運(yùn)的地方,大地象征著拯救人類之地。
在南非文學(xué)的傳統(tǒng)中,土地,尤其是南非的卡魯高原是神話的一部分。阿非利肯人總是用飽滿的熱情描繪神秘的平原和丘陵,把這片土地寫成神話。神話中的英雄總是遠(yuǎn)離人類,遠(yuǎn)離人類的墮落。在《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shí)代》,邁克爾·K與土地的親近暗示了逃避奴役與戰(zhàn)爭。卡魯高原不僅為邁克爾·K提供了逃離社會壓迫的場所,也為他提供了施展藝術(shù)的地方。只有作為園藝師,他的生命才有意義。邁克爾·K似乎繼承了阿非利肯人田園生活的傳統(tǒng)理念:“從一面的地平線到另一面的地平線,滿眼看到的都是空蕩蕩的大地貌。他爬上一座小山,仰面躺下,諦聽著茫茫的沉寂,感覺著和煦的太陽溫暖一直滲透到他的骨髓里。……他能夠理解了,為什么人們會撤到這里來,把自己隔絕在方圓多少英里的沉默、靜謐之中。”[1]57
但K無須將土地?cái)M人化,也無須神化,因?yàn)閷λ麃碚f,南非的地貌不會帶來任何迷思,沒有神秘感。K住到一個(gè)洞穴里,與自然合而為一,同時(shí)他也放棄了任何人類建構(gòu):他不想“把一根根木樁釘進(jìn)地里,豎起一道道圍欄”[1]120,把大地分割開來,他認(rèn)為“試圖再建立一個(gè)新家,開展一場競爭”[1]128的想法是錯(cuò)誤的。K開始把大地看成是大地本身,無須費(fèi)力把它變成別的什么東西。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到自己的洞穴之中,“他像一條蠕蟲一樣開始向自己的地洞蠕動,他一心想的就是:讓黑暗趕快降臨吧,讓大地把我吞下去吧”[1]133。K回歸土地,自我意識和主體性開始瓦解。在荒野中,像動物一樣地生活,K逐漸遠(yuǎn)離了人類社會,從這時(shí)候開始,K逐漸抹去自我,這樣他就可以逃脫主/客二元對立的范式。他不想證明他存在的意義,他在世界的存在同土地本身的存在一樣,無須人類的解釋和釋義來確定他的實(shí)體性。庫切發(fā)現(xiàn)人與土地新的關(guān)系:人類存在的意義并不須要通過征服土地來證明,人與大地可以合而為一。雖然庫切用黑人來表達(dá)這一含義,但并不是要把土地歸還黑人,而是歸還給土地本身。從這個(gè)角度來看,可以說,土地沒有種族、性別、階級,屬于所有在上面居住的人。因此,庫切所構(gòu)建的土地是超越政治、歷史的界限,而從普世的高度、生物的層面來關(guān)注人與土地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
園藝的理念同人類生存相聯(lián)系,同人類與土地互惠的理念相聯(lián)系。邁克爾·K決定留下來伺候土地,而不去參加游擊隊(duì)叛軍,因?yàn)樗庾R到園藝的重要性:必須有人留在后方,使種瓜種菜培植花草繼續(xù)存在。一旦這根線斷了,大地就會變得堅(jiān)硬,就會忘掉她的孩子們。K找到第一顆種子,“他想起那正在拱出地面的南瓜種子,明天就是它們的末日了,他想到:我走后一天,它們就會枯萎。再過一天,它們就會干死了。……有一條溫情的線,從他這里延伸到那塊水壩旁邊的土地。……”[1]81。
這根線就是人類與土地的互惠關(guān)系。大多數(shù)的人都忽視了人與自然的這根線,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毀損土地。叛軍游擊隊(duì)在水壩旁安營扎寨,毀掉了K辛苦培養(yǎng)的秧苗,還浪費(fèi)掉了K儲存的水,把水放到了田里。與游擊隊(duì)的浪費(fèi)行為相反,K把水看做是上天賜予大地的寶物。“把從大地中流出的水儲存起來,成了K最大的愿望,他只用水泵抽取他的園子需要的水,…… 他不知道地下水如何自我循環(huán)重新變得盈滿,但是他知道揮霍和浪費(fèi)絕無好處。他無法想象什么潛伏在他的腳下,是一個(gè)湖泊還是一股流泉,是一個(gè)遼闊的地下海還是深得無底的池塘。每一次他松開制動器,那個(gè)風(fēng)車的輪子轉(zhuǎn)起來,水就流出來。這在他看來就好像一個(gè)奇跡。”[1]75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K對自然的態(tài)度已經(jīng)是宗教式的虔誠,他把大地的供給看做是奇跡。他認(rèn)識到無論是土地里流淌出的水還是生長的植物,都是與大地母親相關(guān)聯(lián)的東西,是生命的源泉,人類應(yīng)該珍視大地的恩賜。庫切似乎在暗示:人類的意義不在于與自然的分離,而在于與自然的聯(lián)系,盡管戰(zhàn)爭給地球帶來大規(guī)模的破壞,但人類的冷漠會給它帶來更大的破壞。園藝師邁克爾·K從與人類歷史逐漸疏離到與自然合而為一的過程是從被奴役狀態(tài)走向自由的過程。K對自由的爭取不是表現(xiàn)在對權(quán)力的爭奪,而是表現(xiàn)在對權(quán)力的讓渡。我們看到的K不是翻倒在“歷史的鍋爐”中,然后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而是一個(gè)“在改變歷史的進(jìn)程中,絕不比一顆沙礫有更多的奢望”的人[1]185。K并不把這片土地耕植成一個(gè)大農(nóng)場,而是只培育了一小塊地,以供他基本的生存之需,斷然拒絕現(xiàn)行的秩序中生產(chǎn)與消費(fèi)的資本主義機(jī)制。K不想在歷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希望被遺忘被忽略。在沒有人際關(guān)系的世界里,K獨(dú)自一人,用沉默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書寫著自己作為園藝師的生活故事。他兜里的種子、他種植的莊稼都在敘說著他的故事,換而言之,他的故事不是通過語言而建構(gòu)起來,而是由事物真實(shí)地呈現(xiàn)出來。盡管他不能融入他人的敘述之中,卻能輕易地同自然融為一體。隨著自然界的節(jié)奏和現(xiàn)象,他生活在一種純粹的存在狀態(tài)之中。
邁克爾·K一無所求,無所期待,園藝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因?yàn)槭撬c生命相聯(lián)系。他把自己降為如動物般的生命存在,因而逃離戰(zhàn)爭的摧殘、社會的壓迫,只有這樣,他才能從土地的角度而不是從人的角度來感知自我。K堅(jiān)信人與土地之間是互惠的關(guān)系,這個(gè)信念使得他生存下來,他口袋中的種子象征著生命的延續(xù)。在播種這些種子時(shí),K完成了生存的藝術(shù)。
南非反抗種族隔離的斗士戈迪默這樣評價(jià)這部小說的園藝主題:“在所有的信條與道德之外,這個(gè)藝術(shù)工作說明,只有一個(gè)信念:使土地保持活力,唯一的拯救來自于土地。”[12]盡管這部小說是對南非黑人所遭遇的痛苦與非人的境遇的描寫,但小說開放性的結(jié)尾也給我們帶來一絲希望。在小說夢一般的結(jié)尾,在K想象的飛機(jī)上,暗示出現(xiàn)實(shí)生存的另一個(gè)出路,另一種選擇,昭示著自由的來臨。庫切在用K與自然的合而為一暗示我們只有放棄那種基于主體性原則之上的傳統(tǒng)理性,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參考文獻(xiàn):
[1] 庫切 J M. 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shí)代[M]. 鄒海侖,譯.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
[2] 艾勒克·博埃默. 殖民與后殖民文學(xué)[M]. 盛寧,韓敏中,譯. 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22.
[3] Coetzee J M. Foe [M]. New York: Penguin,1986.
[4] Marais M. The Hermeneutics of Empire: Coetzee's Post-colonial Metafiction[M]∥Huggan G,Watson 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 M. Coetzee. London:Macmillan,1996.
[5] 海登·懷特. 后現(xiàn)代歷史敘事學(xué)[M]. 陳永國,張萬娟,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3:294.
[6] Penner D. Countries of the Mind: The Fiction of J.M. Coetzee[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9:26.
[7] Coetzee J M. The Novel Today[J]. Upstream,1988(6):2-5.
[8] Head D. J. M. Coetze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98.
[9] Parry B. Speech and Silence in the Fictions of J.M. Coetzee[M]∥Huggan G,Watson 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 M. Coetzee. London:Macmillan,1996:44.
[10] Attwell D. J. M. Coetzee: 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25-26.
[11] Said W E. 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246.
[12] Gordimer D. The Idea of Gardening[J]. New York:Review of Books,1984(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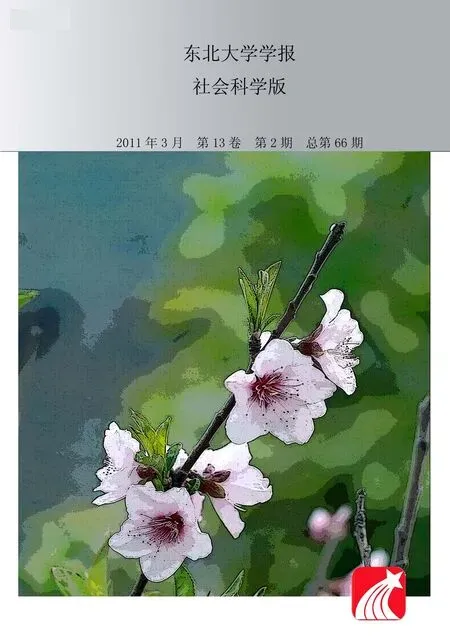 東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11年2期
東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11年2期
- 東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獨(dú)立董事、審計(jì)委員會與信息透明度
----來自深圳證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 - 基于耗散結(jié)構(gòu)理論的資源型城市創(chuàng)新能力評價(jià)
- 從“問題對話”到“方法轉(zhuǎn)向”
----“李約瑟難題”研究進(jìn)路分析 - 股份公司控制權(quán)集中及其對公司治理的影響
- 全球化視角下中國先進(jìn)制造模式動態(tài)演進(jìn)研究
----基于華為公司的案例分析 - 遭遇消費(fèi)時(shí)代的尷尬
----從消費(fèi)景觀看新世紀(jì)以來文學(xué)中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