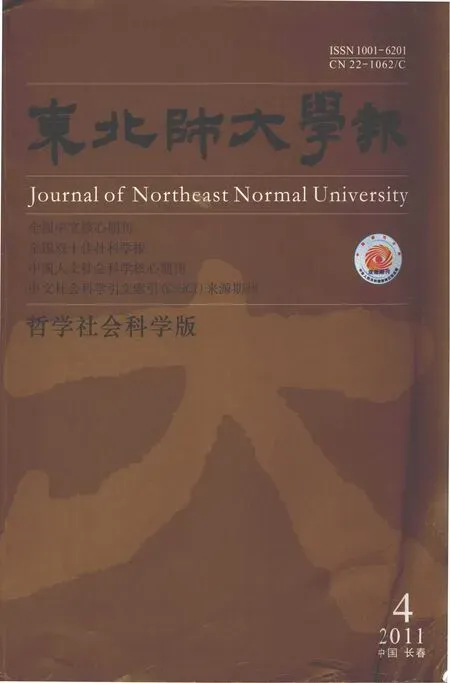略論遼朝民族政策的區域性特征
紀楠楠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吉林長春130024)
略論遼朝民族政策的區域性特征
紀楠楠
(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吉林長春130024)
遼朝民族政策的重要特征是其明顯的區域性,即按照各民族在地理上的遠近,分別采用不同的統治政策。這種區域大體上由內至外可分為核心、外圍和外延三部分,遼朝與不同區域各民族的關系存在由緊密到松散的變化,并對其分別實行直接控制、半羈縻半直接控制、純粹的羈縻和封貢三種統治方式。這種區域性民族政策是對中原王朝統治經驗的借鑒,而且其創新之處也對后世各王朝的邊疆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
遼代;遼朝;民族政策
長達近4個世紀的遼宋金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漢族和少數民族政權對峙的“南北朝”。從這個時代開始,入主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擺脫了隋唐以前不分主次全面照搬漢族政治體制的做法,開始以本政權的實際情況出發,有選擇地吸收借鑒中原制度,并將其與本民族的傳統統治方式相結合,從而在遼、金、元、清總共600多年的歷史中,譜寫出了少數民族王朝最為繁榮和興盛的篇章。這當中,建立于公元10世紀初的遼朝便是開創者,其不僅繼承了從前北方游牧民族政權的統治方式,而且借鑒歷代中原王朝對邊疆民族地區實行的羈縻政策,創造出一整套較為完善且成功的民族政策,其統治經驗對之后的各個王朝的邊疆政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遼朝的民族政策,一般想到的就是“因俗而治”,即“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一國兩制政策。這一著名的體制作為遼代民族政策中最關鍵的部分,確實在整個遼朝歷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此一政策人所共知,對其的研究也相當多且較為深入,筆者這里就不再贅述,而只著重討論遼代民族政策中不常為大家注意的另一面——“因區域而治”,就是按照不同民族所處的不同地理位置劃分親疏關系,對于較近的民族和較遠的民族采用不同的統治政策。那么,這種民族政策的具體內容又如何,其是怎樣劃分和對待不同類型民族的,本文即將對此試析一二。
一
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遼朝的疆域十分遼闊,“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 ,幅員萬里”[1]卷37《地理志一》,438,在其統治范圍之內存在眾多民族。從“畜牧畋漁以食 ,皮毛以衣 ,轉徙隨時,車馬為家”的契丹、阻卜等牧民部落,到“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的漢、渤海等農業人口;從東北平原上的女真各部,到河套周圍與西夏、北宋相鄰的黨項諸族,各民族無論是在生產方式、生活習俗還是社會文化上都千差萬別。這就決定了遼朝統治者不可能用單一的方式去統治所有民族,必須找到更好的方法來應對。
針對這種情況,遼朝統治者除“因俗而治”的雙軌并行措施外,還實行一種帶有顯著區域性的民族政策,也就是以由近到遠、從嚴密到松散的方式分別控制不同區域民族。這種區分,由內至外大體上可分為核心、外圍和外延3個區域。
(一)核心區域
3個區域中最重要的是核心區,其涵括的范圍,可在《遼史》列傳人物的民族構成情況中比較清楚地察覺出來。
通常來講,能夠在紀傳體史書中擁有列傳的人,多半是在當時對國家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產生了影響的人物,尤其是皇親國戚或被統治階級任命為官員的人,無名之輩不會錄于史籍。然而在《遼史》中卻存在這樣的現象:盡管遼朝版圖內民族眾多,可有傳者的民族成分卻集中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以契丹人、漢人為主,輔以奚人、渤海人,其他民族幾乎無人擁有列傳。漆俠先生就曾明確指出過這一點——《遼史》里有傳者,有234人是契丹人,占76.72%;奚人7人,2.31%;漢人58人,19%;渤海4人,1.32%;剩下的只有回鶻和吐谷渾各1人,分別占0.33%。[2]①此有小誤,奚人有傳者實為8人。這其中的回鶻人孩里,又系因其祖先在遼太祖時代入貢而“愿留”,從此后代留于遼朝[1]卷97《孩里傳》,1408;而吐谷渾人直魯古則是阿保機征戰時俘獲的嬰兒,由淳欽皇后述律平撫養長大[1]卷108《直魯古傳》,1475,此二人都是自幼成長于契丹族群之中,完全可以看作是契丹人。
由此可以看出,契丹、漢、奚、渤海這4個民族主要部分所居住的地域,構成了遼朝國家統治的核心區域。
契丹作為遼朝的統治民族,是遼統治者倚靠的基礎。由世選制選拔任命的契丹官員,不僅成為遼朝中央北面官和地方部族官的主體,而且在中央的南面官之中也大量存在,“領燕中職事者,雖蕃人亦漢服,謂之漢官”[3]卷18《契丹官儀》,177;而主要由契丹人組成的御帳親軍、宮衛騎軍和部族軍,則是遼帝國軍事力量的主干。這其中尤以耶律氏皇族和蕭氏后族地位最為顯赫,遼廷對他們的依賴也最為明顯,如北面官中極為重要的南、北二府宰相,其任職者就分別以皇族和后族為主,遼太祖阿保機四年,“以后兄蕭敵魯為北府宰相。后族為相自此始”[1]卷1《太祖上》,4,神冊六年又“以皇弟蘇為南府宰相……宗室為南府宰相自此始”[1]卷2《太祖下》,16。同時,遼廷又在契丹本族中,按照與皇室的關系遠近將其分為內四部族——五、六院部——其余7個部族這3個層次,對其倚靠相對而言由重到輕各不相同,如在遼帝周圍,“出于貴戚為侍衛,著帳為近侍,北南部族為護衛”[1]卷45《百官志一》,697,出征或捺缽時則是“蕃人從行之兵,取宗室中最親信者為行宮都部署以主之,其兵皆取于南北王府千宮院人充之”[3]卷18《契丹官儀》,178,而普通部族平民卻要承擔繁重的邊疆戍守任務,往往“戶少而役重”,“每當農時,一夫為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1]卷104《耶律昭傳》,1454盡管遼廷為了防備宗室對皇位的覬覦和契丹世家大族威脅皇權,不僅拆分了勢力最大的迭剌部,而且也時常任命一些非皇、后族出身的人,如漢人官員等來擔任中央官職甚至是北、南院樞密使和北、南府宰相等高位,但總的來說,以皇、后族為首的契丹族一直是遼朝最為關鍵的統治基礎,其在《遼史》所有列傳中占據3/4的數量,是任何人都不能無視的事實。
契丹之后是漢人。幽云十六州入遼后,擁有數百萬人口的漢族成為遼朝境內最大的民族,而且也是社會發展程度最高、文化最發達的民族。由于地近長城,契丹與歷史上其他任何草原游牧民族政權不同,其從建立伊始就受到中原漢族文化的強烈影響,以韓延徽等為代表的漢族士人為阿保機“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為定配偶,教墾藝,以生養之”,“庶事草創,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1]卷74《韓延徽傳》,1231,1232,幫助遼朝建立了一整套較完善的經濟政治體制,使初興的契丹國家迅速鞏固和繁榮起來;一些漢族文人和武將也在遼朝征伐渤海和中原王朝的戰爭中出力頗多。而因各種途徑自愿或被迫進入遼境的漢人平民,則帶來了先進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令遼朝“擅桑麻棗栗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4]卷11《歷代論五·燕薊》,1279。可以說 ,使遼政權擺脫原始的落后狀態 ,成為可與五代、北宋相并立 200年的穩固大國的最大功臣,非漢人莫屬。而正因為此,遼朝統治者對漢人的態度存在著矛盾:一方面,遼廷在圣宗時修改對漢人的歧視性法律,“凡四姓相犯,皆用漢法”[3]卷18《契丹官儀》,179,又盡力籠絡以韓、劉、馬、趙4姓為代表的漢人大族,不僅任命其擔任重要官職,而且鼓勵契漢上層通婚,使得遼境的部分漢人大姓“分茅土之榮,并擁旌幢之貴”[5]49,變成與遼帝國休戚與共的可依仗力量;但另一方面,遼朝又因其統治者擔心漢人的反抗、以及契丹社會對被擄漢人的傳統歧視,而并不信任“漢人”這個整體,從不允許其在中央北面官和地方部族官中成為足以抗衡契丹人的力量,甚至連對“軍國大計”的參與都受到限制,而下層漢人更是“多為契丹凌辱”[6]卷4,武珪《燕北雜記》,72,處境艱辛。這種對漢人的矛盾態度貫穿遼朝始終,如何既可良好利用又能控制住漢人的問題,耗盡統治階級的腦汁,更加顯示出漢人在遼朝民族核心區域中的重要位置。
奚族與契丹共祖,都是源于宇文鮮卑的東胡系民族。對于奚族,遼朝統治者同樣存在很矛盾的態度:由于契丹人是以少數人口來統治為數眾多的漢人及渤海人,不得不將同源且文化相近的奚人作為“同盟者”來增強自身統治力量,因此給其僅次于契丹族的地位,在征服奚族后“仍立奚人依舊為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7]卷1,引趙志忠《北廷雜記》,1。在圣宗朝以前 ,奚族各部仍然隸于奚王府 ,實際上是半自治屬國 ,奚王享有優厚待遇,“撫其帳部,擬于國族”[1]卷45《百官志一》,711,并掌握奚6部的經濟、政治和一定軍事權力,漢、渤海等民族對此望塵莫及。此外,契丹統治階級還以聯姻來拉近雙方距離,使奚王族“世與遼人為昏,因附姓述律氏中”[8]卷67《奚王回離保傳》,1587。可與此同時,鑒于奚族在遼初被征服時的激烈反抗,遼廷在拉攏奚族時,也并未放松對其防范,從《遼史》中看,遼朝很少選拔奚人做官,尤其是讓其管理奚境以外的地方。《遼史》有傳的奚人不足列傳總數3%,而8個傳主中有5人是奚王,卻很難見到奚人被授任過奚王以外高職的例子,這不僅是因為奚族缺乏漢族那樣的文化和施政能力,而且表明遼統治者并不放心讓奚人進入國家統治集團。統和中,圣宗借口奚王和朔奴出征失敗,“籍六部隸北府”[1]卷33《營衛志下》,387,剝奪奚王府對其下部族的擁有權,不僅廢除奚王私軍、重新調整奚6部的組織成分,而且將其如契丹部族一樣直接劃入北宰相府和東北路統軍司之下,標志著遼朝與奚族的關系從宗主和屬國的關系正式轉化為朝廷和直接統治下的百姓之間的關系。之后奚王“獻土”于皇帝,而遼廷在此建造了中京大定府,并將漢族和渤海人口大量遷入其中,使原本是奚族世居之地的中京道變為“其民皆燕、奚、渤海之人”[9]154的民族雜居地區,說明此時奚這個民族已完全處在遼廷的直接控制之中,經濟政治聯系也相當密切,同樣屬于遼朝的核心區域。
渤海是遼朝核心區域4大民族的最末一個,之所以排在最后,是因為其受到遼朝統治者的歧視和防范最重。遼太祖阿保機于天顯元年滅渤海國,在其基礎上建立了東丹國,表面上似乎和奚族相似,系附庸于遼的屬國,但事實上其不僅以阿保機之子耶律倍為國王,而且四相中左大相和右次相分別為皇弟迭剌和功臣曷魯之弟耶律羽之,而耶律倍南奔后由耶律羽之掌政、穆宗應歷二年明王安端死后其實質上便被廢除的事實,表明東丹國雖名為渤海人之國,其實權卻完全掌握在契丹人手中,建立它的目的只是因為新興的遼朝難以迅速消化立國已久的“海東盛國”,而以此作為籠絡渤海人心的手段而已。同樣是出于這個目的,遼廷對于渤海末代王大一脈“存其族帳 ,亞于遙輦”[1]卷45《百官志一》,711,與大氏家族頻繁通婚,并吸收其做官,確令部分渤海人“世仕遼有顯者”[8]卷80《大傳》,1807。然而遼廷也時刻防范渤海人的離心傾向,其戒備心理甚至更甚于對待漢、奚,早在滅渤海國之初,遼朝便將渤海人“徙其名帳千余戶于燕”[10]19,太宗時又“遣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東平”[1]卷3《太宗上》,30,將大量人口遷離渤海故地 ,圣宗時更是三次遷移渤海人至上京和中京道[11],將主要的渤海人口都納入到遼朝容易控制的地區之內;此外,渤海人做官者的數量雖因其文化程度較高而多于奚人,但和漢人相比就寒酸得多,如其中最主要的大氏《,遼史》所記進入中央任職的僅有15人[12],官居高位者就更少。渤海人在遼朝治下會落于這種處境的原因,是其既在與契丹的親緣關系上不如奚族,在文化和施政能力上又比不過漢人,因此始終受到統治者歧視,而越是不被信任,也就越是陷入核心民族區域嚴密的控制之下。
除部族、州縣和頭下軍州之內的契丹、漢、奚、渤海4個民族的普通人民外,在遼朝核心區域還存在著兩個特殊的群體——宮分戶和非契丹非奚族的部族,前者是宮衛擁有者的私產,分為契丹正戶和蕃漢轉戶,后者則是遼朝54部族中除10個契丹部族、13個奚部族以及五國部之外的部分,主要由原契丹部族和宮衛中的奴隸人口組成。之所以說他們特殊,是因為宮分戶雖然主要出自4個核心民族,來源也與普通民戶及頭下軍州戶相近,但卻打亂了各民族原本的聚居狀況,而混雜成以契丹人為主導的新族群,這在作為宮衛組成部分的部族斡魯朵和行宮斡魯朵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而非契丹和奚族的部族更是來自室韋、突厥、烏古、敵烈、黨項、女真、達盧古等四面八方的非核心民族,他們不但被分散相雜而居,而且部民的生活習俗和民族認同感都已契丹化,尤其是其控制權完全為遼廷所掌握,各部族節度使皆為遼朝派遣的官員。加之遼朝無論是軍事、政治還是經濟活動,都離不開這些宮衛和部族的參與,雙方聯系非常緊密,因此,這兩個特殊的群體顯然也都系遼朝核心區域的組成部分,遼廷對其的掌控和關系密切程度絕不比普通部族和州縣居民為差。
可見,遼朝民族核心區域的特點是控制很嚴,其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都是遼朝的國家根基。盡管依民族成分不同,具體待遇有所差別,但在總的政策上,這一區域的居民都受到遼廷重視,有進入中央或地方官場的機會。
(二)外圍區域
與控制嚴密的核心區域不同,遼朝對契丹、漢、奚、渤海、諸宮衛和部族之外的民族,控制能力和彼此的聯系就遠沒有那么強,政策上的優待更無從談起,這些民族出身的人無法進入遼的中央官場,在《遼史》中也無列傳。對此,雖然《營衛志》有“外十部”一項,列于其中者基本都可視為此類,但事實上遼代的非核心民族遠不止10部。而在這眾多非核心民族中,遼廷對其政策又不盡相同,存在半羈縻半直接控制狀態和純粹羈縻、封貢狀態的差別,施行前者政策的區域可被視作遼帝國的外圍部分,對于中央朝廷鞏固自身統治有著一定的幫助,而采用后者的地區則只是遼朝影響力的外延,受控制狀況和關系密切程度遠不可與前者同日而語。
從整個遼朝200年的跨度來考察,可算作半羈縻半直接控制的民族主要包括五國部、熟女真、烏古、敵烈和黨項。
五國部在《營衛志》中記為剖阿里國、盆奴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大體位于松花江流域至黑龍江下游一線,與女真相鄰而非女真,《遼史》歸其入“圣宗三十四部”,與遼的核心區域諸部族并列,原因是該部自圣宗朝以后就“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13]卷22,212①單置契丹人擔任的五國部節度使始于興宗重熙六年,但圣宗統和二年就已有耶律隗洼任兼治二部的五國、烏隈于厥節度使的記載。,軍事上也屬黃龍府都部署司統轄。但事實上其與核心區域的部族有著本質差別,仔細觀察可以看到,遼54部族中除契丹部族和部分奚人部族外,幾乎全部來自遼廷人為析分,且多數出自戰俘、奴隸,是人造而非天然群體;而五國部的部族組織卻基本沒有后天的人工痕跡,完全是居于故地的土著民族向遼廷臣服而成,其對遼朝不輸賦稅,僅由各部部長入貢方物,在政治上也時有反叛,未被遼廷完全控制在手中,至道宗朝甚至可以說是脫離了遼朝的控制范圍,五國部節度使一名咸雍后也不再見于史籍。因而這個族群不應看作核心區民族,在性質上應屬外圍區域,而遼朝會對如此偏遠的民族有所重視,完全是因為契丹統治者執著于出產海東青的“鷹路”而已。
女真是東北地區的主要民族,部落眾多,根據與遼朝的關系密切程度又可分為熟女真和生女真,“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8]卷一《世紀》,2熟女真中又有北女真、南女真、曷蘇館女真、回跋女真等之分,其與遼的關系不如4個核心民族,如《遼史·百官志》中列有諸國大王府,其首領也皆任命當地女真人充任,而在《兵衛志》里其又被歸于屬國軍等,各部對遼朝承擔的經濟義務有的是官僚機構征收的賦稅,而有的則僅僅是無定額的貢奉,“自意相率赍以金、帛、布……蜜等諸物,入貢北番”[13]卷22,212;但反過來,他們又并非與遼廷缺乏聯系的人群,比如遼太祖時代“恐女真為患,誘豪左數千家 ,遷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 ,使不得與本國通 ,謂之合蘇”[6]卷25,陳準《北風揚沙錄》,453,諸部人口又系于遼籍 ,圣宗時就有“曷蘇館部請括女直王殊只你戶舊無籍者,會其丁入賦役”[1]卷15《圣宗六》,176的記載,其軍隊則有遼廷設置的東北路女直兵馬司、北女直兵馬司、南女直湯河司等機構管轄,而興宗時還在熟女真部落設立詳穩、都監等官,任職的很可能都是契丹人。諸如此類,說明遼對熟女真各部的政策在整體上介于羈縻和直接控制之間,聯系既非核心4民族那樣緊密,又非生女真那般松散。
烏古和敵烈是契丹北方的游牧民族,位于大興安嶺、石勒喀河與克魯倫河中上游之間的廣大區域,學界還有觀點認為烏古即文獻中常見的“羽厥”,至少當是關系密切的臨近族群。由于烏古、敵烈居地緊鄰“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的契丹腹地,遼朝對其重視程度遠較女真為強,在征服這兩個民族后,用派駐契丹官員及設置管理機構、重新調整部落組織、移民戍守的辦法三管齊下,先后在此設立了烏古敵烈都詳穩司和都統軍司,拆分出烏隗于厥等新部,遷入契丹部族并建立了一系列邊防城,至遲到道宗時期,已經可以做到“徙烏古敵烈部于烏納水,以扼北邊之沖”[1]卷26《道宗六》,309。烏納水,王國維認為“疑即今桂勒爾河”[14],也就是在嫩江流域,能將烏古、敵烈的一部分部民遷移如此之遠,充分證明了遼廷對該族群的控制能力。而遼朝對于烏古、敵烈人負有經濟上的義務,在其因受災或賦役過重而面臨困境的時候要進行賑濟,也說明雙方經濟聯系的加強。然而盡管如此,其距離真正的核心民族仍有差距,如興宗末年命烏古、敵烈貢海東青之時,便須特意“遣使”詣之,而非經由當地官署機構按正規程序下令;再如道宗大安十年“敵烈諸酋來降”,顯然說明除契丹人節度使外,其下各石烈的首領都是當地人。拿烏古、敵烈與奚族作個比較就可發現,后者雖然一度作為屬國享有部分自治權力,從而在《兵衛志》中被列入“屬國軍”,但同樣也因其后被廢除屬國地位而直接列于“眾部族軍”之中,在《百官志》里也屬于“北面部族官”;相反烏古、敵烈諸部卻在《遼史》各卷中均被歸于“外十部”和“屬國”,從未被納入“部族”。這說明遼王朝自始至終都沒有能夠像對奚族那樣,絕對控制該族群。
黨項族生活的地區原在青藏高原東北,從唐玄宗開元年間開始逐漸內遷,“安史之亂”后,唐將郭子儀又陸續將其遷往銀、夏等地,其分布范圍日益擴大,10至11世紀時已成為散居在遼、宋、夏三國的跨界民族。對于邊境地區的黨項諸部,遼朝將其歸入“屬國”范疇,遼中央朝廷和這些黨項人有一定程度的聯系,能夠派遣契丹官員去做其中一些部族的節度使;圣宗統和二十三年“振黨項部”[1]卷14《圣宗五》,161,則顯示遼廷與對烏古、敵烈一樣,承擔著保護黨項地區經濟的統治義務;而重熙年間遼廷為遏制元昊而禁止黨項向西夏賣馬,且確實收到效果,也證明其對邊境黨項的經濟、政治有一定控制能力。但另一方面,遼朝對他們的控制程度又遠不如核心區域民族,據《遼史》,與黨項雜居的山西族系由當地首領出任節度使,周圍的黨項諸族理當也是如此,如統和元年“黨項酋長執夷離堇子隈引等乞內附”[1]卷10《圣宗一》,110等。這些對于遼中央政府只是“稱臣而內附”[15]91的自治屬國,原有的部落組織基本上沒有改變,內部不設遼朝官署,也不承擔正規賦役,只是定時或不定時地向遼廷進貢。圣宗至興宗朝,西境黨項時叛時附,幾乎每隔10年左右便會發生叛亂或逃往西夏的事件。與此同時,與中原王朝交界地區的黨項部落亦時見南投舉動 ,早在后晉時就有“沿河黨項及山前、山后、逸利、越利諸族部落等首領”降晉[16]卷98《安重榮傳》,1303,宋太宗、真宗時 ,又分別有勒浪族[17]卷491《黨項傳》,14142、言泥族[18]卷56,1224等部官民投宋。這種情況直至澶淵之盟訂立才得到緩解,譬如統和二十五年宋遼兩國就河東地區來璘、來美等族的歸屬問題進行商議[18]卷67,1505等等。以上種種,都體現了遼廷對于邊境黨項諸部鞭長莫及的無奈境況。
總而言之,這些地處外圍區域的各邊疆民族的特征,就是在與中央朝廷的聯系程度上既有別于受到遼廷嚴密控制、作為統治基礎的核心民族,亦不同于游離在朝廷政治手掌之外的外延民族,而是處在一種介于直接統治和羈縻、封貢之間的狀態,既承擔為遼王朝戍守邊境的任務,又孕育著反抗、背離的傾向,向心與離心因素同時并存。
(三)外延區域
如果說外圍區域還能算是遼帝國實實在在的“國土”的話,那么外延區域就只能說是遼朝“影響力所及的地區”了。在這一區域的民族,基本上與遼只有松散的朝貢、貿易和助兵關系,不服從遼廷的管理,彼此間也不存在經濟義務,正如《營衛志》“外十部”條所說:“附庸于遼,時叛時服”,完全是羈縻、封貢的關系。
外延區域的主要民族,包括生女真、達怛和回鶻等。
生女真與熟女真不同,不入遼籍,在遼朝強盛時期曾一度“為契丹所制,擇其酋長世襲”[13]卷26,246,完顏氏祖先石魯便曾被授予惕隱官職;且遼在咸州設有詳穩司,生女真諸部歸其管轄,對生女真部族內部訴訟事務有裁判權[19];遼帝每年春季至女真地區捺缽,召集各部酋長接受其朝貢,也是一種監督和加強聯系的方式。然而和熟女真相比,生女真的獨立性又顯而易見:遼廷任命的各部官員全是當地女真人;完顏氏景祖烏古乃得授生女直部族節度使時,能夠因不肯系遼籍而拒受之;而遼將曷魯率兵追捕逃民、遼兵進討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之事都因被烏古乃拒絕入境而不得不令女真自往討伐,遼道宗壽昌二年,國舅蕭解里犯罪逃亡,“潛率眾奔生女真界,就結楊割(盈歌)太師謀叛。諸軍追襲至境上,不敢進……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賊魁解里首級,遣長子阿骨打獻遼,余悉不遣”[13]卷9,92的事情,更是說明生女真具有能有效阻止遼朝軍隊過境的自治權,其雖然臣附于遼,但與遼廷之間只是羈縻關系而已。
達怛即韃靼,又稱室韋[20]、阻卜,是遼宋金時代對蒙古高原諸東胡系游牧民族的通稱,與女真、黨項一樣,其族群眾多,其中以九姓達怛中的北阻卜最為強大,叛服無常,在女真崛起前是遼朝最大的邊患。遼朝曾在達怛(阻卜)地區設立眾多大王府,而圣宗時經過皇太妃西征等一系列征服活動后,于其腹地建立鎮州等邊防城并移民戍耕,且更進一步在達怛(阻卜)各部設立了節度使,從《遼史》“節度使往往非材,部民怨而思叛”[1]卷93《蕭圖玉傳》,1378的記載上看,節度使似乎是契丹等族流官。不過這種統治只維持到圣宗朝后期,達怛(阻卜)諸部便群起反遼,此后時戰時和,尤以道宗大安年間北阻卜磨古斯的反遼活動最為激烈,遼朝無力控制該地區,而只能通過不斷的征討來懾服諸部。出于對達怛威脅的擔心,遼朝“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21]乙集卷19《韃靼款塞》,848,完全沒有對外圍民族區域的那種統治信心。可見達怛諸部對于遼朝實屬外延,盡管遼廷曾在此建立過外圍區域式的半羈縻半直接控制形式,但時間太短,從較長的歷史時間段上看,達怛也只能算是遼朝的羈縻屬國、屬部。
唐末以后成為西北民族的回鶻,其主體部分與遼的關系更加疏遠,遼太祖時期“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1]卷2《太祖下》,20,圣宗時討伐甘州回鶻和阿薩蘭回鶻等,可以說是對回鶻少有的征服行為。但此后史料對遼朝與回鶻的關系所記甚少,通常都是關于回鶻各部的朝貢記錄。遼廷對回鶻的統治方式,也僅僅滿足于設立阿薩蘭回鶻大王府、沙州回鶻燉煌郡王府①實為歸義軍漢人曹氏政權。、甘州回鶻大王府、高昌國大王府、回鶻國單于府等冊封性質的官署,只是在興宗重熙二十二年有“詔回鶻部副使以契丹人充”[1]卷20《興宗三》,246的特例,究竟是回鶻哪一部,其具體細節仍不明。由此見之,遼朝與回鶻各部的關系,應該說整體上只維持在封貢的程度,連羈縻都很難算得上。
合而觀之,與前面兩個區域相比,外延區域諸民族如生女真、達怛可視作遼朝的一部分,但聯系太過松散,“猶唐人之有羈縻州也”,而回鶻則干脆是封貢藩臣,無論是遼廷對他們的控制能力,還是其對遼朝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影響,都根本不能與核心區域、甚至也不能和外圍區域相提并論。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核心、外圍和外延的界限并非絕對。同一民族內部的不同群體往往所處狀態不同,有的被控制嚴些,有的則松些;而許多民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情況也有變化,如奚和渤海在早期曾是有一定自治權的屬國,烏古、敵烈則經歷了從被羈縻到被半羈縻半直接控制的漸進,而達怛亦曾設有契丹節度使,等等。因此,這三個區域的劃分只是籠統而言,而決非存在固定的鴻溝。
二
按照各民族距離遠近分區域實行不同政策的做法并非遼朝首創,其鼻祖可追溯到先秦的周代。依周人觀念,天下分為五服:“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不同的區域對周天子承擔的義務也不相同,“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22]卷4《周本紀》,136,越遠者聯系越是松散。至漢代,中原王朝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完善的“羈縻”體制,如唐司馬貞所注:“羈,馬絡頭也。縻,牛韁也。……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22]卷117《司馬相如列傳》,3050,即按照各邊疆民族與漢朝的關系親疏及其自身強弱,將其納入到郡縣、屬國、特設機構、外層藩屬等4種不同的管理體制之中[23]。唐代則更進一步,在邊疆地區建立了大量羈縻府州,以當地民族首領為官員,實現對少數民族及其居住地區的控制。歷史證明,中原王朝的這種政策,其既能避免在控制少數民族地區時過分消耗國力,又可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邊疆的向心力,對于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穩定和統一確實很有幫助。
遼朝雖起于草原,但受中原文化影響甚深,因而其民族政策也呈現出學習漢族政權統治經驗的趨勢:對國家統治基礎所在的核心區域諸民族實行直接控制,并在保證政治穩定的前提下盡可能吸收其人才進入統治集團,爭取更多政治上的支持者與合作者[24];對外圍區域以半羈縻半直接控制的方式保持其向心傾向;而對難以掌控的外延區域,則效仿漢族王朝,采用帶有強烈中原氣息的統治形式——靠任命當地首領為官員來實現羈縻,或是僅僅用冊封國王、接受朝貢的方式維持封貢聯系。
然而同時,遼朝民族政策又非簡單地照搬中原經驗,而是在將少數民族特色與漢族特色相互融合的基礎上,進行了更多的創新,并對后世少數民族乃至中原王朝都產生了影響:
一是將同一民族也按照與中央政權的親疏關系和控制嚴密程度分成不同族群,利用一部分可以信任者去對付其他人,如將擄掠來的奚、烏古、敵烈、黨項等族人口新置部族,反過來又利用這些在廣義上已屬契丹人的“部族”駐扎于其所源出民族的本部,去控制該地區的“屬國”和“屬部”,這種做法很清楚地體現在《遼史》的《營衛志》和《兵衛志》所載各部族的駐地情況上。后來清朝對蒙古的控制就參考了這種方式,即將其分為內、外蒙古,加上已屬滿洲民族范疇之內的八旗蒙古,以親制疏,以內制外,實現了成功的層層控制。
二是不像以往的中原王朝,只滿足于羈縻的現狀,而是不斷加強邊疆民族地區與中央在軍事、政治以及經濟上的聯系,使原本控制松散的邊疆區域,逐漸變成可信賴的御敵根基,如對奚、渤海、烏古、敵烈的政策就是如此。這種“邊疆內地化”政策對后世中國王朝的影響深遠,明、清兩代在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以及清朝對內蒙古和新疆的政策,都帶有這種色彩。正是通過不斷的“邊疆內地化”努力,才使中國的領土邊界在明、清以降逐漸穩定,奠定了今日中國版圖的基礎。
可以說,遼朝這種有特色的區域性民族政策,在中國歷史上占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對使中國古代王朝的民族政策走向成熟、對中國多民族大一統國家在清代的最終成型,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脫脫.遼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漆俠.從對《遼史》列傳的分析看遼國家體制[J].歷史研究,1994(1):75-88.
[3]余靖.武溪集[M].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武溪集·嘉祐集.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5.
[4]蘇轍.欒城后集[M].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劉承嗣墓志[A].向南編.遼代石刻文編[Z].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6]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M].說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楊復吉輯.遼史拾遺補[M].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8]脫脫.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
[9]沈括.熙寧使契丹圖抄[M].賈敬顏編.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4.
[10]洪皓.松漠紀聞[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1]王德忠.中國歷史統一趨勢研究——從唐末五代分裂到元朝大一統[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2]王善軍.世家大族與遼代社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3]葉隆禮.契丹國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4]王國維.金界壕考[M].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712-737.
[15]韓德威墓志[A].蓋之庸.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
[16]薛居正.舊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7]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18]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9]程妮娜.遼代女真屬國、屬部研究[J].史學集刊,2004(2):84-90.
[20]張久和.原蒙古人的歷史——室韋—達怛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1]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0.
[2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3]李大龍.漢唐藩屬體制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24]王德忠.論遼朝社會階層間的流動及其意義[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36-41.
The Territorial Character of L iao Dynasty's Policy Towards Nationalities
JINan-nan
(College of Histo ry and Culture,No rtheast No 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Liao dynasty's policy towards nationalities had a territorial character obviously.The empire considered its peop le as 3 groups:core,periphery and accessorily by distance.And therewere 3 kindsof different policy corresponding to these 3 groups.This system came from dynasties of Han nationality.But it was also refo rmed by Khitat and influenced late Chinese dynasties to construct their ow n policies towards frontier areas.
Liao Dynasty;Policy Towards Nationalities
K246
A
1001-6201(2011)04-0088-07
2011-01-16
紀楠楠(1978-),男,吉林長春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趙 紅]